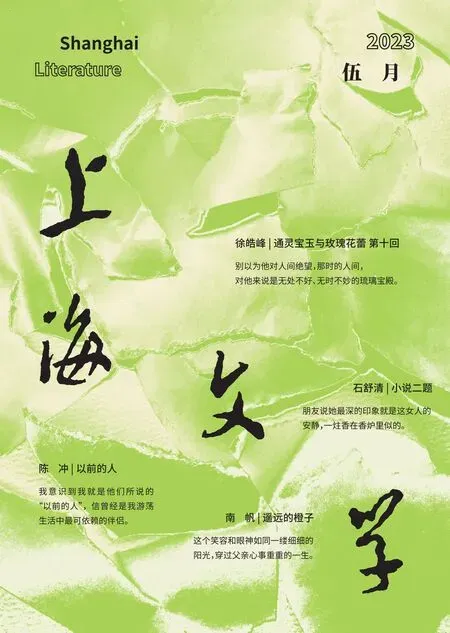草垛里的一根針
淡巴菰
1
門鈴響。我湊到貓眼前望出去,先是嚇了一跳,兩個從上到下裹著白色塑料防護服的家伙立在那兒!再仔細看一頂棒球帽一頂漁夫帽下的臉,才認出是史蒂夫和凱文兩位探險家朋友。
“我們剛才去附近的山上看一處巖畫,打你這兒經過,就過來討杯茶喝。今天真冷,雨一直沒停,不過是好事,洛杉磯太需要雨水……”史蒂夫生怕失禮,一見到我開門立即解釋。旁邊的凱文聽我夸他氣色好,還沒進門就摘下帽子,讓我看他新長出來的黑亮的頭發。
二人都把鞋脫在門口,把身上的防護服也像剝蒜似的剝下來,說是為了防那山上無處不在的毒櫟,上次有人蹭到,皮膚上起滿皰疹,疼痛難忍。
我沏了茶與他們坐在桌前看他們雨中的收獲。刀削似的巖壁上刻有一群牛,三大三小,碳黑和暗棕色的線條,原始又生動,讓人想起那著名的法國拉斯科洞窟壁畫。
“我鑿了點石頭樣本,準備拿到實驗室去測一下年代。估計沒有一萬五千年的拉斯科巖畫那么古老,可即使只有一千年歷史也很說明問題。”史蒂夫興奮地說,他一直想找到美洲大地上史前人類文明存在的證據,雖然他也知道概率極低,像從草垛里找根針一樣難。
凱文則面色冷靜,潑冷水說他懷疑那不過是現代人惡作劇的模仿,“最多不過五十年!”我上次見他是三個月前,我們一起去爬了那三千多米高的禿頭山(Mount Baldy),幾天后他就去了尼泊爾,說要待上四周,去徒步珠峰南坡的薩加瑪塔國家公園。我當時就為他捏把汗,那里雖說美得要命,可海拔從兩千八百至八千八百米,要知道他可是在一年前就被確診為淋巴癌晚期了!“趁還活著還能自由行走,我要走遍這個世界我想去的地方。”他已經把開了多年的公司無償交給了合伙人。六十三歲的凱文,從沒結過婚,更沒兒女,剩下的日子就靠過去的投資回報和一些積蓄。
“那一趟真是太背運了。我先是被蚊子咬染上了登革熱,爬到一半,鼻子就血流不止。在山腳下找到一個小村莊,當地的土大夫非要給我輸血。在那地方我哪兒敢,花錢雇飛機輾轉到了一家大點的醫院,才算慢慢穩定下來。正打算回美國,又染上了新冠!”凱文個頭小小的瘦瘦的,單眼皮,一笑起來帶著頑皮很孩子氣,露出一對小虎牙,絲毫不像年過六十的人。
他說一周前又做了一次化療,感覺現在元氣滿滿了,過兩個月去巴西游歷兩周,他喜歡在那里潛水。
史蒂夫當年介紹我認識凱文,就是因為他是水下攝影師,而我正給國內一家刊物做境外攝影家訪談。二十年前他不過偶爾跟朋友潛了次水,發現鏡頭中的水下世界精彩異常,便欲罷不能。兩千多小時的水下拍攝讓他成了拍海蛞蝓專家。全世界海域他都潛遍了,為許多海洋生物學家拍攝和采集這色彩斑瀾的軟體動物。有一個從未被人發現的新種類還以他的名字命名。
我拿出葵花籽請他們嗑,打趣說,“別小看這瓜子,會嗑與否可看出東西方文化的差別。在中國,連小孩子都嗑得嫻熟,在美國,沒有一個人不是用門牙咬一下,再靠手去剝開的。”史蒂夫先認輸道,“怪不得你過生日指名讓我去中國超市買這東西呢。我可以帶皮嚼嗎?”凱文也沒能幸免,好不容易剝了一粒還掉在了茶水里。我笑他是長著亞洲面孔的美國鬼子。
“你剛說你的生日是這個月二號?我是五號。屬豬。”凱文的單眼皮眨了眨,猶豫了一下說,“當然,這都是別人給我編的,我從不知道自己的生日。”他是那種在人群中極容易被忽略的人,不僅因為身型瘦小,還因為他臉上總帶著飄忽的神態。不同于多數人都下意識地給自己一個符號或角色定位,然后圍繞那個定位有相應的言談舉止和裝扮,凱文像一團沒有活成形的泥,隨時準備著成為這個或那個,可總差點意思,最終無法歸類。
我之前聽史蒂夫提過一句,說出生在韓國的凱文是被美國人收養來的美國。
看我有些不解的表情,凱文問史蒂夫,“我的故事,你沒告訴過她?”
“我想還是由你自己講出來比較好。”猶太大叔史蒂夫甕聲甕氣地說。他比我們兩位都年長,雖然不時也開些玩笑,可在許多時候還是很有長者之風的。
凱文捏了幾粒瓜子,在手里揉捻著。他并沒接口說下去,反倒是望向我問:“你尋過人嗎?”
我想都沒想就說當然尋過啊。在兩人有興趣的目光中,我頗有些興奮地回憶了當年的尋人經歷。
2
我第一次尋人是十五年前。當時我在北京某報當編輯,某天忽然來了個實習生,居然跟我是大學校友。她皮膚光潔微黑,體態飽滿健美,仿佛一枚多汁的水蜜桃。懂得扮美之道的她總把眉毛描得濃而有形,像奧黛麗·赫本,眼影時而暗藍時而灰紫,讓那雙忽閃忽閃的大眼睛率真又神秘。她心無城府,嫉惡如仇,見不慣報社一些蠅營狗茍,不時私下跟我譏諷幾句。我們很快成了鐵姐兒們。我接到采訪線索也總是派她去,她從無廢話,干活利索周到,一次也沒塌過方。她的房東臨時用房退租,她搬去我的公寓住了一段,晚上睡前閑聊,她臉皮很厚地透露她的擇偶三要素:長得帥,有足夠的錢,性能力要棒。被我大笑惡俗也不惱。后來報社版面縮減,正式記者發稿的陣地都少了,實習生更沒了用武之地,于是她離開去了另一家報社。戲劇性的是,她某天在街上遇到一位有魅力的大叔,兩人一見傾心,她不久便離開北京跟去了上海發展。先還偶有信息往來,不久就沒了音信。再打她手機仍有人接聽,卻已是陌生人,說根本不認識她。很惦念她,茫茫人海無處尋,我便寫了一篇散文《那個叫林賽的唐山妞》,發表在《北京文學》,可大海撈針一般,我再也沒能聽到她爽朗的笑聲。
“中國人不用‘臉書’嗎?有‘臉書’的話,這種情況相對容易找到。”凱文幽幽地說。
“即使找不到,這個人已經經過你的記述留存在了文學里。你們的友情也經由這篇文章得到了紀念。結局也不壞。”史蒂夫喜歡用發展的歷史觀看問題,“遺憾總是有的,c’est la vie(法語,這就是生活)。”
“我的第二個尋人故事卻完美得讓我意外。”說到這兒,我也賣了個關子,“你們聽說過在中國的南方有個瀘沽湖嗎?沒有加州的太浩湖遼闊,卻湛藍如寶石,像遠離塵囂的圣物。”他們二人都曾去過中國,都安靜地搖搖頭。
正是為了去看那美麗的湖,我偶遇了一對七八歲的兄妹。“在那個偏遠小鎮的汽車站不遠處,我等車等得無聊,走著走著,邁進了一個簡陋的售賣水產和禽類的院落。冬日陽光下,這對穿著厚敦敦棉服的兄妹,趴在露天的水泥臺上寫作業。看到我給他們拍照,他們有些興奮和害羞。著小紅花棉襖的妹妹,幾次笑著跑開,被哥哥懂事地追回來配合。然后他坐在陽光下專注地讀語文課本,穿著舊球鞋的腳大咧咧地伸在干硬的泥地上。妹妹跑跳著繼續撒歡兒,偶爾扭頭害羞又好奇地看看我。我實在是喜歡這小樹苗般的生命。他們沒有都市孩子的驕嬌二氣,沒有祖輩父輩堅實的物質后盾,可是他們皮實、結實,他們的生命蘊含著煤球一般的密度與無盡的熱量。中國的鄉鎮和村莊,這樣的孩子有著千千萬。無論生活和命運如何對待他們,他們,如小草小樹一般,貼近命運的本質,努力接地氣地成長著。汽車要開了,我卻不想離開,拍著他們,看著他們。”
“后來呢?”兩位不約而同追問道。
“后來我與他們的父母——一對同樣淳樸厚道的中年夫妻,也閑聊了一會兒。兩腮有著高原紅的母親好客地有問必答,一邊蹲在地上手腳麻利地褪雞毛。書生模樣的父親寡言安靜,坐在一張木凳上,埋頭寫了地址給我,他愿意收到我給孩子們拍的照片。
“我回北京當日就找到一個照片打印店。幾天后,這照片已經在奔赴瀘沽湖的路上。怕寄丟,還特意寄了掛號。可是,數天后,這小小信封又回到了我手里,上面多了一塊膏藥似的小紙片:查無此人,退回原址。”
那個紫砂壺里的茶已經淡得沒有茶味,我打住敘述,去廚房換茶續水。
“一晃,已過了十幾個寒暑。某天我整理書架,忽然發現在一本書中夾著的那個鼓鼓的信封。世間許多滄桑輾轉,他們的笑臉依舊純樸如山楂果。那靦腆可愛的笑臉讓我有一種沖動,我要找到他們!盡管明知毫無線索可循。當時不過七八歲的兒童,如今也應當是經風沐雨闖蕩人世的青年了。他們在讀大學嗎?還是已經分擔生活壓力打工謀生?街頭,與我擦肩而過的快遞小伙,可曾就是那個懂事的小哥哥?那微笑著幫我把行李舉到行李架上的文靜空姐,是否就是當年頑皮的小妹?感謝日漸發達的網絡,我把照片掃描后,配上結識他們的來龍去脈發在了網站上——‘淡巴菰之味道’是我在今日頭條的個人主頁。說實話,真沒抱什么希望。”
“我相信你找到他們了。”凱文急切地說,像猜對了謎底。
“沒想到兩天后,就有人留言給我,說那倆孩子是他的堂兄妹,他們如今都在讀大學了。再過了兩天,這兩個孩子就都與我加了微信,感謝我十幾年過去了還惦念著他們。他們甚至跟我訴說對未來的困惑和迷茫,好像我們真是久違的老朋友。”
我說罷,以為他們兩位會興奮地感嘆一番,沒想到,有好一會兒他倆都低頭喝茶沒接話。
“凱文的尋人故事可比這傷感得多……我沒有尋過人,卻被尋過。”史蒂夫說著,試探地望了一眼凱文,然后悠悠地道,“我哥哥已經去世七年了。某天我忽然接到‘臉書’上一個好友請求,說她可能是我的親戚。我接受了那個陌生的名字,沒想到自己被嚇了一跳,她不僅是我親戚,還是很近的血緣,她是我哥年輕時風流的后果——她媽曾和我哥有過一夜情,也就是說她是我侄女!四十多年前,她媽在酒吧當侍者,被我那長相很帥、喝了幾杯酒的哥哥迷上了,雖然彼此完全是陌生人。不久她發現自己懷孕了,而我哥早消失得不知下落。后來那女人生下這女嬰后嫁了人,生活還算順利。在這女孩十歲時父母吵架,她才從那男人嘴里知道他不是親爹。她花了幾十年四處打聽,都沒找到親爹下落。不久前她母親也去世了,她更渴望找到父親,唯一的線索是我哥的姓氏。她終于在‘臉書’上聯系到了我,問我是否愿意做個DNA鑒定。要說這科技真是太發達了,只需要提供一點唾液就可以找到血緣相近的人。結果出來了,我們家又多了個親人。她生父雖然已經死了,可仍和我侄子、我嫂子相見了,每個人都意外又開心。”
說話間,史蒂夫電話響,是他太太打來的,讓他回家去置辦晚飯,說她上午去給阿富汗難民送了些衣物,回家就發燒咽痛,也許感染了病毒。
于是就剩下凱文與我隔桌而坐,繼續就著茶水吃著堅果和幾枚曬干的無花果。
3
凱文慢慢開始了他的講述,語調平緩,甚至有點干巴巴的。
“我不知道那時我究竟幾歲。我只知道,那時的我已經有了記憶。我記得我們住在一個很窮的韓國農舍,泥巴墻,上面是草頂。你看過美國經典的電視劇MASH嗎?劇中那個美軍野戰醫院所在地就是我們的小村莊Uijeongbu,在首爾北邊,離朝鮮不遠。那是個夏天,我媽要去地里干活,把我自己留在家里,叮囑我不要外出。我隱約記得我有哥哥姐姐,記得他們背著書包去上學的樣子。不一會兒,一個鄰居家的小男孩來找我。我們玩著玩著就離家越來越遠,直到了村莊集市上。我看見轟隆隆的機器在挖土,興奮得看呆了,東瞅西望著,再扭頭看,鄰居家的小孩不見了。我就哭了。有人把我送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那房子和我家的一點也不一樣。我不知道那是警察局,很好奇地用手摸著那平整的磚墻和那玻璃門。我進了屋,看到一個穿得很好的男人在跟人說話,可他面前除了我,根本沒有別人。他的手握著一個黑柄,貼到耳朵邊,他就大聲對著它說話。我不知道那東西叫電話。這時來了一個人,給我一塊甜餅,讓我吃著跟他上了車。我很高興,以為要回家了,沒想到,等著我的是一個地獄般的地方。”
凱文臉色平淡如紙,似乎反復的回憶讓痛苦失效了,他講述的只是一段與他有關又無關的往事。
“那是孤兒院,沒父母的孩子才該去的地方。我有家卻沒人送我回去。后來我才知道,孤兒院是政府救濟機構,多一個孩子就可以跟政府多領一個人頭費。警察和院長早有勾結,警察帶去一個孩子,院長就分他一份錢。沒人知道那院長克扣了多少錢,我只記得我們從未吃飽過,個個面黃肌瘦,成天被趕出去撿野果、討飯、掏鳥蛋。我哭鬧著要回家,得到的是棍棒毆打和責罵。我嚇得尿床,他們把床單扔到外面。晚上,我就蓋著那凍了冰的布單發抖。后來我病了發高燒,奄奄一息。怕我死掉壞孤兒院的名聲,他們把我送到另一個孤兒院。在那里我幸運地能吃飽肚子,也沒再被打。一年后的某天,來了一個穿著軍裝的大鼻子藍眼睛的人。他看到我,拿著手里的照片對照了一下說:就是你,給我當兒子去美國吧。”
我看凱文身后的那個小石英鐘已經指向六點,打斷他問是否愿意在這里吃晚飯。
于是,我們的談話從客廳移到了廚房。他坐在一張轉椅上,看我煎魚、拌沙拉。抽油煙機的聲音很響,他的故事中斷了。
“你把這里布置得像個藝術畫廊。太溫馨了。我看出來了,你喜歡舊東西。我有一個老式英國鐘,是我爺爺留下來的,可以送給你。”凱文說。
“謝謝,不過你還是自己留著吧。我相信舊物對我們都意味著特定的感情。”我說著,心里嘀咕,一個孤兒怎么會有家傳舊物?
“什么叫物有所值?在我看來,就是把合適的東西給最能體味這東西價值的人。包括錢。我幾個月前不是生病住在尼泊爾一個小村子嗎?那家人對我的照顧讓我感動。我感到驚奇:那么善良的人們,卻過得很貧苦且知足。我早就知道不要以經濟的富有與否來判定人的快樂程度,可我還是很想幫他們。不久前,我聽說他們的房子需要修補,要五千美金就可以煥然一新,我就給他們如數匯了過去。”凱文仍是那淡然的表情,像在說他給誰寄了個賀卡。
飯好了。我們圍桌吃著。他的吃相有點快有點野,不像在美國也不像在朋友家里,而像是和孤兒院的孩子們搶食,吃慢了就得餓肚子。
我并不餓,跟著吃了幾口,看凱文吃得那么香,打心底高興。鑄鐵鍋底剩了兩塊鱈魚,我建議他吃掉。他提議一人一塊。我依了,撿了小的吃。凱文把他那塊吃掉,還用筷子熟練地把鍋底那些碎掉的魚肉都一一撿起來吃了。
這顯然是一個從小餓怕了的人。我想起上次登山,我與他們失聯后終于匯合,回家前去山下一個意大利餐館吃晚飯。見我剩下一半米飯和一碟西紅柿肉末醬,已吃完了一大盤意大利面的凱文問我是否要打包盒,我搖頭說不用了。他望望我,想說什么又閉嘴沒吭聲,徑直拿起他的勺子舀著那剩飯吃了起來。他吃得那么津津有味那么香甜,就像那盤意大利面根本沒進他的肚子。現在我明白,他是一個不能接受把食物扔掉的人。
我又沏上了茶,這次是碧螺春。
4
“說吧,你的美國生活該開始了。”我笑道,怕他還餓,把一串剛洗好的葡萄放在桌上。
“我的養父是個職銜不低的空軍軍官,他對我很好。除了我,他和太太還從同一個孤兒院領養了一個韓國女嬰。后來才知道她是個聾啞孩子。”凱文仍是那副沒表情的表情。只有在我說話時,他才會望著我。輪到他說話時,他的眼睛總是盯著手中的一個物體,比如他面前的茶杯,好像直面別人的注視會影響他回憶。
“我的好日子沒過幾天,養父就被派去了越南。那惡夢般的日子開始了——我的養母出于寂寞找了個情人,不知她是擔心我會說出去還是內心愧疚,她把我送到一個荒山野嶺的訓練營。我才五六歲,周圍多是送去感化的不良少年,那么小,我居然抽起了煙!從學校到家沒有一個亞裔面孔,我成了孩子們尋開心的對象,動不動就有人用手擠扁眼睛嘲笑我。我開始跟人打架,身上總帶著傷。只要我回到家,養母就找各種理由打罵我。不知多少個夜晚,我哭著醒來,夢里一次次與父母生離死別……那樣煎熬了四年,終于,我的養父回來了。不是他,而是養母提出離婚,她等不急地跟情人結了婚。謝天謝地,我被判給了養父。”
“那不就該有好日子過了?”我跟著長舒了口氣道。
“你接著聽啊。我養父離婚后非常沮喪抑郁,前妻把他的錢花光了,還以那聾啞孩子為由要了那所房子。養父沒心思沒能力照顧我,就把我送到了密蘇里他父親家。我曾去過那里,很喜歡那兒的莊稼地、果園和那對老人。他們是我到美國后對我最和善的人,尤其是老奶奶,在我被養母送到營地的時候還曾給我寄過她烤的蛋糕。可惜沒多久她患癌死了。我跟著爺爺種地養牲畜。我剛才說的那座老鐘,就是我從所謂的美國家人手里繼承的唯一物件。”凱文停住,咧嘴笑了,露出一口小白牙。我才發現,他長得挺像任賢齊,成名前眼神飄忽的小齊。“你的房子如果有任何需要修理的,就找我——還不到十歲,我就跟那老爺爺學會了修理各種東西,水管壞了、門窗關不嚴了、房頂漏水了、汽車打不著火了,我都能修。”
“我以為自己會一直在農場待著,松了口氣,心想當個沒人欺負的農民也不壞。沒多久,我養父來接我了,他找到一個女人,要再婚了。我又開始生活在一個四口之家。繼母帶著個比我小一歲的女孩,她的親女兒。可是這個母親卻沒一點母愛,她恨小孩,她自己女兒的哭聲都讓她無法忍受。我養父迫于她的壓力和嘮叨,只得給我另尋人家。我被送到了一戶本來有五個孩子的夫婦家里,我是最年長的孩子。我被改了新的姓氏。這位養母是我見過的世界上最虛偽的女人。她自稱信仰上帝,每周去三次教堂。除了我,他們的五個孩子中已經有兩個是領養的。我不知道她這么做是為了好名聲,還是為了政府提供的那點養育費,總之對外笑吟吟的她,對我完全是另一張面孔,關起門來,她想打就打想罵就罵。我十四歲那年夏天,從學校回來急著進屋喝水——我總是走三英里路去學校,那天實在太熱,渴極了的我沒脫鞋就進了廚房,被她看到,一個耳光就扇過來。平生第一次,我動了手反抗,本能地推了她一把。她愣住了,沒想到我那么瘦小卻有把子力氣了。從此,她沒再敢打我。我當時已經在麥當勞打工。攢夠了能租一間臥室的錢,我立即搬了出去,直到中學畢業。”
我又長舒了口氣。我曾采訪過很多陌生人,在深圳一家都市報做過類似口述實錄的情感訪談,還真沒聽到過小小年紀就經歷如此曲折的人生。
“高中時我遇到了一個心儀的女孩。她來自典型的白人家庭,父母當然強烈反對她找個亞裔孤兒當男友。但我們愛得很深,商量好先去讀大學,畢業后有了經濟基礎再跟她父母談。那時的我,做著此生最美好的夢。高中畢業兩周后,她的好友開車接她去看電影,回家時經過鐵路和火車相撞,兩人當場死亡。她的雙胞胎弟弟把噩耗告訴我,說我可以去扶欞抬棺。Emma,那是我這輩子抬過的最重的東西!”凱文終于不再盯著那杯子,端起來喝了口茶。
“我當時的天塌了下來,往哪兒走?當個酒鬼、流浪漢似乎是最容易也最方便的。可我知道要想有明天,讀大學是我唯一的出路。我想去讀哲學系,有太多我想不明白的事!可有人說讀哲學的唯一出路是餓死自己。于是我讀了商科,四年的學業我三年修完,在佛州找了份很好的工作。干了兩年,我發現根本靜不下心來。那個困擾我的問題越發讓我想面對——我的親生父母在哪兒?生活在那么多陌生的屋檐下,我究竟是誰的孩子?我開始往韓國投放尋人啟事,凡是能想到的地方我一個都沒落下。那真好比草垛里尋一根針!我確實也得到了一些同情的反饋,說我如果真想找到父母,應該回去找。我便辭了職。沒想到,在韓國一待就是六年。”
凱文找到了他被美國人收養時的孤兒院,可之前的那家已經查不到任何收養記錄——那個與警察勾結的院長把所有檔案全部銷毀一凈,自己帶全家移民到了美國。“你猜他來美國后的職業是什么?非常荒唐且諷刺,他竟然搖身一變,成了牧師!”凱文這次是冷笑了,好像在看滑稽戲。
“韓國并不大,費了這么大力氣難道一點線索也沒有?”我不甘心地問。
“村莊早就沒了,成了城市。有幾家找上門來,見面就說兒子啊終于找到你了,咱們去美國吧。只有一位清瘦慈祥的老人,我真希望他是我爸,雖然他所描述的走失的兒子與我根本對不上,我們仍去做了血液鑒定。檢測結果出來那天,媒體們都來了,當醫生宣布血型不配時,老人當場癱倒了。我也很沮喪。這么多年過去了,我雖然還沒徹底失望,但知道希望也極渺茫了。十年前,我加入了韓國的DNA數據庫,至今沒出現任何相近的血緣。我都六十多了,父母很可能早就不在世了。”像說累了,凱文目光有些茫然,本就不高的聲調更低了。
“如果說尋親未果出于無奈,年過半百,你為何也沒找個女人結婚為伴?那雖然不能替代親情,可也是人生中重要的一部分啊。”我好奇地問。
“沒遇到合適的人啊。也許,我從未淡忘那美好的初戀。離開韓國后我沒回美國,直接去了印度,在那里一待就是十三個月。我看著那些又臟又窮的人臉上快樂平和的笑,我看著一具具尸體在柴火中被燒得變形最后變成灰,我心中的緊張和不安似乎也跟著消散了……我不再恨任何傷害過我的人,也不再恨命運的不公。”凱文在朋友中人緣很好,他總是嘻嘻哈哈,幽默、隨和,如果不是他親口說出來,沒人相信他曾有過那么不堪回首的過去。“Love is thicker than blood,愛比血緣更濃。”這是他常說的一句話。
“你想看看我女友的照片嗎?”凱文不等我回答,摸出手機滑了一會兒伸給我。
凱文蹲在一個墓碑后,雙臂伸開做擁抱狀,笑容像陽光,驅散了他臉上那層好似總也洗不去的灰頹。要放大才能看清墓碑上那極小的頭像照,是一個棕色長發女孩清秀的半側臉,一雙大眼睛很美,有些哀婉地望著前方。
四十多年過去了,她仍是他此生的最愛。
我問凱文是否介意我把他的故事寫出來。
他略作思考說,“寫吧,如果這所謂的隱私對別人是有正面意義的。我的意思是,但凡有人讀后,忽然發現他曾自以為灰暗的人生其實遠非那么可悲,那這故事就沒白寫。”
凱文離去時,夜空上綴滿星星,密且亮。他掏出手機,對著星空教我用一個App識星座。那或明或暗或大或小的星星像撒在夜幕上的塵沙,有些被人為地連成冠了名字的星座,多數都零散在那兒發著清幽的光。
“其實,每顆星星都是孤獨的,不管它們看似離得多么近。”凱文隔著車窗說罷,眨眼就消失在夜色中,像一顆大地上的小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