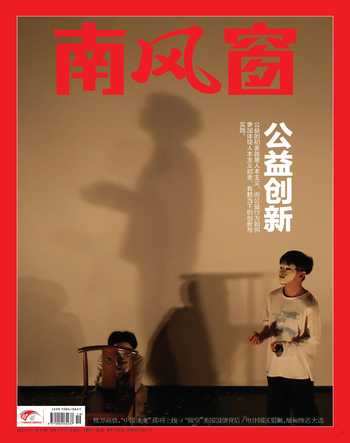逆向招商,上海出牌
賴鎮桃
“我們辦公室的選址很簡單,就看透過玻璃能不能看到東方明珠和‘三件套(上海中心、環球金融中心、金茂大廈)。地段好不好、我們能給客戶留下什么第一印象,全都一目了然。”一位在上海靜安區從事商務服務的合伙人,站在窗前指著黃浦江對岸的地標建筑說道。
很長時間里,這就是上海對不少企業的吸引力所在。只要能進入上海,甚至在炙手可熱的市中心拿下一套辦公樓,就仿佛在國內經濟版圖擁有了一席之地,再疊加這個城市獨有的資本、人才、信息資源,“滬籍”,對企業而言就是一個巨大的加成。
所以,在國內城市激烈爭奪投資項目時,上海大部分時間都置身事外,畢竟企業總會自覺地“用腳投票”。
只是,從近幾個月的新聞看,上海已經不像以往低調淡定。
據上海市投資促進服務中心,8月30日和8月31日,2023上海·粵港澳大灣區投資合作推介會先后在廣州和深圳兩地舉辦,上海吸收的總投資超300億元。
實際上,大灣區是“投資上海·全國行”的第三站,今年的3月和5月這座全國經濟第一大市已經先后奔赴北京和成渝開展招商,對潛在優質企業發起魅力攻勢。
密集的招商行程,可以用馬不停蹄來形容。上海經信委8月初發布的消息顯示,在當前全國掀起的招商引資熱潮下,上海投促人舉辦“投資上海·全國行”招商活動超300次,足跡遍及超60個城市。
一向穩重的上海,為何猛然發力大招商?超級一線也下場“搶企”,將如何攪動城市的招商比拼?
什么是“逆向”
作為國際化大都市,上海招商很多時候是放眼全球的,所以連續多年上海都是當之無愧的實際利用外資第一城,也是目前唯一連續三年實際使用外資超200億美元的城市。除了頻繁和跨國公司接觸之外,上海還推出了《上海市加大吸引和利用外資若干措施》,全年計劃舉辦不少于100場的重點海外招商活動。
上海的態度已有所轉變,一邊繼續鞏固外資這個“基本盤”,另一邊還把目光移向內資企業,簡而言之,就是外資內資全都要。
為了吸引內資,上海展現了前所未有的進取姿態,當中還不乏打破常規之舉。
首先是真金白銀給政策優惠。4月25日,上海市發布《關于新時期強化投資促進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政策措施》,簡稱招商新政“24條”。
值得注意的是,“這應該是上海首次在市級層面出臺一個綜合性的產業招商引資和投資促進政策,以往一般是區級層面”,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副主任劉平說。對內招商,上海罕見地使用了“鈔能力”。
更讓人意外的,是上海到西部城市“逆向招商”。5月19日,2023上海·川渝投資合作推介會在成都舉行,簽約當天,上海在這座西部中心城市引資超過52億。這也成為上海的“第一次”—首次來到西部的川渝地區舉行招商推介,并在成都設立定點招商服務機構。
按照傳統的梯度轉移理論,高梯度地區會向低梯度地區進行大規模的產業轉移,發達地區得以騰籠換鳥、產業升級,欠發達地區也能實現快速發展。
國內中小城市顯然深諳此道。一直以來,上海都是國內招商團隊的“兵家必爭之地”。據統計,上海平均每月要接待高規格(區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國家級高新區、經開區主要領導帶隊)招商考察近百起,很多地方每年都會選擇在上海召開招商推介會。這些城市無不希望將龍頭城市的資源導入本地,從而激活地方產業、做大經濟體量。
今年上海走出去招引的項目,基本對應市“十四五”確立的“3+6”新型產業體系,明顯是在補鏈、強鏈。
但現在,上海打破了這一慣例。東部經濟強市“轉頭”到西部招商推介,傳統意義上的產業溢出地和承接地互換了角色,產業資源不再只是東部發達地區向西部欠發達區域的單向度、雁陣式流動。
成渝還只是開端。上海市投資促進服務中心主任王東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我們3月去了北京,到成都來是第一次,接下來還要去廣州深圳,包括長三角就近區域的中心城市招商。2萬億GDP以上的城市,我們都愿意去看一看,走一走。”
經濟體量達到4萬億的上海,正在“放下身段”四處“撒網”,但這座經濟大市很明白自己要招什么樣的企業。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龔正曾在市投資促進工作會議上提出,上海的招商引資是“提著籃子去選菜”。“籃子”是政策籌碼,“選菜”也就是精準招商。
縱觀今年上海走出去招引的項目,基本對應市“十四五”確立的“3+6”新型產業體系,明顯是在補鏈、強鏈。而且,上海沒有一味瞄準能帶來高投資高稅收的大項目,到成都、蘇州、常州、青島這些城市招商考察時,看上的反而是細分賽道的單項冠軍、科創型中小企業。
為了吸引落戶,上海拿出了實在的政策籌碼。一個是上半年推出的 “24條”政策套餐,另一項則是重點服務招商引資的1000億產業基金。這些年,合肥模式驗證了資本招商的成功,“以投帶引”正成為各地招商的新主流。
但上海還是有著超然的優勢,這里不僅是全球金融中心之一,而且也為風投資本所青睞。一位硬科技投資人解釋,“上海的S基金比較前沿,它能解決很多投資機構遇到的退出問題”。就像沙山路(名為“Sand Hill Road”的VC一條街)成就硅谷,強大的風投機構和產業基金,對比坐地招商、政策招商,顯然更能對新興產業形成強牽引。
制造業“隱痛”
上海如此積極的主動出擊,不免讓人疑惑:緊迫感從何而來?
2022年,雖然北京一度以微弱優勢反超,但很快上海強勢回血,守住經濟第一大市之位。論總量,上海是絕對的經濟中心,但落點到科創和制造業這兩大決定未來的關鍵變量,上海的表現則不如GDP亮眼。
先看科創實力,上海坐擁全國數一數二的高教資源和硬核產業,按理來說在一線城市里可以站上第一梯隊,但研發投入強度作為衡量城市創新力的一大指標,2022年上海為4.2%,深圳5.49%,北京破6%,上海已經明顯被拉開差距。
人才,作為城市創新的第一資源,據《南方周末》統計,在上海的564家上市公司中,2021年有368家披露了研發人員數據,共有22.20萬人。這一數據不足北京的1/3,不足深圳的1/2。
所以,上海對外招商,總是頻頻向科創型、高成長性企業投去橄欖枝,其實不難理解。
只是,更大的擔憂還在制造業。不少人已經關注到上海制造業的兩大數據:一個是2022年工業增加值,上海再度被深圳趕超,失去工業第一城之位;另一個是制造業比重,上海“十四五”定下了25%的目標,實際情況是去年已經跌破24%,同為“制造業三杰”的深圳為35.1%,蘇州超過40%。
這只是宏觀面上的表現,更關鍵的問題在于,上海對某些戰略新興產業鏈的掌控力正在變弱。
以生物醫藥為例,這作為上海三大先導產業之一,從基礎研發到生產制造有很長的鏈條;上海社科院應用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湯蘊懿卻發現,上海各大科研院所產出的優質創新成果,多數不在本地實現轉化,而為周邊江蘇、浙江等地生物醫藥企業做了嫁衣。對總部經濟、研發中心的偏好,過早的技術轉移,讓上海流失了制造的一些關鍵環節。
在不少人看來,制造業的外遷是一種迫不得已,上海作為一線城市,土地資源緊張,生產成本高昂,但事實上,上海近年發力打造的五大新城,還是發展洼地般的存在。
2021年,上海周邊的吳江區、太倉市、平湖市,規上工業總產值分別為 4400億元、2900億元、2600億元量級,而上海郊區的臨港新片區、奉賢區、青浦區,分別在2600億元、2300億元和1800億元的量級左右。顯然,上海不少制造業還沒來得及向郊區輻射,就已經向產業配套更好的周邊地區轉移溢出了。
人文財經觀察家、資深媒體人秦朔曾點出,不覺得上海非要找“中國工業增加值最大的城市”“中國最強的工業城市”等標簽,相反,做中國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最不可缺少的工業城市最重要,為國家擔起研制精深、精尖、精純的核心技術的使命最重要。
重拾制造、忙“明天”的事,上海還有不少可施展的空間。
掐尖還是協作
招商,一直是地方政府近身博弈的戰場,現在上海也在下場“搶企”,更折射出戰況正變得愈加激烈。
龍頭城市可以在跨區域招商中確認產業分工、找到新的合作模式。當然,這強調彼此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
投資邏輯的轉變可以解釋部分原因。在城市化快速推進的年代,投資的重心偏向基礎設施和房地產,但當城市化進入下半場,資金繼續往這些領域傾斜則容易帶來資源浪費和債務風險,而且“鐵公基”為代表的大基建建設周期長、回收慢,對穩增長的貢獻有限。
但產業投資,相較基建可以比較快地形成產能,產能釋放就會貢獻GDP,推動經濟增長。而且,在新舊動能轉換的當下,招商引資是地方培育、做大新興產業的捷徑。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馬亮向南風窗記者表示,今年地方招商引資的積極性空前高漲,但熱潮之下也有了更多理性,更加關注招商引資的質量,而不再像過去一樣不加選擇。
他觀察到,地方招商越來越趨向于產業鏈招商,聚焦本地有優勢和期望做大做強的產業領域進行集群式招商,既可以吸引企業,也能為企業提供產業鏈配套支撐服務。與此同時,招商也更加務求實效,不再是拼土地價格、稅收優惠等投資環境的優勢,而更加強調如何在營商環境優化方面做文章。
只是,今年上海的入局,正在引發“降維打擊”的擔憂—地方苦心孤詣培育出來的高精尖企業,面對市場更廣闊、生態更活躍的上海盛情邀約,如果做出搬遷轉移的選擇,將導致地方被“掐尖”、優質企業流失。
但換另一個角度看,上海這條“鯰魚”加入國內招商的比拼,對于地方優化招商模式和營商環境,或是一種倒逼。馬亮表示,不同城市的發展優勢不同,對不同產業的吸引力也不同,不能大水漫灌和一窩蜂,還是要以特取勝,真正挖掘和強調本地營商環境的特色和優點。補齊短板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揚長補短。
此外,上海在前往國內城市招商推介時,總不忘表示上海和當地有優勢互補、產業協作的空間。無疑,這也打開了新的想象空間,龍頭城市可以在跨區域招商中確認產業分工、找到新的合作模式。當然,這強調彼此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