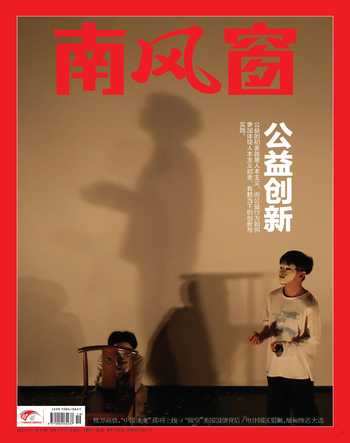黃渤:快樂難得
黃茗婷

聊雕塑時,黃渤好快樂。
兩尊雕像,頭似大象,身是人類,穿著長袍,仙風(fēng)道骨。
為什么創(chuàng)作這樣的雕塑?
黃渤說:“這是天馬行空捏出來的。”說罷,他喜上眉梢,嘴巴笑出了全國人民都熟悉的弧度。
但等到話鋒一轉(zhuǎn),聊到電影時,一絲肅穆躍上了他的臉—這張全中國最出名的以喜劇著稱的演員的臉。
黃渤似乎有兩副面孔。
在大銀幕上最早以喜劇聞名、被貼上“高情商”標(biāo)簽的他,不止一次在采訪中提到,如今能讓他感知到快樂的事情,越來越少。
“人生一路撿、一路丟,路途中一定會拾到很多有趣的美妙的東西,但也會慢慢丟掉一些東西。”坐在我對面不到兩米的他,被那抹蘋果綠襯托出好氣色,卻說出了幾分頗顯出世的話。
這大半年里,黃渤很難能擠出大段空閑時間來做雕塑和藝術(shù)品創(chuàng)作,原因無他,太忙了。
與南風(fēng)窗記者初次見面的當(dāng)天,黃渤正好在出席他今年暑期檔第三部電影《學(xué)爸》的首映會。身穿一件蘋果綠的印花襯衫,黃渤走進了采訪室,頭發(fā)被梳得高高的,很是顯精神,但眼神里的疲憊是藏不住的。
在此之前,他已在多個城市經(jīng)歷了《封神》和《熱烈》兩部電影路演。但這個暑期于黃渤而言,不止三部電影。
“暑期其實正在拍著一個電影,不得不中途停下來宣傳另外三部電影,這中間還加了一個音樂劇在演,然后還有一個裝置現(xiàn)代舞劇,然后可能暑期還要出一個專輯。”剛打開話匣子,黃渤就向我們的鏡頭一頓輸出,表情有點正經(jīng)。
最后他感嘆道:“我天,我說真的是酸爽。”正經(jīng)里不忘打趣。
由此,在今年熱鬧程度和競爭程度不亞于春節(jié)檔的暑期檔,黃渤在《封神第一部》里,不僅飾演了“姜子牙”,還成為了電影監(jiān)制;在大鵬執(zhí)導(dǎo)的《熱烈》里,他和王一博以及一眾街舞高手“斗舞”;而主演的電影《學(xué)爸》,則是黃渤“HB+U新導(dǎo)演助力計劃”計劃的第三部上映的片子。
“責(zé)任”這個詞,落在黃渤肩上,在外界看來,似乎順理成章。他是影帝、中國影史票房最高的男演員之一、觀眾心目中演技擔(dān)當(dāng)?shù)膰裱輪T。
有人說,這是屬于黃渤的夏天。
他從容地應(yīng)答、否認(rèn)道:“這是屬于中國電影的夏天。”
責(zé) 任
初次見面的那個下午,黃渤的行程表被整整齊齊地按照30分鐘的時長,分割成了不同任務(wù):接受好幾家媒體的采訪、錄制ID視頻、參加不同觀影團的映后交流。
黃渤走進了采訪室,瞄準(zhǔn)了放在全場中央的那把椅子,徑直走過去,安靜地坐了下來,觀察著現(xiàn)場工作人員的走動忙碌,若有所思地等待著工作任務(wù)的開啟。
他不做第一個開啟對話的人,但一旦被攝像機“捕獲”,他就變得眼里有光,開始滔滔不絕。在觀影會上,他和王迅妙語連珠對線。這才是我們熟悉的黃渤,舞臺上永遠的角兒。
我問他,這么繁重的工作量,是怎么堅持下來的?
黃渤沉默片刻,吸了一口氣說:“有的時候是不得不,是責(zé)任。”
“責(zé)任”這個詞,落在黃渤肩上,在外界看來,似乎順理成章。他是影帝、中國影史票房最高的男演員之一、觀眾心目中演技擔(dān)當(dāng)?shù)膰裱輪T。
大約十年前,黃渤在易立競的采訪里,分享過一段往事。在一次晚會上,他遇見了陳道明。攀談期間,陳道明有點語重心長,也有點風(fēng)輕云淡地對黃渤說:“我們等于肩上的擔(dān)子慢慢就卸給你們了。”
十年了,那時是“五十億先生”的黃渤,如今累計的票房已經(jīng)超過兩百億,此時的他再次聊起責(zé)任,多的是鎮(zhèn)定且清醒。這份責(zé)任,是傳承,也是他自己主動擔(dān)上的。
黃渤告訴我,他從演員這份職業(yè)里獲得了名聲、觀眾對自己的喜愛,當(dāng)然,還有報酬。那么,“有付出的必要,無論是對行業(yè),還是對新人的扶持”。
8月12日,《封神第一部》的編劇之一曹昇發(fā)布了自己的《編劇日志》。在2018年4月6日這天,曹昇寫道:“黃渤對封一劇本提出了強烈的批評。”
隨后,從故事到角色到臺詞,黃渤給出了自己的意見。
曹昇像做會議記錄一樣把黃渤的意見一一記了下來:每一場戲的節(jié)奏、動作戲的目標(biāo)、姜子牙和哪吒、楊戩三人的關(guān)系和作用、紂王逼迫姬昌食子的重點、新人演員的引導(dǎo)、臺詞風(fēng)格的摳細(xì)扣緊……
隨著這段劇本會的軼事流出,不少觀眾才發(fā)現(xiàn),黃渤在《封神》劇組中,不僅在臺前飾演了“姜子牙”這個核心人物,還是幕后的監(jiān)制。對于這段故事,在采訪中,黃渤稱之為“是盡一點自己的綿薄之力”。
不過,這似乎可以解釋,為何在《封神第一部》里,戲份遠比不上“質(zhì)子團”大戰(zhàn)的黃渤,如此賣力宣傳。在這個行程滿滿當(dāng)當(dāng)?shù)氖罴倮铮子硶⒓恿耍喑锹费菀矃⒓恿恕!扒懊嬉呀?jīng)那么多人付出的努力,當(dāng)然希望它(《封神第一部》)會有一個還不錯的結(jié)果,當(dāng)然要努把力,竭盡所能。”
黃渤很多年前,就已經(jīng)消解過票房于自己的意義,只談?wù)摂?shù)字而忽略電影本身,是無意義的。但這次不一樣的是,中國電影市場剛剛經(jīng)歷了三年的“蟄伏”,一切歡欣景象都在今年的春節(jié)開始復(fù)蘇,在這個暑假開始熱鬧。

看著好友陳思誠《消失的她》以35億票房打響暑期檔的“開門紅”,好友王寶強的《八角籠中》不落下風(fēng),《長安三萬里》成為了一匹黑馬,黃渤說:“作為一個電影從業(yè)者,為暑期檔的熱鬧感到開心。”
“當(dāng)然不能完全看數(shù)字。”他話鋒一轉(zhuǎn),繼續(xù)說道,“但是這些數(shù)字確實給了我們很多的信心的提振,觀眾開始大幅度地回到電影院,重新把它當(dāng)作一種生活方式,目光重新回到電影上,這本身當(dāng)然是件好事。”
我們的對話,自然落到了《封神第一部》上。最開始,黃渤的參演,“可能更多的意義是在幫助導(dǎo)演完成他的宏圖大業(yè)”。
此時的黃渤,語氣從“官方”變得柔和了起來,原本放松敞坐在椅子上的他,正了正身子繼續(xù)說道:“跟烏爾善導(dǎo)演再次合作(《封神》),歷盡千難萬險終于上映了,然后(票房)又是千難萬險。現(xiàn)在終于結(jié)果開始向越來越好的方向走了,大家可以接受它、開始喜歡它,這個還挺欣慰的。其實,也真的是希望費了那么多努力、那么多人辛苦、智慧和熱血的一個電影不要被大家給忽視掉。”他語重心長地,仿佛在談到自家侄子的成長故事。
對于《封神》三部曲,黃渤看得更遠,最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中國電影工業(yè)一些想象的實現(xiàn)。
“《封神》它對于中國的電影工業(yè)來說,是很有進步意義的一次嘗試跟探索,是一個將近一萬人的集體創(chuàng)作。”
“《封神》它對于中國的電影工業(yè)來說,是很有進步意義的一次嘗試跟探索,是一個將近一萬人的集體創(chuàng)作。”
單是一個美術(shù)小組,在封神劇組里,就被拆分成了舞臺美術(shù)、置景美術(shù),特效美術(shù)等等。“這變成了一個非常專業(yè)化、工業(yè)化的創(chuàng)作,所以說,這些嘗試對于中國電影真正邁向工業(yè)化來說,是很有進步意義的一件事。”黃渤說。
傳 承
也是這個夏天,黃渤發(fā)現(xiàn),現(xiàn)在和他搭戲的演員,是只有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甚至還有6歲的孩子。而自己已經(jīng)很久沒有接到愛情片的劇本了,采訪中,黃渤不忘打趣說道。
在《封神第一部》里,黃渤出演“白首牢騷類野人”的“姜子牙”,是白袍加身、皺紋爬上臉的“顯老”裝扮,與之搭戲的是1997年出生的“楊戩”此沙、2007年出生的“哪吒”武亞凡。他們組成的“地三仙”快遞小隊,給刮起血雨腥風(fēng)的“朝歌風(fēng)云”,帶來一點詼諧的色彩。
在《熱烈》里,他和王一博還有一眾行業(yè)里已為佼佼者的舞蹈演員,為熱愛的事?lián)]灑汗水。無論片場里外,黃渤認(rèn)可王一博的認(rèn)真和努力。“如此認(rèn)真跟敬業(yè)地對待自己的工作,他當(dāng)然就會有所回饋。”
為了改好《學(xué)爸》的劇本,蘇亮“天天潛伏在各種媽媽群里頭,在學(xué)校門口的家長群里頭,采風(fēng)收集”。對于這么一位有“韌性”的導(dǎo)演,黃渤想用HB+U新導(dǎo)演助力計劃,為他“提供第一把燃料”。
2016年,在老搭檔寧浩和好友周迅的陪同下,黃渤在上海宣布了HB+U新導(dǎo)演助力計劃。
黃渤在現(xiàn)場講了一個故事。最初,還是小透明的他和寧浩合作了一部小成本電影,用現(xiàn)在的話來說就是“三無作品”—無IP、無流量、無大投資。在當(dāng)年的上海電影節(jié)上,一開始它并沒有激起太大的水花。
冷場的情況,隨著劉德華的出現(xiàn)而有了轉(zhuǎn)機。這部電影是劉德華“亞洲新星導(dǎo)”計劃的扶助項目之一,而劉德華親臨了電影發(fā)布會現(xiàn)場,還留下來和媒體一起看片。劉德華評價這部電影:“那種感覺就像是被爸媽安排去相親,進去一看里面坐著的是全智賢。”
從此,這部成本只有300萬的電影,獲得了媒體的關(guān)注,上映后獲得了2534萬的票房,一躍成為該年度的票房和口碑的黑馬。這部電影,叫《瘋狂的石頭》。而從電影里走出來的寧浩和黃渤等人,也從此不再是小透明,成為了大人物。
當(dāng)然,別忘了還有最重要的,是真摯。“告訴他們,這個階段最好用的武器,就是真摯。一真遮百丑。”黃渤說。
十年后,2016年時候的黃渤,已經(jīng)是中國票房最高的演員之一。但他沒有忘記“瘋狂的往事”,他要把這種關(guān)照,傳承下去。
這是一個行業(yè)正常生態(tài)的光景。年輕一代像青苗一樣一茬一茬地冒頭、拔尖兒,而不服老的一代,看似往下退了一點,讓出了空間,實質(zhì)是像麥穗一樣,將經(jīng)驗心得積累成養(yǎng)分,沉甸甸的,飽滿而低調(diào)。
這幾年,和年輕演員搭戲搭多了,黃渤也把心得和養(yǎng)分順著代際的合作傳遞了過去。搭戲時,他看到了年輕演員身上的問題,自然會給他們調(diào)整。一場戲,表演痕跡無需過重,輕巧地處理是最好的。一句臺詞,先把戲找準(zhǔn)了,語句邏輯重音自然會出現(xiàn)。
當(dāng)然,別忘了還有最重要的,是真摯。“告訴他們,這個階段最好用的武器,就是真摯。有的時候,當(dāng)你沒有那么多方法技巧支撐的時候,真摯是你最好的武器,一真遮百丑。”
真摯和純粹,何嘗不是我們對黃渤的初印象呢?
小人物
21世紀(jì)前十年,一切事物都在往開放和繁榮的方向奔去。農(nóng)民、打工仔、外地人,他們懷著盼頭朝著城里遷徙,構(gòu)成了中國當(dāng)代史里第三次民工潮的流動。社會現(xiàn)實為創(chuàng)作注入了養(yǎng)分,聚焦小人物,成為了當(dāng)時華語影視創(chuàng)作的一股潮水。
黃渤,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闖進了大眾視野。

黃渤初踏影視圈,是以一名奔赴北京的山東青年的形象出現(xiàn)的。在好友高虎的帶動下,他參演了導(dǎo)演管虎的《上車,走吧》。
從此,山民、小偷、民工、廚子、落魄青年,一個個小人物在黃渤的演藝生涯里成為了注腳。黃渤的形象,是那個向上年代里所有人努力拼搏的國民代表。
黃渤有多拼?在《瘋狂的石頭》里,他繞著高架橋跑了一天,跑到人快要虛脫了;一邊忍著惡臭,一邊把淤泥渣滓抹到皮膚、頭發(fā)上,鉆到下水道里,被汽車壓在井蓋下面。
在《瘋狂的賽車》中,黃渤為了拍好“在雨中被師傅打”這場只有40多秒的戲,他在雨中、在泥水里被踹了2個多小時,手掌心、小臂、額頭被打出了傷痕。在和“東海”的“互毆戲”中,他被打得砂石塞進了血肉里,驚心動魄。
《斗牛》里,他蓬頭垢面、衣衫襤褸、聲音沙啞,操著一口膠東方言,傻里傻氣地也暗含悲情地說:“村里面人全死了,俺就在這一個人養(yǎng)的(牛)。”“俺跟那個牛,俺就以后就在山上,俺高低不下來了俺。”
為了拍好《斗牛》,黃渤每天往自己頭發(fā)上倒地瓜汁水,為的是讓牛啃自己頭發(fā),把戲拍出來。情緒到位了,臺詞理順了,等到人快拍好的時候,牛不是“出戲”了,就是早已經(jīng)跑遠了。
山民、小偷、民工、廚子、落魄青年,一個個小人物在黃渤的演藝生涯里成為了注腳。黃渤的形象,是那個向上年代里所有人努力拼搏的國民代表。
繞著沂蒙山區(qū)的一個山頭,黃渤來來回回跑了36趟,把鞋磨得破破爛爛報銷幾十雙,皮膚、骨頭磕磕碰碰了上百次。一個鏡頭,幾十遍、上百遍地重來,本來定好一個半月的拍攝檔期,硬生生拖成了四個月。
后來,黃渤對導(dǎo)演管虎說:“《斗牛》太苦了,老虎(管虎的昵稱)你后邊這個戲鐵定拿奧斯卡了,我也不去,我得留條命,太苦了。”
但那時候的黃渤,是苦中有樂。如此勞累,疲勞的是肉體,但激動的是靈魂,因為充分調(diào)動發(fā)揮身體到極致。黃渤說,是默契,是溝通,是他和管虎在藝術(shù)審美上慢慢地接近,讓他苦中作樂。
《斗牛》殺青時,黃渤“嚎啕大哭”,“終于有結(jié)束的一天”,那段每天驅(qū)車40分鐘的進山路,終于可以告別了。
告別了苦日子,黃渤開啟的是“好日子”。2009年,黃渤憑借《斗牛》中“牛二”一角,捧得最佳男主角的獎項,剛剛還在臺下緊張得表情凝重、在鏡頭前勉強維持鎮(zhèn)定的他,已然站在臺上如夢初醒地問:“是真的嗎?”
是真的,黃渤成為了全中國最出名的喜劇演員。
后來和管虎繼續(xù)合作的《殺生》中,黃渤的角色叫“牛結(jié)實”,和《斗牛》中的“牛二”一樣的接地氣。“為啥角色名字里都有牛?”做客《魯豫有約》時,黃渤問管虎。
管虎用六個字來回答:摔不死、打不爛。“這個結(jié)實勁還是挺性感的,這倒不開玩笑。”他有點嚴(yán)肅地說。
這種“性感”,和黃渤身上的生命力是分不開的。再往前溯源黃渤的成長之路,他走的路子,主打“野蠻生長”的調(diào)性。
黃渤出生在1974年,父母都是知識分子,但他卻讀完高中不想讀下去了,要去實現(xiàn)自己的“歌舞夢”。

1994年,黃渤成立了“藍色風(fēng)沙”組合,從青島出發(fā),開始了走南闖北的“走穴”生涯。他扛過80斤重的箱子,坐過飯味、汗味、餿味混雜的車子,最多一天要趕11場駐唱。賺到錢了,每人拿兩千寄回家,剩下的,一起吃、一起喝、一起玩。
杭州沒去過,他們坐著大巴去了;之后南下廣州、深圳的酒吧駐唱,還跑到東北三省,假冒了一次“香港歌手”,最后回到北京,和萬千年輕人一樣,過上了“北漂”的生活。
黃渤曾說過:“中國東西南北四個地方的流氓怎么欺負(fù)人我都能學(xué)。天天在接收這些東西。一邊受著,一邊還得嘻嘻哈哈,還得笑。”
話里話外,有苦有樂,雖然還沒出人頭地,但“對一件東西一知半解的時候是最美好的”,黃渤繼續(xù)向我解釋著說:“心思到了能力還達不太到,所以往前行進的路途是很美妙的,每個階段又找到了一個新的目標(biāo)。”
從最初的怯場,到敢站在臺上,后來唱歌也不慌了,唱完歌還有掌聲了,那時候黃渤的快樂之源,就是這樣被自己一點點進步、一點點改變填充的。
直到后來,唱歌唱到有人要求黃渤返場,還可以跳舞了,接著去拍電影了,他也沒有懈怠。回想起那時二十出頭的生活,他感覺“每一天都是嶄新的,每天都在進步,每天都在收獲,每天都是欣喜,帶來的喜悅感、幸福感和滿足感當(dāng)然就是最好的”。
1994年,黃渤成立了“藍色風(fēng)沙”組合,從青島出發(fā),開始了走南闖北的“走穴”生涯。他扛過80斤重的箱子,坐過飯味、汗味、餿味混雜的車子,最多一天要趕11場駐唱。
“若一生都在這樣的狀態(tài)里邊,得多美妙。”說這句話的時候,他目視前方,雙手抱著翹起來的二郎腿,輕微前后搖晃著身體,語氣里滿是感慨。
尋找快樂
后來,黃渤日漸成名,“五十億先生”“百億影帝”等標(biāo)簽貼到“演員”的頭銜后面時,“身邊都是好人”了;等到他下意識地想去保護那份純粹的快樂的時候,卻如掌心間的沙子一樣,越是想攥緊,漏走的就越多。
出演今年上映的《熱烈》,緣由聽起來輕飄飄的。原本是導(dǎo)演大鵬幾番邀約,陰差陽錯都沒合作成,直到遇到《熱烈》,原本的故事都不具體,但因為出現(xiàn)了“丁雷”一角,黃渤一拍腦袋,心動了。“我跳過舞,也教過舞,也當(dāng)過教練,也有過類似的青春,所以說這個人物離我不遙遠。”
原來,在《熱烈》里,有自己心心念念的過往。
為了丁雷,黃渤發(fā)了一條微博:“慶幸自己在年輕迷茫時有過一段為熱血熱愛不顧一切的日子。”
“為什么懷念?”我問他。
因為,“(現(xiàn)在的自己)確實是沒有之前純粹”。黃渤的坦誠,來得突然,但也意外。“現(xiàn)在創(chuàng)造完一個角色,自己也高興,但不會像年輕時一樣欣喜若狂,因為自己和觀眾都認(rèn)為這是自己應(yīng)該的,這就是我現(xiàn)在面臨的每天的工作。”

他很少在公眾場合收斂自己的坦誠,無論是在采訪里,還是在活動上。今年49歲生日的前兩天,他上熱搜了。這一次,裹挾著他的聲浪,不再似從前充滿贊美和掌聲。
《學(xué)爸》路演時,一名觀眾站起來質(zhì)問他,前兩年出演的《外太空的莫扎特》,“為什么這么爛?”
顯而易見的,這名觀眾質(zhì)疑的,并不是黃渤的能力。
黃渤的演技,一直獲得認(rèn)可。無論是“影帝”的成績,還是周星馳口中“喜劇王中王”的夸贊,抑或是其作為國民演員的口碑。
在現(xiàn)場,黃渤不忘先打圓場:“(觀眾)說出來說明他還是關(guān)注我、愛我,所以他有時候才會替你覺得你怎么會這樣,因為他之前對你可能有一定的標(biāo)準(zhǔn)。”
他也十分真誠和得體地回應(yīng)了這位觀眾的質(zhì)疑:“我們會面臨失誤、面臨選擇,像有一些題材你不去嘗試就會永遠站在原來的地方,去嘗試它有可能成有可能不成。往前走一步都有可能是分岔口,這個過程得到很多也失去很多,人不可能永遠都走在上坡的路上,無論起伏這都是我需要面對的人生。”
黃渤不想做一個安于現(xiàn)狀、不去嘗試的人,因為這樣不會讓他找到快樂。
尋找快樂對于大多數(shù)人來說,往往意味著一場冒險。在未知之境等著的,可以是驚喜,也可能是迷途。
但黃渤總想多試試。
他總是笑稱自己是“努力派”,是努力讓黃渤得到了長時間的順?biāo)欤酥痢兑怀龊脩颉返难荻鴥?yōu)則導(dǎo)。在《一出好戲》以13億票房真正成為“一出好戲”后,黃渤繼續(xù)在音樂劇領(lǐng)域里把“好戲”進行下去。
人生或許也存在一種能量守恒定律:與外界的摩擦減少了,與摩擦相抵消的作用力也會變得微弱;與內(nèi)心的斗爭慢下來了,激情的火花也可能會熄滅。
黃渤渴望保持那團創(chuàng)造的火種不要熄滅。他還在向外索求,不斷去跨界,去畫畫、攝影、做泥塑,沉迷于明清家具,帶著藝術(shù)品去參加展覽。
黃渤在尋找快樂。
黃渤最“出圈”的創(chuàng)作,應(yīng)該是拿透明材料創(chuàng)作出了雕塑作品“激浪”(breaker)。從另一層面來看,“激浪”通體呈一個浴缸的形態(tài)。
在實現(xiàn)藝術(shù)審美的同時,黃渤也追求實用,“當(dāng)一個器具得到使用了,存在才構(gòu)成意義”。他會把“激浪”放進海里,讓“激浪”和海水融為一體,構(gòu)成了液體和固體的統(tǒng)一。他把“激浪”搬到現(xiàn)代舞的劇場里,讓舞者從“浪花”邊緣自由滑落,或從“浪邊”恣意伸展。在舞臺上的“激浪”,可以是一個浴缸,也可以在血一般紅的燈光落下后,變成生命的原點,在強光直射下,似乎隨時會跟著生命的消逝沖向死亡的火海。
黃渤最“出圈”的創(chuàng)作,應(yīng)該是拿透明材料創(chuàng)作出了雕塑作品“激浪”(breaker)。從另一層面來看,“激浪”通體呈一個浴缸的形態(tài)。
器物與身體、舞臺,構(gòu)成了一首散文詩。這首散文詩,是黃渤和舞蹈家高艷津子跨界合作的現(xiàn)代裝置舞劇《談·香·形》。
結(jié)束《學(xué)爸》上海首映會的第二天,黃渤坐著最早的班機回到北京。這一天的他,不見風(fēng)塵仆仆和疲憊,反而精神煥發(fā),工作人員說他“狀態(tài)極好”。
在劇場內(nèi),褪下了“演員”的外衣,黃渤露出了一個藝術(shù)創(chuàng)作者嚴(yán)肅的面目。
在彩排時,他露出了處女座的“挑剔”屬性。站在控制臺正中央,目視前方舞臺,盯著舞臺上的一舉一動,對攝影師說,“鏡頭切入慢了”;跟演員說,“下臺時要趁燈亮起前完成”“淺色衣服容易被觀眾看到”。
哪怕是對于作為舞臺裝置的雕塑作品“激浪”,或是作為背景的泥雕人像,黃渤也講究打光的強度和方向、作品擺放的位置和跟整體環(huán)境的協(xié)調(diào)。他叫來工作人員,搬搬抬抬,死磕每一處細(xì)節(jié),也不會輕易容許一丁點缺陷的出現(xiàn)。
一動一靜,力求完美。
晚上7點30分,這場舞劇開始了。廣播提前通知在場人員,不要錄制,此次是內(nèi)部首演,
黃渤看起來有點緊張。演出期間,他一直站在觀眾后方的位置,一直朝舞臺看著,時不時雙手抱胸,或者右手托著左手、左手托著下巴。
接近一個半小時的演出,在多番鼓掌中結(jié)束。黃渤看起來松了一口氣。他坐在高腳椅上,主持一場觀后交流。
大鵬站了起來,調(diào)侃道:“今天是《學(xué)爸》全國上映的首日,但渤哥出現(xiàn)在這里,而不是電影路演的現(xiàn)場。”大鵬像個“托兒”一樣,將黃渤的心思說了出來。
演員譚卓原本在京郊,也為黃渤騰出了一個晚上來給好友捧場。導(dǎo)演李玉原本在閉關(guān)構(gòu)思劇本,也為此前來觀摩尋找靈感,不得不離場后,不忘發(fā)來一段“觀后感”,讓一同前往的好友程青松代為表達。
黃渤臉上寫滿雀躍,期待著從這群最熟悉的好友身上得到最真實的反饋,在一個全新的跨界合作中感受創(chuàng)作的新鮮,“在不同的創(chuàng)作里邊,體驗到已經(jīng)丟掉的一些快樂”。
這是此時的黃渤最想做的事。
畢竟創(chuàng)作不易,快樂難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