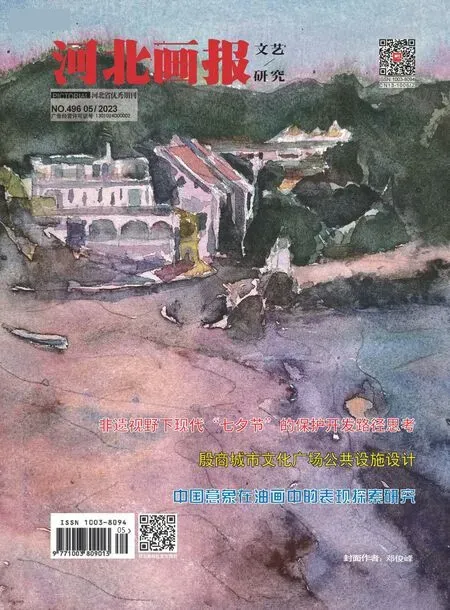欽州傳統民居文化元素在中國畫創作中的應用研究
黃國存
(欽州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
中國畫創作有鮮明的空間感,能夠營造出較強的情感氛圍,使得繪畫技巧與水平達到較高標準。中國畫創作中的空間感源于諸多元素,其中,便包括民居元素。欽州民居具有極為豐富的社會內涵,且裝飾藝術形式具有多樣化,能夠滿足建筑風格融合的實際要求,是我國獨特的文化元素,為中國畫創作提供了豐富資源。另外,得益于獨特的地理位置與海洋文化元素影響,欽州民居的藝術表現力更加明顯,不僅能夠實現對傳統建筑文化的繼承與發展,而且有利于增強中國畫的文化特性,使得畫作更具有民族性。
一、欽州傳統民居的特點
(一)院落漢族民居
欽州漢族民居的基本單位是“進”,每進包括三間或三間以上,即兩側的客房和中間的廳堂,兩側客房數量以廳堂為軸對稱增加[1]。外側客房前方是廊坊,廊坊和“進”共同組成了院落。
欽州院落式漢民居中,一進住宅是最為基本的院落形式,這一進中包括三間房和兩廊,而且還配有一個天井;多進住宅是以廳堂的中軸線為基準,不斷基于一進格局不斷向縱深發展而成的住宅形式,五進是民居中最大的進數。在多進院落格局當中,年紀最長者居住在最深一進中,該進的廳被稱為祖廳。從現存的院落式漢民居中不難發現,欽州地區漢族民居的進數以及開間數并無定數,這種不統一與業主身份地位、經濟實力有關,更與宅基地的寬窄深淺有直接關系。
在保存至今的欽州院落式漢族民居中,長田村的余屋鑊耳樓以及大蘆村勞氏古建筑群最為典型。鑊耳屋是家境殷實的象征,這種建筑形式只有獲得了功名的鄉紳才能夠使用,象征著官帽兩耳,唯有功名的鄉紳方能采用,用于壓頂擋風的龍船脊和鑊耳墻形似官帽,寓意“獨占鰲頭”前程遠大。余屋鑊耳樓為三座三進宅院,每一進都是有著兩層三開間的磚石結構,所有山墻頭均為“鑊耳”造型,這個宅院保留著欽州最完整的屋頂灰塑。勞氏古建筑群當中也建有鑊耳樓,不過這一占地總面積為22萬m2歷經明清兩代建設而成的建筑群中還包含以下建筑:(1)沙梨園;(2)蟠龍堂;(3)三達堂;(4)雙慶堂;(5)陳卓園;(6)東園;(7)東明堂;(8)富春堂;(9)中公祠。勞氏古建筑群的整體格局顯現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狀態,宅前設塘、屋后種樹,后山的七棵蓽樹形似北斗七星。勞氏古建筑群不僅建筑類型以及格局獨具特色,古宅中沿用百年的楹聯也極具代表性,這些內容豐富、辭藻雋永的楹聯使得古宅的人文氣息更加濃厚,也讓它享有“廣西楹聯第一村”的美譽。
(二)圍屋客家民居
客家人多善于自我保護以及遷徙,這也決定了客家民居以圍屋建筑最為常見,其特點是多戶同宗居民共同居住在一起,民居四周為防護墻,內有祠堂,且每戶居民均有獨立的房屋及院落。福祿劉氏圍屋、坡賴氏圍屋均為典型的圍屋式民居,前者位于福祿村,有數十戶同宗居民居住于此,圍墻內有多個單獨的四合院,布局靈活,可以隨意走動;后者位于社邊坡村,圍屋四周的防護墻由石頭砌筑而成,高約4m~5m,厚約0.8m~1.0m,防護墻表面設有多個槍眼,此外,還建有數個炮樓,門樓門洞高2.8m、寬1.8m,裝有三重樓門,由內至外分別是雙開推門、閘門還有拖櫳門。
二、將民居元素用于中國畫創作的特點
(一)客觀寫實
畫家多使用寫實的手法創作中國畫,簡單來說,就是通過準確刻畫日常生活所存在事物的方式,對自身情感進行表達。作為相對質樸且原始的創作手法,寫實的關鍵是再現客觀世界,畫家可以通過寫實的方式,還原傳統民居的特點和民居內人們的生活狀態,使民居形象躍然于紙上,這樣做的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使地域文化得到傳承;二是為生態文明建設及相關工作的開展助力;三是為地域文化基因提供全方位的保護,為鄉村振興目標的實現奠基。
(二)抒發情感
將民居元素融入中國畫,可使中國畫在情感抒發方面所具有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對比含有民居元素的畫作和不含民居元素的畫作能夠發現,民居元素的加入,能夠使畫作色彩變得更加豐富且明亮。另外,考慮到我國幅員遼闊,各地的藝術風格、生活方式和民居特點均有所不同,因此,在畫作中加入極具地方特色的民居元素,一方面能夠使畫作更加復雜且華麗,另一方面可以賦予畫作更為豐富的內涵,其現實意義有目共睹[2]。
(三)夸張多樣
隨著科技的發展,各國之間的聯系變得越發緊密,西方文化給中國畫所帶來影響逐漸顯露了出來,藝術交融成為大勢所趨。在此背景下,一部分畫家選擇跳出寫實手法的“舒適圈”,進而選擇利用藝術手法對民居、民居內人們的生活加以展示,這樣做的優點在于能夠使個人情感得到更加直接的體現,畫作的視覺沖擊力也會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強。對現階段常用表現手法進行分析不難看出,現有表現手法普遍具有變形、夸張等特點,將全新的表現手法、變化多樣的色彩與傳統水墨相結合,可以使中國畫的題材得到拓展,在賦予畫作民族文化內涵的前提下,使畫作文化內涵變得更加豐富[3]。
三、將民居元素用于中國畫創作的意義
行走在欽州民居青石板小徑中,能夠感受到傳統民居的美感與文化氣息。這一點也能夠觸動畫家的內心情感,與之相關的民居文化元素自然成為畫家筆下描繪的對象。傳統民居中文化元素符號較多,例如,民居的墻體與瓦頂之間形成了鮮明的疏密、虛實關系,充分體現出中國畫創作中虛實結合原則,再例如,畫作中的留白部分與物象之間具有交相呼應特點,二者形成具有流動性的畫面,體現出“虛中有實”“實中有虛”的獨特感覺,另外,上述創作方式也符合中國畫的基本要求,由此達到“入畫”的境界。對民居題材的畫作而言,可借鑒的研究理論較少,針對中國畫的創新方向展開研究,不僅是研究人員關注的重點,同時也是畫家們不斷創新表現形式的有效方法,鑒于此,在目前中國畫創作過程中,需要融合傳統民居文化元素,并探索出符合現實情況的創作路徑,為中國畫創新助力賦能。
對繪畫創作的一般情況加以分析可知,藝術創作的主要路徑是對景寫生、非對景創作。其中,對景寫生部分,要求畫家以真實的自然景色作為參照物,并在繪畫創作中重點關注“景物寫真”,非對景寫真則強調對繪畫理論的理解,并根據個人想法進行創作。欽州傳統民居作為重要的文化元素符號,為中國畫創作提供了現實題材,為確保該文化元素與中國畫有機結合,要求畫家一方面保留民居的客觀特征,另一方面融入主觀情感,充分發揮中國畫創作的精神內涵,實現去粗存精、虛實結合的創作目標。
四、將民居元素用于中國畫創作的難題
文章以欽州民居建筑風格、文化元素為出發點,圍繞民居元素在中國畫中的運用展開討論,希望能夠在宣傳欽州當地獨有人文及景觀資源的前提下,使中國畫題材變得更加豐富。研究發現,導致民居元素難以在中國畫中得到充分運用的原因主要有三個,分別是:
(一)表達語言的使用
以中國畫的山水寫生為例,作為中國畫創作的一大難題,寫生既要求畫家快速確定自然景物獨有的美感,還要具備使用不同語言對景物之美進行充分表達的能力,由此可見,要想創作出優秀的畫作,畫家不僅要明確畫什么,同時還要了解怎么畫。翻閱相關文獻資料不難發現,以“民居”“中國畫”為關鍵詞的文章數量十分有限,如何科學運用語言符號,使民居元素成為畫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便成為困擾畫家的一大難題。要想解決該難題,畫家應深入了解民居的風貌、歷史和造型,在此基礎上,結合民居元素確定創作的切入點,保證畫作具備有別于其他畫作的視角。另外,將民居元素用于中國畫創作還存在以下阻礙:隨著時間的推移,群眾對民居的認知基本固定,這也在無形中提高了畫家運用民居元素的難度,極易由于畫作最終呈現出的效果未能達到人們的心理預期,而導致畫作面臨失敗的風險。
(二)造型和筆墨的關系
造型不僅是承載語言形式和內容的載體,還是民居極為重要的表現內容,要想準確地描繪民居,關鍵是要做到以民居的造型為落腳點,靈活運用不同的方式對其加以表現。黃格勝教授判斷民居是否具有美術價值的標準有三個,首先是民居所在地區的地形是否具有明顯起伏,其次是民居是否具有古樸的韻味,最后是民居附近是否存在過多的干擾因素。
中國畫與油畫等繪畫形式的區別,主要是中國畫往往需要使用墨和線描述想要表現的對象,對筆墨進行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創作中國畫時,畫家既要保證自己所使用的筆墨具有審美價值,還要保證筆墨和物象高度匹配,切記不得將筆墨視為獨立存在的個體,而是應當將筆墨與物象充分融合。由此不難看出,要想使民居完全融入中國畫,關鍵需要做到兩點,一是充分發揮書法用筆獨有的特點,突出畫作的生動性和趣味性,二是根據物象更改筆墨的用法,使二者成為一個整體[4]。
(三)形成獨具特色的圖式
創作不僅是畫家對個人見解和看法的表述,同時還與畫家的綜合素質密切相關,換言之,要想準確掌握畫家的藝術水準,關鍵是要對其所創作畫作進行深入分析。其中,最應當引起重視的部分便是圖式,作為中國畫常見的表現形態,圖式可以簡單地理解為畫家通過畫作所展現出的獨特面貌及語言形式,對曾在中國畫發展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的畫家們進行剖析不難發現,這些畫家均具有極為鮮明的藝術特征,由此可見,要想使畫作更具有藝術價值,關鍵是要確保畫作風格兼具唯一性、獨創性。畫家只有不斷發散思維,對畫作主題和所包含元素進行創新,才能使畫作具有相應的圖式,也才能使自身影響力得到進一步的提升。
五、民居元素在中國畫創新過程中的具體應用
將民居元素融入中國畫的初衷,主要是民居元素既符合中國畫所遵循的創作規律,又具有傳承歷史文化、文明發展成果的功能。新時期,畫家應深入挖掘民居元素所蘊含的美學價值,堅持求真務實與開拓創新相結合,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畫得到可持續發展。要想使民居元素的價值得到最大化實現,關鍵需要從形式、內容和色彩等方面出發,將民居元素與中國畫充分結合,具體做法如下:
(一)形式方面
創作中國畫時,畫家應做到充分利用多種形式語言,例如,在畫作中加入民居元素,通過元素再創造的方式,增強民族文化所具有的創新性,與此同時,賦予畫作本身更符合預期的觀賞效果和欣賞價值。欽州各民族民居的布局形式均較為特殊,畫家可以充分發散思維,對民居元素、主體內容進行提煉并夸大,突出畫作所具有的簡約化、平面化特征,充分彌補中國畫缺少現代感的不足,在保證所創作畫作充分展示民居元素的前提下,對其所具有時代感進行凸顯。
(二)內容方面
欽州境內生活著多個少數民族,這也使得當地民居始終保留著極為鮮明的特色。在創作中國畫時,畫家應當從內涵、形式等方面出發,對傳統民居獨有的文化元素進行挖掘,確保自身對民居元素具有準確的了解,在此基礎上,以中國畫為載體,對民居元素進行傳承與革新,確保欽州民居所具有文化特色能夠通過畫作得到全方位的展示[5]。
(三)色彩方面
我國民間文化普遍習慣利用裝飾性色彩強調文化的原生態和原始性,欽州的傳統民居也是如此。因此,在創作中國畫時,畫家可以打破傳統思維的桎梏,大膽使用裝飾性色彩,對自身情感進行表達。事實證明,將裝飾性色彩融入畫作的作用有三個,首先是強調民居特有的原生特點,確保人們通過畫作便能夠感受到當地的風情,其次是充分展現民居元素,能夠使畫作的效果最大程度接近畫家預期,最后是靈活運用不同色彩,可以轉變中國畫過于追求空靈境界的情況,通過賦予畫作時代韻味的方式,使欽州人獨有的情感與觀念融入其中,從而使欽州民居元素得到傳承以及發展。
六、結語
綜上,研究中國畫創作中欽州民居文化元素的運用,先對欽州傳統民居的特點等內容加以說明,隨后,論述了中國畫創作中民居元素融入存在的難題,指出畫家應當做好語言規范表達、明確造型與筆墨之間關系等工作,并且在創作形式、內容、色彩方面對中國畫進行創新,才能使民居元素得到有效應用。未來研究人員應重點關注中國畫的創作背景,對不同文化元素所具有優勢與特征進行分析,同時注重民居文化元素創新,使得傳統文化迸發出活力,在凸顯欽州民居文化的歷史地位的前提下,為中國畫的創新發展提供明確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