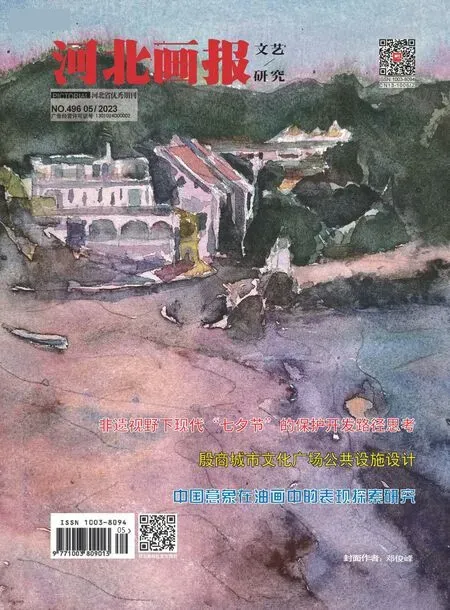高低語境理論視角下陶瓷產品跨文化傳播研究
——以紀錄片《我是你的瓷兒》為例
丁凱豪 胡藝馨 張智 張艷
(河北經貿大學 外國語學院)
陶瓷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代表,具有獨特的美學及實用價值。隨著“一帶一路”倡議和“國內國際雙循環”發展新格局的提出,加強陶瓷文化的對外宣傳,對塑造陶瓷企業形象及產品推廣意義重大。近年來,通過紀錄片這一形式傳播中國陶瓷文化正在成為一種新趨勢[1]。因此,提升陶瓷類紀錄片的拍攝質量,使其為廣大非漢語語境的觀眾所接受,是增強傳播效果的關鍵。
1976年,美國人類學家愛德華·霍爾,在其著作《超越文化》中提出了高低語境理論,即按照人們傳遞信息時對語境的依賴程度,將文化分為高語境文化和低語境文化。霍爾在書中寫道:“他的行動的背后潛藏的東西越多,他能告訴你的東西就越少。”[2]可見,在高語境文化中,大多數信息都存在于物理環境中,很少的信息被編碼在口頭信息中,而在低語境文化中卻正好相反。
如今,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為不同文化間的碰撞提供了平臺,引發了思想與文化的交換,反映在文化價值維度上,則是由高語境社會向低語境社會的位移[3]。在信息由高語境文化(如中文)向低語境文化(如英文)傳播過程中,文化間難免發生碰撞。降低跨文化傳播中的矛盾、提升傳播效果,則是本研究要解決的問題。本文基于高低語境理論,以紀錄片《我是你的瓷兒》為例,分析我國陶瓷紀錄片跨文化傳播的有效路徑,以期為我國文化傳播與經濟交流提供建議。
一、高低語境下的符號特征
(一)語言符號
高語境文化所屬的社會成員在表達感情和傳遞信息方面,喜好用含蓄、間接、隱晦的方式;低語境文化所屬成員則喜好用坦率直白的方式進行溝通[4]。由此可見,高語境文化是含蓄內斂的;低語境文化是簡單直接的。成功的跨文化傳播必須要完成從高語境到低語境的轉換,用簡單清晰的語言來傳播高語境文化。紀錄片《我是你的瓷兒》利用直接準確的詞匯進行敘述,實現從高語境向低語境的信息輸送。
例如,在第二集介紹制瓷的工序時,解說詞說道“他們赤著腳光著膀子……開山、碎石、淘洗……燒窯、拉坯。”運用一系列簡單的動詞并列,生動地展現了制瓷的主要工序,便于低語境文化受眾的理解。簡單易懂的語言,加上化學方程式,符合低語境理性的特點,有利于完成高語境到低語境的傳播。
(二)非語言符號
非語言是紀錄片內在品格的體現和要求,是紀錄片實現跨文化交流和傳播的有效手段,也是促進紀錄片創作的動力之一[5]。適當的非語言符號的運用有利于低語境文化受眾的理解,該紀錄片中的畫面和音樂就頗具特色。
在第一集介紹老包燒制茶葉末(茶葉末釉:我國古代鐵結晶釉的品種之一)的過程中,鏡頭運動豐富。先是推鏡頭,鏡頭由遠及近推向制釉瓷石和老包的手,然后是掰開、砸碎釉果的特寫鏡頭,之后,把攝像頭置于缸底,仰拍注水的過程,再到混合時的俯拍。鏡頭的運用十分巧妙,讓觀眾有身臨其境、置身于陶瓷作坊之感。
該紀錄片運用了多種主觀音樂,即功能上的音樂,在畫面上沒有聲音的來源,是對畫面的補充、解釋,起到充實、烘托主題等作用[6]。不同畫面配上不同的音樂,推動人物的出現,有利于感情的抒發。在第三集中,介紹李磊穎教授的嬰戲圖和古彩時,運用舒緩歡快的音樂,突出了創作的主題,表現了小孩的無憂無慮。不論是畫面還是音樂,都符合當代美學審美,容易進行文化傳播。
(三)思維方式
中國文化具有五千年的歷史,古人留下的哲學思想指引著中國人思考問題的方式。以美國為代表的低語境國家歷史較短,側重于邏輯關系,是典型的線性思維。文化歷史的差異造成中美兩國人民在思維習慣方面的不同,包括思辨思想與經驗主義,邏輯分析與直觀體驗[7]。
在第一集中提到的老于和老萬,運用熒光光譜分析常量元素,對比微量元素,進行定量分析,探索單色釉的無限可能。這些科技手段具有現代科學研究的嚴謹性、邏輯性,符合低語境理性思維的特點,有利于西方觀眾理解陶瓷文化。
景德鎮陶瓷匠人羅小聰,二十年前就開始研究“剔青”工藝,主要從版畫和漆畫中獲取靈感。青花剔青過程中,匠人暫時放棄傳統工藝,憑借自己的感覺進行創新。從最初的沒有層次、沒有感覺到后來成為一種新的陶瓷裝飾工藝,匠人運用個人直觀體驗進行突破創新符合低語境的文化特點,有利于低語境受眾理解匠人在陶瓷創作過程中的心路歷程,有利于該紀錄片的跨文化傳播。
二、高低語境下的敘事結構
(一)微觀、淺層、個人的敘事視角
中華文化歷史悠久,文明博大,處于一個語境階梯的高語境的極端[8]。反映在中國紀錄片中,則是大量信息多存儲于物質環境中,顯性信息非常少。《我是你的瓷兒》以第一人稱的視角介紹本片的主角——中國瓷器。高低語境的劃分并非是絕對清晰的兩個不可交疊的對立體,實際上是一個連續體的兩端[9]。“我,來自北宋景德元年,為了見到你,我已經走了一千年……”在高語境-低語境這一連續體上,本片的解說視角處于低語境的一端,將信息編碼為顯性代碼,第一人稱的解說詞加強了故事的真實性,不需要借助語境就能直接獲取信息。
高語境的交流需要編程,如果沒有編程,交流是不完全的,而低語境交流可以超高速度延伸[10]。《我是你的瓷兒》采用了“板塊化”的敘事方法,通過介紹不同類型的瓷器來講述瓷器的故事。故事之間看似關聯不大,但每一部分始終圍繞“新老碰撞,由簡入繁”的主題來講述陶瓷的故事。這些故事皆由微觀淺層出發,以小見大,觀眾不需要有深厚的理論基礎就能夠讀懂中國陶瓷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蘊,領略中國陶瓷的魅力。
(二)生活化的敘事
生活化敘事中,即采用敘述者個人的經歷來敘述故事,這種敘事方法更具親切感,同時又能產生代入感。《我是你的瓷兒》從生活中出發,按照生活中的故事描繪生活。依據敘述者與敘述對象的關系,敘述者有異敘述者與同敘述者之分,同敘述者就是故事中的人物,異敘述者則相反[11]。《我是你的瓷兒》的第五集采用同、異敘述者并行的策略,緊跟人物身后,充當故事的記錄者。
“景德鎮的新一天,是從一籠胡蘿卜素包子開始的”這是俄羅斯留學生塔西雅的一天。她為了創作一幅新作品,從找熟人求助解決問題,到完善自己的作品……此時記錄視角從異敘述者轉化為了同敘述者,從異敘述者向同敘述者無縫地轉換,既是純粹的故事記錄者,也是故事的參與者,兩者相結合的方式對于處于低語境環境中的西方觀眾來說也更加容易接受。
(三)平直的敘事結構
人們發現,在跨文化語境中造成溝通不暢的主要原因是語篇模式的差異,而語篇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思維模式[12]。在低語境文化的國家,尤其是英語語系的國家,他們的思維模式是一條直線,因而直接的表述方式對于他們極為重要。高語境國家恰恰相反,稱之為“螺旋型”思維模式。正是由于兩者之間的差異,部分西方人一度對東方人持有偏見,不如西方人直率,這種偏見降低了跨文化交往的效果。
“要想窮,燒郎紅”,就算沒有燒制瓷器的相關知識,也能從這句話了解到郎紅釉燒制的困難。通過高勇旺夫婦的故事,觀眾可以了解到:“郎紅釉的紅色來源于銅元素,當溫度達到1300攝氏度時,釉面呈現出紅色,允許誤差的范圍只有20度”從實踐到理論,從郎紅釉的前世今生到現代科學解釋,無論東西方的觀眾都能從其中清晰、直觀地了解到中國的瓷器文化,這對于破除西方固有觀念至關重要。
三、高低語境下的價值觀
(一)關照個體
1983年,吉爾特·霍夫斯塔德基于對60個國家的大量樣本調查研究后提出了文化維度理論,其中最引人關注的是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兩個維度[13]。那么在面對相同的《我是你的瓷兒》時,高低語境受眾的認知焦點是否會有所差異呢?
在《我是你的瓷兒》中的每一集均展示了關照個體的特征。例如第二集中,景德鎮開啟了工業化燒制時代后,黃國軍遠離城市喧囂,傳承了四百多年前的古法制瓷工藝。高語境受眾在觀看視頻時關注到他個體背后的集體背景,而低語境受眾更多地關注黃國軍作為個體的個人特質。這一檢驗結論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霍夫斯塔德所提出“個人/集體主義”文化維度的觀點,同時也證明了不同文化語境對跨文化傳播認知焦點的影響。
(二)以小見大
華麗的語言風格多見于高語境社會,使用細節性、描述性的詞匯,以豐富且富有表現力而著稱。精確的語言風格類似于Grice的“數量準則”,即“個人提供給他人的信息不應多于或少于必要的數量。”信息用精確的詞語清楚地表達出來,通常不需要使用額外的詞語等。這種風格主要見于低不確定性規避和低語境文化,比如美國,在那里“缺乏共同的假設,要求美國說話者用語言表達他或她的信息,使他或她的離散意圖清晰而明確[14]。”
在第四集中,“十二花神杯”有花有詩,正面繪制十二個月份的花卉,對應著花卉的花神。背面題著詩文,既是歌頌花朵,也是歌頌花神。詩詞歌賦,盡顯華麗,生動地體現了高語境國家語言風格的特點。通過細致地描述匠人代表制作陶瓷的工藝,不僅傳神地展現了“工匠精神”,更展示了景德鎮陶瓷欣欣向榮的景象,也折射出歷史悠久、源遠流長的中國陶瓷文化。
(三)勞動美學
美學產生于勞動之中,審美即是人類勞動生產所固有的特性之一[15]。非遺文化的歷史也是人的歷史。支撐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發展的是一群堅守匠心、精益求精的人。第一集中,主人公小陳出身于瓷器世家,她的研究課題是誕生于北宋的影青瓷。為了復刻影青釉,小陳按照古法上山收集枯盡的樹枝制作釉灰。樹枝燃燒形成的硅酸鹽是釉的主要成分。在整個研究、制作影青瓷的過程中,小陳憑借對瓷器的熱愛,躬耕田園,不采用現代機械工藝,體現了工匠們的一代代傳承古典制瓷技法和勞動精神,是延續中國古老文明的最好詮釋。
四、結語
本文基于高低語境理論視角,以《我是你的瓷兒》紀錄片為例,研究陶瓷產品跨文化傳播的路徑。可以看出,客觀寫實的手法、有機結合的畫面和音樂,符合低語境文化的敘事策略和敘述結構,使西方觀眾更容易接受。價值觀層面來看,關照個體,以小見大的手法對于展示中國陶瓷文化的深厚底蘊至關重要。作為一部向國際宣傳中國陶瓷文化的短視頻紀錄片,《我是你的瓷兒》不僅助力了瓷器的傳承,還探索著瓷器的多重可能,有利于打破西方國家對中國文化的刻板印象,讓世界看到多元的、燦爛的中華文化。對于企業而言,在跨文化交際中要注意到語境差異,在傳播過程中關注高語境到低語境的轉換,避免文化沖突,使雙方經濟合作和文化交流順利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