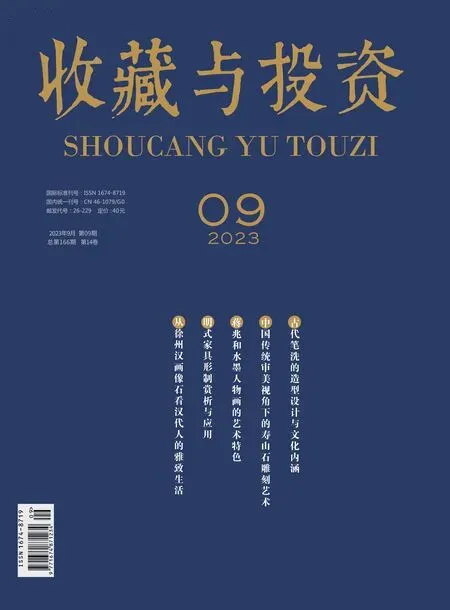蔣兆和水墨人物畫的藝術特色
薛玉敏(西北師范大學,甘肅 蘭州 730070)
20世紀的中國,是社會發展日新月異的時代,伴隨著經濟、政治的變革,文化藝術也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封建王朝衰亡,其長期孕育的傳統人物畫也開始由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轉化。蔣兆和便是在中國人物畫變革中脫穎而出的一位大師。時代造就了蔣兆和,他以其藝術成就促進了時代的變革。蔣兆和順應時代的發展,博采眾家之長,為中國人物畫的轉變與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一、蔣兆和水墨人物畫的藝術表現形式
(一)融合中西的造型
蔣兆和認為在進行水墨人物創作時,不僅要學習西方素描的造型基礎,還要結合中國傳統畫的特色。1980年6月,蔣兆和曾對程永江及劉曦林說:“沒有成立國畫系之前,我教過一段時間素描……要發揚六法論里的這個原則,在傳統的基礎上吸收外來畫法,融會貫通,形成具有現代寫實能力的造型基礎。”我們現在所講的造型,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當然,也不是對西畫素描的照搬,而是在傳統繪畫的造型基礎上更進一步,彌補自己的不足,推陳出新,建立具有現代時代精神、中華民族風格的造型藝術。
蔣兆和融合中西造型的本質是以傳統繪畫造型為主,西方素描造型為輔。西畫素描有其自身的優點,西方人對解剖學、透視學、光學等的研究十分深刻,故而繪畫時所用的觀察方法和在形象上的刻畫大多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繪畫形象更加準確,畫面的效果也很統一。中國的繪畫造型,籠統地說,其基本規律就是“骨法用筆”。骨者,乃是構成人體形狀之解剖關系;法者,即是在平面的紙上畫出有體積感,能體現各部分長短比例和角度等透視關系的形象。古人通過“骨法用筆”,將人物形象表現出來,顯然有些脫離客觀現實。所以,我們所要做的,是融合中西方的造型優點,只有把西畫的素描手法融入中國畫的形式結構之中,才能將中國畫的形式美感發揚光大。蔣兆和在創作水墨人物時,特別重視人物的寫生,在人物寫生時他會運用科學知識,例如解剖學等來觀察人物形象,根據西方的素描知識來分析人物形象,但并不以素描的表現方式來描繪人物形象,而是在力求人物形象結構精準的同時,利用傳統繪畫的線條以及皴擦點染等技巧來表現人物形象,使其具有體積感和空間感。比如《賣子圖》,蔣兆和整合了中國畫的傳統技法和西畫中的光影變化,所繪人物形象真實、淳樸、感人,向世人展現了母子之間難以割舍的情感。
(二)靈活精湛的筆墨
中國畫之所以不同于西畫,最明顯的就是作畫工具不同,我們使用的毛筆區別于西畫的油畫筆、炭筆,使用的墨水區別于油畫顏料。中國畫的筆墨千變萬化,繪畫行筆時勾、皴、點、染,墨又分濃、淡、干、濕、焦,散發國畫獨特的韻味。蔣兆和認為,筆和墨的用法雖有不同,但是它們之間的聯系緊密。蔣兆和曾說“以筆為主見其骨,以墨為輔見其肉”。就是說要用筆法對所繪人物的形象進行概括,然后再用墨法去充實人物形象,使其形象更加飽滿。通過筆法、墨法的巧妙結合,完整地表現有筋有骨、有血有肉的具有生命力的形象。
用筆用墨雖然變化豐富,但還是要建立在所繪人物形象之上。繪畫前要全面地分析所繪的人物形象,哪里是主要的,哪里是次要的,哪里是凹進去的,哪里是凸起來的,人物情緒是開心的還是難過的,都要做到心中有數,才能達到“意在筆先”的效果。在繪畫過程中要盡力表現人物形象的真實性,通過筆墨的濃淡虛實來體現所繪人物的前后關系,利用線條的變化來表現所繪人物形象的內在結構,當線條表現不足時,還要通過筆墨的皴法來使所繪人物形象更加完善。當然,僅將所繪人物的外在形象畫好是不行的,還要表現所繪人物的精神氣質。畫家要對所繪人物的形象有所感受,讓這種情感在筆墨之間流轉。如《杜甫像》中,蔣兆和用白描加皴的手法塑造了這位詩圣的形象。畫中杜甫的衣紋寥寥數筆,面部著意采用皴染的方式刻畫,表現了杜甫直面現實、憂國憂民的情懷,堪稱對杜甫的寫心之作。
(三)傳神、寫心的技巧
蔣兆和在創作水墨人物時,都是用自己獨特的方式來傳達內心的情感。蔣兆和重視繪畫的形式,通過對畫面形式感的處理,來抒發情感。如作品《賣花女》,這幅作品中的女孩面部干凈,沒有用過多的筆墨修飾,反而襯托出賣花姑娘的純潔善良。再如作品《盲人》,蔣兆和在創作時讓盲人的臉朝向陰影一側,采用了側逆光的手法,表達了蔣兆和的心情“人間黑暗地,有目其豈吾如”,同時反映了蔣兆和的感情在當時已經不局限于對底層百姓人生不幸的同情,更多的是對黑暗社會的抗爭。蔣兆和在繪畫時,善于用人物靜態來表達內心的情感。畫中的人物大多不是以動態的形式出現,但是就像人們常說的“無聲勝有聲”,這樣安靜的表現手法反而襯托出人物內心流動的情感。如《流民圖》,畫中描繪了百姓在死亡邊緣掙扎的場景,雖然這些人的動作幅度并不大,面部表情也不夸張,但是每個人的臉上都展現了一種走投無路的無奈,向世人訴說著那個時代的悲哀。
二、蔣兆和水墨人物的藝術情感表達
(一)藝術乃“真、善、美”的體現
蔣兆和曾在1981年10月對劉曦林說:“藝術的境界,無論人物、山水、花鳥,都包括真、善、美三個字。真,是反映生活的真實;善,是一種從善的精神;美,是各種物象特征的美。只要體現這種精神,就是好的藝術品。”“真、善、美”這三個字不是由蔣兆和創造的,但是蔣兆和的水墨人物畫卻對這三個字做了最好的闡述。
蔣兆和的水墨人物作品都是個人生活的反映,抒發的是對人生、對整個社會的感受,這樣的作品才是真實的作品。蔣兆和所處的是一個動蕩的年代,但是蔣兆和在創作時并沒有規避當時的社會現狀,而是將自己的所見所感用繪畫的方式表現出來,如《母親的希望》,作品的題頭詩“奶罷兒歡樂,兒肥母自夸。朝朝盼成長,帶上光榮花,”前兩句是對畫面的概括,把母親希望子女健康成長的心情表達出來,后兩句反映的是當時社會的現狀,也是畫家本人的心聲。他希望年輕的一代能艱苦奮斗,在這個時代能夠有所作為、報效祖國。再如作品《朱門酒肉臭》(圖1),畫中的一個小孩癱坐在地上,靠著墻邊,奄奄一息,無人救助,反映了當時社會的腐敗、人情的冷暖,值得人們深思。石濤說:“筆墨當隨時代。”在進行繪畫創作時,只有像蔣兆和這樣根據一個時代的特征,去展現一個時代的“真、善、美”,創作出的作品才能引發人們共鳴,才更加感人。

圖1 蔣兆和 《朱門酒肉臭》 88 cm×61 cm 1937 年
(二)深沉的悲劇意識
劉曦林曾說:“我認為蔣兆和是一位悲劇藝術家,并不是說他是一位莎士比亞式的悲劇藝術家,而是說他在造型藝術可行的范圍內,以訴諸視覺的形象,把人生最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給人以悲劇般的感受。” 蔣兆和從1936年創作的《賣小吃的老人》到1948年創作的《一籃春色賣遍人間》(圖2),展現了他在整個水墨人物創作盛期,都是從大眾人民生活角度出發,表現了在特殊歷史條件下普通平民的人生悲劇。

圖2 蔣兆和 《一籃春色賣遍人間》 98 cm×52 cm 1948 年
蔣兆和的這種悲劇情感是時代造就的,是時代帶給人們的創傷。蔣兆和將這些情感融入了自己的作品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蔣兆和在1943年完成的《流民圖》(圖3),這幅作品高2米,長約26米。畫中有在痛苦中沉思的知識分子,背井離鄉的農民,奄奄一息的老者,受傷的工人,食不果腹的婦女、疾病纏身的兒童……尸身橫臥、路皆乞丐,這些場景深刻地表現了畫家“哀民生之多艱”的悲情。除了《流民圖》,蔣兆和還創作了以兒童為題材的《流浪的小子》《賣線》等,這些都是當時社會帶給孩子不幸的體現,蔣兆和也借助這些作品表達了自己童年的辛酸、痛苦。此外,表現母子題材的《賣子圖》《轟炸之后》等,都是通過描寫當時母子的生離死別,反映時代的悲哀。

圖3 蔣兆和 《流民圖》 局部 1943 年
蔣兆和的繪畫題材總是能觸發人們的共鳴,兒童、親情、青春……一些本該體現人世間美好的場景,卻因為動蕩不安的時代而變得破敗不堪。但這些充滿時代傷痕的畫作從側面表現了蔣兆和對人民深摯的情感,以及對人生的思考和對社會的關注。
三、結語
蔣兆和在繪畫中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在水墨人物畫方面。他認為繪畫既要繼承傳統,又要推陳出新,要學會通過繪畫表達自己的內心情感。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其繪畫形式、思想內涵都帶有濃厚的時代特色。蔣兆和的一生,充滿坎坷,又受到戰爭的洗禮,算不上十分幸運,所以他的畫作總是充滿著現實主義色彩和憂國憂民的情感。蔣兆和的這些思想與成就將中國的水墨人物畫推向了一個新的歷史高度,并對其后水墨人物畫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