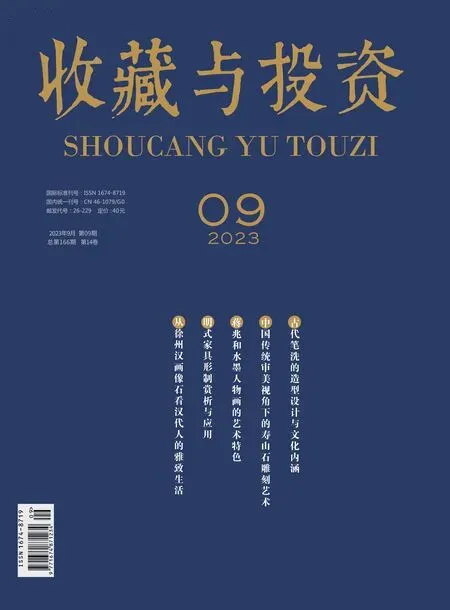古代筆洗的造型設計與文化內涵
王科苗(南京大學 歷史學院,江蘇 南京 210023)
一、筆洗之說
洗由商周時期的盤匜演變而來,《禮記·內則》載:“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沃盥之禮在商周時期很普遍,是一種特有的禮儀制度,但隨著制度的瓦解,盤匜也被洗所取代[1]。北宋曾鞏《墨池記》有記載,王羲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可見魏晉時期還沒有出現專用的筆洗,文人要在池中洗筆。宋代開始對洗有了考證和定義,但還沒有專門的分類。“筆洗”這一名詞真正出現是在明代,變成了浣筆的專用器具。明代屠隆《考槃余事》中記載:“凡妙筆書后,即入筆洗中滌去滯墨,則毫堅不脫,可耐久用。”這說明了筆洗的功能,因墨中含膠,為了不傷筆,需要在毛筆用完后進行清洗,以延長使用壽命。明文震亨的《長物志》記載:“陶者有:官、哥葵花洗、磬口洗、四卷荷葉洗、卷口蔗段洗。”可見,明代為了適應功能的改變,筆洗的器型也變得小巧,造型變得豐富多樣,迎合文人的審美趣味,真正走上了文人的書桌。
二、師法自然:筆洗的造型手法
(一)制器尚象之寫實造型
自然是人類最早的模仿對象。人類從自然界中獲取食物和生存經驗,從而躲避天災人禍,找到與自然相處之道。明清時期仿生器型十分流行,這類器物模擬自然界的萬事萬物,動物、植物甚至人物形象都可以融入筆洗的造型設計,造型往往寫實逼真,惟妙惟肖。筆洗作為浣筆之用的盛水器,造型多取材于水中植物,如荷花、蓮藕等,水中的動物:魚、蟾蜍、螃蟹、烏龜等。植物中的荷葉、艾葉、蕉葉等葉形是常見造型,這可能和原始人類用樹葉盛水有關。在陶器出現之前,人類翻卷葉片成勺形就成了天然的取水容器,葉片造型的筆洗帶有一種天真爛漫、返璞歸真的自然野趣;筆洗之中還常見一種以池塘為原型的設計,大抵因為在筆洗出現之前,文人最早在池邊洗筆。王冕的《墨梅》中寫道:“我家洗硯池頭樹,朵朵花開淡墨痕。”這種筆洗的設計思想很大程度來源于池塘,模擬的是池塘的自然生態,荷花魚鳥組成一個小小水世界,將池塘中常見的動植物:魚、蟹、荷花、荷葉組合在一起,有方寸之間見天地之感。圖1中,青玉把蓮水蟲荷葉洗,主體部分是翻卷成勺形的荷葉,葉片四周圍繞著荷花、水草,小蟹、螺、青蛙蟄伏于葉邊之上,正伺機而動,整個造型好似池塘一角,富有自然生趣。除了池塘之外,大海也是水的意象代表。器物造型也常被設計成海螺、海獸、蚌殼等常見的海中動植物形象,生動逼真。

圖1 清代青玉把蓮水蟲荷葉洗 故宮博物院藏
(二)忘形得意之抽象造型
中國畫大多有尚意的觀點,北宋歐陽修在《盤車圖》的詩中云:“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他提出了忘形得意的繪畫思想。唐代張彥遠的“形似之外求其畫”也是類似觀點,追求畫的意境之美與思想表達。文人畫的尚意觀點在文房用具中也體現得淋漓盡致,這類器具往往不追求過度模仿自然,而是從自然造物中提取相關意象,化用抽象的藝術手法,達到離形得意的目的。宋代花口形筆洗就蘊含著這樣的設計思想。花口形筆洗的樣式極為豐富,多采用葵花、梅花、海棠花等。從外觀上看,筆洗并不追求與花朵的形狀一模一樣,而是從不同花瓣的形狀中提取基本特征,用于口沿之上,達到不似而似的藝術境界。故宮博物院的藏品宋鈞窯天藍釉葵口淺洗,就是抓住了葵花花瓣較寬,邊緣內凹的特點,其造型雖不完全與花瓣相似,但是又表現了葵花的特征,清新雅致。
孟子曰:“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筆洗的器型中有一類特殊的幾何形器,大多是方形、圓形,造型樸素簡單,不加修飾。這種器型可能來源于古代“天圓地方”的造物思想。天圓地方,是古代勞動人民對自然環境的總結,日、月、果實、花朵,自然界中圓無處不在;圓被認為是圓滿團圓的象征,蘇軾詞云:“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當中表達了古人對團圓的追求;圓還有循環往復的寓意,太陽東升西落,周而復始,太極圖首尾相接,陰陽相生,萬事萬物都在圓的規律中運行。方在中國古代歷史中代表著莊嚴與秩序,《管子·形勢解》中談道:“人主身行方正……行發于身而為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方正是衡量古人品性的重要標準,是古代士人的道德準則和行為規范。方與圓承載著中國傳統造物思想和對美好品德的人格化追求。
三、器以載道:筆洗的造型觀念
(一)吉祥寓意
吉祥觀念早在原始社會就已經出現。原始先民將吉兇禍福寄托于神,創造了帶有吉祥寓意的圖案以求神靈庇佑[2]。在儒、釋、道三教以及神話傳說的影響下,吉祥圖案的題材越來越豐富,自然而然影響了文人的設計觀念。筆洗中常見一類帶有吉祥寓意的器型,題材廣泛,有桃子、石榴等植物造型,羊、鷹、魚等動物造型,也有取材自神話故事的龍、鳳凰造型,人物題材多以童子為主,還有部分取材自吉祥符號,如如意、祥云等。石榴造型寓意著多子多福的生育觀;靈芝被視為有起死回生之效的仙草,代表吉祥富貴、長壽福祿;桃子造型筆洗,受道家思想影響,有長壽之意;還有龍鳳呈祥、雙龍戲珠等諸如此類含有吉祥寓意的造型。除此之外,由于中國古代科舉取士的特殊性,文人想要尋求仕途、報效國家就必須要通過科舉考試。因此,帶有金榜題名、狀元及第、五子登科寓意的筆洗造型也屢見不鮮。如青玉鏤雕五子登科洗(圖2),洗身為圓形,周圍鏤雕有五個姿態各異的童子,童子神情天真自然,憨態可掬。將其擺在案頭不僅是對未來前程的祝福,也蘊含著對自己奮發讀書的激勵。

圖2 清代青玉鏤雕五子登科洗 故宮博物院藏
(二)君子比德
比德源自儒家美學,是以自然界中的某些景象與特征比作人的品格,孔子提出了“仁者之樂”的觀念,將自然界中景物與人的心性一一相對,使抽象的品德觀有具體的表現對象,自然美上升為人格美。文人通過與自然景物人格化對比進行反思,對理想人格的追求也演變成了對特定景物的贊美[3]。筆洗作為文房用具,自然而然地承載了文人的思想以及追求,梅蘭竹菊四君子是常見的題材和比德對象,它們都有堅韌不拔、卓爾不群、超脫世俗的品質。筆洗以梅蘭竹菊為器型,不僅高潔雅致,而且美觀實用。筆洗中還常見一種松竹梅“歲寒三友”的造型,梅花凌霜傲雪,竹子經冬不凋,松樹四季常青,通常作為整體出現,象征高尚的情操。
(三)禪宗思想
禪宗思想在筆洗造型設計中也體現得淋漓盡致。佛教從漢代傳入中國后就十分流行,唐宋時期,儒、釋、道三教融合,誕生了本土化的宗教門派——禪宗。“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中國文人一生都在出世入世中痛苦和煎熬,需要尋求一種精神寄托來消解心中苦悶[4]。禪宗吸收了道家“物我兩忘,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張在與天地自然的接觸中頓悟,這種超脫世俗的思想與文人尋求內心安定的精神需求一拍即合,成了文人士大夫的精神花園。王維在《終南別業》中寫道:“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詩句中蘊含了對人生境界的看法。這種獨特的禪宗思想也體現在文人所用日常器具中,筆洗中多見蓮花、佛手造型,蓮花在佛教中有著特殊寓意,是佛門圣物,《四十二章經》第二十八章中有記載:“我為沙門,處于濁世,當如蓮華,不為泥污。”這是在告誡世人不要與環境同流合污,要保持心性高潔。小小蓮花濃縮了人們對佛理的感悟,本質上也是一種對心靈的釋放。
(四)師古之風
師古之風從宋代興起,青銅禮器是夏商周文明的代表,有維護社會穩定的作用。宋代為了維護社會穩定開始大規模制作禮器[5],除此之外,從宋代開始,金石學大為發展,文人雅士開始收藏古物,著書立說。宋徽宗時期仿古之風盛行,一時間出現了仿鬲、鼎、尊、壺等器型的瓷器。到了明清時期,這股風氣更甚,明清皇帝嗜好古器,帶動了整個朝代對仿古器物的追求。明清筆洗造型除了單純仿古之外,也擅長改造舊器型。如將五大名窯的裝飾手法運用在新器型上,將哥窯的金絲鐵線、紫口鐵足、釉片開裂的特征運用在樹葉形筆洗上,或將青銅器特征加以提煉,形成一種筆洗新造型。故宮博物院的藏品清代青玉獸面雙魚紋獸耳銜活環洗就仿造了青銅器中簋圓腹獸耳的造型,去掉了圈足和底座,保留了青銅器中的常見紋飾——獸面紋,整體造型既帶有三代的古拙之氣,又簡化了青銅器粗獷厚重之感。
四、材美工巧:筆洗的設計理念
早在先秦時期的《考工記》中就有記載:“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要順應天時,適應地氣,精心選材,巧用工藝,才可以制作出好的物品。明清時期筆洗的選材多種多樣,有陶瓷、玉、金屬、玻璃、竹、象牙等,其中以瓷和玉最多,瓷器由高嶺土制成,耐高溫、硬度大、耐用性好、吸水性差,適用于盛水浣筆,表面也不容易磨花損傷,材料隨處可得,經濟實用,有良好的普世性。玉料的應用也比較廣泛,是一種比較珍貴的原材料,具有質地堅硬、細膩光潔、韌性好、不吸水的特點。玉器早在史前時期就已經有所應用了,君子以玉比德,表明玉筆洗不僅具有美觀實用的特點,還承載了文人士大夫對美好人格的追求。
五、經世致用:筆洗的設計功能
手工藝最初的目的是方便器物使用。宋代米芾在《硯史》的“用品”條中云:“器以用為功,玉不為鼎,陶不為柱。”他認為,器物要能夠使用,這體現了經世致用的思想[6]。筆洗的主要功能是盛水與浣筆,在設計過程中就要考慮盛水的穩定性和浣洗的便利性,因此,筆洗的形狀大多是敞口狀,口徑較大,方便浣洗攪動,有一定的容積,方便盛水。為了防止浣筆時傾倒,筆洗多采用低重心設計,也有采用三足式設計以提高底盤穩定性。除此之外,部分器型還帶有把手,方便清洗和拿取。筆洗之中還有一種特殊造型的三連洗,三個圓形小洗組成三角形,提高了筆洗的利用率,簡單實用。葉形洗也很常見,器型口沿大多是翻卷的葉邊造型,不僅能很好地防止水流溢出,且增強了器物的美觀與實用性,如故宮博物院的藏品明代石灣窯灰黑釉葉式洗,整個器型呈卷邊葉片狀,葉心內凹便于盛水,葉邊上卷,防止側漏,葉柄微微翹起,呈手柄狀,便于取握,葉底帶有小足,以穩定器身,這些細節無一不體現功能與造型相適用的設計理念。
六、結語
筆洗的造型設計體現了中華民族最樸素的造物觀,被歷朝歷代加以利用和改進,兼具美觀性與實用性,蘊含文人的精神追求。筆洗背后內涵豐富的文化寓意、天人合一的設計思想、因材施質的設計理念、經世致用的功能價值都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鑒。現代設計也需要從傳統造物思想中汲取養分,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理念,找尋設計背后隱藏的人文精神與情感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