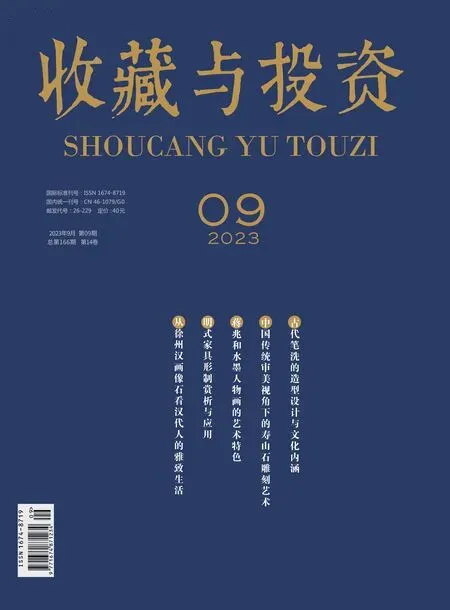“以玉問道”
——玉器與道教的融合與發展
肖睿涵(西安美術學院,陜西 西安 710000)
玉器,是幾乎獨立于中國傳統工藝美術品之外的特殊藝術品。相較于漆器、瓷器、木雕類,玉一方面是大自然的產物,另一方面又擁有厚重的人文底蘊、輝煌的藝術成就、可觀的經濟價值。究其根本,玉所承載的文化底蘊與人文沉積,與人類社會政治經濟、宗教道德等方面息息相關。魯迅先生曾說:“中國文化的根底全在道教。”說明在玉文化與玉器的發展歷程中,道教文化發揮了巨大作用。同樣的,玉對于道教也有至關重要的特殊作用。
一、“玉神物論”與玉道相融的起源
(一)玉靈物論至玉神物論
玉石承載了神靈的信仰觀,即“萬物有靈論”。玉石在宗教思想發展的最原始階段,在我國乃至世界范圍內都有悠久的歷史,可追溯至石器時代。歐洲舊石器時代末,澳大利亞土著阿龍塔人將圖騰崇拜寄托于一種彩繪石片“丘靈加”之上。阿龍塔人認為丘靈加是祖先與氏族人民的靈魂寄存處。歐洲中石器時代早期南部的阿齊爾洞穴內發現了繪以紅色紋樣的礫石,玉可與其并稱為世界范圍的起源[1]。賈蘭坡先生認為,我國舊石器時代晚期山頂洞遺址發現的一件扁圓形、似染三道紅色的小礫石,與阿齊爾洞穴發現的涂紅色礫石十分相似[2]。除此之外,我國許多遺址出土的未知用途的帶孔小石器、梭形小石器,均有此類“靈魂石”的特點。此類靈魂石即最初的“靈物玉”。玉靈物論一般被認為是玉神物論的始祖。
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在我國早期部落氏族崇拜中,“君權神授”賦予部族首領威信,與“神授之人”一起出現的玉,理所應當便是神物玉。《越絕書》·卷十一中風胡子云:“至黃帝之時,以玉為兵,以伐樹木為宮室、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龍臧。”這段話提出了玉為神異之物的觀點,普遍被認為是玉神物論的起源。玉神物論的提出,使得玉在根本上超越了其他自然物質的價值,擁有了物質與精神的雙重屬性。
“禮神以玉”的出現使得古人基本上明確了“神”的概念。人們對于神、靈的想象大多都反映在玉上。如紅山文化中的“天下第一龍”玉龍、石家河文化的“天神鳳鳥”、鳳形配以及同一時期的龍、鳳、龜、鳥蟬類動物玉雕。此時的玉基本成為各類動物的靈魂載體,被古人用作人與神靈溝通的禮器。

圖1 玉龍 紅山文化出土

圖2 鳳形玉佩 石家河文化出土

圖3 白玉嵌彩石鵪鶉如意 故宮博物院藏
(二)禮玉制度的衰落與玉道相融的起源
商周以后,禮樂制度與古代部落氏族用玉的傳統相結合,在經歷儒家宗法倫理道德的影響后,成為獨特的儒家禮玉制度。玉在日常生活、禮儀制度中的使用頻率逐漸增加。禮玉制度體現的是以宗法封建為基礎的禮法、禮儀、禮俗,佩玉制度體現的是維護等級制度的道德規范和儀節[3]。這類禮制興盛的太平盛世是擁有一定教化意義與文化意義的,然而在亂世,禮玉、佩玉制度就成了一紙空談。早在西漢末年王莽篡位時,禮玉制度就受到了一定的沖擊。到了三國時期,儒家因“不周世用”而式微,禮玉制度便逐漸走向衰落,道教逐漸轉變為玉文化的主要傳承載體。
東漢末年,道教形成并開始興起,除去大眾普遍認知的由張道陵創建的“五斗米教”(即后世道教的天師道與正一派),還有東方由張角創建的太平道。二者的道義延續了古代五行、陰陽等說法,追求得道成仙與長生不老,在自然上具有永恒屬性,在文化上具有神物屬性的玉成為道教方士們煉制丹砂的主要成分。
二、道教尚玉的原因
第一,道教認為玉是連接人與神靈的紐帶。起源于部落時期的玉神物信仰導致古人認為玉是山石之精髓,汲取天地之靈氣和日月之精華的神物。道教普遍認為玉器可以被用來制作與天地神靈溝通的法器,早期很多玉器種類都與通神類祭祀文化有關。如內圓外方形制的玉琮有溝通神靈與鬼魂的作用;玉璧、玉璋、玉圭類玉器則在祭祀中具有法力效用。人們以玉為媒介,通神、祭神,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圖4 青玉浮雕福壽三多如意 故宮博物院藏
第二,玉自最初就帶有天然的“神物”文化屬性,其與神仙思想緊密聯系。除去大眾熟知的“玉皇”“瓊樓玉宇”等名稱,人們也將仙界描繪為由美玉裝點的世界,《水經注·河水》中云:“昆侖之墟……面有九井,以玉為檻……沙棠、瑯軒(美玉的一種)在其東。”西王母所在的昆侖一般被認為是“百神之所在”,上有供神仙食用的玉制樹木,井檻也是用玉制作的。《神異經·東荒經》記載:“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仙人住石室,食用的也是玉石,東王公所居住的東荒也由玉石籠罩。這與道家向神仙靠攏,認為人可以通過修煉羽化成仙的思想是相近的。
第三,東晉葛洪《抱樸子》中記載:“金玉在九竅則死者為之不朽。”古人有玉殮葬習俗,認為玉衣、含玉、握玉等擁有一定法力。《抱樸子》又引用《玉經》中“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的說法,倡導服食金玉可以成仙。這與道教追求長生的思想是一致的。
三、玉器在道教發展與宗教融合中的作用
魏晉南北朝至唐時,佛教的大規模傳播使其在玉文化領域同儒、道兩教展開激烈碰撞,雖然三者擁有不甚相同的用法與思想,卻在玉器的使用上呈現了融合趨勢。它推動了中國玉文化向生活化發展的進程,也在玉器紋飾、制作、選材方面為中國玉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一)佛道相融的玉如意
譬如代表佛道交融的玉如意。如意在史料記載中起初是被作為兵器使用的,但在發展過程中,其主要功能逐漸轉變為辟邪。如意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就已經有生產制作并被使用。《采蘭雜志》中記:“如意者,昔有貧士多玄善,陰德旁及鳥獸,而菽水不贍,忽遇一道士遺以一物,謂之‘如意’……”巧合的是,梵語中的“阿那律”也是如意的意思。唐代佛教造像開始出現手持如意的形象,如意也開始作為佛教圣物出現。如意作為道教辟邪壓勝的法器,又作為佛教圣物出現,體現了佛道兩教在吉祥觀念上的融合。
(二)儒道交融的觀景石
再如儒道交融的體現:觀景石。起先,人們欣賞觀景石是為理解道家思想中“不加雕琢,天然成趣”的概念。然而從唐代開始,儒家寄情于石的思想開始與這一觀念結合,從此便開始賦予觀賞石人文情感氣息,將觀賞石的自然美與儒家的寄情于物巧妙結合[4]。自此也演變出“盛世為儒,亂世道佛”的審美思想。在亂世道佛之間,文人墨客群體的玉審美也衍生出“避世求道,亂世造佛”的審美趨向[5]。
四、道教對玉器發展的利與弊
英國皇家學者李約瑟認為:“道教有一套復雜而微妙的概念,這是后來產生的中國一切科學技術思想的基礎。”同樣的,道教在中國玉器工藝與玉文化發展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道教對玉器發展的利處
1.玉器功能的豐富與轉變
魏晉南北朝時期以前,儒家“德化玉”的思想一直占據玉文化的主流地位,君子“以玉比德”,玉器被賦予講究人格修養的道德教化作用,然而魏晉時期禮崩樂壞,“盛世為儒,亂世道佛”,伴隨著儒家禮玉制度的衰落,玉器不再脫離百姓層面,逐漸深入俗世生活,道教也開始轉化為玉文化傳承的載體。道教“貴生”“貴術”[6]的用玉思想成為主流,此時玉文化功能轉化為玉能養生、玉能護身此類想法。
2.重現玉器的神圣性
在道教的神仙信仰體系中,玉器永遠高居神圣的祭壇上。人們常以玉器為法器,用以除惡辟邪、祈求平安順遂。或用玉陪葬,以求人死后羽化成仙。道教在魏晉以后玉文化中的主流地位,使得玉器脫離了長久以來儒家給其所扣的道德倫理功能枷鎖,重回先秦乃至原始玉文化中玉的神圣性。
3.豐富造型紋飾的題材
在道教思想文化與道教歷史典故的影響下,玉雕的題材與圖案選擇范圍不斷被擴展,大量具有道教教義的題材被產出,譬如祝福類的“吉祥如意”“福祿壽喜”“福如東海”,典故類的“八仙過海”“老聃騎牛”等仍是現代玉雕的重要題材。
(二)道教對玉器發展的弊處
1.食玉觀念
仙人食玉或凡人食玉成仙的事例在道教發展之中廣為人所接受,古籍中也多有記載。《山海經》云:“嶺山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饗。”《搜神記》云:“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冰玉散,以教神農。”葛洪在《抱樸子內篇·仙藥》亦云:“玉亦仙藥,但難得耳。”至魏晉時,食玉竟已經成為社會風尚。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玉雕史上的低潮期,此時的傳世玉器極為罕見[7]。究其原委,便是當時人們不愛雕玉琢玉,而是熱衷吃玉,并且達到了瘋狂的程度。早期關于玉器的美學價值、禮儀觀念,在這時消失殆盡[8]。
2.葬玉觀念
葬玉是指在人死后陪葬大量玉器,試圖讓死者羽化升仙。古人認為玉衣、玉塞、含玉、握玉等具有一定的法術作用。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一些弊端,譬如后代藝人無法觀摩學習玉器工藝,使得部分技藝失傳。一些珍貴的軟玉在地下長期儲存后發生化學反應,遭到嚴重的破壞[9]。但葬玉制度仍然有其好的一面,葬玉的傳統使得后世通過大量由墓葬出土的玉雕了解歷代玉文化的特征與玉雕技藝的發展。
五、結語
道教與玉器兩者之間互相聯系,互相融合,也互相滲透。一方面,道教為玉器編造出傳說與功用,使得民眾相信玉器的神奇力量,促使玉器蓬勃發展。同時,道教故事與道教文化也是玉器設計的重要源泉之一。另一方面,道教本身也將玉器引入自己的宗教領域,玉器反作用于道教。人們對于玉器的熱愛也使得群眾加深了對道教傳說及其文化的了解,促進了道教的發展與壯大[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