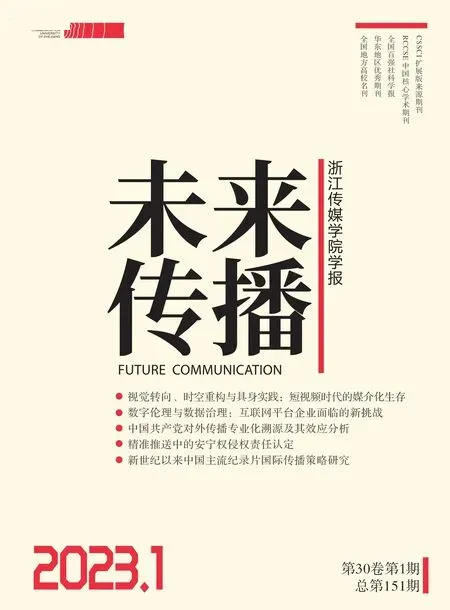視覺轉(zhuǎn)向、時(shí)空重構(gòu)與具身實(shí)踐:短視頻時(shí)代的媒介化生存
李文冰,趙舒悠
(1.浙江傳媒學(xué)院浙江省傳播與文化產(chǎn)業(yè)研究中心,浙江杭州310018;2.暨南大學(xué)新聞與傳播學(xué)院,廣東廣州510632)
一、引 言
人類實(shí)現(xiàn)媒介化生存了嗎?早在尼葛洛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提出“數(shù)字化生存”的預(yù)言之際,人們似乎就已經(jīng)相信媒介技術(shù)天然具有賦權(quán)的潛力,而這一特質(zhì)將會(huì)引發(fā)積極的社會(huì)變遷。在大眾媒體時(shí)代,狹義的媒介化生存是指以傳統(tǒng)媒體(報(bào)紙、廣播、電視等)為中心的生活方式,媒介成為生產(chǎn)生活中工具性的存在。當(dāng)今新媒體技術(shù)的一個(gè)重要特征是,媒介不再僅僅是受制于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的專業(yè)信息系統(tǒng),而是通過對(duì)社會(huì)生活全方位、全時(shí)空的滲透,成為人類基礎(chǔ)性的生存框架。[1]隨著移動(dòng)終端的普及和網(wǎng)絡(luò)的提速,短視頻自“出道”以來便以視覺信息的全景、立體、陪伴和體驗(yàn)顛覆了傳統(tǒng)媒介觀中的現(xiàn)實(shí)再現(xiàn),經(jīng)由算法武裝的短視頻平臺(tái)也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媒介依賴,轉(zhuǎn)而作為一種技術(shù)配置體系,深刻地影響、訴說甚至決定著人這一主體在虛擬與現(xiàn)實(shí)世界中的媒介實(shí)踐和生存體驗(yàn)。[2]短視頻的傳播實(shí)踐與大眾傳媒相比,顯著的區(qū)別就在于,在時(shí)間維度上,人的媒介接觸已不再是大眾媒體時(shí)代的讀報(bào)紙、聽廣播、看電視等相對(duì)集中清晰的片段,短視頻應(yīng)用以其碎片化、強(qiáng)社交、移動(dòng)性的特征持續(xù)地嵌入日常生活;在空間維度上,人的身體被標(biāo)記的符號(hào)意義能夠逃離生物軀體所固在的某一特定場(chǎng)景或地點(diǎn),媒介化生存伴隨著人在多重時(shí)空中的移動(dòng)同步展開。[3]
如果僅僅將短視頻平臺(tái)定義為社交媒體有利于引流和變現(xiàn)的新樣態(tài),將短視頻看成是時(shí)間長(zhǎng)度相對(duì)較短的影像形式,便遠(yuǎn)遠(yuǎn)低估了短視頻應(yīng)用打開關(guān)于人類生存方式的媒介“想象力”。那么,應(yīng)該如何理解人們以短視頻為形式、以平臺(tái)為載體的媒介化生存呢?首先,本文從技術(shù)哲學(xué)的角度出發(fā),闡釋在當(dāng)代文化的“視覺轉(zhuǎn)向”和網(wǎng)絡(luò)社會(huì)的“時(shí)空重構(gòu)”的背景下,人們的媒介化生存依托于短視頻平臺(tái)的合理性證據(jù)和合法性內(nèi)涵;其次,通過對(duì)平臺(tái)生態(tài)的追蹤和觀察,以視覺奇觀、互動(dòng)儀式和時(shí)空(再)生產(chǎn)三大現(xiàn)象為例,分析人們媒介化生存具體的動(dòng)機(jī)、手段和過程;最后,以技術(shù)具身為切入點(diǎn),探討短視頻平臺(tái)對(duì)媒介化生存底層邏輯的改寫,以及傳播主體的根本性轉(zhuǎn)變。
二、短視頻平臺(tái)的技術(shù)哲學(xué)
(一)當(dāng)代文化的“視覺轉(zhuǎn)向”
人類社會(huì)的主流文化經(jīng)歷了三個(gè)階段的演變:第一階段是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報(bào)以懷舊之慨嘆的“說故事”類口傳文化;第二階段是以文學(xué)和新聞為代表的印刷文化;第三階段是巴拉茲(Béla Balázs)以機(jī)械復(fù)制的電影藝術(shù)的誕生為標(biāo)志提出的視覺文化。[4]當(dāng)代社會(huì)呈現(xiàn)高度圖像化或視覺化趨勢(shì),從印刷、影視作品到服飾、美容、商品包裝,從城市建筑、廣場(chǎng)、街道等公共場(chǎng)所到室內(nèi)裝飾、家居環(huán)境等私人空間,視覺形象顯而易見且無處不在,幾乎已經(jīng)成為強(qiáng)迫性的生存體驗(yàn)。對(duì)此,弗萊博格(Anne Friedberg)稱,新的視覺文化重塑著人們的記憶和經(jīng)驗(yàn),“不管是‘視覺的狂熱’還是‘景象的堆積’,日常生活已經(jīng)被‘社會(huì)的影像增殖’改變了”。[5]一個(gè)如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所預(yù)言的“世界圖像時(shí)代”正在發(fā)生,其典型癥候是 “世界被把握為圖像”,并逐步趨向于德波(Guy Debord)所描繪的“景觀社會(huì)”。[6][7]圖像化并非現(xiàn)代專屬的狀況,每個(gè)時(shí)代都存在視覺藝術(shù)的繁榮時(shí)期。[8]但是,隨著短視頻成為當(dāng)下最為流行的視覺傳播手段,文化的“視覺轉(zhuǎn)向”在技術(shù)和內(nèi)涵兩個(gè)層面經(jīng)歷了新一輪更迭:首先,短視頻平臺(tái)通過多種媒介技術(shù)的融合,革新了視覺生產(chǎn)的實(shí)踐方式,從而深刻地影響和重構(gòu)著人的思維指向和邏輯形式;其次,圖像化的感知和存在形式不僅改變了意義交流本身,更在根本意義上確立了人對(duì)世界的主體性地位,并形塑著人的生存經(jīng)驗(yàn)。
根據(jù)埃呂爾(Jacques Ellul)的“技術(shù)自主論”,技術(shù)可以以隱匿的方式?jīng)Q定其中的文化形式。[9]從技術(shù)的發(fā)展和應(yīng)用來看,短視頻作為視覺藝術(shù)的新形態(tài),成功促成包括錄音、攝影等多媒體音像技術(shù)的融合和簡(jiǎn)化,豐富了媒介文本的生產(chǎn)、呈現(xiàn)和作用方式。當(dāng)下的短視頻平臺(tái)已經(jīng)搭建形成完整的技術(shù)框架,其主要貢獻(xiàn)在于,將以專業(yè)性著稱的影像生產(chǎn),通過特色濾鏡、創(chuàng)意混剪、肢體識(shí)別、舞蹈跟拍、3D渲染等功能,化解為方法上簡(jiǎn)單但效果上專業(yè)的用戶操作,顯著降低了個(gè)人的技術(shù)門檻和技術(shù)成本。[10]就意義的生產(chǎn)和接受而言,語言是抽象和線性的,文字產(chǎn)生意義的基礎(chǔ)本質(zhì)上是一個(gè)概念化的過程,所指是形成于人的心理再現(xiàn)中與能指相對(duì)應(yīng)的概念。而影像生產(chǎn)基于其機(jī)械復(fù)制的特性,具備復(fù)現(xiàn)物質(zhì)現(xiàn)實(shí)的功能,且復(fù)現(xiàn)的方式和結(jié)果具有唯一指代性。以現(xiàn)實(shí)影像作為素材,無論是直接捕捉現(xiàn)實(shí)生活,還是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再加工,都體現(xiàn)出更強(qiáng)的物質(zhì)性。[11]因此,視覺圖像作為一種特殊的話語形態(tài),撼動(dòng)了語言所建構(gòu)的抽象邏輯認(rèn)知,短視頻成為新的勸服性生產(chǎn)實(shí)踐,而人的觀看行為則是一個(gè)在影像中聯(lián)系和錨定現(xiàn)實(shí)對(duì)象的過程。視覺符號(hào)(短視頻)對(duì)于語言符號(hào)(以文字為基礎(chǔ)的博客、推文等)的優(yōu)勢(shì),并不意味著文字將從日常實(shí)踐中消失,而是影像成為文化的“主因”,其深層涵義在于人們?cè)絹碓揭兄赜谝曈X形象來理解世界和自己。
所謂“觀看先于語言”,媒體正日益從對(duì)世界、社會(huì)、事實(shí)的“言說”轉(zhuǎn)為更加直接的“再現(xiàn)”甚至“體驗(yàn)”,短視頻成為一種新的“符號(hào)術(shù)”,對(duì)人的存在以及人與世界的相對(duì)關(guān)系作出新的哲學(xué)解釋。[12]按照伯格(John Berger)的“觀看之道”,一切認(rèn)識(shí)從觀看出發(fā),一切知識(shí)和經(jīng)驗(yàn)在觀看中模仿習(xí)得,有選擇的觀看行為確立了人在周圍世界中的地位。[13]海德格爾則認(rèn)為,現(xiàn)代的本質(zhì)在于“世界成為圖像”和“人成為主體”這兩大進(jìn)程的相互交叉。[6](89)在世界圖像中,存在者整體(指除人以外的其他存在)以下述方式被看待,即“唯就存在者被具有表象和制造作用的人擺置而言,存在者才是存在著的”。[14]這意味著,人只有將世界表象化,世界對(duì)人而言才是可感可知的,而通過將世界轉(zhuǎn)化為能夠被人把握的表象,人就為真實(shí)性尋找到了確定性的根基。[8]于是,現(xiàn)代化被描述為對(duì)作為圖像的世界的征服過程,人自行確立了自身的主體地位,力求成為一切尺度和準(zhǔn)繩,并以此來擺置其他存在者。與此同時(shí),圖像成為現(xiàn)代基本的形而上學(xué),人們不再觀看圖像,而是通過圖像來體驗(yàn),圖像系統(tǒng)從根本上塑造并規(guī)制著人們的生存、感知,以及全部的社會(huì)經(jīng)驗(yàn),自我、他人甚至整個(gè)社會(huì)被整合為一個(gè)自動(dòng)的圖像“裝置”。[15]簡(jiǎn)言之,在這個(gè)圖像的時(shí)代,短視頻成為人們把控周遭(umwelt)的新媒介技術(shù),又反過來使人本身以某種“圖像”或“景觀”被表征,從而形成對(duì)人的規(guī)訓(xùn)力量和存在的確證。
(二)網(wǎng)絡(luò)社會(huì)的“時(shí)空重構(gòu)”
時(shí)間和空間是人類感受萬事萬物的先驗(yàn)的“感性形式”,也是構(gòu)成人類理性主義思維的兩大基本維度。在時(shí)間和空間的博弈中,時(shí)間長(zhǎng)期處于支配地位,被視為豐裕的、辯證性的和具有生命活力的概念,而空間則在時(shí)間強(qiáng)大的話語邏輯下遭到隱匿和貶斥,被認(rèn)定為固定的、靜止的、非辯證的,無論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還是康德,都僅將空間看成純粹的物質(zhì)載體或容器。[16]20世紀(jì)70年代興起的“空間轉(zhuǎn)向”思潮倡導(dǎo)了一種重視空間的本體論,福柯(Michel Foucault)著眼于權(quán)力的空間化,認(rèn)為空間既是權(quán)力相爭(zhēng)的場(chǎng)域,也是權(quán)力運(yùn)作的工具;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提出“空間生產(chǎn)”的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理論和“空間三元”辯證法,指出社會(huì)秩序的空間化不僅指的是事物處于某一地點(diǎn)或場(chǎng)景之中的經(jīng)驗(yàn)性設(shè)置,也是通過人類主體有意識(shí)的活動(dòng)而產(chǎn)生的一種習(xí)慣實(shí)踐;而索亞(Edward Soja)則從社會(huì)實(shí)踐的角度探索“他者化”的“第三空間”,強(qiáng)調(diào)物質(zhì)空間和精神空間相互勾連、亦此亦彼的混雜特質(zhì)和無限開放性。[17][18][19]
在網(wǎng)絡(luò)社會(huì)中,人們的生產(chǎn)生活實(shí)踐既基于又進(jìn)一步改寫了基礎(chǔ)性的時(shí)空要素。首先,新媒介技術(shù)顛覆了傳統(tǒng)意義上的時(shí)間性和空間性,創(chuàng)造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時(shí)空組織形式。在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關(guān)于聲音技術(shù)的討論中,聲音這種被黑格爾稱為“在形成過程中消失的存在”,由于留聲機(jī)的出現(xiàn),首次跨越時(shí)間的界限,逝去的人和事得以“以真實(shí)聲音的方式存在”。[20]留聲機(jī)還可以化無形為有形,將人無法直接看到的自然界中的部分物質(zhì),以實(shí)際可見的形式呈現(xiàn)出來,而不再借助象征符號(hào)。以電影為代表的影像技術(shù)與此類似,電影制作在原則上不過是剪輯與拼接,即“在鏡頭前對(duì)連續(xù)運(yùn)動(dòng)或線性時(shí)間的切割”,而膠片為操縱這一“虛幻國(guó)度”的可能性提供了物質(zhì)基礎(chǔ)。[20](136)于是,視聽媒介實(shí)現(xiàn)了時(shí)間的逆轉(zhuǎn),而逆轉(zhuǎn)的必然結(jié)果是,“各類媒體在時(shí)間上相互交錯(cuò),已不再遵循線性的歷史次序了”。[20](133)對(duì)于新型時(shí)間軸的誕生,孫瑋解釋為,“當(dāng)單一線性時(shí)間被切割,就形成了與真實(shí)時(shí)間并置的多個(gè)時(shí)間鏈條,它們以各種方式交織在一起,構(gòu)成了人類生存的多重時(shí)間性”。[1]
針對(duì)時(shí)間與空間的相互關(guān)聯(lián)性,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提出的假設(shè)是,“在網(wǎng)絡(luò)社會(huì)里,是空間組織了時(shí)間”。[21]移動(dòng)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對(duì)于媒介時(shí)空的革命性突破,其一為“無時(shí)間的時(shí)間”,即最大可能地取消事情發(fā)展的先后順序,其二為“流動(dòng)的空間”,即時(shí)效的提高克服了遠(yuǎn)距離空間互動(dòng)的域限和障礙。[21]相較而言,傳統(tǒng)媒介鑄造的想象空間缺乏多重感官的并置和即時(shí)性的互動(dòng),因此只能算作一種隱喻意義上的空間,而短視頻平臺(tái)不但創(chuàng)造了遠(yuǎn)程虛擬的在場(chǎng)方式,而且實(shí)現(xiàn)了虛擬空間和現(xiàn)實(shí)空間無時(shí)無刻不在進(jìn)行的轉(zhuǎn)換與交融。[1]以視聽體驗(yàn)來說,短視頻的媒介技術(shù)和平臺(tái)的信息網(wǎng)絡(luò)解放了視覺敘述對(duì)物理媒介的依賴,信息在任何時(shí)間、任何場(chǎng)所都可以以視覺圖像的感知形式存在。[22]就社交方式而言,線上交流得以從時(shí)空的束縛中解脫,然而交流者同樣需要置身于一種被感知的空間狀態(tài)之中,這種感知狀態(tài)離不開視覺圖像的建構(gòu)。[22]從具身實(shí)踐的角度出發(fā),短視頻的空間(再)生產(chǎn)既涉及網(wǎng)紅地點(diǎn)在虛擬空間里被合目的地“重新發(fā)現(xiàn)”,又要求人們的身體和感官在真實(shí)時(shí)空中相會(huì)。
三、媒介化生存的平臺(tái)觀察
(一)視覺奇觀:個(gè)人生活的可見性賦能
對(duì)于視覺行為所涉及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福柯使用了一個(gè)形象的比喻:視覺乃“權(quán)力的眼睛”。[17]從邊沁的“圓形監(jiān)獄”、福柯的“全景監(jiān)獄”再到波斯特的“超級(jí)全景監(jiān)獄”,觀看機(jī)制已經(jīng)從監(jiān)督者對(duì)身處封閉暗室的囚禁者的偷偷觀察,變成了權(quán)力運(yùn)作在全景式的透明建筑中受到全社會(huì)全天候的監(jiān)視。穆爾維(Laura Mulvey)則從視覺快感的角度分析看與被看的角色相對(duì)位置,認(rèn)為攝像機(jī)后的掌控者和熒幕前的觀看者是主動(dòng)的、欲望性的權(quán)力主體,而畫面中的被觀看者則是被動(dòng)的、被“凝視”的弱勢(shì)客體。[23]然而,短視頻平臺(tái)的視覺展演形式使看與被看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發(fā)生了消解。繪畫、雕塑、電影等傳統(tǒng)視覺藝術(shù)的符號(hào)建構(gòu)者通常對(duì)自己的作品擁有絕對(duì)的話語權(quán),而短視頻作品一經(jīng)發(fā)布便不再有明顯的主客體之分,人人觀看他人的節(jié)目,也都成為被他人觀看的“節(jié)目”。[22]正如周憲所言,“圖像就是力量”,視覺經(jīng)驗(yàn)發(fā)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被把握為圖像”的東西才充斥著文化影響力,看見意味著優(yōu)勢(shì)和權(quán)力,看不見的東西不可避免地遭到排斥。[4](8)可見性(visibility)成為當(dāng)代社會(huì)最重要的文化資源之一,可見不再是手段(means),而變成了目的本身(end)。[24]抖音的廣告語是“記錄美好生活”,快手的廣告語是“看見每一種生活”,這兩大頭部短視頻平臺(tái)雖然商業(yè)定位不同、視頻風(fēng)格和平臺(tái)文化差異明顯、吸引的人群也少有重疊(前者更具都市時(shí)尚色彩,后者更鄉(xiāng)土化、“接地氣”),但它們的共通之處是,讓廣闊世界中人微言輕的個(gè)體通過視覺內(nèi)容的奇觀化(spectacle)和視頻形式的蒙太奇(montage)為生活的可見性賦能。
從電影理論的角度來說,奇觀電影的首要任務(wù)是通過畫面的組接來傳遞具有視覺吸引力和快感的影像,蒙太奇則是把不同的視覺素材組合成為有意義的整體的方法。鑒于短視頻平臺(tái)對(duì)用戶群體較強(qiáng)的開放性和包容性,除了受制于15秒至60秒的主流視頻時(shí)長(zhǎng),用戶享有對(duì)音樂、場(chǎng)景、內(nèi)容等的自由選擇權(quán)和裁量權(quán)。基于“短平快”的宗旨,短視頻的視覺內(nèi)容不再嚴(yán)格以理性原則組織線性的敘事結(jié)構(gòu),而是追求奇觀效果和快感最大化,也不再堅(jiān)持以話語為中心打造故事情節(jié)和主題深度,而是轉(zhuǎn)向強(qiáng)化畫面的造型性和視聽的沖擊力。傳統(tǒng)視覺敘事文本的嚴(yán)肅性和神圣性被消除,取而代之的是為直接引發(fā)快樂情緒而采用的簡(jiǎn)單夸張的肢體表演搭配“洗腦”神曲、“魔性”音效的組合。
在創(chuàng)作實(shí)踐中,人們的媒介化生存主要體現(xiàn)為不斷尋找、發(fā)現(xiàn)和創(chuàng)造視覺素材的過程。取材于真實(shí)生活,素材的易得性成為人們拿起手機(jī)拍攝的基本動(dòng)力,而素材的獨(dú)特性又能夠大大增強(qiáng)視頻的可見性,這就驅(qū)使人們隨時(shí)審視周圍環(huán)境、規(guī)劃自身行為。[11]短視頻中的每個(gè)畫面都是對(duì)現(xiàn)實(shí)場(chǎng)景的記錄,通過鏡頭、場(chǎng)面、段落的分切與組接,實(shí)現(xiàn)對(duì)日常生活的創(chuàng)造性再現(xiàn),最終形成獨(dú)特的個(gè)人敘事。因此,“美好生活”就是獨(dú)居女孩悉心籌備每日餐食、寶媽奶爸帶娃的趣味崩潰日常,平凡的生活中也有值得記錄和分享的不平凡之處;“每一種生活” 既有賣工地盒飯的阿姨在奮力翻炒、卡車司機(jī)在日夜奔赴,也有紐約白領(lǐng)參加街頭快閃,人們互相邀請(qǐng),既看見他人,也收獲他人的關(guān)注與承認(rèn)。[25]
(二)互動(dòng)儀式:社交情境的新玩法
作為人類社會(huì)中特有的文化現(xiàn)象,儀式是“被一個(gè)群體內(nèi)的人們普遍接受的按照某種既定程序進(jìn)行的身體的活動(dòng)與行動(dòng)”,經(jīng)常固定地、重復(fù)地在某個(gè)時(shí)間或某一特定情況下舉行,并且承載著某種象征意義。[26]涂爾干(émile Durkheim)認(rèn)識(shí)到宗教儀式是一種在社會(huì)水平上促進(jìn)團(tuán)結(jié)的強(qiáng)大力量,而戈夫曼(Erving Goffman)則將這一思想延伸至日常生活層面,認(rèn)為面對(duì)面的互動(dòng)形成大量情境,人們?cè)诓煌榫持懈鶕?jù)自己不同的角色和目標(biāo)與他人進(jìn)行互動(dòng)。[27]在此基礎(chǔ)上,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從微觀情境著手探究?jī)x式中的互動(dòng)作用機(jī)制,提出“互動(dòng)儀式”這一核心概念,指出互動(dòng)儀式鏈的生成需要四個(gè)條件:人們共同在場(chǎng)、對(duì)局外人設(shè)定界限、有共同的關(guān)注焦點(diǎn)、分享情感體驗(yàn)。[27](61)短視頻平臺(tái)中的一切互動(dòng)都是在短視頻生產(chǎn)的情境里展開的,根據(jù)梅洛維茨(Joshua Meyrowitz)的“新媒介—新情境—新行為”的關(guān)系模型,短視頻的流行改變了人們的交往形式,導(dǎo)致傳統(tǒng)社交情境的重構(gòu)和新情境的誕生,而新情境又衍生出與之相適應(yīng)的互動(dòng)行為。[28]短視頻平臺(tái)生態(tài)催生了社交情境的新玩法,人們的媒介化生存在社交方面的互動(dòng)實(shí)踐表現(xiàn)為以“模仿創(chuàng)作”為標(biāo)志的共同行動(dòng)和以“視頻直播”為代表的共同在場(chǎng)以及其中被激活的情感聯(lián)結(jié)。
“模仿創(chuàng)作”的共同行動(dòng)可以概括為,基數(shù)龐大的普通用戶通過欣賞熱門作品獲得情感刺激并試圖加入流行話題,在技術(shù)引導(dǎo)和反饋強(qiáng)化的激勵(lì)下產(chǎn)生循環(huán)往復(fù)的創(chuàng)作熱情和創(chuàng)作行為。[29]在抖音歷屆潮流榜單中,有簡(jiǎn)單易學(xué)的舞蹈,如“海草舞”“C哩C哩舞”,有對(duì)明星語錄的復(fù)刻,如海清的“你是我的神”(表示夸獎(jiǎng))、斯琴高娃的“這是可以說的嗎”(表示欲言又止),還有圍繞某個(gè)主題進(jìn)行的劇本表演,從“今天你真好看”“我媽不讓我跟你玩”到對(duì)《甄嬛傳》《小時(shí)代》經(jīng)典橋段的“素人”翻拍。抖音為大眾模仿秀提供充分的技術(shù)支持,既結(jié)合用戶瀏覽偏好設(shè)計(jì)了對(duì)熱門話題和優(yōu)質(zhì)內(nèi)容的推送機(jī)制,又在最大程度上優(yōu)化二次創(chuàng)作的流程,用戶可以使用“拍同款”(套用動(dòng)作模版)或“一鍵生成”(系統(tǒng)智能選擇相冊(cè)內(nèi)容并自動(dòng)生成視頻)直接加入熱門內(nèi)容的生產(chǎn)和傳播中。[29]轉(zhuǎn)發(fā)、點(diǎn)贊、評(píng)論等互動(dòng)方式相當(dāng)于觀看舞臺(tái)表演時(shí)觀眾的歡呼聲和掌聲,通過贏得關(guān)注度和互動(dòng)熱度(即柯林斯所說的“反饋強(qiáng)化”),內(nèi)容創(chuàng)作者所產(chǎn)生的愉悅的情感能量代替實(shí)質(zhì)性的經(jīng)濟(jì)回報(bào),激勵(lì)下一輪的短視頻生產(chǎn)。[29]這樣的社交情境中所激活的群體符號(hào),如“奪筍”(多損)、“針不戳”(真不錯(cuò))等諧音梗,承擔(dān)了在參與者和局外人之間設(shè)定身份區(qū)隔的功能,甚至演變?yōu)閰⑴c者共享的特色文化資本,從而使屬于該圈層的用戶迅速產(chǎn)生群體認(rèn)同感和歸屬感。
由于無法實(shí)現(xiàn)身體在物理意義上的聚集,柯林斯對(duì)遠(yuǎn)程儀式的效果不無擔(dān)憂。然而,短視頻平臺(tái)為用戶創(chuàng)設(shè)了一個(gè)流動(dòng)的接入界面,人們不僅可以對(duì)眼前的時(shí)空?qǐng)鼍斑M(jìn)行數(shù)字編碼和傳播,還可以將其他空間的活動(dòng)圍繞自身形成與他人的共同在場(chǎng),實(shí)現(xiàn)“沒有地域鄰近性的社會(huì)共時(shí)性”,身體的虛擬共在和情感的遠(yuǎn)程聯(lián)結(jié)已經(jīng)成為當(dāng)今互動(dòng)交往的基本特征。[21]以視頻直播為例,彭蘭視其為由主播創(chuàng)造的個(gè)人媒介事件,其中所展現(xiàn)的不是生活的碎片,而是一個(gè)個(gè)完整、持續(xù)的真實(shí)生活情境。[11]盡管直播在很多情況下是無主題、無事件的,觀看者依然樂此不疲,這是因?yàn)橹辈サ膱?chǎng)景往往也是主播生活的空間,而手機(jī)攝像頭與主播的超近距離容易轉(zhuǎn)化為“進(jìn)入”和“在場(chǎng)”感,來自他人的注視使主播的私人生活公開化。[11]人們還可以隨時(shí)進(jìn)出不同的直播間,仿佛“在不同的聚會(huì)上同時(shí)現(xiàn)身”,這種隨機(jī)性和隨意性帶來陌生人之間的相遇和想象中的親密關(guān)系,卻不會(huì)造成心理上的負(fù)擔(dān)。[11]在直播間內(nèi),觀眾群體分享了共同的情感體驗(yàn),比如考公考研的學(xué)習(xí)直播和劉畊宏的健身直播起到督促的作用,被比喻為“電子榨菜”的下飯吃播和ASMR助眠直播具有陪伴的效果,人們正在將參與視頻直播融入個(gè)人的生活儀式。
(三)空間(再)生產(chǎn):具身化的媒介實(shí)踐
談及媒介與空間或地方之間的關(guān)系,亞當(dāng)斯(Paul Adams)的觀點(diǎn)是,“傳播既發(fā)生在地方之中,又創(chuàng)造著地方”;列斐伏爾則將空間作為一種生產(chǎn)話語進(jìn)行考察,認(rèn)為空間是有目的地被生產(chǎn)出來的,“空間不是生產(chǎn)背景,而是生產(chǎn)對(duì)象”。[30][18]在抖音熱門城市視頻的搜索發(fā)現(xiàn)中,西安的大雁塔、廈門的鼓浪嶼、重慶的洪崖洞等網(wǎng)紅景點(diǎn)都榜上有名,甚至司空見慣的民宿、咖啡店、清吧、廣場(chǎng)等城市空間和土炕、瓦房、田野等鄉(xiāng)村景致也紛紛成為短視頻創(chuàng)作的舞臺(tái)和展示的焦點(diǎn),這種現(xiàn)象就是短視頻的空間(再)生產(chǎn)。短視頻生產(chǎn)所依托的空間經(jīng)過創(chuàng)作者的挑選與設(shè)計(jì),“在哪里”拍視頻被賦予了意義,現(xiàn)實(shí)空間于是融入虛擬空間的象征結(jié)構(gòu)中。這種生產(chǎn)實(shí)踐并非對(duì)時(shí)空?qǐng)鼍暗摹盁o中生有”,而是采用“增強(qiáng)”或“修辭”的策略對(duì)現(xiàn)實(shí)空間進(jìn)行解構(gòu)、拼貼和再現(xiàn),從而使當(dāng)?shù)鼐吧邆涞纳鐣?huì)意義或商業(yè)價(jià)值在原有基礎(chǔ)上發(fā)生“復(fù)合”和“疊加”。[10]人們的媒介化生存發(fā)生在虛擬與真實(shí)的交錯(cuò)中,“種草”虛擬空間中呈現(xiàn)和流轉(zhuǎn)的影像成為具身體驗(yàn)的動(dòng)力,而后通過“打卡”實(shí)現(xiàn)身體在物質(zhì)場(chǎng)景中的相遇。
從古時(shí)的“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到圖像時(shí)代的“人在家中坐,走遍全世界”,人與世界的關(guān)系常常呈現(xiàn)出這樣一種狀態(tài):人的位置固定不變,關(guān)于世界的信息則擺脫其固有的地域性,通過影像的遠(yuǎn)距離傳輸使世界成為手機(jī)屏幕里跨越時(shí)空、往來穿梭的景觀。[31]這便是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描繪的“脫域”與“再嵌入”,即媒介以虛擬再現(xiàn)的方式,使位置從物理空間中脫出、挪移,實(shí)現(xiàn)與以肉身為存在形式的固定主體的接合。[32][31]然而,現(xiàn)代空間的異化正是源自虛擬移動(dòng)性對(duì)身體物質(zhì)性的剝奪,與物理空間的長(zhǎng)期隔離遮蔽削弱了人介入現(xiàn)實(shí)的行動(dòng)力,身體的重要性或從現(xiàn)實(shí)時(shí)空中退卻。[33]
短視頻建構(gòu)性的視覺力量驅(qū)使人們的生存方式由媒介表征向具身實(shí)踐轉(zhuǎn)型,倡導(dǎo)以“體驗(yàn)”作為人的時(shí)空穿梭方式。第一步是“種草”,指的是把一個(gè)事物推薦給他人,使他人也喜歡這個(gè)事物的過程,人們透過手機(jī)屏幕被空間影像所吸引,產(chǎn)生親臨現(xiàn)場(chǎng)以確認(rèn)其價(jià)值或意義的沖動(dòng)。下一步是“打卡”,代表著自媒體標(biāo)記某事物,在時(shí)間或空間中留存印跡,涉及人們接觸網(wǎng)紅事物、拍攝影像、上傳至社交平臺(tái)、引起其他用戶的關(guān)注和互動(dòng)的一系列行為。[31]在具身實(shí)踐中,“打卡”意味著以身體感官體會(huì)物質(zhì)場(chǎng)景中的種種活動(dòng),比如親眼目睹某一個(gè)景色、建筑,親口品嘗某一種佳肴、小吃,親手觸摸某一樣器物、動(dòng)植物。[31]人們前往網(wǎng)紅景點(diǎn)留影紀(jì)念,僅就表面現(xiàn)象來看往往被界定為跟風(fēng)、蹭熱度,但人們所追求的實(shí)際上是在虛擬世界和現(xiàn)實(shí)世界之間建立一種切身的聯(lián)系。區(qū)別于一般旅游,“打卡”也不只屬于個(gè)人的經(jīng)歷,其更深一層的意義在于創(chuàng)造存在感,即“創(chuàng)造現(xiàn)身于新媒體平臺(tái)與他人共在于某個(gè)環(huán)境中的感受”,通過在虛擬平臺(tái)上基于同一地點(diǎn)的內(nèi)容匯聚,以及在現(xiàn)實(shí)場(chǎng)景中共同“打卡”的相遇,虛實(shí)之間形成了多重循環(huán)。[31]
四、具身的傳播主體與生存形式
移動(dòng)網(wǎng)絡(luò)時(shí)代的新型傳播實(shí)踐,在根本上改寫了媒介化生存的底層邏輯,以短視頻應(yīng)用為核心的人類生存方式已經(jīng)進(jìn)入重造主體的階段,傳播的主體從掌握工具的自然人轉(zhuǎn)變?yōu)榧夹g(shù)嵌入身體的賽博人(cyborg)。[3]
主流傳播學(xué)將大眾傳播定義為中介化的傳播,信息必須借助符號(hào)才能從傳播者到達(dá)接收者,傳受雙方的身體及其所依附的物質(zhì)時(shí)空?qǐng)鼍岸际切枰豢朔恼系K。[34]基于“傳播是精神交往及互動(dòng),基本和身體無關(guān)”的共識(shí),傳播研究所論述的“人”多以價(jià)值認(rèn)同、態(tài)度和意見的流動(dòng)為尺度,交流者被確定為擁有理性意識(shí)的主體,從而形成對(duì)于一切身體感覺的拒斥。[35][36]這一去身體化(也作離身性)取向強(qiáng)化于第一次技術(shù)革命,也就是包括電力、鐵路交通、冶金在內(nèi)的工業(yè)技術(shù)的發(fā)展,此時(shí)“技術(shù)的界限很大程度上與人類身體的界限,是同構(gòu)的”。[37]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將“存在”解釋為有且僅有的兩種意義:“人作為物體存在,或作為意識(shí)存在”,正常的身體必定是身心統(tǒng)一的身體。[38]在基特勒看來,大眾媒介的每一種形態(tài)都是對(duì)人體感官的肢解與剝離,所謂的“人”被割裂為生理結(jié)構(gòu)和信息技術(shù),因此失去了完整意義上的身體。[20](17)這種二元分立的身體觀源自西方哲學(xué)傳統(tǒng),在技術(shù)革命的加持下成為現(xiàn)代社會(huì)的標(biāo)志,也構(gòu)成了主體的現(xiàn)代性危機(jī)。[34]
在第二次技術(shù)革命,也就是計(jì)算機(jī)、互聯(lián)網(wǎng)、移動(dòng)通信、多媒體技術(shù)等信息技術(shù)的浪潮中,技術(shù)的具身性趨勢(shì)顯著加劇。關(guān)于人與技術(shù)的關(guān)系,伊德(Don Ihde)堅(jiān)信,“我們始終通過我們的身體存在于世界上,始終存在著無法與技術(shù)相互分離的真實(shí)主體”。[39]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早就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但是孫瑋認(rèn)為,這一觀點(diǎn)未能進(jìn)一步預(yù)見媒介對(duì)于感知的介入并沒有停留在對(duì)人體感官的復(fù)制和加強(qiáng),而是“創(chuàng)造了一種交織媒介技術(shù)與人類有機(jī)體雙重邏輯的新型感知”。[40][31]在梅洛-龐蒂看來,身體具有連接可見之物與不可見之物的橋梁性功能,主要表現(xiàn)在“用身體及其感覺來同化這個(gè)世界,就能把陌生的、 異質(zhì)的、不可見的事物轉(zhuǎn)化成可感覺的、可見的、 可理解的事物,從而在人與世界之間架起一座溝通的橋梁,創(chuàng)造出一種關(guān)系和意義”,具身是人們參與這個(gè)世界的實(shí)踐方式。[41]在人與世界的鏈接中,視覺媒體技術(shù)承擔(dān)了必不可少的轉(zhuǎn)化作用,也就是將人的身體所感受和所經(jīng)驗(yàn)的,轉(zhuǎn)化為關(guān)于圖像的現(xiàn)象。伊德所謂的技術(shù)具身,意味著短視頻不再被理解為外在于身體的工具,而是越來越透明化、越來越深地嵌入人的“知覺—身體”經(jīng)驗(yàn)中。人們?cè)诿鎸?duì)和處理視覺圖像時(shí),知覺對(duì)象與認(rèn)知器官之間的距離被抹除,甚至可以通過視覺幻象統(tǒng)領(lǐng)聽覺、味覺、嗅覺、觸覺等其他感官體驗(yàn),直接進(jìn)入感知本身(比如觀看“吃播”激起人對(duì)食物的味覺渴望)。[22]
因此,人們的媒介化生存主要依托于人本身成為自我延伸的新媒介,即賽博人,其所擁有的連接力實(shí)現(xiàn)的不僅是媒體間的相互融合或媒體機(jī)構(gòu)與外界的融合,而是人類基本生存系統(tǒng)的解構(gòu)與重組。[3]從梅洛-龐蒂的“身體—主體”視角出發(fā),“人類的存在既非離身的心智也非復(fù)雜的機(jī)器,其主體性即在于作為活躍的生物以人類身體所特有的生理結(jié)構(gòu)介入世界”,這一理論的重點(diǎn)在于引入感性知覺以反駁笛卡爾的身心二元論。[42]海勒(N. Katherine Hayles)指出,人這一主體擁有兩個(gè)身體,“表現(xiàn)的身體以血肉之軀出現(xiàn)在電腦屏幕的一側(cè),再現(xiàn)的身體則通過語言和符號(hào)學(xué)的標(biāo)記在電子環(huán)境中產(chǎn)生”。[43]相較于電影、電視等傳統(tǒng)影像,短視頻在時(shí)長(zhǎng)之短和技術(shù)之靈便的基礎(chǔ)上,通過平臺(tái)的技術(shù)介入將“表現(xiàn)的身體”和“再現(xiàn)的身體”結(jié)合起來,解決身體在場(chǎng)的問題。首先,作為“接收器”的身體,其視聽感官讓人能夠感知、解碼、內(nèi)化外界的訊息;其次,身體亦“發(fā)射端”,人通過(肢體)語言、穿著、表情等身體表現(xiàn)以及對(duì)時(shí)空?qǐng)鼍暗膭?chuàng)造性(再)生產(chǎn)向外界傳達(dá)信息。[29]通過人的不同媒介器官端口的輸入和輸出,身體不再是私人的、隱蔽的,而是同外界開放共享,成為真實(shí)時(shí)空和虛擬情境的共生軀體。賽博人作為可以將“表現(xiàn)的身體”和“再現(xiàn)的身體”隨時(shí)分離或融合的傳播主體,其“化身”(avatar)能夠隨時(shí)現(xiàn)身于短視頻傳播的路途之中,在網(wǎng)絡(luò)空間進(jìn)行虛擬表演,也能夠以肉身之軀抵達(dá)真實(shí)空間的任意角落。
五、結(jié) 語
回溯尼葛洛龐帝關(guān)于人類生存方式的最初想象,媒介技術(shù)的實(shí)踐已歷經(jīng)數(shù)次主流傳播形態(tài)和主導(dǎo)方法論的更迭,引起了愈來愈清晰的媒介觀念轉(zhuǎn)向:從前,人們將媒介視為客觀世界的再現(xiàn),是附屬于現(xiàn)實(shí)的次要事物以及通達(dá)世界的手段和工具,人們以大眾傳媒作為感覺器官來感受社會(huì)、感知新事物;現(xiàn)在,媒介不僅是“情景”的生成方式和“現(xiàn)實(shí)”的組織裝置,媒介事件與日常生活的區(qū)隔、人與媒介的區(qū)分正在逐漸消失,長(zhǎng)久以來外化于人的媒介融入主體、成為人的組成部分,人即是最終的媒介。[2][1]盡管人們以短視頻為形式、以平臺(tái)為載體的媒介化生存革新了個(gè)人生活的敘事方式和社交互動(dòng)的在場(chǎng)形式,并且通過具身化的實(shí)踐不斷地確證了人在世界中的主體性地位,但短視頻應(yīng)用顯然不會(huì)也不必是媒介技術(shù)和社會(huì)生活的最終樣態(tài)。基于人工智能、云計(jì)算、AR/VR/MR、區(qū)塊鏈等技術(shù)集的成熟應(yīng)用,以往縱深方向演進(jìn)的技術(shù)譜系被組織整合,人類社會(huì)可以預(yù)見一個(gè)元宇宙的誕生,主體的存在形式、生存法則、交往方式正面臨再一次的解構(gòu)和重構(gòu),新的生存方式值得期待,人文倫理的動(dòng)蕩或?qū)⒁鸬钠v、迷茫、墮落也值得保持冷靜的擔(dān)憂。[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