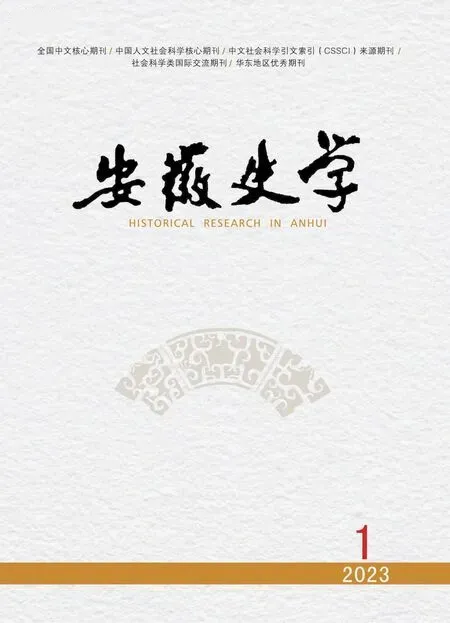從“同頻”到“共振”:抗戰(zhàn)時期晉綏和陜甘寧邊區(qū)的多維經(jīng)濟(jì)互動
劉巖巖
(電子科技大學(xué) 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四川 成都 611731)
晉綏邊區(qū)是抗戰(zhàn)時期華北三大根據(jù)地之一,陜甘寧邊區(qū)是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敵后抗戰(zhàn)的指揮中心,學(xué)界對二者的研究,歷來著述頗豐,尤其在其經(jīng)濟(jì)發(fā)展方面,不乏經(jīng)典之作。(1)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劉欣、景占魁主編:《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山西經(jīng)濟(jì)出版社1993年版;黃正林:《陜甘寧邊區(qū)社會經(jīng)濟(jì)史(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閆慶生、黃正林:《陜甘寧邊區(qū)經(jīng)濟(jì)史研究》,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張曉彪、蕭紹良、司俊編著:《陜甘寧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中國財政經(jīng)濟(jì)出版社2017年版,等。已有研究成果主要是圍繞晉綏邊區(qū)和陜甘寧邊區(qū)的發(fā)展進(jìn)行分別論述,對二者之間的經(jīng)濟(jì)聯(lián)系則著墨不多。按照物理學(xué)的解釋:同樣頻率的東西會共振、共鳴或走到一起。晉綏邊區(qū)和陜甘寧邊區(qū),雖然分別位于華北和西北兩大經(jīng)濟(jì)系統(tǒng),但在地理上相毗鄰,二者隔黃河而望,地理環(huán)境上有諸多相似之處,歷史上往來亦較為頻繁,抗戰(zhàn)時期又同屬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根據(jù)地,內(nèi)部治理和外部應(yīng)對之策相似,本屬“同頻”,但囿于主客觀諸多因素,在抗戰(zhàn)時期一度交流受阻,一段時間內(nèi)并未產(chǎn)生理所當(dāng)然的“共振”。此中原因頗耐人尋味。借助物理學(xué)相關(guān)概念,并從區(qū)域經(jīng)濟(jì)學(xué)的相關(guān)角度切入,對晉綏邊區(qū)和陜甘寧邊區(qū)二者的經(jīng)貿(mào)互動進(jìn)行深入探究頗為有益。
一、同頻之源:抗日根據(jù)地之間經(jīng)濟(jì)互動的基礎(chǔ)
(一)抗戰(zhàn)爆發(fā)前晉陜兩地的商貿(mào)傳統(tǒng)
抗戰(zhàn)時期的晉綏邊區(qū)和陜甘寧邊區(qū),地理上分屬華北和西北地區(qū)。從經(jīng)濟(jì)地理角度分析,因為兩地相鄰,“晉陜綏一河相隔,疆界毗連”(2)張萍主編:《西北近代經(jīng)濟(jì)地理》,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第245頁。,且傳統(tǒng)商路較為通暢,商業(yè)上磧口、河曲等主要市鎮(zhèn)向為秦晉交通要道,“為西北與沿海各大城市貨物輸出入的集散地”(3)⑨中共晉西區(qū)黨委:《晉西北稅收工作情況》(1941年12月),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編寫組、山西省檔案館編:《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資料選編·財政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4、336頁。,所以抗戰(zhàn)前這兩大區(qū)域在經(jīng)濟(jì)上一直保持著較為緊密的聯(lián)系,從而為諸如鹽、堿、甘草、麻油等傳統(tǒng)商品的流通提供了基礎(chǔ)。于陜西而言,雖緊鄰山西,但因其內(nèi)部按照經(jīng)濟(jì)地理層面劃分,又分為陜北經(jīng)濟(jì)圈、關(guān)中經(jīng)濟(jì)圈和陜南經(jīng)濟(jì)圈。因交通的相對便利,和山西經(jīng)濟(jì)聯(lián)系比較緊密的是陜北經(jīng)濟(jì)圈,“而陜北當(dāng)時與山西僅一河之隔,有多處渡口之便,又因山西境內(nèi)同蒲鐵路連接正太鐵路,貫通平(京)漢鐵路,可以直達(dá)對外貿(mào)易的商埠天津”。(4)③王一成、韋葦編著:《陜西古近代對外經(jīng)濟(jì)貿(mào)易研究》,陜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71頁。基于此,陜北本地的出產(chǎn)如羊毛、皮貨等經(jīng)過山西轉(zhuǎn)運到天津港出口,具體貿(mào)易路線上,以陜北的榆林、安邊、神木為集中地,“榆林、神木兩處集中的貨物經(jīng)米脂、息蜊峪(即螅蠣峪——作者注)、離石過河到山西汾陽達(dá)榆次,再由榆次用火車轉(zhuǎn)運至津。而安邊所集中的羊毛,則運經(jīng)寧條梁、石灣、綏德、吳堡、宋家川過河到汾陽而達(dá)榆次,然后裝車轉(zhuǎn)津。”(5)③王一成、韋葦編著:《陜西古近代對外經(jīng)濟(jì)貿(mào)易研究》,陜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71頁。通過山西的轉(zhuǎn)運,陜西等西北地區(qū)的出產(chǎn)進(jìn)入到國際市場,逐步實現(xiàn)了經(jīng)濟(jì)外向化的過程。陜西所需產(chǎn)品的進(jìn)口路線中,山西同樣是重要的中轉(zhuǎn)站,“日用品如石油、洋煙、肥皂、火柴、糖,其他雜貨如文具、紙張、瓷器、五金等,戰(zhàn)前全部由津、晉運來”。(6)⑥張萍主編:《西北近代經(jīng)濟(jì)地理》,第246頁。
在工業(yè)發(fā)展水平方面,長期主政山西的閻錫山在抗戰(zhàn)前推行“造產(chǎn)救國”,推動了山西重工業(yè)的迅猛發(fā)展,“僅太原一地,西北制造廠與東北沈陽兵工廠并駕齊驅(qū),是中國最大的兵工廠,而其他如火力發(fā)電廠、煉鋼廠、大小型卡車制造廠、機(jī)械制造廠、汽車配件制造廠、洋灰廠、各種化學(xué)制造廠以及卷煙廠、紡織廠等,均在國內(nèi)處于領(lǐng)先地位。”(7)劉建生、劉鵬生等著:《山西近代經(jīng)濟(jì)史》,山西經(jīng)濟(jì)出版社1995年版,第684頁。具備一定規(guī)模的山西工業(yè)在民國時期頗有實力,其生產(chǎn)的商品較為豐富,不但滿足省內(nèi)需要,并且行銷多省,其中就包括西北的陜甘寧地區(qū),如西北火柴廠生產(chǎn)的火柴,西北實業(yè)公司晉華卷煙廠生產(chǎn)的香煙,皆把陜西等西北區(qū)域作為重要的銷場。除了工業(yè)品,山西出產(chǎn)的糧食、棉花亦多供給陜北地區(qū)。(8)⑥張萍主編:《西北近代經(jīng)濟(jì)地理》,第246頁。在工業(yè)發(fā)展水平方面,長期主政山西的閻錫山在抗戰(zhàn)前推行“造產(chǎn)救國”,推動了山西重工業(yè)的迅猛發(fā)展,“僅太原一地,西北制造廠與東北沈陽兵工廠并駕齊驅(qū),是中國最大的兵工廠,而其他如火力發(fā)電廠、煉鋼廠、大小型卡車制造廠、機(jī)械制造廠、汽車配件制造廠、洋灰廠、各種化學(xué)制造廠以及卷煙廠、紡織廠等,均在國內(nèi)處于領(lǐng)先地位。”(9)劉建生、劉鵬生等著:《山西近代經(jīng)濟(jì)史》,山西經(jīng)濟(jì)出版社1995年版,第684頁。
由此可知,抗戰(zhàn)前,晉綏地區(qū)和陜甘寧地區(qū)兩地的經(jīng)濟(jì)交流,基本以農(nóng)礦初級產(chǎn)品為主,山西因為在陜西東部,距離東部沿海港口更近,其在陜甘寧經(jīng)濟(jì)外向化的轉(zhuǎn)變過程中,扮演了“二傳手”的角色。兩地在抗戰(zhàn)前的經(jīng)貿(mào)往來傳統(tǒng),為抗戰(zhàn)時期晉綏邊區(qū)和陜甘寧邊區(qū)經(jīng)濟(jì)層面的同頻共振打下了基礎(chǔ)。
(二)中國共產(chǎn)黨經(jīng)濟(jì)因應(yīng)之策的趨同
作為中國共產(chǎn)黨在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保存下來的唯一根據(jù)地,陜甘寧根據(jù)地在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根據(jù)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有關(guān)精神,更名為邊區(qū)政府。抗戰(zhàn)時期,“中共除了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以外,并未建立中央一級的行政機(jī)構(gòu)”,并且,“中央主要是從黨和軍隊的角度對根據(jù)地進(jìn)行一元化的領(lǐng)導(dǎo)和管理”。(10)李金錚:《抗日根據(jù)地的“關(guān)系”史研究》,《抗日戰(zhàn)爭研究》2016年第2期,第11、13頁。但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作為中共領(lǐng)導(dǎo)敵后抗戰(zhàn)的總后方,中共的政治、經(jīng)濟(jì)、軍事、文化政策首先在陜甘寧邊區(qū)得到實施后,才在其他根據(jù)地推行。”(11)黃正林:《陜甘寧邊區(qū)社會經(jīng)濟(jì)史(1937—1945)》,第62頁。此兩種觀點,在陜甘寧邊區(qū)和地方根據(jù)地關(guān)系之表述上確有差異,但從求同存異的角度來看,都承認(rèn)陜甘寧邊區(qū)的領(lǐng)導(dǎo)地位,只是在經(jīng)濟(jì)治理的方式上有不同認(rèn)識。陜甘寧邊區(qū)和晉綏邊區(qū)同屬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抗日根據(jù)地,二者在抗戰(zhàn)過程中面對復(fù)雜的斗爭形勢和艱巨的斗爭任務(wù),既要堅持對敵斗爭,又要自力更生發(fā)展生產(chǎn),并且兩地皆屬于經(jīng)濟(jì)落后地區(qū),工商產(chǎn)品需要大量輸入,所以大體上處于同一個頻率。同時,因為兩地都屬于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區(qū),經(jīng)濟(jì)構(gòu)成也頗為相似,“陜甘寧邊區(qū)和晉西北一河相隔都是農(nóng)業(yè)地區(qū),對外來品需要和能輸出的貨物相差不多”(12)⑨中共晉西區(qū)黨委:《晉西北稅收工作情況》(1941年12月),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編寫組、山西省檔案館編:《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資料選編·財政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4、336頁。,所以在經(jīng)濟(jì)同頻的基礎(chǔ)上,理應(yīng)引起雙方深層次的共振,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二、“共振”之困:晉綏邊區(qū)和陜甘寧邊區(qū)經(jīng)濟(jì)互動的障礙
(一)交通和運輸條件落后
作為華北各抗日根據(jù)地的樞紐,晉綏邊區(qū)的戰(zhàn)略地位尤其重要,“西面經(jīng)過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據(jù)地陜甘寧邊區(qū),通到大后方。東面是抗日民主的模范根據(jù)地晉察冀邊區(qū)。東南是晉冀魯豫邊區(qū)。南面是晉西南。”(13)牛蔭冠:《晉西北行政公署向晉西北臨時參議會的工作報告》(1942年),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編寫組、山西省檔案館編:《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資料選編·總論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6頁。看似和各根據(jù)地四通八達(dá),但實際上溝通聯(lián)系起來卻很困難,因為除了和西面的陜甘寧邊區(qū)隔著黃河外,與其它方向的根據(jù)地均隔著敵人的封鎖線,這就使得晉綏邊區(qū)三面被敵人包圍,處境較為兇險。從根據(jù)地分布的物產(chǎn)資源上看,晉綏邊區(qū)雖然有產(chǎn)糧區(qū)、紡織區(qū)、煤鐵區(qū),也蘊含各種礦產(chǎn),但因為地處黃土高原,“境內(nèi)溝壑縱橫,交通極為不便”(14)劉欣、景占魁主編:《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第221頁。,社會經(jīng)濟(jì)條件落后,所以直到抗戰(zhàn)爆發(fā),也沒有得到綜合開發(fā)和有效利用。陜甘寧邊區(qū)對外交通運輸同樣落后,“考其原因,并不是完全由于運輸力量不夠,而主要是因為沒有建設(shè)應(yīng)有的交通運輸設(shè)備,未能合理的保證草料的供給,以至有了運輸力量不能使用。”(15)《三十一年度交通運輸工作計劃》(1942年),陜甘寧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編寫組、陜西省檔案館編:《陜甘寧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料摘編·第三編工業(yè)交通》,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7頁。運輸工具的落后亦是大問題,兩地位居內(nèi)地,遠(yuǎn)離現(xiàn)代交通運輸線,既無鐵路,也少公路,現(xiàn)代交通運輸工具極其匱乏。抗戰(zhàn)時期陜甘寧邊區(qū)只有十幾輛汽車,“而且由于缺乏配件,能夠開動的就更少了,還不能真正用于商業(yè)運輸。邊區(qū)馬車的數(shù)量也極為有限,最多時沒有超過二百輛。”(16)鄧文卿:《陜甘寧邊區(qū)的騾馬店》,商業(yè)部商業(yè)經(jīng)濟(jì)研究所編:《革命根據(jù)地商業(yè)回憶錄》,中國商業(yè)出版社1984年版,第40頁。由于陜甘寧邊區(qū)交通的落后,隔幾十里外的原料就不易利用,“運鹽、運糧運費常超過成本”。(17)《陜甘寧邊區(qū)政府工作報告》(1941年4月),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經(jīng)濟(jì)研究所中國現(xiàn)代經(jīng)濟(jì)史組編:《革命根據(jù)地經(jīng)濟(jì)史料選編》中卷,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頁。因邊區(qū)依然是使用牲畜承擔(dān)主要運輸任務(wù),不但運量有限,而且時間成本高,給兩地經(jīng)貿(mào)往來帶來諸多不便。
(二)日軍的搶掠和封鎖
抗戰(zhàn)爆發(fā)后,晉綏邊區(qū)原本脆弱的生產(chǎn)事業(yè)和經(jīng)濟(jì)基礎(chǔ)在日軍反復(fù)的“掃蕩”下,遭受極大破壞,“特別是1940年一年四次大規(guī)模掃蕩,使內(nèi)地興臨各縣開始遭到戰(zhàn)爭的直接破壞”。(18)⑦晉綏地區(qū)行政公署:《晉西北三年來的生產(chǎn)建設(shè)》(1943年),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編寫組、山西省檔案館編:《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資料選編·總論編》,第493、494頁。原本薄弱的工礦事業(yè),幾乎遭到滅頂之災(zāi),“整個生產(chǎn)都走向急劇衰落的趨勢,織布幾乎完全停止了,造紙的也減到戰(zhàn)前的半數(shù)以下,煤瓷均比戰(zhàn)前減少一半以上,一部分工商業(yè)破產(chǎn),人口轉(zhuǎn)為小農(nóng)維持生活。”(19)⑦晉綏地區(qū)行政公署:《晉西北三年來的生產(chǎn)建設(shè)》(1943年),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編寫組、山西省檔案館編:《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資料選編·總論編》,第493、494頁。除了對根據(jù)地大規(guī)模的“掃蕩”外,日軍還在游擊區(qū)進(jìn)行搶掠,至于對邊區(qū)經(jīng)濟(jì)封鎖更是異常嚴(yán)厲,1941年的“三次強(qiáng)化運動”,日軍按地區(qū)實施封鎖,“各據(jù)點均設(shè)有經(jīng)濟(jì)班,負(fù)責(zé)進(jìn)行查緝,不許物資出據(jù)點。即在據(jù)點之內(nèi)其辦法也異常嚴(yán)格,違者處死。”(20)晉綏邊區(qū)行署:《晉綏邊區(qū)貿(mào)易工作材料》(1944年8月29日),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編寫組、山西省檔案館編:《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資料選編·金融貿(mào)易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5—566頁。境況之慘烈,使得原本和陜甘寧邊區(qū)保持的經(jīng)濟(jì)互動頗受影響,想要在經(jīng)濟(jì)層面產(chǎn)生共振非常困難。陜甘寧邊區(qū)雖然沒有直接遭受日軍侵略,但形勢也異常嚴(yán)峻,“日軍屯兵柳林,積極準(zhǔn)備著進(jìn)攻陜北”(21)肖勁光:《加強(qiáng)河防反對造謠破壞的陰謀家》,西北五省區(qū)編寫領(lǐng)導(dǎo)小組、中央檔案館編:《陜甘寧邊區(qū)抗日民主根據(jù)地·文獻(xiàn)卷》上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36頁。,并出動空軍,對延安地區(qū)頻繁轟炸,給兩地正常的經(jīng)貿(mào)交流,帶來極大破壞。
(三)國民黨軍隊的阻撓和破壞
無論是晉綏邊區(qū)還是陜甘寧邊區(qū),在抗戰(zhàn)過程中如何處理和國民黨軍隊的關(guān)系都是重要問題。作為戰(zhàn)時名義上一致對外的“友軍”,國民黨軍隊對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抗日根據(jù)地表現(xiàn)得卻不甚友好。針對晉綏邊區(qū),國民黨軍隊封鎖食鹽不準(zhǔn)運過來,造成食鹽價格昂貴,從1941年每百斤70元漲至1944年的2000元以上。對黃河上游船只和去陜北貿(mào)易的商人經(jīng)常隨意扣留甚至迫害。(22)晉綏邊區(qū)行署:《晉綏邊區(qū)貿(mào)易工作材料》(1944年8月29日),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編寫組、山西省檔案館編:《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資料選編·金融貿(mào)易編》,第568頁。如果遇到極端的反共摩擦事件,則損失更大,1939年,山西閻錫山集團(tuán)挑起晉西事變,一度給晉綏邊區(qū)的對外貿(mào)易帶了重大損失,“境內(nèi)對貿(mào)易的市場,大部停頓”;“外來販貨商人減少了。境外商人販貨入境的,一時減到很少”;“外來貨物減少了。短期內(nèi)就很少有外貨進(jìn)來”。(23)中共晉西區(qū)黨委:《晉西北商業(yè)貿(mào)易發(fā)展概況》(1941年12月),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編寫組、山西省檔案館編:《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資料選編·金融貿(mào)易編》,第507頁。此種損害,需要相當(dāng)長的時間才能使經(jīng)濟(jì)恢復(fù)到事變前的狀態(tài)。
陜甘寧邊區(qū)作為中共中央所在地,更是受到國民黨軍隊的重點封鎖,“正規(guī)軍五十余萬人,各級地方政府稅收機(jī)關(guān)、地痞流氓組織起來的各種便衣隊到處都是”。(24)貿(mào)易公司:《國民黨對邊區(qū)經(jīng)濟(jì)封鎖材料》(1944年10月),陜甘寧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編寫組、陜西省檔案館編:《陜甘寧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料摘編·第四編商業(yè)貿(mào)易》,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2頁。除了頒布法令禁止貨物進(jìn)出邊區(qū),國民黨軍隊直接搶劫沒收進(jìn)出邊區(qū)的貨物,槍殺從事貿(mào)易的商民,并根據(jù)陜甘寧邊區(qū)不同地方的特點,針對綏德、隴東、三邊地區(qū)采取不同的封鎖方式。國民黨對陜甘寧邊區(qū)封鎖之嚴(yán)厲,讓人瞠目結(jié)舌,以至?xí)r人驚呼,“國民黨和邊區(qū)雖然同屬于一個國家,共同抗日,但在貿(mào)易上卻比蘇德協(xié)定期間,法西斯德國對社會主義國家蘇聯(lián)關(guān)系還要壞。借貸關(guān)系固然不必講,國民黨根本就不讓物資進(jìn)來,并斷絕了匯兌關(guān)系。”(25)貿(mào)易公司:《邊區(qū)區(qū)際貿(mào)易差額的實質(zhì)》(1945年3月),陜甘寧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編寫組、陜西省檔案館編:《陜甘寧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料摘編·第四編商業(yè)貿(mào)易》,第73頁。在這樣極端惡劣的環(huán)境下,陜甘寧邊區(qū)很難對外開展大規(guī)模的正常經(jīng)貿(mào)活動,其和晉綏邊區(qū)雖有地理毗鄰的便利,但在極端惡劣的外部環(huán)境下一樣處處受限,二者若要實現(xiàn)經(jīng)濟(jì)上的共振,僅憑借經(jīng)濟(jì)規(guī)律這只無形的手是不可能的,只有主動作為尋求突破。
三、“同頻”到“共振”的轉(zhuǎn)變:邊區(qū)政府的因應(yīng)
(一)基于戰(zhàn)時比較優(yōu)勢的兩地貿(mào)易往來
按照比較優(yōu)勢理論,“每種物品應(yīng)該由生產(chǎn)這種物品機(jī)會成本較低的國家生產(chǎn)”(26)[美]曼昆著,梁小民、梁碩譯:《經(jīng)濟(jì)學(xué)原理:微觀經(jīng)濟(jì)學(xué)分冊》,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第64頁。,此種理論同樣適用于國內(nèi)的不同地區(qū),一個地區(qū)在本地生產(chǎn)一種產(chǎn)品的機(jī)會成本低于在其它地區(qū)生產(chǎn)該產(chǎn)品的機(jī)會成本的話,則該地區(qū)在生產(chǎn)該種產(chǎn)品上就擁有比較優(yōu)勢。抗戰(zhàn)時期,由于東中部地區(qū)大片國土的淪喪,抗日根據(jù)地周邊和自身的經(jīng)濟(jì)情況也發(fā)生變化,原本不是優(yōu)勢的因素成為新的比較優(yōu)勢。所以,根據(jù)戰(zhàn)時比較優(yōu)勢理論,晉綏和陜甘寧邊區(qū)基于不同的資源稟賦,將本地區(qū)的特色出產(chǎn)輸出到對方,從而實現(xiàn)二者在抗戰(zhàn)時期的互通有無。
陜北的傳統(tǒng)特產(chǎn),向有三寶之說,即食鹽、甘草和皮毛。戰(zhàn)時環(huán)境下,“甘草因運量大,不能大量出境,絨毛多自用,出口很少,只有食鹽尚可能維持”。(27)西北財經(jīng)辦事處:《抗戰(zhàn)以來的陜甘寧邊區(qū)財政概況》(1948年2月18日),陜甘寧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編寫組、陜西省檔案館編:《陜甘寧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頁。陜甘寧邊區(qū)的三邊地區(qū),是邊區(qū)食鹽出口的主力,每年約產(chǎn)鹽60萬馱,每馱150斤,共9000多萬斤。陜甘寧邊區(qū)150萬人口食用的需求為1000萬左右,剩下的都可以出口。(28)陳凱:《隴東鹽業(yè)貿(mào)易的反封鎖斗爭》,商業(yè)部商業(yè)經(jīng)濟(jì)研究所編:《革命根據(jù)地商業(yè)回憶錄》,中國商業(yè)出版社1984年版,第52頁。加之抗戰(zhàn)以來,東部所產(chǎn)的海鹽斷絕,西北各省和華北地區(qū)對于陜甘寧邊區(qū)出產(chǎn)的食鹽需求量大增,1938年邊區(qū)食鹽運銷還只有7萬馱,1939年增加到19萬馱,1940年為23萬馱。(29)中共西北中央局調(diào)查研究室編:《一九四三年的運鹽工作》(1944年),陜甘寧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編寫組、陜西省檔案館編:《陜甘寧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料摘編·第三編工業(yè)交通》,第693頁。晉綏邊區(qū)所需食鹽,多依靠外部輸入,“全晉西北食鹽、白堿賴河西供給”。(30)⑥中共晉西區(qū)黨委:《晉西北商業(yè)貿(mào)易發(fā)展概況》(1941年12月),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編寫組、山西省檔案館編:《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資料選編·金融貿(mào)易編》,第502、501頁。“河西”即是黃河以西包括陜甘寧邊區(qū)在內(nèi)的西北地區(qū)。由于晉綏邊區(qū)產(chǎn)鹽甚少,所以根據(jù)地所需食鹽,需要完全從外部購入,全年約需400萬斤,具體到不同地區(qū),晉綏邊區(qū)的三分區(qū)由陜邊區(qū)輸入240萬斤,二分區(qū)由府谷輸入約80—90萬斤,興縣經(jīng)神府由神木輸入約45萬斤。(31)晉綏邊區(qū)行署:《晉綏邊區(qū)貿(mào)易工作材料》(1944年8月29日),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編寫組、山西省檔案館編:《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資料選編·金融貿(mào)易編》,第571頁。由此可知,陜甘寧邊區(qū)出產(chǎn)的食鹽,至少解決了晉綏邊區(qū)所需的60%。除了食鹽,作為棉花重要產(chǎn)區(qū),陜西棉花儲備頗豐,陜甘寧邊區(qū)收購的棉花,“不僅供給了全年機(jī)關(guān)部隊棉花的需要,而且供給了晉西北大部分的棉花”。(32)喻杰:《土產(chǎn)公司工作報告》(1944年),陜甘寧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編寫組、陜西省檔案館編:《陜甘寧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料摘編·第四編商業(yè)貿(mào)易》,第215頁。
相較于陜甘寧邊區(qū),晉綏邊區(qū)經(jīng)濟(jì)有一定基礎(chǔ),“晉西北建設(shè)的物質(zhì)條件,自然環(huán)境較優(yōu)于陜甘寧邊區(qū)。物資豐富(糧食、工業(yè)、原料、畜產(chǎn)、森林、藥材等)富饒,蘊藏深厚(如各種礦產(chǎn)煤、鐵、錳、陶土、硫磺、火硝等)。”(33)中共中央財政經(jīng)濟(jì)部:《關(guān)于對晉西北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的建議》(1940年6月29日),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編寫組、山西省檔案館編:《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資料選編·總論編》,第465頁。因此晉綏邊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在自給的同時,如有合適機(jī)會,亦對外輸出,“糧食除河曲、寶德自給不足外,其他縣份都可以自給。游擊區(qū)食糧大量運輸根據(jù)地,一部運往河西”。(34)⑥中共晉西區(qū)黨委:《晉西北商業(yè)貿(mào)易發(fā)展概況》(1941年12月),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編寫組、山西省檔案館編:《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資料選編·金融貿(mào)易編》,第502、501頁。煤炭是晉綏邊區(qū)的大出產(chǎn),“估計全邊區(qū)產(chǎn)煤達(dá)十?dāng)?shù)萬萬斤。其中自用一部外,輸出數(shù)也在近十萬萬斤。”(35)⑧《晉綏邊區(qū)一九四五年一月至一九四六年六月貿(mào)易工作綜述》(1946年7月10日),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編寫組、山西省檔案館編:《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資料選編·金融貿(mào)易編》,第646頁。對外輸出的區(qū)域除了綏遠(yuǎn)、懷朔平川、同蒲路東各地以外,渡過黃河向西輸出的自是不少,“一、二、三分區(qū)從黃河向西輸出的炭也不少,只柳林渡口每月即可用炭換回鹽一萬斤”。(36)⑧《晉綏邊區(qū)一九四五年一月至一九四六年六月貿(mào)易工作綜述》(1946年7月10日),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編寫組、山西省檔案館編:《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資料選編·金融貿(mào)易編》,第646頁。
為了使物資交換和商貿(mào)往來更加順暢,步調(diào)更趨一致,晉綏邊區(qū)和陜甘寧邊區(qū)于1943年簽訂了物資交換協(xié)定書,“雙方議定以綏德分區(qū)之螅蠣峪為物資交換地區(qū),由雙方派員在螅蠣峪設(shè)聯(lián)合辦事處”。(37)⑩《晉西北行政公署、陜甘寧邊區(qū)物資局物資交換議定書》(1943年4月1日),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編寫組、山西省檔案館編:《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資料選編·第四編商業(yè)貿(mào)易》,第408頁。照此規(guī)定,晉綏邊區(qū)負(fù)責(zé)黃河以東采購?fù)廉a(chǎn)的工作,必須保證按陜甘寧邊區(qū)需要數(shù)字將土產(chǎn)運至螅蠣峪聯(lián)合辦事處,全部交給對方,概不自行出售,亦不向邊區(qū)內(nèi)地運送,同時陜甘寧邊區(qū)停止過河?xùn)|采購?fù)廉a(chǎn),專門在聯(lián)合辦事處收貨。(38)⑩《晉西北行政公署、陜甘寧邊區(qū)物資局物資交換議定書》(1943年4月1日),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編寫組、山西省檔案館編:《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資料選編·第四編商業(yè)貿(mào)易》,第408頁。這樣雙方既能保證物資交流的便捷和高效,同時為兩區(qū)域在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更深層次的協(xié)同打下了基礎(chǔ)。為了推動兩地貿(mào)易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1944年12月晉綏邊區(qū)在延安成立“晉綏邊區(qū)辦事處”,并規(guī)定:“今后晉綏邊區(qū)各財經(jīng)貿(mào)易單位與陜甘寧邊區(qū)財經(jīng)貿(mào)易公司的往來,一律經(jīng)過晉綏邊區(qū)辦事處;陜甘寧邊區(qū)部隊、機(jī)關(guān)、學(xué)校如赴晉綏邊區(qū)進(jìn)行貿(mào)易事項,須一律經(jīng)由晉綏邊區(qū)辦事處的介紹,否則晉綏邊區(qū)一概拒絕。”(39)《西北財經(jīng)辦事處通知》(1944年12月30日),陜甘寧革命根據(jù)地工商稅收編寫組、陜西省檔案館編:《陜甘寧革命根據(jù)地工商稅收史料選編》第5冊,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5頁。晉綏邊區(qū)辦事處的成立,進(jìn)一步掃除了兩根據(jù)地直接貿(mào)易的障礙,有利于二者經(jīng)貿(mào)層面的協(xié)同一致。
(二)騾馬大會的恢復(fù)和發(fā)展
從功能上看,北方根據(jù)地的騾馬大會是傳統(tǒng)社會農(nóng)耕文明中具有經(jīng)濟(jì)功能的廟會在抗戰(zhàn)時期的調(diào)整和發(fā)展,其前身的廟會作為農(nóng)村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到20世紀(jì)初,商品交易已成為許多大中型廟會的主要功能,廟會演變成特種定期集市或中小型商品展覽會。”(40)劉太祥、吳太昌主編:《中國近代經(jīng)濟(jì)史(1927—1937)》下冊,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730—1731頁。抗戰(zhàn)軍興,因為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需要,騾馬等牲畜交易就成了廟會交易的主要形式,“民眾對廟會中騾馬交易的重視與根據(jù)地政府借廟會活躍牲畜、農(nóng)具市場的初衷不謀而合,因此,在恢復(fù)廟會的過程中,有地方政府就將傳統(tǒng)廟會直接改稱騾馬大會或騾馬百貨市場進(jìn)行宣傳動員。”(41)韓曉莉:《革命與節(jié)日——華北根據(jù)地節(jié)日文化生活(1937—1949)》,社會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9年版,第78頁。受此影響北方各根據(jù)地的騾馬大會都有不同程度的恢復(fù)和發(fā)展。
無論是晉綏邊區(qū)還是陜甘寧邊區(qū)的騾馬大會,除了具有牲畜交易的基本功能外,在溝通兩地經(jīng)濟(jì)交流以及密切區(qū)域經(jīng)濟(jì)合作方面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1944年7月15日,晉綏邊區(qū)的興縣舉行騾馬大會,到會群眾和客商達(dá)7萬人,交易額1300多萬元,陜甘寧邊區(qū)的客商也趕來參會,推動了兩地商業(yè)貿(mào)易的發(fā)展和市場的繁榮。(42)李樹萱、晉曉偉:《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工作大事記》(1937年7月至1949年9月),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編寫組、山西省檔案館編:《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資料選編·金融貿(mào)易編》,第44頁。陜甘寧邊區(qū)的騾馬大會同樣開展得有聲有色,延安的騾馬大會級別高,規(guī)模大,中共領(lǐng)導(dǎo)人毛澤東、朱德親訪現(xiàn)場,周邊商旅熱情踴躍,并吸引了晉綏邊區(qū)商業(yè)機(jī)構(gòu)參加,“而晉綏過載行市部門,永福祥、萬瑞祥、晉豫合、德盛玉的四商店聯(lián)合門市部,以及新上市街上的國貨公司,婦女合作社營業(yè)部門,購物者均極擁擠”。(43)《延安騾馬大會盛況空前》(《解放日報》1943年11月16日),陜甘寧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編寫組、陜西省檔案館編:《陜甘寧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料摘編·第四編商業(yè)貿(mào)易》,第403頁。隴東的騾馬大會會期共10天,場面熱鬧非凡,“萬商云集,貿(mào)易鼎盛,與會者不僅有邊區(qū)各縣群眾,并有友區(qū)人民,包括陜、甘、寧、青、晉、豫等省遠(yuǎn)近客寄”。(44)《隴東舉行騾馬大會》(《解放日報》1942年6月2日),陜甘寧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編寫組、陜西省檔案館編:《陜甘寧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料摘編·第四編商業(yè)貿(mào)易》,第406頁。騾馬大會的恢復(fù)和發(fā)展,和抗戰(zhàn)以來尤其是1943年后根據(jù)地經(jīng)濟(jì)形勢的好轉(zhuǎn)有密切關(guān)系,所以能借助傳統(tǒng)商品展銷會的形式,促進(jìn)以牲畜為核心的農(nóng)貿(mào)產(chǎn)品的交流,從而密切邊區(qū)間的經(jīng)濟(jì)聯(lián)系。
(三)兩地金融的互動
1940年晉西事變之后,晉綏邊區(qū)取得對閻錫山斗爭的勝利,于5月成立了西北農(nóng)民銀行,其發(fā)行的農(nóng)幣在1941年1月成為邊區(qū)唯一合法的本位幣。與之相鄰的陜甘寧邊區(qū)亦有其銀行,并在抗戰(zhàn)初期發(fā)行光華代金券。因為良好的信用,光華代金券甚至流入陜甘寧以外的地區(qū)。之后隨著經(jīng)濟(jì)形勢的變化和實際對敵斗爭的需要,陜甘寧邊區(qū)銀行還發(fā)行過邊幣和流通券。無論是晉綏邊區(qū)還是陜甘寧邊區(qū),抗戰(zhàn)時期都需要從外面輸入生產(chǎn)生活的必需品和軍需用品,尤其是醫(yī)藥、軍火和日用品還必須從淪陷區(qū)或者國統(tǒng)區(qū)購來。同時,和國統(tǒng)區(qū)地理環(huán)境上的緊密相連,也使得被根據(jù)地軍民稱之為“友區(qū)”的國統(tǒng)區(qū)的法幣在邊區(qū)一度大行其道,以陜甘寧邊區(qū)為例,“在邊區(qū)三十一個縣市二百十八個區(qū)中,有二十四個縣八十一個區(qū)是與友區(qū)犬牙交錯著的邊境,約占百分之四十的地區(qū)人民生活與友區(qū)經(jīng)濟(jì)密切相聯(lián)系,因此,他們要使用法幣交易。”(45)王思華:《再論如何穩(wěn)定目前金融》,陜甘寧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編寫組、陜西省檔案館編:《陜甘寧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料摘編·第五編金融》,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6頁。邊區(qū)百姓對法幣的選擇不是簡單靠行政命令就能禁止的,因為邊區(qū)和“友區(qū)”甚至邊區(qū)之間彼此金融上不能通匯,必須使用對方的貨幣,所以邊區(qū)軍民一般先在邊區(qū)銀行完成相應(yīng)的貨幣兌換,“匯兌工作雖已建立,但范圍非常狹小,并只能與陜甘寧邊區(qū)有來往”。(46)《晉西北貨幣金融的發(fā)展簡況及現(xiàn)狀》(1942年9月),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編寫組、山西省檔案館編:《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資料選編·金融貿(mào)易編》,第86頁。
晉綏邊區(qū)管理對外貿(mào)易匯兌時,雖然給予了陜甘寧邊區(qū)特殊待遇,“陜甘寧邊區(qū)基本上以內(nèi)地論”(47)《晉綏邊區(qū)管理對外貿(mào)易匯兌辦法實施細(xì)則》(1944年10月28日),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編寫組、山西省檔案館編:《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資料選編·金融貿(mào)易編》,第418頁。,但是因為兩邊區(qū)使用不同的貨幣,也就是說陜甘寧的邊幣過了黃河到對岸的晉西北即不能使用,晉西北邊區(qū)政府發(fā)行的農(nóng)鈔到了陜甘寧邊區(qū)亦不能流通,這就給基層百姓帶來困惑,“群眾的反映:都是八路軍的票子,如何不能互相使用?”(48)《陳希云、劉卓甫、王恩華統(tǒng)一兩個根據(jù)地的貨幣之意見書》(1944年2月15日),陜甘寧革命根據(jù)地工商稅收編寫組、陜西省檔案館編:《陜甘寧革命根據(jù)地工商稅收史料選編》第5冊,第21頁。由此導(dǎo)致的后果是老百姓不但對兩邊區(qū)的貨幣都不信任,邊區(qū)之間物資交流更多還是使用銀元或者法幣,并且因為折算的不同,帶來新的爭端,反而增加了銀元和法幣的優(yōu)勢,打擊了根據(jù)地自己發(fā)行的貨幣,“黃河沿岸,銀洋暗流,很難禁絕,以致影響金融,阻礙物資交流”。(49)劉卓甫:《晉綏金融工作報告》(1948年4月2日),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編寫組、山西省檔案館編:《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資料選編·金融貿(mào)易編》,第286頁。受戰(zhàn)時條件所限,晉綏邊區(qū)和陜甘寧邊區(qū)一直到解放戰(zhàn)爭時期的1947年,隨著兩地銀行的合并,才真正實現(xiàn)貨幣的統(tǒng)一,“陜甘寧邊區(qū)銀行與晉綏西北農(nóng)民銀行合并,統(tǒng)稱西北農(nóng)民銀行”。(50)西北局常委辦公廳:《陜甘寧邊區(qū)銀行與晉綏西北農(nóng)民銀行合并》(1947年11月),楊世源主編:《西北農(nóng)民銀行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頁。
(四)邊區(qū)政府層面的溝通和政策的協(xié)同
商貿(mào)往來、騾馬大會及金融互助,都需要晉綏邊區(qū)和陜甘寧邊區(qū)在政府層面進(jìn)行高效溝通,并從政策方面給予制度保障。為了統(tǒng)一晉綏邊區(qū)和陜甘寧邊區(qū)的軍事指揮,中共中央軍委1942年5月13日決定在延安成立陜甘寧晉綏聯(lián)防軍司令部,以統(tǒng)一兩塊根據(jù)地的軍事行動和建軍工作。(51)《中共中央軍委關(guān)于成立陜甘寧晉綏聯(lián)防軍司令部的決定》(1942年5月13日),西北五省區(qū)編寫領(lǐng)導(dǎo)小組、中央檔案館編:《陜甘寧邊區(qū)抗日民主根據(jù)地·文獻(xiàn)卷》上冊,第241頁。八路軍120師師長賀龍任陜甘寧晉綏聯(lián)防軍司令員兼財政經(jīng)濟(jì)委員會副主任,“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陜甘寧和晉綏兩地區(qū)的軍事指揮和財政經(jīng)濟(jì)工作”。(52)喻杰:《陜甘寧邊區(qū)的貿(mào)易工作》,西北五省區(qū)編寫領(lǐng)導(dǎo)小組、中央檔案館編:《陜甘寧邊區(qū)抗日民主根據(jù)地·回憶錄卷》,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58頁。120師自抗戰(zhàn)爆發(fā)后,就開始在晉西北地區(qū)活動,并長期承擔(dān)保衛(wèi)陜甘寧邊區(qū)的任務(wù),所以由師長賀龍負(fù)責(zé)陜甘寧晉綏聯(lián)軍,自然是最合適人選,同時由其兼任財政經(jīng)濟(jì)委員會副主任,也有利于統(tǒng)籌兩地的各種力量,“這就進(jìn)一步達(dá)到對外貿(mào)易的統(tǒng)一,便利于我方價格斗爭,增加了財政收入”(53)南漢宸:《陜甘寧邊區(qū)的財經(jīng)工作》(1947年),陜甘寧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編寫組、陜西省檔案館編:《陜甘寧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35頁。,從而有助于具體工作的開展。
財政經(jīng)濟(jì)的統(tǒng)一不是一蹴而就的,包含了很多具體而且復(fù)雜的問題,邊區(qū)政府首先統(tǒng)一兩地的經(jīng)濟(jì)政策,“以確定共同努力的方向,然后依此方向,再發(fā)展成為具體的合作”。(54)《陜甘寧邊區(qū)一九四二年上半年財政報告及今后意見提綱(節(jié)錄)》(1942年),陜甘寧革命根據(jù)地工商稅收編寫組、陜西省檔案館編:《陜甘寧革命根據(jù)地工商稅收史料選編》第3冊,陜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1頁。除了前文所述兩地在物資交換的深度合作外,在稅收方面也推進(jìn)統(tǒng)一工作。1942年陜甘寧邊區(qū)和晉綏邊區(qū)為了發(fā)展雙方貿(mào)易,將雙方貨物過境稅取消,在此之后,雙方合作更加密切,步調(diào)愈加趨于一致,尤其在對敵經(jīng)濟(jì)斗爭方面,斗爭策略統(tǒng)一同步,且互相配合,“如一區(qū)允許進(jìn)口,一區(qū)禁止進(jìn)口之物資則不得由允進(jìn)區(qū)轉(zhuǎn)入禁進(jìn)區(qū),否則禁進(jìn)區(qū)得按物資管理規(guī)章及辦法處理;如允進(jìn)區(qū)需用之物資,又必須經(jīng)過禁進(jìn)區(qū)時,允進(jìn)區(qū)得托禁進(jìn)區(qū)之貿(mào)易公司代為購運,但須得保證不在禁進(jìn)區(qū)銷售。”(55)⑨《西北財經(jīng)辦事處關(guān)于陜甘寧晉綏兩邊區(qū)貿(mào)易稅收之決定》(1945年7月10日),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編寫組、山西省檔案館編:《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資料選編·金融貿(mào)易編》,第421頁。此舉就規(guī)避了敵人利用根據(jù)地之間溝通不暢的缺陷,采用迂回的辦法,向根據(jù)地傾銷奢侈品等禁止非必需品的經(jīng)濟(jì)侵略方式。同時,兩邊區(qū)還規(guī)定不同根據(jù)地之間的土產(chǎn)品互相銷售時一視同仁,“在兩區(qū)內(nèi)各地銷售,與本區(qū)之土產(chǎn)同等看待”。(56)⑨《西北財經(jīng)辦事處關(guān)于陜甘寧晉綏兩邊區(qū)貿(mào)易稅收之決定》(1945年7月10日),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編寫組、山西省檔案館編:《晉綏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資料選編·金融貿(mào)易編》,第421頁。
四、被區(qū)域分割的新民主主義經(jīng)濟(jì)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全面抗戰(zhàn)時期,晉綏邊區(qū)和陜甘寧邊區(qū)的經(jīng)濟(jì)貿(mào)易互動雖然始終在進(jìn)行著,但是受幣制的不統(tǒng)一等因素的影響,雙方在貿(mào)易上遇到的障礙也比較多。以陜甘寧邊區(qū)為例,“譬如邊區(qū)與敵區(qū)直接交換的貨物而在晉西北方面都是禁止入境的,他就不準(zhǔn)運過,這樣就交換不成,以致影響與地區(qū)的貿(mào)易。”(57)②綏德分區(qū):《貿(mào)易總結(jié)材料》(1944年3月),陜甘寧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編寫組、陜西省檔案館編:《陜甘寧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料摘編·第四編商業(yè)貿(mào)易》,第552、553頁。此外,不同根據(jù)地的本位主義、各自為政的稅收政策以及對一切貨物的極端統(tǒng)制也一度給根據(jù)地間正常的貿(mào)易帶來種種困難。1942年,隨著隸屬于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西北財經(jīng)辦事處的成立,陜甘寧邊區(qū)和晉綏邊區(qū)向著在財政經(jīng)濟(jì)上統(tǒng)一為一個整體而努力,雙方政府之間也通過系列談判達(dá)成共識,頒布了一系列有助于加強(qiáng)兩地經(jīng)貿(mào)往來的政策,并達(dá)成了形式上的統(tǒng)一,總體趨勢雖好,“實際上還有些問題沒解決(如稅收手續(xù)問題,收算歸款問題,雙方貿(mào)易配合問題等等)”。(58)②綏德分區(qū):《貿(mào)易總結(jié)材料》(1944年3月),陜甘寧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編寫組、陜西省檔案館編:《陜甘寧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jì)史料摘編·第四編商業(yè)貿(mào)易》,第552、553頁。在此過程中,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根據(jù)地經(jīng)濟(jì)建設(shè),雖受到區(qū)域的分割,也不同于十年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的形勢,但已具有新民主主義性質(zhì),“現(xiàn)在各根據(jù)地的政治,是一切贊成抗日和民主的人民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政治,其經(jīng)濟(jì)是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因素和半封建因素的經(jīng)濟(jì),其文化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此,無論就政治、經(jīng)濟(jì)或文化來看,只實行減租減息的各抗日根據(jù)地,和實行了徹底的土地革命的陜甘寧邊區(qū),同樣是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各根據(jù)地的模型推廣到全國,那時全國就成了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59)毛澤東:《關(guān)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jié)》(1941年5月8日),《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5頁。由此可知,毛澤東對于不同根據(jù)地實踐新民主主義經(jīng)濟(jì)的形式,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認(rèn)為地方根據(jù)地好的做法具備在全國推廣的價值,這也是新中國經(jīng)濟(jì)治理的雛形。問題也隨之產(chǎn)生,同樣是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根據(jù)地經(jīng)濟(jì),為什么會產(chǎn)生不同的表現(xiàn)形式?問題的核心還是在于新民主主義經(jīng)濟(jì)在空間地理的分割作用下,雖然處于同一頻率,但在相互共振過程中表現(xiàn)出的差異性。
由于根據(jù)地生產(chǎn)要素的非流動性和分布的非均勻性,一方面構(gòu)成不同區(qū)域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比較優(yōu)勢,另一方面則導(dǎo)致抗戰(zhàn)時期中共中央的宏觀經(jīng)濟(jì)政策在下達(dá)到各根據(jù)地時,因不同根據(jù)地斗爭形勢的不同以及受區(qū)域間利益關(guān)系的影響而出現(xiàn)不同的實踐模式。在戰(zhàn)時極端困難的外部環(huán)境下,根據(jù)地之間商品交易的空間障礙更多,導(dǎo)致交易成本更大,經(jīng)濟(jì)效率勢必降低,這也是根據(jù)地經(jīng)濟(jì)即使同頻卻不容易共振的原因。根據(jù)地的區(qū)域經(jīng)濟(jì)屬性,使處于同一頻率的不同根據(jù)地之間存在一種非均衡力,從而讓它們之間戰(zhàn)前單一的商貿(mào)往來形式的線性流動,升級為戰(zhàn)時經(jīng)貿(mào)、金融和政策的多維互動。在此過程中,無論是中共中央的經(jīng)濟(jì)指導(dǎo),還是根據(jù)地政府從實際出發(fā)的經(jīng)濟(jì)模式創(chuàng)新,都在不斷的共振中反復(fù)調(diào)試,進(jìn)而達(dá)到協(xié)同統(tǒng)一,從而為日后取得全國政權(quán)后的宏觀治理提供了經(jīng)驗。中央和地方良性的互動、區(qū)域經(jīng)濟(jì)政策的整合和推動、同一頻率經(jīng)濟(jì)體之間的和諧共振,對今天區(qū)域間經(jīng)濟(jì)的協(xié)同發(fā)展亦有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