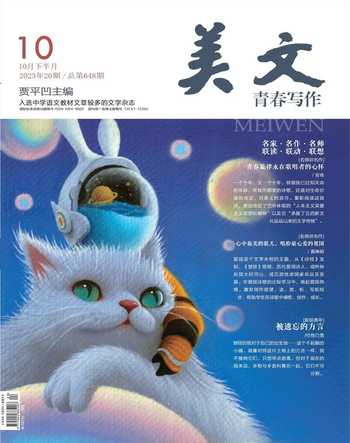主持人語
2023-10-08 02:44:46楊晨潔
美文 2023年20期
這期的兩種植物,都與人類的生活密切相關,但又在歷史的演進中,逐漸淡出人類的生活,或者還會轉換面貌以另一種姿態登場。祁云枝這次造訪驪山老母殿旁的一棵古皂角樹,與兒時記憶中“梆!梆!梆”相映襯的青石板,小溪水,捶洗的衣服,解開的長發,仿佛伴著皂角成為皂角樹旁定格的永恒畫面。如今,包裹在皂角殼里的果實不再是人們青睞的對象,被“我”長久忽視的,樹干和莖枝上粗大的皂角刺,讓“我”重新認識了皂角樹。當皂角不再提供清洗之用,可治療風痛和惡瘡的中藥的皂角刺一躍成為皂角樹的價值所在。賀蘭山的花,或者說曾經的染料、藥材——地黃是田鑫這期給我們帶來的“嘉賓”。從《詩經·采苓》到《本草綱目》《齊民要術》,地黃以各種名稱混跡于歷史,苓、芐、芑,都是對它的稱謂。而這位在古時廣受關注,名稱繁多的植物,到了科技發達的時代,卻悄悄隱匿了。除了在中藥材中還能偶爾見得它的身影,其他的染料之用,詩情畫意之功能,大多隨著過往消散了,地黃的豐富性被人為地削減。這或許在提醒面對植物的我們,切莫只貪戀對人類有益的一點,而望不見樹和花的全貌。

楊晨潔,文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八十年代文學,曾參與國家重大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獲第七屆“陜西省文藝評論獎·優秀評論獎”,并在《揚子江文學評論》《南方文壇》等刊物上發表多篇文學評論文章。
猜你喜歡
哈哈畫報(2022年4期)2022-04-19 11:11:50
大科技·百科新說(2021年6期)2021-09-12 02:37:27
英語文摘(2021年2期)2021-07-22 07:56:54
好孩子畫報(2020年5期)2020-06-27 14:08:05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6期)2019-07-24 08:13:50
少兒科學周刊·兒童版(2017年5期)2017-06-29 22:24:28
少兒科學周刊·兒童版(2017年5期)2017-06-29 16:46:33
紅領巾·萌芽(2017年5期)2017-06-23 10:35:59
爆笑show(2016年7期)2017-02-09 09:36:13
少兒科學周刊·兒童版(2015年10期)2015-11-07 03:4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