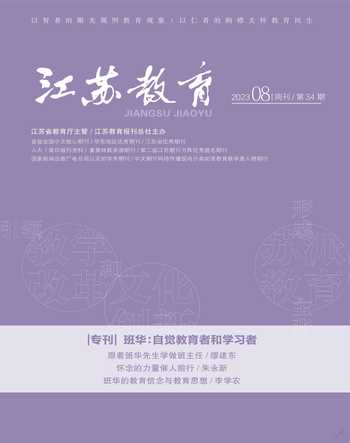為人·為師·為學
劉守旗


少時不知時光短,年長更覺時如金。因緣際會,從大學時代起,我有幸跟隨先生學習,后碩士,再博士,加之同處一城聯系方便,在長達40年的時間里,先生的許多研究活動我多有參與,受益受惠于先生的關心教誨更多。先生是教育大家,更是一位值得尊敬和學習的師長。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教育學,首先是人學。先生不僅學問高深,涉獵領域廣泛,更重要的是,他注重以身立教、為師以德,其本身就是一本打開了的厚重教育學。
為人:“掛名的事,
我從來不做”
2003年,先生受人民教育出版社所邀,擔任基礎教育義務教育階段七到九年級《思想品德》教材的總主編。在教材編寫過程中,因編寫理念不同,在一些問題上產生分歧是難免的。有一次因一個學術觀點問題,經多次溝通,雙方仍未能達成一致。一天一大早,出版社打來電話溝通,但溝通并不順暢,這時對方說了一句也許是實話但卻令先生非常反感的話。意思是請先生擔任主編,主要是看重先生的學術聲望,希望先生不要過于較真。誰知聽對方這么一說,在一旁的我發現先生非常生氣,立馬不客氣地責問對方:“請問這是您個人的想法,還是你們社里的想法?”對方可能從語氣上也覺察到了先生的不滿,馬上說:“班老請您息怒,這純粹是我個人想法。”聽對方這么說,先生也語氣稍緩地說:“您這么說我不同您計較,但我可以明確地告訴您,掛名的事,我從來不做。”說實話,與先生接觸近40年,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先生發火。就憑這句話,我覺得當年選擇先生做導師,真是選對了!
是的,先生不僅正直,而且非常和藹可親。眾所周知,研究生實行導師制,學生們常會以導師的姓來稱呼“某門”或“某門弟子”。很自然地,我們常被稱為“班門”或“班門弟子”。相對來說,我們師門內部的活動會多一些,這讓其他師門的人非常羨慕,每次聽到其他人羨慕的話語時,那種身為“班門”弟子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見圖1)。
為師:“訓練和讀研,
只能二選一”
人生是由許許多多個偶然所組成。當然,從哲學上講,偶然中蘊含著必然。1987年,我陪同學去報考研究生時,這個喜歡開玩笑的同學用拋硬幣的方法讓我也跟著報了名。有趣的是,我竟然還考上了。當時我報的是心理學而非教育學,只是因為當年報考教育學的學生全軍覆沒,黎光和、李偉、周桃平、連思源和我,分別被從其他學校或其他專業調劑到了教育學專業。當年招生簡章里的導師共有3人,分別是魯潔、丁沅和班華,一共招5人。入學后不久,魯潔先生召集我們開會選導師,黎光和、李偉選了魯先生,我、周桃平、連思源選了班先生,丁先生因為有研究生,當年就沒再帶。至今我依然非常清晰地記得,在魯先生說完后,我第一個毫不猶豫地選了班先生。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我對先生相對熟悉和了解一些。一是大學時先生教我們《教育學》;二是逢年過節先生總會到我們學生宿舍來走走看看,和大家聊聊天、敘敘家常,總感覺先生平易近人、和藹可親。
因材施教、尊重熱愛與嚴格要求相結合,是教育學上兩個最重要的原則。大學期間,我的短跑成績尚可,研究生入學后不久,有幸入選校田徑集訓隊,備戰當年的全國大學生運動會。作為集訓隊一員,加班加點訓練是常事。一天下午,正在訓練的我無意中發現先生站在操場邊。我以為他找我有事,就跑了過去。先生面帶笑容地說:“守旗,你參加大學生運動會訓練我不反對,但在訓練和讀研之間只能二選一,你考慮一下,不必現在就回答我。”聽后,我幾乎沒做任何思考,立馬回答說還是讀研究生。之所以很爽快地回答,一是我知道即便堅持刻苦訓練,以我當時的成績,參加大運會估計也僅是陪跑而已;二是先生的期許,我們這一屆是先生第一次帶研究生,他當然希望我們能夠心無旁騖地學習。后來,我們確實也沒讓先生失望,都以較優異的成績順利畢業了。如今想想,先生因材施教、尊重熱愛與嚴格要求相結合的原則,運用得可謂爐火純青、恰到好處。俗話說“嚴師出高徒”。雖然我算不上高徒,但先生是嚴師,這是毋庸置疑的,何況先生門下確實還是出了不少高徒的。
“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這是大學畢業時先生給我的畢業贈言(見圖2)。這句名言,源自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先生用這句話相贈,其用意可謂良苦。在他看來,學生尊敬和愛戴老師是必須的,但在對老師的尊敬愛戴與追求真理發生矛盾沖突時,我們更應高舉追求真理的大旗。與先生相處越久,我對這句贈言體會愈深。
為學:“研究應該走在發展的前面”
作為一位學者,先生一生中提出了許多獨創性的概念或命題,如品德能力、隱性課程與德育、個性教育、班主任等。當然,有些概念或命題并不是一開始就能夠為學界所接受。比如,心育問題提出后,質疑聲不斷。有人質疑它的可行性,如“心”能否教育,“心”是不是教育對象,心理怎么可以教育,意志、情感怎么教育,價值教育與心理教育要融合嗎,怎么融合?有人質疑它的超前性,認為“心理教育對農村學校說太奢侈了,不可能實施,好比我們都是穿草鞋的,你要在草鞋上繡花,這是不可能的”。更有人質疑它的科學性。有代表性的是2007年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上發表的《“心理教育”質疑——簡論“心理健康教育”的邏輯悖論》,文章說心理教育“沒有定義”“是一個虛假命題,存在著嚴重的邏輯悖論”等。對這些質疑,先生并沒有簡單地予以否定,而是通過學術探討或商榷的方式進行了回答。如對心理教育太過超前的看法,先生認為:“這位老師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不僅農村,即使城市的學校也不是都有條件實施心理教育的。但我認為這并不意味著心理教育沒有意義,以后有了條件總是可以實施的。” 對心理教育“沒有定義”“是一個虛假命題,存在著嚴重的邏輯悖論”的質疑,他說:“本人提供的定義不能被認可,還有其他更多的人提供了定義,絕不是‘沒有定義’。”在列舉了國內外眾多學者的研究成果后,先生說:“不知以上這些著述有無心理教育定義,有哪些‘邏輯悖論’?能否回答心理系教授質疑的問題?”
先生一生中之所以能夠提出許多獨創性的概念或命題,與他的“研究應該走在發展的前面”的理念密切相關。1998年秋天,我有幸進入母校讀博。自入學起,我就認真思考博士論文的選題問題。后經與先生商量,決定研究網絡社會的兒童道德教育問題。次年5月借擔任陳佑清博士論文答辯秘書的機會,我又請教了前輩專家,得到肯定。后陪先生在揚州梅嶺小學聽取課題匯報時,學校提及學生網上交友問題,更加堅定了我的想法。但是,在開題時有專家明確指出:“目前在我們國家研究這一問題為時過早!”怎么辦?專家意見聽不聽?最終,還是先生一錘定的音。他認為,“研究應該走在發展的前面,具有超前意識,富有挑戰性”。先生的鼓勵對我論文選題的確定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最后我的論文順利通過答辯,出版后還獲第三屆全國教育科學優秀成果獎三等獎的榮譽。我想,這既是對我個人的褒獎,又是對先生“研究應該走在發展的前面”理念的肯定。
“一個人遇到好老師是人生的幸運。”作為人生的幸運者,我對習近平總書記的這句話,體會尤深。
(作者系江蘇第二師范學院教授,江蘇省教育學會心理教育專業委員會名譽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