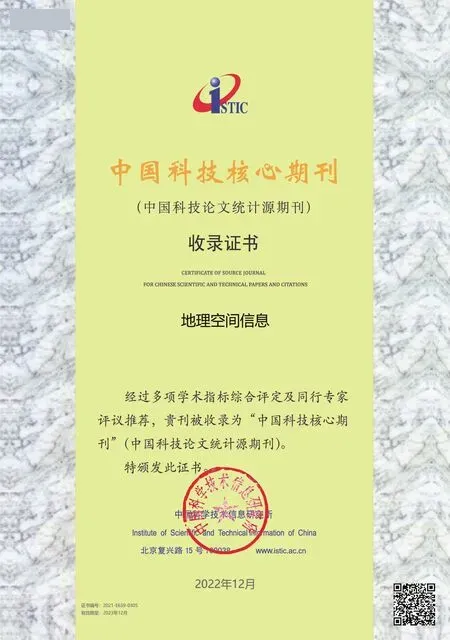1992 年以來貝加爾湖湖區水位變化特征分析
楊佳儀,周佳軒,吳紅波,2,3*
(1.陜西理工大學 地理科學系,陜西 漢中 723000;2.西北大學 陜西省地表系統與環境承載力重點實驗室,陜西 西安 710127;3.中國科學院 青藏高原地球科學卓越創新中心,北京 100101)
作為歐亞大陸最大淡水湖,貝加爾湖的水位變化受自然和人類活動的共同影響,在全球變暖背景下,其水位升降對維系流域生態系統與社會發展至關重要[1]。由于流域范圍跨度大,受較大空間尺度的降水和氣溫影響較明顯,在過去50年貝加爾湖流域已成為全球升溫速率較快的區域之一[2],而地表氣溫升高將直接影響湖面水位、水儲量、入湖徑流量等變化[3],因此貝加爾湖是研究湖泊水文要素的理想場所。衛星測高是利用衛星、航天飛機等運載平臺攜帶的激光、雷達測高儀測定搭載平臺到陸地表面、瞬時海平面、湖水面[4]、水庫表面等垂直距離的技術和方法。隨著衛星遙感技術的進步和發展,衛星測高技術利用各類測高儀實時測量衛星平臺到地表面的高度、后向散射系數、風速和波高等參數[5],開展了大地測量學、地球物理學、水文學和海洋學研究。與傳統水文觀測方法相比,衛星測高技術可近實時、較大空間尺度地監測湖泊水域、濕地、水庫的水面高度變化[6],降低了人力、物力和財力成本。
王冠[7]等指出1900 年以來,貝加爾湖水位變化由自然和人類共同作用引起,并直接影響著湖泊水量變化及其周邊生態環境;宋桂英[8]等分析發現2012年7月貝加爾湖流域低渦異于常年,擾動對流層高層大氣,導致7月下旬內蒙古高原極端降水事件的發生;李想[9]等指出近40年來貝加爾湖區水位整體呈先升后降的態勢,并將貝加爾湖水位升降轉折歸因為氣候變化驅動型、氣候變化與人類活動共同驅動型和氣候變化下的人為調控驅動型3 種類型;孟國杰[10]等認為貝加爾湖地區地質層處于膨脹狀態和近西北方向的拉張狀態,水位變化僅是新生代以來地殼運動的延續。為分析貝加爾湖水域水位的時變特征,楊小東[11]等借助衛星測高技術分析貝加爾湖水位的年內變化特征發現,每年7、8月水位上升到最高值,隨后下降,次年5月為最低水位;李靜[12]等利用重心偏移法與子波形提取法的波形重定技術分析得出,2009—2012年貝加爾湖年際水位異常時間序列具有較強的正相關性和較顯著的周期性變化,夏、秋季水位高,冬、春季水位低。上述研究總體上對貝加爾湖水域的水位時間特征和空間特征描述不足,且目前對貝加爾湖水位變化的人為活動干擾和氣候要素變化響應[13],已鮮有相關報道[14]。因此,本文利用ICESat-1、ICESat-2 衛星測高資料以及Hydroweb、Legos 水位數據,分析了貝加爾湖1992—2022年湖區水位變化的年內和年際特征;并利用趨勢面和線性回歸分析,提取了2018 年10 月—2021 年10月貝加爾湖水位的空間變化特征,旨在為貝加爾湖水儲量變化、生態環境保護、人工調水等研究提供理論參考和案例借鑒。
根據流行病學調查,泔水喂豬是傳播非洲豬瘟的重要原因。因非洲豬瘟病毒可在泔水中長時間存活,禁止使用泔水喂豬對阻斷疫病傳播起到關鍵作用。同時據檢測表明,泔水中還含有其它許多致病性細菌,對環境和人畜健康均構成嚴重威脅,故使用泔水喂豬存在諸多安全隱患。
1 研究數據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貝加爾湖地處俄羅斯布里亞特共和國和伊爾庫茨克州境內,范圍為51°29′~55°46′N、103°41′~109°57′E,屬于地震斷層陷落型湖泊,周邊山脈海拔均在1 000 m以上。貝加爾湖為東北—西南走向,狹長彎曲呈新月形,長636 km,東西向平均寬度為48.0 km,水域面積為3.15 萬km2,水系流域面積為56.0萬km2;總容積為23.6 億m3(2015 年),平均水深為730 m,最深處達1 637 m(2015年),是全球蓄水量最大、深度最深的湖泊,湖水通過安加拉河向北匯入葉尼塞河,最終流入北冰洋;屬溫帶大陸性氣候,氣溫日較差、年較差大,1 月均氣溫為-26~-33℃,7 月平均氣溫為17~21℃,年降水量的一半以上發生在夏季(6—8 月),位于上游的色楞格河、巴爾古津河、上安加拉河的徑流補給貝加爾湖的湖水。
1.2 研究數據
本文采用2003-10-22—2009-10-11 的ICESat-1/GLAS 測高產品GLA01 和GLA14 重建貝加爾湖湖區水位的時間變化序列。GLA01、GLA14 的產品格式為HDF 5.0,數據發布版本為V34[15],從美國國家冰雪數據中心網站(URL:https://search.earthdata.nasa.gov/search)獲取,并提取湖區光斑的經度、緯度、高程、大地水準高度等參數信息。ICESat-2 衛星于2018-09-15在美國范登堡空軍基地發射成功,其搭載的ATLAS 激光測高儀采用綠色波段532 nm 處激光脈沖和單光子敏感探測器來測量地表空間信息[16]。ATLAS 測高儀采用3 對光束,每對軌道約間隔3 km,間距約為90 m;每束脈沖在地表形成的光斑直徑為17 m,沿軌道采樣間隔為0.7 m。ICESat-2 衛星約重155 kg,ATLAS測高儀每秒向地表發射10 000個激光脈沖,激光脈沖3.3 ms 即可到達地球表面并返回。ATL13 產品主要用于湖泊、河流、水庫等水位估計[17],本文采用2018-10-14—2022-04-22的ATL13中的6束測高脈沖提取貝加爾湖水面高程。1992年9月—2022 年4 月Hydroweb 水位日志記錄數據可從URL:https://hydroweb.theia-land.fr/申請獲取。1992 年9 月—2010 年9 月貝加爾湖Legos 水位記錄從法國地球物理學和海洋學太空觀測研究中心實驗室網站(URL:http://www.legos.obs-mip.fr/en/soa/)獲取,包括日期、日均水位和偏差。1992—2021年位于安加拉河上游的伊爾庫茨克水文站水位觀測資料來源于俄羅斯聯邦自然資源與環境部的《貝加爾湖狀態及保護措施》年度報告(2003—2017 年報告網址URL:http://geol.irk.ru/baikal/activ/mactiv2003、2012—2021 年 報 告 網 址URL:http://www.baikalake.ru/en/security/info)。
1.3 技術路線
首先對ICESat-1、ICESat-2 衛星測高產品中異常水位進行粗差剔除,利用貝加爾湖流域湖泊水域邊界和湖區激光脈沖的經度、緯度等數據進行掩膜化,并將激光腳點位置與高程參考系統地理配準后,提取湖區內ICESat-1和ICESat-2衛星的星下點和有效水位信息;然后結合1992—2022 年貝加爾湖的Hydroweb 水位、Legos 水位、水文站觀測等數據,驗證ICESat-1、ICESat-2衛星瞬時水位的估計誤差,并重建湖區水位的時變序列;最后根據湖區日均、月均和年均水位特征,借助趨勢面和線性回歸分析,分析1992—2022年貝加爾湖水位變化率、趨勢和空間異質性。
1.4 衛星測高數據估計湖泊水位的方法
2001年以前,貝加爾湖的水位按照《安加拉河梯級水電站水庫水資源利用條例》進行調蓄。俄羅斯聯邦政府于2001-03-26 頒布的第234號文件決定[21],將貝加爾湖的可調節庫容范圍限制在1 m之內,即由正常蓄水位457.00 m 調節至該湖極限消落水位456.00 m。1992年以來貝加爾湖水域日均水位曲線見圖2,可以看出,1992—2022年貝加爾湖水域日均水位總體呈上升趨勢,2018—2022年受下游水電站調蓄影響,湖泊日均水位波動較小;1992-01-13—2002-01-13日均水位變化幅度較大,為0.20±0.21 m,受自然氣候變化影響較大;2002-01-13—2022-01-13日均水位變化幅度減小,為0.12±0.09 m。與伊爾庫茨克水文站觀測的日均水位相比,ICESat-1、ICESat-2 測高數據估計的日均水位絕對RMSE分別為0.18±0.08 m和0.08±0.06 m。
激光雷達測高儀的脈沖信號是從與有效波高和風速有關的平面反射的,受軌道誤差、大氣總質量、水蒸氣含量等影響,必須對其進行相應改正。
式中,hd為湖盆地形變化值;為某時段內湖盆地形變化均值;hg為大地水準面高程;為某時段內大地水準面高程均值;ei為第i個隨機誤差;為某時段內誤差均值。
數字人文研究是一種新的文獻打開、查詢、呈現方式。數字人文最受人文學者青睞之處在于數字技術與人文領域的緊密融合。數字技術應用到史學,最典型的是將實體文獻掃描為數字化,最直接的體現是數據庫建設和史料數字化。并通過數據庫來集中揭示,可以讓你了解數字技術對人文學科或你的特定項目能起到什么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式中,halt,lake為EGM2008重力位模型下的湖泊水面高程,單位為m;a為斜率;b為高程偏移常數,單位為m。
式中,Hlake為湖泊水位高度,即貝加爾湖湖面相對于參考橢球的高度;Halt為衛星質心相對于參考橢球體表面的距離;Hran為衛星距離貝加爾湖面的距離;Hgeoid為大地水準面高程差值;Hcor為各類誤差校正;ICESat-1 衛星的參考橢球體與ICESat-2 衛星相同,需轉換到統一高程坐標系。
式中,e為參考橢球體的偏心率;ha為測高儀估計的瞬時湖泊水面高度;r為衛星的地心距;rp為衛星星下點的地心距;δhi為瞬時海面和似靜海面之間的高差;δhs為似靜海面至大地水準面的差距;φ為地理緯度;N為大地水準面高度。
式中,wtc為濕對流校正;dtc為干對流校正;ic為電離層校正;setc為固體潮校正;ptc為極潮校正。
對于環境要素(見圖1),事件e2的發生地點同時也是事件e3和事件e4的發生地點,這時就要在事件e2的環境要素屬性lid中進行標注.
確定ICESat-1、ICESat-2衛星高度和激光脈沖往返于衛星與貝加爾湖水面的傳播時間,即可確定衛星到貝加爾湖面的距離、風速、有效波高等參數。ICESat-1、ICESat-2衛星測高數據估計湖泊水面高度的公式為:
測高儀的激光脈沖在湖泊水面的航跡其實是湖區水面高程的輪廓線[19],該航跡覆蓋區可能包含湖面設施、漂浮物、湖岸的雜草等,因此應剔除異常最大、最小值,則湖泊水位均值為:
湖面高程異常變化被定義為任一時段內湖面高程與平均湖面高程的高度差,即
總之,充分發揮退役復學高職生的作用,讓他們參與學校教育管理,不僅可以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教育管理貫穿于高職生日常生活,使學生受到潤物細無聲式的教育、引導和熏陶,而且能使退役復學高職生在參與管理的過程中得到鍛煉,實現自身價值并增強自信。
ICESat-1和ICESat-2測高儀的激光脈沖在地表或水域表面形成近似橢圓形的光斑,光斑腳點的高程偏差主要由配準誤差、地形誤差和系統誤差等導致[20]。均方根誤差(RMSE)是指參數估計值與參數真值之差平方的期望值,常用于衡量觀測值與估計值之間的偏差。貝加爾湖湖區日均水位的RMSE為:
由于衛星測高儀在測量過程中,光學信號會受外部環境、地球物理變化等影響[18],產生不同程度的水平位移和高度偏差,本文參考1992年9月的平均水位值對不同時段內ICESat-1和ICESat-2衛星激光光斑估計的水位值進行線性修正,即
式中,為修正后的湖泊水位估計值;為任一時段內湖面水位均值;n為湖區內航跡覆蓋區內激光光斑數量。
2 研究結果與分析
2.1 湖泊水位的驗證與對比
由于ICESat-2 衛星測高數據的空間分布不均勻,為描述ICESat-2估計的日均水位與Hydroweb水位記錄之間的偏差,本文對ICESat-2衛星的瞬時水位做平滑處理(圖1),可以看出,2018 年10 月—2021 年12 月ICESat-2估計的貝加爾湖日均水位與Hydroweb水位記錄存在一定系統性偏差,絕對誤差為0.34±0.08 m,ICESat-2估計的水位略高于Hydroweb水位,但具有相同的周期變化規律,擬合曲線峰谷節點較一致;日均水位的最高值出現在9月底—10月初,最低值大多出現在4 月或5 月,與伊爾庫茨克站日均水位觀測值和ICESat-2衛星估計的日均水位時間節點一致。

圖1 2018年10月—2021年12月貝加爾湖湖區日均水位曲線
2.2 貝加爾湖水域日均水位變化
衛星測高原理的基本關系式為:

圖2 1992—2022年貝加爾湖水域日均水位變化
2.3 貝加爾湖水域水位月均變化
基于Hydroweb、ICESat-1、ICESat-2 衛星的月均水位估計值,本文對Hydroweb月均水位進行線性擬合(圖3),可以看出,1992—2022 年貝加爾湖水域月均水位出現了3次較低水位,分別為1997年2月的454.69 m、2016年2月的454.75 m、2018年4月的454.84 m;月均水位總體略有上升,為0.14±0.10 m;2018—2022年月均水位波幅增大,增加了0.35±0.06m;月均水位變化具有顯著的季節性,春季(3—5月)水位偏低、夏季(6—8月)上升、秋季(9—11月)水位處于較高值、冬季(12月—次年2月)水位下降,且月均水位波動幅度較小。ICESat-1、ICESat-2衛星測高儀激光光斑在湖區覆蓋范圍具有代表性差異,月均水位的絕對RMSE分別為0.13±0.12 m和0.05±0.06 m。

圖3 1992—2022年貝加爾湖水域月均水位變化
2.4 貝加爾湖水域水位年均變化
本文利用Hydroweb 水位記錄、ICESat-1 和ICESat-2 測高數據重建貝加爾湖水域的年均水位時變序列(圖4),可以看出,1992—2022年貝加爾湖年均水位總體呈上升趨勢,共上升了0.13±0.15 m;由于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的共同影響,1992—1997年年均水位大幅下降0.56±0.12 m;1997—2004年年均水位呈上升趨勢,上升了0.42±0.13 m;2004—2017 年年均水位呈下降趨勢,下降了0.42±0.15 m;2017—2021年受人工調蓄影響,年均水位上升了0.63±0.10 m。ICESat-1、ICESat-2測高數據估計的年均水位與Hydroweb年均水位的變化趨勢一致,RMSE分別為0.13±0.06 m和0.07±0.04 m。

圖4 1992—2022年貝加爾湖水域年均水位變化
2.5 年均水位變化的空間異質性
本文利用2018 年10 月—2021 年11 月貝加爾湖的ICESat-2衛星測高數據,借助流體靜力學平衡和湖區水位高度異常計算,得到2018—2021年貝加爾湖的年均水位變化率(圖5),可以看出,貝加爾湖水位變化存在空間異常和速率差異,湖區東段的年均水位上升趨勢明顯,湖區西段的年均水位上升較弱,主要是由于典型西北風風況下的水位變化和三維流場分布特征,湖區科氏力作用明顯,有增減水的現象,表層水流主流由北向南,橫剖面上存在順時針方向的垂向環流[22]。

圖5 2018—2021年貝加爾湖水域年均水位的變化率
3 結語
1)由于較大水域湖泊水位變化的隨機性、動態性、空間異質性和動力學特征,使得在較長時間尺度上同步觀測較困難,因此空間數據質量和時間不連續一直是研究湖泊水文、流體動力學特征的障礙。本文借助Hydroweb、水文站和ICESat-1、ICESat-2 星載測高儀資料快速重建了貝加爾湖水位變化序列,方法簡單易行,不僅使衛星測高數據在時間維度的變化表達可信度較高,而且在空間維度上從二維轉向三維,使高空間分辨率更加細化描述水位變化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高管內部薪酬差距、高管與員工薪酬差距與公司績效的關系 ………………………… 劉春旭,丁 鵬(5.22)
2)ICESat-1、ICESat-2測高數據在空間覆蓋代表性和水位估計精度方面能有效提取湖泊水位變化特征信息。與伊爾庫茨克水文站觀測的日均水位相比,ICESat-1、ICESat-2 測高數據估計的貝加爾湖水域日均水位的絕對RMSE 分別為0.18±0.08 m、0.08±0.06 m。
“兩個出剪刀的人當中,有一個立刻意識到自己干了件超級大蠢事,當下便說他沒臉再待在心理社了,于是退社。”秀珊學姐說。
積極落實地方機構和編制,進一步明確業務安全管理職責,開展管理人員培訓,加強安防系統建設,為現代化人影服務提供保障。
3)1992 年以來貝加爾湖的年均水位總體呈上升趨勢,且東部水域年均水位上升速率大于西部水域。1992—2022年年均水位上升了0.13±0.15 m,變化幅度小于1 m。此外,貝加爾湖的月均水位出現了3次較低水位:1997 年2 月的454.69 m、2016 年2 月的454.75 m、2018年4月的454.84 m。
4)貝加爾湖的日均和月均水位波動在時間和空間上表現出異質性,既有人類活動的干擾,也有自然氣候變化的影響。1992—2017年貝加爾湖的日均、月均水位波動具有一定隨機性,而2018—2022年湖區的月均、年均水位波動具有明顯的季節性和周期性,位于安加拉河上游的伊爾庫茨克水電站的水位調蓄作用使湖區水位的波動幅度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