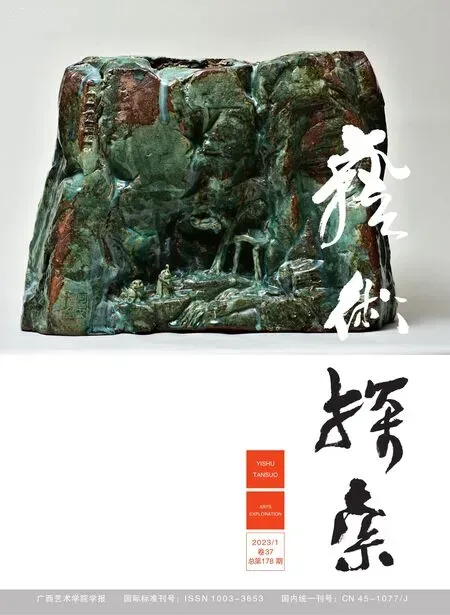臧懋循改評當朝傳奇“當行”論
伊崇喆 楊緒容
(1,2.上海大學 文學院,上海 200444)
臧懋循晚年四處訪書,開辦“雕蟲館”,專門從事圖書出版、刻印。因坊間雜劇版本駁雜,他特從麻城劉延禧處“得抄本雜劇三百余種”,而細加勘校,“摘其佳者若干,以甲乙厘成十集”,于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編成《元曲選》百卷。[1]4648他自謂“頗得元人三昧”[2]624,并期待“使今之為南者知有所取”[3]621。此后臧氏先后改評湯顯祖《玉茗堂傳奇》、屠隆《曇花記》等五部當朝傳奇,意欲為當朝傳奇作品樹立“當行”之標桿。
一、臧懋循改評當朝傳奇的意圖與標準
以湯顯祖《牡丹亭》為代表的《玉茗堂傳奇》甫一脫稿,便產生很大影響,如沈德符說:“《牡丹亭夢》一出,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4]206,王思任說:“(《牡丹亭》)至其傳奇靈洞,散活尖酸,史因子用,元以古行,筆筆風來,層層空到。即若士自謂一生四夢,得意處惟在《牡丹》”[5]。然而也有不同的聲音,如臧懋循以《玉茗堂傳奇》為“案頭之曲,非筵上之曲”,且“曲每失韻,白多冗詞”,恐“為元人所笑”,乃在一病之后將“一切圖史悉已謝棄,閑取《四記》,為之反覆刪訂”,以期使“《玉茗堂傳奇》與王實甫《西廂》諸劇并傳樂府”。[6]622-623湯顯祖逝世后的第二年,臧氏改評《玉茗堂傳奇》成。后又改評屠隆《曇花記》。他認為,屠隆《曇花記》不僅“加損”“唱法、做法”①本文所引批語,皆出自湯顯祖撰、臧懋循改評《玉茗堂新詞四種》,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雕蟲館刊本;屠隆撰、臧懋循改評《曇花記》,日本內閣文庫藏明代萬歷年間朱墨套印本。,還存在“音律未甚葉,于搬演未甚當行”,故“暇日取而刪定為正論”,打造出一部重要而至今少為人知的傳奇改評本②如:傅惜華《明代傳奇全目》一書,只收錄屠隆《曇花記》,而未在臧懋循名下錄該本;俞為民、孫蓉蓉合編《歷代曲話匯編:新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明代編)》及《中國古代戲曲理論史通論》亦未提及該本。關于此評點本,請參見筆者《臧懋循改評〈曇花記〉的思想藝術價值論》,《藝術探索》2021年第35卷第6期。。
臧氏通過改評當朝名家名作,表達了獨特的戲曲批評意識。臧氏編選《元曲選》,自謂得“元人三昧”,對當朝南戲作家頗為不滿,認為當朝南戲作品成就遠不如元:“今南戲盛行于世,無不人人自謂作者,而不知其去元人遠也”[3]620。緣何南戲成就遠不如元代?臧氏認為,關鍵在于不夠“當行”。臧氏將戲曲作家分為兩類:一為“名家”,二為“行家”。名家指當下“文彩爛然”[3]621的文人作家;而“行家”則指關漢卿一類能夠“躬踐排場,面傅粉墨,以為我家生活”,“隨所妝演,不無模擬曲盡,宛若身當其處”,[3]620-621熟悉表演,語言自然的作家。臧氏認為,戲曲作家要先親自登臺表演,深諳舞臺表演的現場體驗,如此才能創作出“當行”的“上乘之曲”[3]621。由此可見,臧氏以“當行”為戲曲批評的主要標準。
在明代戲曲批評中,“當行”時常與“本色”并舉,但在元代之前,未見二者用于戲曲批評領域中。王驥德《曲律》說:“當行本色之說,非始于元,亦非始于曲,蓋本宋嚴羽滄浪之說詩。”[7]152實際上,比嚴羽更早將“本色”用在文學批評領域的是劉勰。劉勰《文心雕龍·詮賦篇》曰:“文雖雜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乃指賦體語言不能“膏腴害骨”[8]47;宋代嚴羽《滄浪詩話》首次將“本色”“當行”的概念引入詩詞批評中[9]81,《滄浪詩話·詩辨篇》曰:“惟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強調做詩要學“盛唐詩人惟在興趣”。[10]12“本色”與“當行” 的概念被引入戲曲批評中后,各家觀念不同,爭議較大。李開先將戲曲概括為“詞人之詞”和“文人之詞”,以“本色者為詞人之詞”。他要求戲曲家創作以“金、元為準”,語言通俗而不俚俗。[11]412徐渭曰:“語人要緊處,不可著一毫脂粉,越俗、越家常、越警醒,此才是好水碓,不雜一毫糠衣,真本色。”[12]243可見一些評論家只重“本色”,而不論“當行”。何良俊認為:“《西廂》全帶脂粉,《琵琶》專弄學問”,故而“本色語少”[13]462-463,強調填詞要“用本色語,方是作家”[14]6,以《拜月亭記》為“本色”之作,贊其“其才藻雖不及高,然終是當行”[13]470。何良俊雖論及“當行”,但大多是針對戲曲語言而談的。臧氏雖也提及“本色”,但在戲曲批評中著重強調“當行”,使“當行”與“本色”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15]31。在何良俊的基礎上,臧氏進一步發展,將“當行”發展為一種以舞臺表演為核心的理論,使其外延更加廣闊。從這個方面來說,臧氏改本《玉茗堂傳奇》及《曇花記》相較于其他明代戲曲評點本更具代表性和現實性。
臧氏未見有戲曲批評專論,其《元曲選序》《元曲選后集序》及評改《玉茗堂傳奇》和《曇花記》的序文和批語就顯得特別重要。通過這些批語和序文,我們可以大致了解其有關“當行”的戲曲批評理論觀念及其在明代傳奇中的具體貫徹。臧氏對“當行”的要求主要有四:一是曲調“諧葉”;二是語言“穩稱”;三是關目“緊湊”;四是表演要有“做法”。他提出“當行”論,是為了將當朝傳奇作品搬上舞臺,并希望啟迪當朝的南戲作家,以創作出真正適合舞臺表演的南戲作品。
二、音律要“諧葉”
臧氏“怪今之為曲者,南與北聲調雖異,而過宮下韻一也。自高則誠《琵琶》首為‘不尋宮數調’之說,以掩覆其短”[16]619。臧氏所謂之“短”,即指當下南戲作家不熟音律以至“失韻”[6]622-623。他崇尚北曲,批評當下南戲作家如汪道昆造曲駢儷,徐文長又淺俗近鄙。湯顯祖譜曲雖較近元人,但因其“生不踏吳門,學未窺音律。艷往哲之聲名,逞汗漫之詞藻,局故鄉之聞見,按亡節之弦歌”[6]623,“音韻少諧,不無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之病”[16]619,以致“往往乖謬”“面目愈離”[3]621,為“元人所笑”[6]622。又批評《曇花記》,或“音律未甚諧葉”,或“終折無一曲”[16]619,認為音律“諧葉”是作曲的“一大難”[3]619。
臧氏在改評《玉茗堂傳奇》和《曇花記》時,對原作不諧音律的曲調做了大量改訂。據統計,原作《牡丹亭》共有曲403支,臧氏改訂后余195支;[17]44原作《南柯記》共有曲308支,臧氏改訂后余212支;[18]17臧改本《曇花記》增曲12支,刪曲50支,改曲41支,共改訂103支。[19]99臧氏對原作曲調的改訂,出于兩個方面:一是使曲調“諧葉”;二是使曲白協調,以調劑冷熱,提高舞臺表現力。
首先,臧氏崇尚“元人三昧”,強調音律“諧葉”。他要求曲家“精審于字之陰陽,韻之平仄”,不得以“吳儂強效傖父喉吻”。[3]620他在評改當朝五部傳奇時,刪改大量不諧葉的曲調。如原本《紫釵記·赴洛》出有旦獨唱【貓兒墜】曲,臧氏批云:“ 【貓兒墜】曲,無一句入調者,或謂予好改竄以掩人美,亦惟臨川能諒之”,改為【琥珀貓兒墜】曲,并令生、旦合唱:“(旦唱)渭河春水,偏不駐蘭橈。多少愁心付柳條,只為功名兩字苦相拋。(合唱)英豪,準望你脫卻藍袍,換了紫袍”;又如屠隆原作《曇花記·公子尋親》出,有【二郎神】曲,臧氏批云:“原本‘知些’‘因依’二句不葉,故改之”,改為:“ 【前腔】(小生唱)悲啼,逢人借問說,南游湘澧。衡岳峰頭捫只履,又聞公相,天然道骨仙姿。門外時時到云水,儻萬一知些因依,尋消息,沒奈何來叩階墀”,使“儻萬一知些來歷,問因依”葉韻而更有余味。臧氏批評當下南戲作家時常改變曲調格律,使得曲調不協調,他對原作曲調的修改,大多出于音律葉韻考慮,以求“悅人耳”[3]620。
其次,《玉茗堂傳奇》及《曇花記》有的終折無曲,有的賓白過多而曲白不協調,在舞臺上冷熱不均。如原本《曇花記》第三出《祖師說法》,整場只白無曲,臧氏眉批云:“終折無曲,幾于冷淡”,故特增【清江引】一曲,以調劑冷熱;第三十一出《卓錫地府》,由小生、生、末、外四腳互問互答,情節枯燥無味,臧氏于此出增【香柳娘】四曲③此四曲原本在《奸相造謀》出,因臧氏刪改關目,故將此四曲并入該折。、【懶畫眉】二曲,眉批云:“原本無【香柳娘】四曲,俱增”,“此二曲必不可少,若原本則終折無曲矣”。又如《邯鄲記·望幸》折,臧氏批云:“原本驛丞白幾千言,甚惡,盡削之”。臧氏贊揚《西廂記》:“白少可見,尤不欲多駢偶”[3]619,即是說創作戲曲當如《西廂記》,賓白不宜過多,而使曲白協調,注重表演時的舞臺效果。
三、語言要“穩稱”
臧氏云:“曲本詞而不盡取材焉,如六經語、子史語、二藏語、稗官野乘語,無所不供其采掇。而要歸于斷章取義,雅俗兼收,串合無痕,乃悅人耳,此則情詞穩稱之難”。[3]620臧氏認為,元雜劇語言之妙在“其精者采之樂府,而粗者雜以方言”[16]619。他批評徐渭“雜出鄉語,其失也鄙”,又道汪道昆等人“純作綺語,其失也靡”。[3]620臧氏批評戲曲“當行”,首先要求戲曲語言要“雅俗兼收”。如《曇花記》,《郊游點化》折有【節節高】曲:“(外)抱負了經綸,經綸才調。只不曾悟禪,悟禪開道。偌大英雄,正好得意時無常來到。別了夫人,拋了愛妾,將兒孫撇掉。舍了金寶,丟了第宅,辭了圣朝,獨自個苦伶仃黃泉路杳”,臧氏批云:“【節節高】語言淺近,極是當行”;《夫人內修》折,臧氏批【簇御林】二曲云:“【簇御林】二曲亦穩妥”;《尼僧說法》折有【一江風】二曲,臧氏批云:“ 【一江風】二曲是尋常語,妙在不迂不俗之間”;《義仆遇主》折有凈腳唱【二郎神】,臧氏批云:“凈色曲不必太文,妙在當行耳,以后曲得之”。臧氏贊賞戲曲的語言既不過俗,也不過于靡麗,既不至于使人厭惡,又能令下層百姓聽得懂。
另,“宇內貴賤、妍媸、離合之故,奚啻千百其狀!而填詞者必須人習其方言,事肖其本色”[3]620。臧氏要求戲曲作家熟悉生活和舞臺,戲曲語言要符合人物性格,更要符合現實生活和舞臺表演的邏輯。從舞臺表演方面來看,臧氏之“本色”實是其“當行”論的一個側面。如《邯鄲記·織恨》折有旦、貼唱【漁家傲】:“(旦)機房靜,織婦思夫痛子身。海南路,嘆孔雀孤飛,海圖難認。(貼)待織出雙鴛宮樣錦,細細的商量分寸。(旦)還說甚翠繞珠圍,權廝守荊釵布裙。(合)問天,天怎昨日今朝,今朝來似兩人”, 臧氏批云:“‘問天,天怎昨日今朝,今朝來似兩人’是當行語”,即是說盧夫人失勢的窘境,與之前天差地別,此曲語言符合盧夫人前后的身份。《曇花記·超度沉迷》折,有生唱【尾聲】:“繁華棄置因求道,論歌妓,吾家不少,為甚孤身云外飄”,臧氏批云:“此當家語也”,意指此處將木清泰出世前后的反差一曲道盡。《邯鄲記·入夢》折中,呂洞賓借用北宋范仲淹《岳陽樓記》描繪岳陽樓盛狀,臧氏批云:“道人述二篇《岳陽樓記》,唐時神仙亦善讀《宋文鑒》耶”,當是說唐人吟誦宋文,違反了現實常理,不符合“事肖”的要求,故將《岳陽樓記》刪去,改換賓白,使情節合理。《曇花記·禮佛求禳》折有【金索掛梧桐】曲,原本由郭、賈合唱,臧氏批云:“原本郭、賈同唱一引上場,恐抱病之人不宜如此,故改之”。此時郭、賈受到驚嚇,抱病在床,再上場顯然失當,因此臧氏將此曲改為老旦、小生合唱,更加合理。
四、關目要“緊湊”
臧氏云:“境無旁溢,語無外假,此則關目緊湊之難”,他認為湯顯祖“作傳奇長,怪其頭緒太多”,批評屠長卿“加損”“錯綜照應”,是說作家創作戲曲時,要“圍繞著主要人物與劇作主題來設置情節,情節發展緊湊集中,不枝蔓,結構完整”[20]380。《牡丹亭》原作五十五出,臧氏改為三十六折;《邯鄲記》原作三十出,臧氏改二十九折;《南柯記》原作四十四出,臧氏改為三十五折;《紫釵記》原作五十三出,臧氏改為三十六折;《曇花記》原作五十五出,臧氏改為三十一折。臧氏對原作關目的刪改和整合,縮短了原作的篇幅,使情節更加緊湊、連貫,更適應舞臺表演。
臧氏改評《曇花記》,刪去原作十六折,簡化了情節,使結構更加緊湊,豐富了舞臺表現力。原作有《群魔歷試》《天曹采訪》《奸相造謀》《士女私奔》《仇邪設謗》等出,情節拖沓,語言迂腐,臧氏批云:“原本有《歷試》折、《采訪》折、《造謀》折、《私奔》折、《設謗》折,則未免太冬烘矣,并刪”。《紫釵記·張燈》出敘旦與老旦元宵賞燈,臧氏以為“非傳奇關要”,故刪之。《紫釵記》原作第十出、第十二出情節關聯性強,臧氏將其合并為一折,刪去原來的第十一出,整合成新的《仆馬》折,使情節連貫緊湊,增強了舞臺效果,且便于演員改扮。
臧氏總批《紫釵記》云:“計玉茗堂上下共省十六折,然近來已無長于此者,自吳中張伯起《紅拂記》等作,止用三十折,優人皆喜為之,遂日趨日短,有至二十余折者矣。況中間情節非迫促而乏悠長之思,即牽率而多迂緩之事,殊可厭人。予故取玉茗堂本細加刪訂,在竭俳優之力,以悅當筵之耳。”臧氏批評有些當朝南戲作品過長,結構松散,且不注重舞臺效果。他所謂“竭俳優之力,以悅當筵之耳”,就是說創作要貼合舞臺表演。換言之,創作劇本是為了表演,而表演則為了觀眾。臧氏贊賞關漢卿等元雜劇作家熟悉劇場,“躬踐排場”,善于制造舞臺效果。如此,才能將“案頭之曲”發展為“場上之曲”。
五、表演要有“做法”
臧氏在評改當朝傳奇時,反復強調“做法”的概念。如他在《曇花記小序》中指出:“既云曲矣,則登場有唱法、有做法”。 有學者認為,他“用的‘做法’,是強調具有獨特性的舞臺表演”[21]72。筆者認為,“做法”即指戲曲登臺的表演方法。前人認識到,臧氏對“做法”的重視,有很強的針對性。“他們認為湯顯祖自有其可傳的價值,特別是《牡丹亭》最為人所欣賞,但由于不諧音律,搬上舞臺(其實主要指昆腔舞臺)存在一定的困難。”[22]94為了使當朝傳奇更有“做法”,臧氏主要對腳色配置、上下場方式等方面做了改訂。
首先是對演員腳色的改訂。湯顯祖、屠隆在創作戲曲時,忽視了場上表演的現實問題,或曲、白太長,或過渡太短,或一位演員扮演多個劇中腳色。這不僅耗費演員氣力,也不方便演員表演時改扮。臧氏批《曇花記·卓錫地府》出云:“長卿頗有傷時之意,但不是戲止數人。而曹操等不啻數十輩,則改扮極難,且非做法,故削之。”評《邯鄲記·死竄》出說:“北稱‘旦末雙全’,蓋謂‘有唱有做’,此折得之”,贊賞此出頗得元雜劇之做法、唱法,曲白、腳色分配合理,舞臺效果好。
除刪去多余腳色外,臧氏還創造性地引入了新的腳色。在較早的南戲作品中,大多只有生、旦、凈、末、丑五種腳色。徐渭《南詞敘錄》中又增添外、貼兩腳[12]245,此后腳色進一步分化,又出現外旦、小外等腳色。王驥德《曲律》中記載的腳色則更多,包括正生、貼生、正旦、貼旦、老旦、小旦、外、末、凈、丑、小丑在內的十余人。[7]143除了這些腳色外,臧氏還首次將元雜劇中的搽旦一腳引入傳奇創作和表演,用于裝扮“沒有身份的配角,比如校尉、內官等”,或“身份清楚的人物,如鮑四娘”。[21]75臧氏改評《曇花記》時,令老旦扮衛氏、旦扮房氏,并增小外、搽旦等幾個新的腳色。批《紫釵記·觀燈》出云:“凡戲舊稱‘八腳’,后始增老旦。而蘇松間有官凈、副凈、大丑、小丑至十一人極矣。此折自老旦而下已用九人,更為王孫仕女,縱觀燈火,恐非倉卒可辦。故直用老旦引旦、貼上,而內佐以鼓吹稱賞,亦不冷場矣。”臧氏增添新的腳色,一方面節省了演員氣力,便于改扮,另一方面豐富了舞臺腳色。
其次是演員上下場的編排。湯顯祖、屠隆原作未能為演員的上場、下場做合理安排,不能很好地適應場上表演。臧氏在改評本中,為演員重新設置了上下場方式,使表演更加自然。如《曇花記·土地傳書》折,敘末指點小生尋父事。原本小生唱【青歌兒】后徑直下場,末腳如何下場卻沒有說明。臧氏批云:“原本小生先下,非做法也,改之。”在改評本中,他令“末做挑柴徑下,小生做追不及介”,不僅使銜接更加自然,又增添了未盡之意,為下文設置了懸念。《紫釵記·濟友》出開場,湯顯祖沒有為旦腳安排上場方式。臧氏批云:“旦上即作對鏡,正為‘玉釵’句也,此是戲中緊要關目,唱者須知。”在改評本中,臧氏改為“旦對鏡妝,浣隨上”,規定了旦腳、貼腳的上場動作。《紫釵記·述懷》出,崔、韋二生上臺開場,湯顯祖沒有為二腳設置自我介紹,不免使觀眾疑惑。臧氏批云:“崔、韋二生登場,各自述姓名,庶使觀者了然,知某色為某人也。”他將情節改為:“[崔云]自家崔允明是也。[韋云]自家韋夏卿是也”,清晰了然。《邯鄲記·讒快》出,宇文融唱完【黃鶯兒】曲后,使者磕頭謝過,沒有安排二腳下場,后緊接凈腳上場,銜接處十分混亂。臧氏在此處安排宇文增唱一首,使二腳一同下場。臧氏批云:“不增此一曲,宇文相何以下場?”再如臧氏改本《曇花記·義仆遇主》折,仆人木韜偶遇舊主木清泰,將別之際,“(凈叩頭先下,又回介)愿老爺早些回來”,這“一下一回”生動地表現出木韜對木清泰的思念和不舍。故臧氏批云:“凈下時極有做法,此曲家三昧也。”臧氏為演員重新設置上下場的方式,規范傳奇中的動作、腳色,這些使得演員的上下場和銜接處更為自然,同時增添了表演的敘事、抒情功能。
除此之外,臧氏評改戲曲時,還提出了一些戲曲表演方法,為舞臺表演提供了有益的參考,對作家創作也有一定的啟迪。《紫釵記·觀燈》出,臧氏刪去【玉交枝】、【川撥棹】、【玉樓春引】、【六犯清音】四曲,另作尾聲,使鮑四娘求聘之計首尾相連,使情節更加完整連貫,此謂“前后照應法”;《紫釵記·仆馬》出,臧氏令李、崔、韋分唱【孝順歌】,節省了演員氣力,此謂“串戲法”或“錯綜法”;《曇花記·土地傳書》出,臧氏增土地傳信,為木龍駒尋父作結,此謂“斷流法”;等等。對于這些方法,前輩學者認為其雖“不無巧立名目之嫌,但臧懋循確實在這些細節上注意到了場上安排,從演出實際考慮了腳色裝扮的問題”[21]74。
六、臧懋循改評當朝傳奇的得失
臧氏改評當朝傳奇作品,世人褒貶不一,爭議較大。閔光瑜譏其曰:“新刻臧本,止載晉叔所竄原詞,過半削焉,是有臧竟無湯也”[23];茅暎譏其“截鶴續鳧”[24];吳梅在《顧曲麈談》一書中批評其“孟浪”,但又認為從排場、腳色、曲白協調角度來看,臧氏實是“玉茗之功臣”。[25]147總體來說,吳梅的觀點較為公允。經臧氏改評后的傳奇作品,關目簡略,情節連貫,節省了演員力氣,豐富了舞臺效果。若從表演的角度來審視,臧氏可稱有功之臣。而若從戲曲作為文學作品的角度來看,臧氏在改訂過程中對曲白大規模地改竄和增刪,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作的文學性,消解了其藝術價值,這也是需要關注的問題。
從曲律方面來看,前輩學者認為:“以曲譜來對照,臧本更為貼合曲律,平仄韻腳,皆吻合規范。從文學的角度來衡量,臧本在表現人物的情感方面,遜色于湯本。”[17]46如《牡丹亭·鬧殤》出,有【集賢賓】曲:“(旦唱)海天悠,問冰蟾何處涌?玉杵秋空,憑誰竊藥把嫦娥奉?甚西風,吹夢無蹤,人去難逢,須不是神挑鬼弄。在眉峰,心坎里別是一般疼痛”,臧氏批云:“有不合調處,俱改正”,而改為:“(旦唱)海天孤月何處涌,望來玉杵秋空,憑誰竊把嫦娥奉,怕聽他風馬叮咚,更紙條窗縫,攪破我一床幽夢。(貼合)心自恐,漸覺的四肢難動”。此處寫杜麗娘一夢成癡,思念夢中的柳夢梅,湯顯祖原曲更有情,經臧氏改竄后,雖更合律,卻失去了獨特的韻味。
從情節方面來看,臧氏苛求情節的緊湊連貫,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原作的藝術和思想價值。如《邯鄲記·雜慶》出,敘盧生起復后家眷在府中歡慶的場景,臧氏刪之。閔光瑜本《邯鄲記》批云:“眾人喜慶如此,盧生降遇何如?是作者善形容處,止與《南柯·風謠》一律,臧每削之何也?”[23]閔光瑜本認為,此處是湯顯祖善于摹情寫景處,襯托了人物歡喜的心情,不該刪去。《曇花記》作者屠隆崇尚儒、釋、道并治天下,而臧氏改本刪去與道有關的關目、腳色,刪道存佛,背離了作者的原意。《邯鄲記·度世》出,原本有呂洞賓集唐語,交代何仙姑由來,臧氏改本盡皆刪去,并刪何仙姑獨唱二曲。《邯鄲記》原旨是勸誡世人——功名富貴只是大夢一場,因此湯顯祖先引出呂洞賓度脫何仙姑成仙一則。臧氏刪去,則少一處鋪墊。閔光瑜本批評臧氏云:“何姑亦從塵世度來,臨川引之,當自有意,未可刪去”[23],當是譏諷臧氏一味迎合表演,卻未得湯顯祖要旨,刪去了不應刪去的內容。
在臧氏同時或稍后,戲曲評論家如呂天成、馮夢龍等,均關注戲曲作品的搬演問題,曲壇形成了一股改評戲曲的熱潮。可以說,“晚明演劇理論的發生、發展,在某種程度上,得力于文人傳奇改本的推動”[21]78。雖然這些零散的戲曲批評觀念沒有形成專論,卻為戲曲藝術由案頭走向舞臺做出了突出貢獻。臧氏的戲曲批評理論是在改評的基礎上形成的,是明代戲曲評論的大膽創新,應受到公允評價。臧氏對傳奇的改評,為明代曲壇注入了新的活力,對當時的戲曲表演和創作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