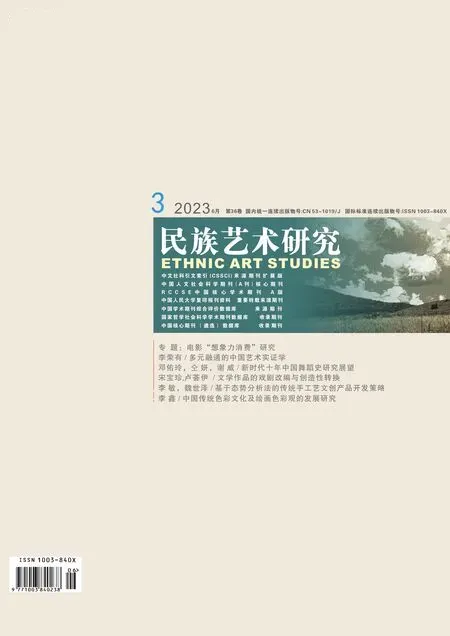面對 “闡釋危機”:電影 “想象力消費”的理論自覺與方法論思考
陳旭光,張明浩
一、關于想象力消費類電影的“闡釋危機”
當下,一種“闡釋危機”,在文藝界出現。這既表現為互聯網多媒介時代“批評的泛化”和眾聲喧嘩,也表現為理論與對象不對位甚至錯位的窘境。在后一種情況下,“闡釋”脫離“經驗對象”而成為某種“闡釋的闡釋”“闡釋的循環”或“能指的飄移”“理論的游戲”,正如尤西林對文學理論危機的反思,“當代文學理論危機主要不在于理論自身的概念或邏輯問題,而根源于文學理論脫離文學經驗的結構性危機。”①尤西林.以文學批評為樞紐的文學理論建構[J].文藝理論研究,2015(3):69-74.當下的某些文藝闡釋,同樣面臨著脫離“闡釋”的“對象主體”(經驗材料)的問題,很多“闡釋”成為無須“經驗”的“空中樓閣”、空洞的能指漂移和話語流淌。有的 “闡釋”則存在“強制闡釋”的問題——如尤西林反思西方文論那樣,其“生成和展開,不是從實踐到理論,不是通過實踐總結概括理論,而是用理論閹割、碎化實踐,這是‘強制闡釋’的認識論根源。”②張江.當代文論重建路徑:由“強制闡釋”到“本體闡釋”[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6-16(A04).顯然,“闡釋”絕非簡單的“理論套用”,更要警惕強制闡釋,也要防止“闡釋冗雜”或“闡釋過度”。海倫·加德納在《捍衛想象》一書中對“闡釋冗雜”現象進行過反思,“解說、闡釋、新解越來越泛濫,文本只是一個競技場、角斗場或書單,各路人馬在上面展示創新和智謀”③海倫·加德納.捍衛想象——哈佛大學查爾斯·艾略特·諾頓講座,1979-1980[M].李小均,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197.。盡管文本是無限的,甚至“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萊特”,但過度闡釋或強制闡釋,就像泡沫經濟那樣,并不會賦予文本生命力,反而會使文本缺失已有的活力與鮮活度。
在此“闡釋危機”背景下,想象力消費類電影面臨的“闡釋危機”尤其嚴峻。
相較于頗為適合文藝片的“作者論”分析方法,適應現實題材和現實主義創作的現實主義分析方法,中國目前并沒有一套“闡釋”想象力消費類電影的理論體系。文藝批評者借助西方文藝理論或藝術電影批評的方法來“闡釋”想象力消費類電影,或過于強調中國文藝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則容易得出“脫離現實” “藝術水平低”、商業化、缺乏“作者風格”等評價。但想象力消費類電影在生產邏輯與目標受眾上,都明顯不同于現實主義類作品,也異于藝術電影,不能在精英主義的視角下對其進行簡單分析和機械化價值判斷。美國學者奧椎基曾言,“如果以西方批評的標準批判東方的文學作品,那是必然會使東方文學減少其身份的。”①古添洪.中西比較文學:范疇、方法、精神的初探[C]//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科研處、《文學研究動態》編輯組.比較文學論文選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44.以知識分子精英主義視角批判、闡釋想象力消費類電影,也與此有相似之處。
不妨說,很多批判者、闡釋者對想象力消費類電影存在 “偏見”,例如一提及如《蒼蘭訣》等魔幻甜寵類作品時,便會直接以精英的立場“嗤之以鼻”,甚至認為批評、闡釋這些作品“掉價”。但以《蒼蘭訣》《美人魚》《捉妖記》《香蜜沉沉燼如霜》為代表的想象力消費類影視作品都在播映期間獲得了很多青少年、網生代的喜愛,這是不能回避的事實。如果批評家缺乏“正視”這些作品的胸懷和視野,沒有客觀研究其“爆款”背后的文化消費與藝術生產邏輯,此類作品自然無法得到客觀理性的有效評價。
毋庸諱言,想象力消費類影視作品長期處于不發達狀態或“被邊緣化”的位置。一方面,想象力消費類電影在總體數量上不多,影響力不大。在好萊塢幻想類大片不斷進入中國電影市場的21世紀前10年,中國想象力消費類電影更處于缺失、失語的狀態。而且,想象力消費類影視作品的生產受制于中國傳統文化語境與文藝生產語境的影響。在文化傳統方面,中國有著自孔子以來“不語怪力亂神”的傳統,對“超驗”性想象力并不鼓勵,甚至將魔幻類、“民間亞文化”類文藝作品列入封建迷信糟粕的行列中;就創作環境而言,近代以來,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一直是國家層面所提倡的主流性創作方法,這就要求文藝作品反映社會、寫實記錄、避免“怪力亂神”。這些復雜的“歷史多元決定”,導致了幻想類作品發展不足,也多少導致其缺乏有效闡釋的“闡釋危機”。
因此,我們需要直面想象力消費類電影的“闡釋危機”,為其找到適當的“闡釋話語”。伍曉明對文藝“缺乏闡釋理論”的現象曾經犀利指出:“研究者和理論家通常都不會承認,自己是因為缺乏解釋作品的理論或找不到相應的話語,才無法辨認出這些作品的價值,相反總是會言之鑿鑿地聲稱它們本來就沒有什么意義。”②伍曉明.理論何為?[J].文藝研究,2022(1):13-25.與此相似,想象力消費類影視作品也因為缺乏有效闡釋的理論或話語,而常常被批評家、理論家視而不見或定位為邊緣、另類、支流電影。但毫無疑問,此類非主流作品卻贏得了“大眾” “常人”、很大一部分“人民”的喜愛。我們無疑應該直面這一問題,重估想象力消費類電影的價值。而這種價值的重估、厘定則需要相應理論闡釋話語的支撐,也需要該話語背后相應的主體立場確立與價值觀設定。否則,就難免南轅北轍、自說自話,“一葉障目不見泰山”。
二、經驗與現實:想象力消費類影視的崛起
所謂想象力消費是指“受眾(包括讀者、觀眾、用戶、玩家)對于充滿想象力的藝術作品的藝術欣賞和文化消費”③陳旭光.論互聯網時代電影的“想象力消費”[J].當代電影,2020(1):126-132.,想象力消費類電影包括玄幻、魔幻類電影、科幻類電影、影游融合類電影等。
想象力消費類影視作品一直比較受歡迎,此類作品呈現的超現實想象力和極具視覺體驗的觀影享受,使其在我國擁有龐大的收視群體(以青少年群體為主)。
據燈塔數據統計,自2014年以來,中國年度票房TOP10之中,想象力消費類電影一直占據重要地位。2014年年度票房TOP10中有6部都為想象力消費類電影—— 《變形金剛4:絕跡重生》(19.77億元)、《西游記之大鬧天宮》 (10.45億元)、 《星際穿越》(8.77億元)、 《X戰警:逆轉未來》 (7.22億元)、《美國隊長2》 (7.18億元)、《猩球崛起2:黎明之戰》(7.08億元)。2015年年度TOP5中有4部均為想象力消費類電影——《捉妖記》 (24.41億元)、 《速度與激情7》(24.26億元)、 《尋龍決》 (16.81億元)、《復仇者聯盟2:奧創紀元》 (14.63億元)。2016年年度票房TOP5更是全部都為想象力消費類電影—— 《美人魚》 (33.93億元)、《瘋狂動物城》 (15.34億元)、 《魔獸》(14.71億元)、《美國隊長3》(12.45億元)、《西游記之三打白骨精》(12.00億元)。2017年年度票房TOP10中一半均為想象力消費類電影—— 《速度與激情8》 (26.71億元)、《功夫瑜伽》 (17.53億元)、 《西游降魔篇》(16.56億元)、 《變形金剛5:最后的騎士》(15.51億元)、 《尋夢環游記》 (12.29億元)。2018年年度票房TOP10中也有6部作品為想象力消費類電影—— 《復仇者聯盟3:無限戰爭》(23.88億元)、《捉妖記2》 (22.37億元)、《海王》(20.13億元)、《毒液:致命守護者》 (18.70億元)、 《侏羅紀世界2》(16.95億元)、《頭號玩家》(13.96億元)。
想象力消費類電影的成功與其符合大眾文化消費、體驗消費的心理相關。根據如上數據及梳理可見,美國好萊塢想象力消費類電影一直占據著年度票房榜的主體地位。而且,從2014—2018年這些想象力消費類電影(無論中外)的數量、票房占有量及影響力與號召力來看,依靠奇觀視覺、幻想滿足與震撼場面沖擊而立身的想象力消費類電影的確在電影市場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想象力消費類電影是大眾尤其是“青少年大眾”進入電影院消費的重要動力。
相較于好萊塢大片而言,中國本土想象力消費類作品至少在2018年之前并未擁有強大的影響力,科幻類作品尤其缺失。當然,想象力消費類作品中玄幻、魔幻類還是有相當大發展的。如在電視劇領域, 《仙劍奇俠傳》《花千骨》《香蜜沉沉燼如霜》《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千古玦塵》《蒼蘭訣》《重紫》等魔幻類電視劇一直保持著較高影響力(每次播放都能夠登頂同期電視劇觀看指數的頭部位置),這些作品立足于中國奇幻、奇觀“民間亞文化”或“中國神話元素”,其較高的收視率反映了中國民眾尤其是青年網生代對“虛擬奇觀”的消費訴求。
近年來,尤其是2019年以來,中國本土想象力消費類影視作品呈現崛起之勢。
近年來頗有熱度的《哪吒之魔童降世》《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以及《蒼蘭訣》等玄幻類影視作品的熱映、熱播都引發了現象級的討論和關注。另外,靈感源于中國古代志怪故事的盜墓類文學作品改編的影視劇如《尋龍訣》、網絡電影 《盜墓筆記》系列等,前些年也在我國觀眾群體中掀起了一股“想象力消費”熱潮。
自2019年開始,中國本土的想象力消費類電影或電視劇的表現尤為突出,甚至有超越好萊塢大片之態勢——2019年的《哪吒之魔童降世》 (50.35億元)、 《流浪地球》(46.88億元)成為年度票房TOP2;2021年“春節檔”更是集中出現了諸多 “想象力消費類電影”—— 《你好,李煥英》呈一種“穿越想象”,《刺殺小說家》呈一種“雙重世界”“文學與未來世界”之互文想象,《新封神:哪吒重生》呈一種魔幻奇觀+賽伯朋克的“過去+未來”想象,游戲改編電影《侍神令》呈一種魔幻奇觀想象;2022年開始的網絡劇《開端》,及2022年的中式科幻電影《獨行月球》《外太空的莫扎特》《熊出沒:重返地球》等的火爆,也進一步凸顯出“想象力消費”時代或正在來臨。
想象力消費類電影尤其是中國本土想象力消費類電影的崛起,實際上是一種青年“象征性權力”①陳旭光.青年亞文化主體的“象征性權力”表達——論新世紀中國喜劇電影的美學嬗變與文化意義[J].電影藝術,2017(2):112-116.的表達使然。在青少年必然經歷的“身份焦慮”階段,青少年主體力圖進行“話語”表達與 “焦慮宣泄”,而想象力消費類電影,恰恰是“青年圈層”的一種“象征性權力表達”——青年群體借助虛擬奇觀的想象力消費在“虛擬”中“改變世界”“拯救世界” “為自己發聲”,甚至拯救老一代群體(如《開端》中游戲青年利用游戲循環思維拯救老一代人),這無不表現出青年群體進行文化觀念傳達與個人身份彰顯(或者迫切想要得到社會認同)的文化心理,隱含了某種意識形態訴求,也是在呼喚人們對青年文化的同情與理解。
2023年“春節檔”期間,想象力消費類影視作品的集中出現與優異成績更印證了筆者所預期的“一個想象力消費的時代正在來臨”!2023年春節檔,《流浪地球》系列電影《流浪地球2》斬獲21.64億元票房,講述人機關系、探討機器情感與機器倫理的動畫軟科幻電影 《熊出沒:伴我 “熊芯”》斬獲7.48億元票房;春節檔之后,兩部電影持續發酵, 《流浪地球2》獲40.26億元票房、《熊出沒:伴我 “熊芯”》獲14.92億元票房,兩部電影均位列當前年度票房榜前3名。而電視劇領域,根據燈塔專業版數據顯示,電視劇版《三體》的同期播放量、同期市場占有率為16.51%,均穩居榜首。此類想象力消費類影視作品尤其是“面向未來”空間的想象力消費類作品的集中出現與其被廣泛關注、熱烈討論,表現出中國民眾一直以來對“仰望星空”式想象的訴求,也體現出中國式想象力消費的“擴容”。
顯然,在想象力消費的時代,尤其是中國本土想象力消費類電影崛起的當下,更應建構一種與之匹配的本土理論話語,來對這些作品進行“恰當”的有效分析,并發掘其各種價值和意義。
三、理論自覺或方法論思考
(一)理論自覺:直面 “真問題”與“范式革命”
想象力消費理論的提出是一次對“真問題”的“直面”,也是對“實踐的回應”,是理論與實踐的互動與實踐發展后對理論的自覺探索。正如尹鴻認為的,“電影的理論評論是在與電影發展實踐的互動中不斷創新、不斷發展的。理論與實踐互動,才能夠更好地推動話語體系、研究體系的建構。在電影理論批評發展歷史上,電影理論批評只有面對電影實踐的變化,提出真問題、研究真問題,才能獲得發展的空間和繁榮的局面。蒙太奇學派、新現實主義、新浪潮、新好萊塢、巴贊、布萊希特、克拉考爾是這樣,即便是麥茨的符號學,德勒茲對影像的運動、時間、空間的重新定義,也都體現了對電影實踐中的真問題的應對、回應和闡釋。”①尹鴻.電影理論評論要提出真問題、鉆研真問題[N].中國電影報,2022-08-31(002).因此,一方面,想象力消費理論立足現實實踐。在現實語境與影視現實發展之中,想象力消費類影視作品不斷涌現且影響日益增強。另一方面,想象力消費理論建構是一種 “理論自覺”,直面、縫合“理論”與“實踐” “闡釋”與“產業發展”之間的“縫隙”,力圖緩解“理論闡釋危機”,也是一次為青年群體和想象力消費類作品 “正名”的話語實踐,是面對“范式的危機” (即已有研究范式無法確切闡釋研究對象)的一次研究范式創新與探索。正如美國學者托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所指出的那樣,科學革命“起源于科學共同體中某一小部分人逐漸感覺到:他們無法利用現有范式有效地探究自然界的某一方面,而以前的范式在這方面的研究中是起引導作用的。在政治發展和科學發展中,那種能導致危機的機能失靈的感覺都是造成革命的先決條件。”②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M].金吾倫,胡新和,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85.想象力消費理論正是筆者意識到已有范式的闡釋失語,因“范式危機”而進行的一次研究范式創新的理論自覺努力。當然,正如馬斯·庫恩所言:已有范式因起到“引導作用”,具有“權力話語”的“先決性”;所以,突破已有范式便尤為不易——這也是想象力消費理論所面臨范式創新后的理論接受問題——想象力消費理論因建構起不同于以往的“引導范式”即理論研究方法與理論話語,勢必會面臨已有范式的挑戰與爭鳴等。但研究者并不能因理論建構可能會導致范式沖擊而引起話語爭議,而怯于真問題研究與范式創新;更要“但開風氣不為師”,要有推動理論創新的勇氣與魄力。
總之,想象力消費理論的建構力圖推動范式創新,挑戰已有的引導性范式,“以人為本”,為“人”(尤其是當前影視受眾主體的青少年們)發聲,為作品正名。故此,想象力消費理論是一次理論自覺意識的實踐,更是一次科學范式創新的探索。
(二)方法論原則:“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
馬克思與恩格斯認為“人的活動是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合規律性是指現實的人認識到了自然規律或社會歷史規律,使自己的行動自覺遵循和符合客觀規律的要求,自覺按照規律辦事,它體現了人的主體性與自覺能動性;合目的性是指人認識和把握了事物發展的規律性,在實踐中能夠達到自己的目的,把理想客體變成現實。”①宋德孝.科學發展觀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統一之哲學分析[J].求實,2008(2):29-31.可見關注“現實的人”是馬克思、恩格斯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論述的宗旨。在 《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又指出:“我們開始要談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條,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開的現實前提。這是一些現實的個人,是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包括他們已有的和由他們自己的活動創造出來的物質生活條件。”②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6-67.而想象力消費理論的建構及其方法論思考在根本上也是一次理論建構與方法搭建的“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實踐;且在建構理論與方法時,核心是以現實為前提,關注現實中的“人” (側重于青少年受眾群體)。
想象力消費理論的方法論原則的“合規律性”追求,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合乎當前時代的消費規律。之所以將文學文藝理論領域的“想象力”,與經濟領域的“消費”相融合,是因為筆者關注到當下受眾消費或審美趨好已經轉向一種“體驗享受式” “想象式”消費。或者可以說,就受眾的電影院觀看或消費行為而言,其背后就表現出受眾的審美偏好。而以消費視角研究想象力消費類作品,則能夠發現此類作品都具有某種共性——能夠滿足絕大部分受眾“觀看-沉浸”的體驗享受式消費需要。
二是合乎理論延伸規律。“想象力消費”這一術語既有“感性審美”的已有學理支撐,也與沉浸、體驗、1V1互動、游戲即刻反饋等新媒介審美有關聯。針對理論研究邏輯方法的建構與方法論思考,黑格爾曾說:“方法不是某種跟自己的對象和內容不同的東西”,方法是“對象的內在原則和靈魂”。③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邏輯學:下卷[M].楊一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536-537.想象力消費的研究方法正是對想象力消費類作品(如《微微一笑很傾城》 《頭號玩家》 《蒼蘭訣》 《流浪地球》等)中的“沉浸生成”與“體驗生成”進行研究,分析其“沉浸生產原因”與“如何讓受眾產生互動體驗”。顯然,這種分析方法是“貼合”著文本的分析,是如黑格爾所言的與 “對象靈魂”相一致、步伐相同的分析與闡釋。也正因如此,想象力消費理論方法中的分析法,既有傳統美學的分析方法,又吸納了當前游戲美學(如筆者所總結的互動美學的“即刻反饋式”美學機制④陳旭光,張明浩.影游融合、想象力消費與美學的變革——論媒介融合視域下的互動劇美學[J].中原文化研究,2020(5):49-57.)的分析方法,以此在既有理論上進行擴容與創新,并達到真正分析文本如何使游戲受眾、網生代受眾喜愛的目的。
想象力消費理論方法論原則的“合目的性”追求,是為“青年的人” “現實的人”發聲,其努力表現于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跨學科視角的分析方法探索。顯然,想象力消費類作品的崛起與受眾廣泛關注其背后的原因,遠不止于影視內部。為更好分析文本,想象力消費理論引入一種跨學科的分析方法——將藝術學分析、美學分析、心理學分析、經濟學分析相融合,以此探究“問題”背后的 “多元決定”,獲得方法的“合目的性”——分析文本,揭示深層內容。筆者在分析《流浪地球2》時,便從心理學“原型”視角、經濟學產業發展即系列生產視角、藝術學文本創新視角及美學呈現視角對其進行了全面剖析。①陳旭光.人類命運共同危機的“世界想象”與“中國方案”——評影片《流浪地球2》[J].當代電影,2023(2):26-29,184.
二是研究范式的初步建構與確立。要使方法論“合目的性”,就要能夠讓方法真正從宏觀或微觀層次上深入到文本,可以進行“有效闡釋”。想象力消費理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四維度分析方法——藝術消費(審美心理)、文化消費、經濟消費與意識形態再生產。借助這四個層次的分析方法,能夠對某部作品或某種、某類想象力消費現象進行深入立體的研究。如筆者在研究 《頭號玩家》《微微一笑很傾城》等時,從這四個維度進行層次性分析,得以窺見爆款作品的成功之道——滿足了青年文化的消費訴求,并且這些作品在形式上的景觀美學、奇觀美學呈現能夠刺激并滿足受眾的相關藝術消費訴求,不僅如此,這些作品的消費背后,還有著消費群體力圖通過消費進行“圈層劃分”與“意識形態再生產”的意識。如《開端》的消費群體便在生產一種游戲青年有用甚至能夠拯救世界的觀念意識。另一方面,這幾個層次的分析方法能夠“各自獨立”地運用,即可以單獨采用其中任一種分析方法進行文本闡釋。
所以,想象力消費理論不僅與想象力消費類、幻想類作品的青年文化性、“象征性權力表達”等特性或話語共通,更能結合這些作品的文本規律、時代表征與生產生成機制進行方法論思考與范式探索。
四、“理論批評化”:有效闡釋的驗證
實踐是檢驗理論是否有效的關鍵與標準。理論的有效性體現在理論能否恰當闡釋文本、能否提供闡釋框架,能否分析現象等具體維度上。所謂“理論批評化”,是筆者近年來總結建構電影工業美學理論時所凝練的——“能讓理論充實、 ‘接地氣’,理性面對中國電影現實提出問題、解決問題。電影工業美學——根本上而言是一種‘批評的理論’而非抽象玄思的理論。因此,以‘電影工業美學’為理論視域或批評框架,可以對電影作品、導演和現象進行分析,這種‘批評實踐’是對電影工業美學理論的一種檢驗。無疑,‘理論批評化’是理論保有生命力的重要手段。只有通過批評實踐,留其有效,棄其無效,理論才能有所調整有所提高。這是一個不斷反轉,對流和互逆的過程。”②陳旭光.“理論批評化”與電影工業美學“接著講”——兼與朱曉軍教授商榷[J].藝術評論,2022(11):8-21.想象力消費理論的建構也秉承理論批評化、理論實踐化、理論與產業對話的話語建構邏輯。
想象力消費理論的有效性首先體現在理論批評的影響力上。就一定程度而言,研究數量、被引頻次能夠表現出理論研究的集中性與理論的傳播度即接受認可程度。自2020年1月筆者正式對“想象力消費”理論進行系統概述至今僅僅兩年多的時間,知網檢索平臺有關“想象力消費”主題的研究文章已120余篇,總被引726次,總下載量高達105271篇次。并且筆者的《論互聯網時代電影的“想象力消費”》(《當代電影》2020年第1期)這篇文章被引高達120余次。此外,在由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發起的“2022年度文化產業十大關鍵詞”網絡評選中,“想象力消費”名列第6(十大關鍵詞依次為:元宇宙文化產業、沉浸式文旅體驗、數字賦能鄉村振興、數字虛擬人、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想象力消費、超級數字場景建設、人工智能技術、城市記憶活化傳承、冰雪產業)。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作為本土理論建構的理論話語,想象力消費理論在學界的較大影響力和較為廣泛的接受度。
想象力消費理論的有效性其次體現在其被學界其他學者廣泛探討與運用于批評實踐中。影視學界知名專家黃鳴奮、陳林俠、范志忠、李建強、楊俊蕾、向勇等人都曾基于其進行批評實踐或理論探討。影視學界青年學者李立、袁一民、李玥陽、宋法剛、田亦洲、石小溪、李卉、劉強、張立娜、張明浩、薛精華、張振、黃瑛、劉婉瑤、申朝暉等人也都曾利用這一理論進行現象分析、作品分析或文化研究。顯然,與消費影響生產的邏輯相近——有效的理論才可促進生產的延續與討論的持續;數位影視學者共同深入探討、進行批評實踐想象力消費理論的現實,在一定程度上佐證了這一理論的有效性。
想象力消費理論的有效性還體現在“理論可實踐化”與“理論可批評化”上,即運用想象力消費理論的理論框架、方法論或研究范式進行影視批評實踐,大體體現在如下幾個維度。
一是想象力消費理論能夠較為貼切地用在“具體案例分析”與批評上。目前學界利用想象力消費理論對《流浪地球》 《流浪地球2》《哪吒之魔童降世》 《征途》 《倩女幽魂:人間情》 《姜子牙》 《想見你》 《沙丘》等影視作品均有分析,代表性文章如《〈哪吒之魔童降世〉:游戲化敘事、重構式人物與想象力美學》①張明浩.《哪吒之魔童降世》:游戲化敘事、重構式人物與想象力美學[J].齊魯藝苑,2020(5):89-95,115.宋法剛,丁明.當下國產動畫電影的文化景觀與想象力消費[J].電影新作,2021(1):100-105.、《〈刺殺小說家〉的雙重世界:“作者性”、寓言化與工業美學建構》②陳旭光.《刺殺小說家》的雙重世界:“作者性”、寓言化與工業美學建構[J].電影藝術,2021(2):86-88.、《〈獨行月球〉:想象力消費美學視域下的科幻表達與英雄建構》③邵梓洛.《獨行月球》:想象力消費美學視域下的科幻表達與英雄建構[J].電影文學,2022(22):136-141.、《〈開端〉:影游融合劇的創新實踐與想象力消費》④黃瑛.《開端》:影游融合劇的創新實踐與想象力消費[J].電影新作,2022(3):22-28.、《雙重世界的寓言、影游融合的動向——評電影 〈刺殺小說家〉的想象力消費與奇幻美學》⑤劉婉瑤.雙重世界的寓言、影游融合的動向——評電影《刺殺小說家》的想象力消費與奇幻美學[J].電影新作,2022(3):36-43.、 《論游戲改編電影想象力與工業化的高度及限度——以〈征途〉的跨媒介改編為例》⑥陳旭光,張明浩.論游戲改編電影想象力與工業化的高度及限度——以《征途》的跨媒介改編為例[J].電影新作,2022(3):6-15.等。這些文章大多按照想象力消費理論的三個層次(文化消費、美學消費與意識形態再生產)為主體分析框架,并進行延續。比如張明浩的《“想象力消費”視域下科幻動畫 〈瑞克和莫蒂〉的“虛擬滿足” “荒誕”美學與科幻想象創新》一文,便是在想象力消費理論基礎上進行了主體批評的框架搭建—— 《瑞克和莫蒂》想象力消費的外在視覺層面:奇觀畫面與“異類”建構;內在“人物”層面: “反叛”屬性與后假定美學;“空間想象”層面:虛擬性的時空想象; “劇作”與 “價值”層面:解構屬性、非中心化與“戲仿”;《瑞克和莫蒂》的文化消費: “游戲滿足”及“部落劃分”。⑦張明浩,趙航.“想象力消費”視域下科幻動畫《瑞克和莫蒂》的“虛擬滿足”“荒誕”美學與科幻想象創新[J].東南傳播,2022(4):52-56.顯然,在想象力消費的理論框架下,這些引起大部分受眾共鳴、共情、備受矚目的作品,都找到了屬于“自身”的批評話語。
二是想象力消費理論能夠用于影視類型或形態分析。利用想象力消費理論能夠分析出想象力消費類影視作品的類型或形態,如《論中國科幻電影的想象力與 “想象力消費”》⑧陳旭光,薛精華.論中國科幻電影的想象力與“想象力消費”[J].電影藝術,2021(5):54-60.、 《論中國魔幻類電影的“想象力消費”》⑨陳旭光,張明浩.論中國魔幻類電影的“想象力消費”[J].電影新作,2021(1):84-92.、《中國奇幻電影的想象力消費與認同建構》⑩申朝暉.中國奇幻電影的想象力消費與認同建構[J].電影新作,2021(1):93-99.、 《當下國產動畫電影的文化景觀與想象力消費》?、 《論影游融合的想象力新美學與想象力消費》?陳旭光,李雨諫.論影游融合的想象力新美學與想象力消費[J].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37(1):37-47.等文章,都在 “想象力消費理論”的理論視域與研究范式下,分析此類想象力消費類電影的“想象力生產生成呈現邏輯”。這些文章從想象力消費類電影的想象力空間、想象力技術支撐、文化原型轉化、青年文化認同機制等方面進行“理論批評化”,分析科幻、魔幻、奇幻、動畫、影游融合等的本質特性,在進行“有效闡釋”的同時指出了這些類型作品的現實價值與實踐意義。不僅如此,還有諸多學者將想象力消費理論運用到 “非想象力消費類作品”上,以此看類型作品的想象力美學變遷,如《“想象力消費”視域下城市形象片的敘事轉向與美學重構》一文便將城市形象片的“想象力消費”制作趨勢進行分析,并指出當前此類作品的敘事“正從真實性敘事轉向想象力敘事,從宣傳敘事轉向消費敘事。”①楊怡靜.“想象力消費”視域下城市形象片的敘事轉向與美學重構[J].電影新作,2021(1):106-110.陳林俠,李雙.“飛離在場”:當下中國電影的想象力消費[J].當代電影,2022(1):45-51.此文雖將此一走向的范圍過于擴大化,但顯然受到了想象力消費的“想象力美學”與“消費”范式的影響。
三是想象力消費理論能夠用于對一些影視作品、現象進行較為具體深入的“理論批評化”實踐。在文化現象方面,很多學者借用想象力消費理論分析前沿文化現象,比如田亦洲以想象力消費理論視角分析近年來比較突出的“電影混剪視頻”現象,并指出其遵循一種想象力生產與游戲化體驗的“生產邏輯”②田亦洲.論電影混剪視頻的想象力生產與游戲化體驗[J].當代電影,2022(6):44-52.;再比如還有學者借用想象力消費理論研究“虛擬角色現象”并發布《想象力消費語境下的中國影視虛擬角色創設》③汪少明,王會霞.想象力消費語境下的中國影視虛擬角色創設[J].電影文學,2022(14):43-48.等研究文章。而在產業方面,有學者利用想象力消費理論分析 “魔幻玄幻類系列電影生產現象”④陳旭光,劉之湄.“白蛇傳”系列電影: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與“想象力消費”[J].文化藝術研究,2022(5):78-87,115.、“網絡玄幻小說改編現象”⑤覃媛元.網絡玄幻小說改編電影的中國式想象力消費[J].文化藝術研究,2022(5):88-95,115.、“太空類科幻電影生產現象”⑥張振.“想象力消費”視域下的文化冷戰——論蘇俄太空類科幻電影的美學特征[J].文化藝術研究,2022(5):96-102,116.、“神話IP的想象力消費改編現象”⑦張明浩,滿勝寵,郭培振.論中國動畫電影對“神話”IP的現代化改編[J].電影文學,2021(10):44-49.、 “網絡電影的想象力消費生產現象”⑧陳旭光.想象力消費、現實主義回潮與影游融合發展——論電影的“互聯網+”時代與網絡電影的發展趨勢[J].中國電影市場,2021(5):5-11.。
四是想象力消費理論的“理論批評化”還表現于可以不斷進行其 “理論擴容”與“理論再生產”,從而促使學界進行相關理論生產;想象力消費理論的維度及建構也在學界相關爭鳴探討中不斷完善。如《電影“想象力消費”理論的若干基本問題》⑨李建強.電影“想象力消費”理論的若干基本問題[J].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2):118-128.、 《電影想象力消費理論構想及與中國電影學派關系思辨》⑩陳旭光.電影想象力消費理論構想及與中國電影學派關系思辨[J].當代電影,2022(1):31-38.、《“飛離在場”:當下中國電影的想象力消費》?、 《電影想象力如何被消費:一種基于文化資本考察的視角》?袁一民.電影想象力如何被消費:一種基于文化資本考察的視角[J].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21(3):56-63.、 《略論電影“想象力消費”的三個層面》?李建強.略論電影“想象力消費”的三個層面[J].民族藝術研究,2022,35(6):39-47.等文章從想象力消費理論的底層邏輯、中國電影學派歸屬、現實語境、文化資本邏輯等方面對想象力消費理論進行了“擴容”與“再生產”。
就此而言,想象力消費的理論宗旨在實踐中真正得以“落地”,也由此承擔并實現了直面“闡釋危機”,為想象力消費類影視作品定位,為青年一代群體“發聲”的理論建構初衷。
五、問題與自省
安托萬·孔帕尼翁在《理論的幽靈》中說,“真正有效的理論只能是反躬自問并對自己話語進行質疑的理論”①安托萬·孔帕尼翁.理論的幽靈:文學與常識[M].吳泓渺,汪捷宇,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247.。想象力消費理論無疑需要不斷自省、自糾,時刻保持 “警覺”。
其一,理論的邊界與限度。
查爾斯·E.布萊斯勒在《文學批評:理論與實踐導論》中清醒指出,“不可能存在一種元理論(metatheory)——一種主宰性、總括性的文學理論,涵蓋讀者就某個文本提出的所有可能性闡釋。也不存在一種唯一正確的文學理論本身……沒有一種理論能夠窮盡針對任一文本提出的所有合法問題”。②查理斯·E.布萊斯勒.文學批評:理論與實踐導論[M].趙勇,李莎,常培杰,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13.想象力消費理論的搭建也應保持這種清醒,研究對象要聚焦于玄幻科幻、影游融合類的電影,嚴格地說,現實主義意義上的想象和想象力應該不在這一理論適切之列。
無疑,理論可以延伸,思維可以拓展,但延伸和拓展均應有其邊界。想象力消費理論堅守理論聚焦性、理論有限性,但想象力消費理論依然可以向社會學、心理學、美學、傳播學、經濟學等學科延展。想象力消費理論的跨媒介、跨學科性知識再生產無疑是理論發展的必要環節與未來路徑。但總之,想象力消費理論要在“無限”中探索“有限”即“邊界”,要了然理論不可能窮盡或適應一切文本。
其二,理論不能預設和先行,不可將想象力消費理論變成“預設前提”式理論來進行“按圖索驥”式的研究。喬納森·卡勒在《文學理論入門》中說,“理論的本質是通過對那些前提和假設提出挑戰來推翻你認為自己早就明白了的東西,因此理論的結果也是不可預測的。即使你無法最終掌握理論,你還是取得了進步。你對自己閱讀的內容有了新的理解,你針對它們提出了不同的問題,并且對這些問題的意義有了更清楚的理解”③喬納森·卡勒.文學理論入門[M].李平,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8:18.。借此思考,不能將想象力消費變成“按圖索驥”的“前提理論”,而是要將想象力消費理論作為一種研究切入口,以此發現文本中不可預測的新問題、新現象、新趨勢。
其三,關注電影本體即電影語言、技術與形式的研究,尤其是技術時代下想象力消費類電影背后的電影本體研究。喬納森·卡勒在《當代學術入門:文學理論》中曾反思研究的“廣泛性”:“確切說,他們指的是非文學的討論太多了;是關于綜合性問題的爭辯太多了,而這些問題與文學幾乎沒有任何關系;還有,要讀那么多難懂的心理分析、政治和哲學方面的書籍。”④喬納森·卡勒.當代學術入門:文學理論[M].李平,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1.這與鮑德維爾對大理論的反思異曲同工。想象力消費理論也應以此為鑒,避免“非電影”的討論,避免進入玄虛的空中樓閣理論場域。這就要求想象力消費理論要堅守實踐性,堅守問題意識,要不斷研究新現象,豐盈理論內涵,聚焦理論問題本身,堅持理論的實踐性與具體針對性。另外,電影中想象力的呈現需要技術支撐,因而技術美學維度的研究尤其需要“接著講”。
其四,理論應該始終立足實踐,在時時與業內、現實對話的過程中發展。筆者曾與《刺殺小說家》導演路陽進行對談,就該片的想象力問題進行探討,發現想象力消費不可僅僅有想象之緯,還應有現實關注、倫理反思:“我本來期待更為大膽,虛擬性更強的想象力,但現在看了《小說家》,覺得與現實保持平行、互文關系的虛擬世界設定也很不錯。這會比較接‘地氣’,而且還容易產生寓言、隱喻意義。”⑤路陽,陳旭光,劉婉瑤.現實情懷、想象世界與工業美學—— 《刺殺小說家》導演路陽訪談[J].當代電影,2021(3):61-72.訪談之后,筆者還結合《刺殺小說家》上映時的票房表現及想象力消費產業價值進行及時的理論糾偏:“我曾以為互聯網虛擬時代的想象力消費,架空性很強,可以超越現實,可以如鮑德里亞的‘擬像’一樣,與現實毫無關系。現在我相信,更應該建立起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的某種關系。太過虛擬的‘擬像’可能還是走不太遠,在中國觀眾中還很難受到歡迎。《刺殺小說家》在春節檔不敵《唐人街探案3》和《你好,李煥英》,從一個側面也證明了這一點。”①陳旭光.《刺殺小說家》的雙重世界:“作者性”、寓言化與工業美學建構[J].電影藝術,2021(2):86-88.再如《三體》原著的想象力雖然極為奇特超凡,但在忠實于《三體》文學原著第1卷即《三體》劇集中,卻有大量的篇幅交代葉文潔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災難,以豐富、鋪墊其性格行為的成因,這絕對是立足大地的一種想象力創作。相應的《流浪地球》系列科幻電影也大多是“近景想象”而非“遠景想象”,雖然必須面對未來300年后的太陽氦閃、地球災難,但必須是近期(《流浪地球》標明2075年,《流浪地球2》作為前傳設定在2050年前后)完成移山工程后準備實施地球流浪計劃。并且,《三體》 《流浪地球2》等作品“想象力”的“器物”呈現,實際上都有現實支撐。比如:《流浪地球2》中的“行星發動機”在現實生活中有著真實對照物——中國環流器二號A(HL-2A)。《三體》中涉及的“可控核聚變技術”,在現實中也有藍本——中國新一代的“人造太陽” (HL-2M)裝置等離子體電流突破100萬安培,其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核聚變的可控; 《三體》中的“納米飛刃”也有現實材料“碳納米管”為支撐。顯然,《三體》《流浪地球2》中的想象,是一種“踮著腳尖”腳踏實地而又“仰望星空”的想象,是與現實關聯度較大的想象。
也就是說,想象力不可完全脫離于現實、與現實無關甚或凌駕于生活之上,而是要在想象中指涉、再造或“寓言”現實、虛擬現實、混合現實。這也促使筆者在現實倫理等維度思考 “想象力消費”理論如何 “接著講”——與筆者關于電影工業美學 “接著講”的相關思考異曲同工,殊途同歸。
結 語
著名文學理論家韋勒克曾反思實證主義的機械性與批評的“懶惰性”問題,他犀利地指出, “無用的歷史考證,沉悶的事實羅列,與無政府的懷疑主義相聯系的偽科學以及批評趣味的缺乏等等,這樣一種研究,今天仍司空見慣。這種體系簡直太容易成為人們嘲笑的對象了。但是,我們必須承認,也許是因為有一種慣性吧,這種研究方法即使在今天也沒有消失。它對于那些迷戀其機械性精確和那種超然、不偏不倚風格的人,對于那些只不過是溫順、勤勉的人來說,它仍然有一種吸引力。”②勒內·韋勒克.批評的諸種概念(英文版)[M].康涅狄格州:耶魯大學,1963:299.轉引自孔耕蕻.論批評的理論化——對文學研究中純經驗描述主義的批判[J].文藝理論研究,1994(2):11-16.顯然,在當前互聯網新媒介時代——我們不能也不可繼續遵循一種機械的“強制闡釋”與“不偏不倚”不犯錯誤式空洞的廢話式闡釋;應該突破,也必須突破:不管這個突破將會面臨何種挑戰,哪怕頭破血流,也不可自縛于“理論的鐵屋子”里“自說自話”“囈語”喃喃。
我們應該清醒地認知想象力消費類電影長時間以來的高影響力,更應該在《流浪地球》等想象力消費類電影不斷崛起的當下,充分認知此類作品重要的社會價值、文化意義與產業價值。也正因如此,我們需要為這些常常被理論批評界所忽視、 “嫌棄” “不屑”的影視作品發聲、發言,為其尋覓、建構起真正屬于它們以及它們背后的青年消費群體、青年亞文化的理論體系。顯然,知識分子不應只是“高高在上”地進行批評,更應有馬克思所言的“關鍵問題在于改變世界”的啟蒙意識、人民意識、時代意識與問題意識。只有這樣,理論之樹才能常青,啟蒙精神亦可綿綿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