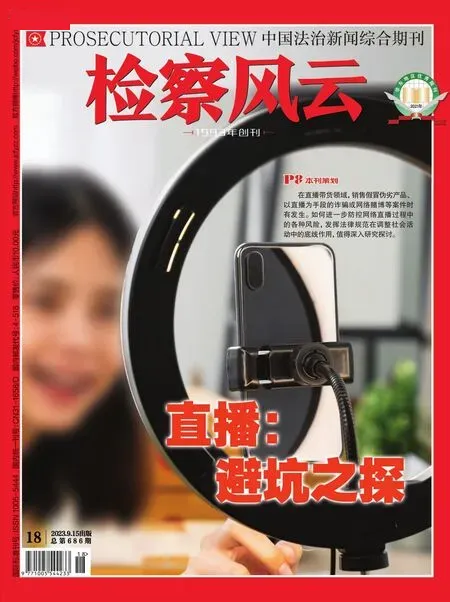輕微暴力致傷案件的罪與罰
文/龔笑婷

準確定性輕微暴力致傷案件
近期,最高檢和公安部聯合發布《關于依法妥善處理輕傷害案件的指導意見》,破除“唯結果論”,讓辦案過程呈現豐富的正義維度。在這一法治精神下,司法機關應著重審視輕微暴力致傷案件的定罪思路和辦案要點,確保同類案件法律適用的統一性和公正性。
入罪路徑
在社會生活中,人與人之間難免產生矛盾沖突,可能因此發生肢體上的暴力對抗,并忽視人的身體有時候很脆弱。輕微的暴力,在特定情況下也可能造成輕傷或更嚴重的后果。應當站在客觀歸責的立場,遵循從客觀到主觀,從違法到責任的犯罪認定過程。首先認定被告人的行為性質,其次考察該行為與結果的因果關系與歸責,最后分析被告人的主觀過錯,這樣才能準確定性。
歸責的前提是危害行為的存在,要判斷該行為是否制造出法所不容的風險。判斷的一個要素是法益侵害的緊迫危險性,即輕微暴力對他人的人身安全產生了緊迫的危險。
攻擊性行為究竟是一般毆打行為還是傷害行為,可以考查案發起因、雙方關系、毆打工具、毆打部位(如擊打耳朵容易造成鼓膜穿孔)、毆打力度和頻次、雙方體格(如對年老體弱者實施輕微暴力即可造成傷害)、外部介入、具體時空環境(如工地、道路等易發生事故的場所)等因素,立足于該行為實施時社會一般人的認識能力和水平,進而判斷該行為是否有損害他人生理機能的現實危險性。
在肯定了攻擊性行為的存在及風險結果的實現后,需要進行因果流程的判斷,即判斷結果的出現是否行為人所實施的“制造風險”的行為所引起的。此時如果能夠否定該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則可直接得出無罪的定性結論。如果能夠肯定該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那么就要對行為人的“有責性”繼續進行考察。
成立故意傷害罪,要求行為人具有傷害的故意,即對傷害結果具有認識和希望或放任的態度。如果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結果,并對之希望或者放任,則構成故意傷害罪;如果行為人對危害結果的發生有預見的可能性,但由于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或者已經有所預見但輕信能夠避免,則構成過失致人傷害罪;如果危害結果是由不能預見的因素引起的,即不存在預見的可能性,則為意外事件,不構成犯罪。
對因果關系的考察
輕微暴力案件多發于民間糾紛,往往存在雙方都有過錯,雙方行為共同致傷的情況,例如雙方在扭打中共同倒地致傷。行為人的行為并非導致最終傷害結果的唯一因素。理論上應著重厘清因果關系,以及各自原因力的大小,其判斷的是結果的原因歸屬問題。
第一種情況:輕微暴力行為是被害人受傷的主要原因。
在此類案件中,雖然涉案行為與被害人行為共同導致了傷害結果,但被害人行為主要是由涉案行為引發。對此應立足于案發時的具體條件,結合一般人在當時的情況下可能作出的反應去判斷。比如行為人欲掌摑被害人,被害人出手阻攔,雙方共同作用下導致被害人手指骨折。此時被害人受傷的結果系由雙方行為所導致,但被害人的行為系行為人的暴力行為所引發的正常反應。行為人的暴力行為原因力較大,應將傷害結果主要歸因于行為人的輕微暴力行為。
在輕傷結果下,如果客觀上該輕微暴力行為可以認定為刑法意義上的傷害行為,且主觀上行為人對傷害結果具有直接或間接的故意,即認識到可能發生輕傷結果,則直接認定其犯故意傷害罪;如果行為人意在造成被害人暫時的肉體疼痛或輕微的神經刺激,則不能認定為有傷害的故意,即不構成犯罪。
在重傷結果下,故意傷害罪中的“故意”并不要求行為人對傷害的具體程度有所認識。只要行為人具有傷害故意,且輕微暴力行為最終造成了重傷結果,由于行為人的行為是主要原因,因此可以認定其犯故意傷害(致人重傷)罪。
如果行為人沒有傷害的故意,則要考慮行為人對重傷結果是否具有預見的可能性。如果是應當預見而沒有預見,或者是過于自信而沒有采取防范措施,那么以過失致人重傷罪論處;如果不存在預見的可能性,則屬于意外事件。
第二種情況:被害人行為是傷害結果的主要原因。
這是指被害人的行為成為獨立的危險流,且對結果的發生起到了較大的作用。例如行為人對被害人施加了輕微的暴力,被害人直接上前毆打行為人,在撕扯中摔倒致傷。此時,被害人實施毆打的行為并不是行為人引發的正常反應。被害人的行為是獨立的,屬于異常的介入因素。根據危險的現實化理論,介入因素的作用較大,因此傷害結果是介入因素制造的危險的現實化結果。這樣一來,就不能將傷害結果歸因于行為人的輕微暴力行為。
致人摔倒或磕碰受輕傷的定性
被害人摔倒或者磕碰受輕傷,即并不是涉案行為直接導致傷害,對此類案件定性應當抓住“行為危險性”這一關鍵詞。首先判斷涉案行為是否制造出對人身安全法益侵害的緊迫危險,再判斷行為人主觀上是否認識到行為危險性的存在,最終進行有責性考察從而綜合判斷。當然,前提是該行為屬于故意傷害罪中的傷害行為。
考察行為人對行為危險性的認識,要綜合案發時的多重因素。首先,行為人能否認識到涉案行為有造成對方摔倒的可能性。一般來說,向前猛推、猛拽衣領、鏟腳等行為極易使人因重心不穩而摔倒。行為人本身在實施此類行為時,可能帶有致人摔倒的目的,一般人也能夠對后果有明確認知。其次,行為人是否能認識到被害人的特殊身體狀態,例如腿腳不便的人、老年人、兒童、體弱者等,此類特殊人群本身就容易摔倒磕碰。
此外,還應當考察現場環境。如爭執發生在馬路邊、行進的公交車上、石子路面上等極易摔倒遭受磕碰的場合,行為人對現場環境有明確認知的,可以認定其具有故意心態。
對案件事實的還原從來不是單一的、平面的,而是多維度、立體化、全過程的,對涉案行為的危險性也應當基于全案的多個因素去做整體性評價,才能得出準確的結論。
出罪與化解
輕微暴力致輕傷案件進入司法環節后,如果在偵查、檢察環節能夠實現矛盾的化解,對于犯罪情節輕微、社會危害性不大的,檢察機關可以綜合運用檢調對接、不捕不訴、釋法說理等手段予以妥善處理。當案件進入審判環節后,從司法實踐來看,對于無刑事處罰必要性的案件,過往判決多用刑法中的“但書”條款予以出罪,但適用的標準不一。“但書”條款將未達到實質可罰性的行為排除在犯罪之外。對“但書”的解釋重點在于“情節”與“危害”的內容,應當結 合主觀惡性、客觀行為、認罪態度、賠償情況、被害方的情況、矛盾化解、社會輿論等,綜合評判其行為的不法性和有責性。
在當前的刑事政策理念之下,在關注刑事手段的實體價值之外,也應當關注其程序價值和手段價值,從而促使矛盾化解,避免次生傷害,最終達到罪責刑相適應,社會矛盾充分化解的結果。
對此類案件是否作出罪處理,需要司法機關在辦案的過程中綜合考量,不僅要對犯罪構成作出規范性評價,還要基于矛盾化解、修復司法的理念作出價值判斷。對于情節顯著輕微、主觀惡性不大、已經賠償和解、社會矛盾已經化解的案件,可以適用“但書”條款予以出罪。而對于部分情節較為惡劣、社會矛盾尚未修復的案件,予以出罪則要特別慎重。同時應該考慮到被害人的傷害結果伴隨而來的是經濟、家庭、職業、生活的多重困難和壓力,民事途徑的救濟畢竟有限。在刑事處理的過程中,可以敦促行為人以及相應的組織、集體共同承擔矛盾化解責任,更好地緩解被害人的困難和壓力。
總體來看,準確定性、適當處理輕微暴力致傷案件,能夠達到修復社會關系、實現公平正義的最終目的。這也體現出司法機關踐行司法為民,傳導法律溫情的價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