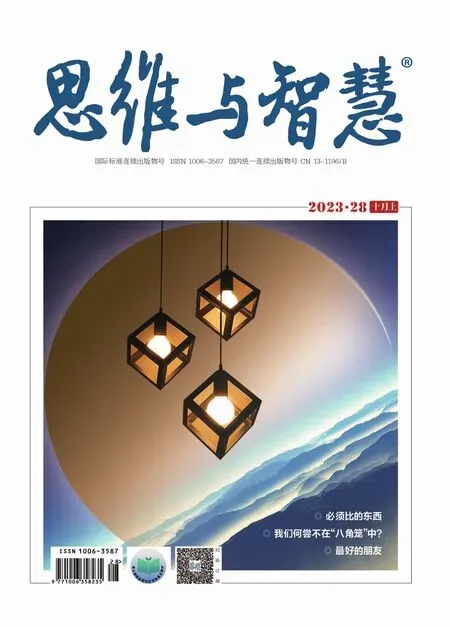技術的白刃滑過時間的粗手
◎ 甘正氣

我喜歡坐飛機。
不是因為航站樓比候車廳漂亮,也不是因為能吃到好像免費的午餐,更不是為了更加悅耳的聲音、更加悅目的風景,而是因為只有坐飛機時,我才可以心安理得地關上手機。
這時我關機不是為了屏蔽加班通知,不是為了逃避債主,躲開掮客,不是為了遁藏我參謀、顧問、知事、學長、前輩、寫手、編輯的身份,我關機是為了整個航班的安全,是為了全體乘客和機組人員的共同利益,所以這個手機我關得正大光明、理直氣壯,關得問心無愧、堂而皇之,關得大義凜然、正氣浩然,所以關上手機時,雖然早已不是翻蓋、滑蓋手機,我都仿佛能聽見一聲無比清脆無比利落的吧嗒聲。
只有關上手機后,時間好像才真正屬于我自己,我可以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顧,把帽檐拉下來,衣領翻起來,身子蜷起來呼呼大睡,拿出紙,抽出筆,寫寫畫畫、涂涂改改,職責、義務先放一放,天職、使命暫緩一緩。
民航的發達為我節約時間,讓我更快抵達目的地;而飛行中要關閉手機,讓我終于可以安靜一會兒。航空技術讓我更像時間的主人;但是發達的通信技術,又常常讓我做了時間的奴仆,時間之手順著信號抓住我,摟住我,拖拽我,我像被困在拳擊場上,時間像拳王泰森一樣對我全場壓制,讓我似乎無處可逃。
《飛鳥集》中有一句詩:“樵夫的斧頭,問樹要斧柄,樹便給了它。”時間被技術擠壓、勒索,我們也只能以技術的刀斧為自己砍出一片陽光下的開闊地。時間之手雖長,但在他粗大的手指之間,技術讓我們能夠從他的指縫里鉆出來吐一口氣。
我們在手機上辦稅,在電腦上辦公,我們視頻開會,我們網上購物,我們讓電器做家務,讓導航做向導,汽車可以“無人駕駛”,測試可以無人監考,評分可以機器閱卷,炸彈可以讓無人機運載投擲,地雷可以讓機器狗探測排除,這時,技術又讓我們從簡單、重復、瑣碎、危險的時間沼澤里脫身。我們不再深陷泥淖,不再被污泥湮沒頭頂,只冒出幾個半球形的透明的泡。
技術仍然誘惑著我們。海量的小游戲、小視頻比比皆是,他們張開如刀似戟的黑手要來侵占我們的人生,一點進去幾個小時就不知不覺溜走,靜靜地,悄無聲息地,“日月逝于上,體貌衰于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或許我們只能像奧德修斯一樣,面對塞壬女妖們優美誘人的放歌,高聲疾呼:“給我綁上更多的繩索!”或者像辛棄疾,“以手推松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