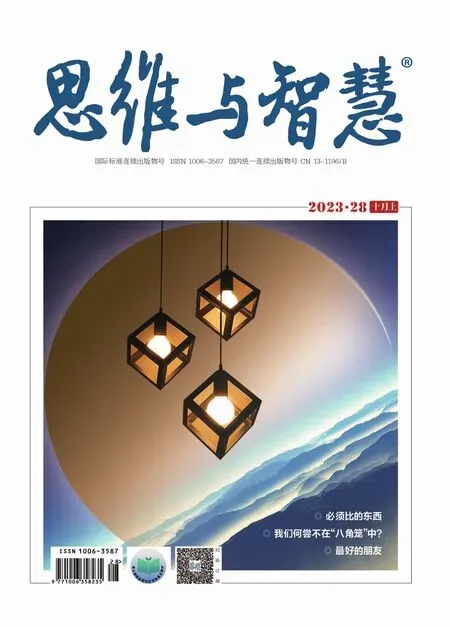食 聲
◎ 草 予

世人皆需食稻粱,也在為稻粱謀。一飲一食,不僅是一種需要,也是一種信仰。
人間至味,夸到上上等:色香味俱全,關照了眼、鼻、舌,沒有耳,有意也無意。大概吃事上,耳是無足輕重者,貢獻不及唇齒,愉悅不及鼻舌。
其實可以喊喊冤。煎、炒、熗、炸、燉,樣樣聽得見,甚至腌、糟、釀、醬、風,也能聽得見。入口之前,耳已飽餐。
吃事上,也唯有聲,貫穿始終。
遙遙聽見一聲吆喝:好甜的瓜,好嫩的菜喲,還不見人影,先已舌尖生津,那甜,那鮮嫩早從耳入口了。王婆賣瓜,自賣自夸,自然要夸,不可不夸,夸是讓瓜甜飄到耳朵里,甘心情愿大包小袋買回來。
香,其實也是“聲”,無聲的聲,透明的聲。祭天祭祖,食物的香氣上了天,也就把味道送達天上。炊煙幢幢的日子,望見自家房上白煙通天,就好像聽見灶下柴火燒得噼啪作響,鍋里吱吱啦啦叮當一串。野孩子瘋在拐拐角角,也知道該回家了,母親不需出面。
兒時一到夏天,豇豆便拿下餐桌上的半壁江山。對付那青綠色的絲絳,母親從不借刀,總是用手掰成寸段,溫柔待它。老過頭的豇豆,只有兩層皮,撕開了,食其豆,瓦紅色,那么疏疏幾粒。那時,最喜歡聽“絲絳”寸寸斷,清清脆脆,沒有刀斧氣。
肉類只得用刀,切成絲,切成塊,切成片,厚切,薄切,順紋切,逆紋切,聲音全不一樣。老友家的貓,愛吃生肉。刀肉相見,貓已在腿間左蹭右磨,急不可耐,耳朵靈極。在這之前,那只貓還在窗臺,睡成一攤液體。
七碗八碟碼齊,蔥姜蒜各就各位,熱鍋起油,轟轟烈烈就起來了。煎炒蒸燉,一類烹調一路動靜,一個廚房一種風格。廚房的門閉著,人在客廳坐,只聽聲響,幾葷幾素幾菜幾湯,也猜得八九不離十。
做飯的人,酒菜上桌已覺不餓,因為耳和鼻一直沒歇。
大吃,小吃,聲息也有區別。大開大合的席面,觥籌交錯,你為我斟酒,我為你添杯,眼前明明晃晃幾口熱爐,沸湯咕嘟咕嘟冒氣。席面越大,席面越是意義所在,吃什么不重要,吃個場面與氣氛。家常飯,往往吃得安靜,一人貪杯,也自斟自飲無人勸,有一搭沒一搭的家常話。
忘了在哪里看過,一個人忽然饞起醋來,買了一瓶老醋站在路邊喝,咕咚咕咚落肚,喝得眼淚流了下來。只覺得那呷醋的聲音很感動,那眼淚也流得轟隆大作,能叫人這般饞的,大抵也只有故鄉了。
吃事結束,殘湯剩水,杯盤狼藉,收拾起來也是乒乒乓乓,是個續曲尾聲。身邊有人愛洗碗,只因對這續曲著迷。愛洗碗的人,比愛做飯的人更顧家。
食聲,也為吃個響,聲音比滋味誘人。很多地方腌蘿卜,必須脆,脆才得味,震得齒牙抖擻。聽說有道地方菜,名即響肚,吃來咯吱有聲,遠近可聞。零嘴嚼頭,一聲脆也招人喜歡,聲音就是招牌。食家前輩汪曾祺,發明塞肉回鍋油條,油條切成寸半長小段,用手指將內層掏出空隙,塞入肉茸、蔥花、榨菜末,下油鍋重炸。口感酥脆,“嚼之真可聲動十里人”。聲動十里,香味只得自嘆不如。
等自己老了,大油大鹽都不想了,當然,五臟六腑也不答應。那時就喝白粥就咸菜。偶爾饞蟲上來,跑去灶間聽一回煎炒烹炸蒸煮燉,洋洋盈耳,也算解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