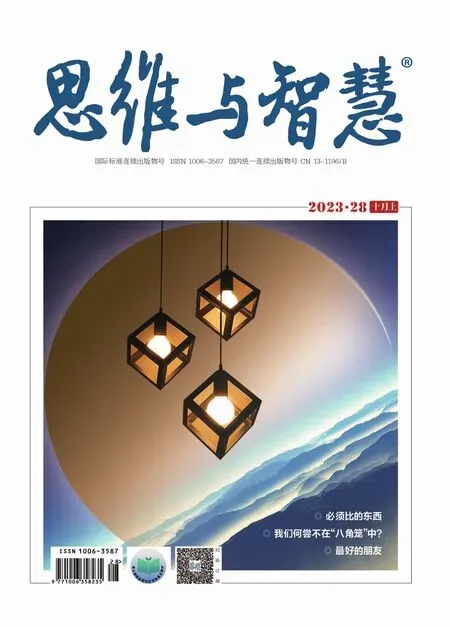草垛睡在鄉土的漣漪里
◎ 錢國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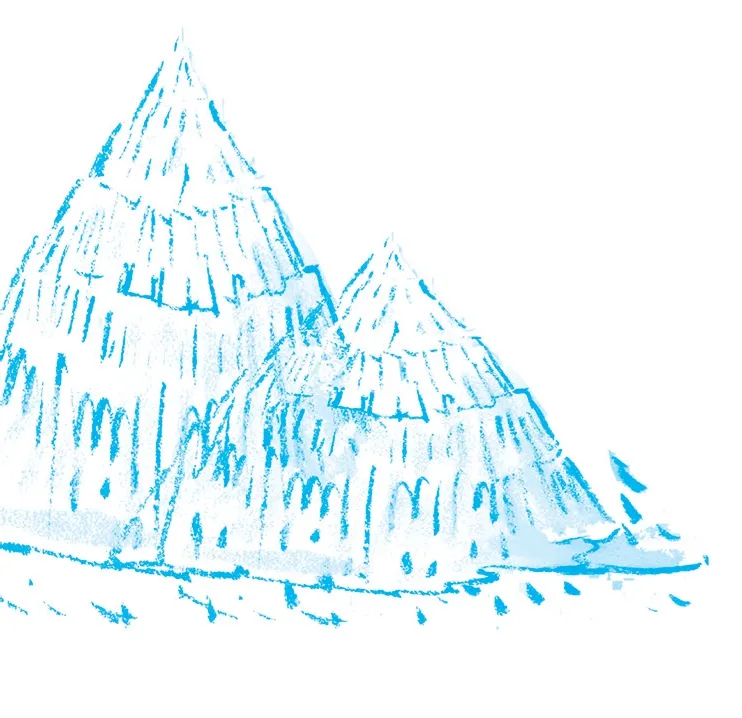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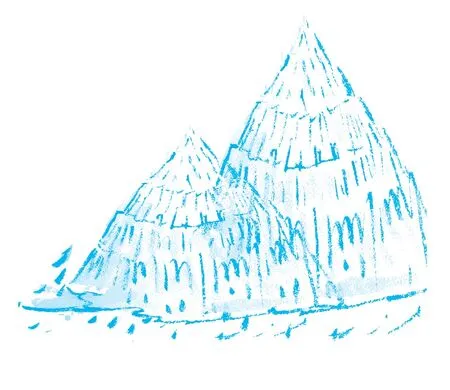
金黃湛亮的草垛碼在鄉村里,如一個個彌漫草香的夢境,植入五谷六畜的深處;又如一枚枚碩大的太陽,流淌在村莊的血管里,溫暖著鄉村的四季,并以其高貴的卑微彰顯著生命的張力。
草垛是莊稼人眼中一道平素的風景。夏季歇涼的時候,男女老少喜歡坐在草垛旁邊,嗅著清清的草香,侃些鄉土逸事;晚飯后,草垛旁人頭攢動,笑語聲喧,勞累了一天的鄉親們圍坐在一起,談論一些家事國事。談著談著,便有疲憊的漢子沐浴著清泠的月光,枕著干草,酣然入夢;放學的孩子,喜歡搬個小桌,圍在一起寫作業。這個念,那個寫,一臉的稚氣換上了嚴肅的神情,以至于把這里當成“賓館”的母雞和它的孩子們,都敬畏地遠遠避開,生怕攪了這里的寧靜和莊嚴。作業完成后,草垛便熱鬧起來,孩子們把這里當成了戰場,你上我下地相互追逐、打滾,喊殺陣陣,卻又不見硝煙,個個臉現紅光,額頭沁汗——與干草這樣的植物親近,通體康泰呢!
草垛是鄉村版面上發表的頭條新聞。秋收過后,麥草、稻草被扎成捆,一列列碼在空曠的田野里,頗有“沙場秋點兵”的意境。秋陽如烈酒,幾天的工夫就把草捆醉出足金的成色,套上車,拉回村,碼成垛。在農家院里,堆草垛是一項看似簡單實則頗有講究的技術活。父親生前是把堆草垛的好手,經他手堆的草垛結實,棱角分明且不蔓不枝,任你在上面滾上幾個來回也不會“滾包”、倒塌;也好看,遠遠望去,竟有著《幾何學》中圓錐體的優雅弧線。夕陽中,草垛披一身霞光,靜靜地臥在村莊里,流光溢彩,莊嚴肅穆,任畫過《干草垛》《睡蓮》的法國著名畫家莫奈也會心醉神怡。
草垛是鄉村最美的感性載體。進入深秋,最愜意的事是拋開一切塵間瑣事,靜靜地躺在草垛上,看夕陽。向晚的風柔柔地吹著,草垛散發出的清香與悠閑的童年一起,定格在黃昏的底片上,成為珍藏在記憶深處的如詩畫卷,就連草屑鉆進袖筒里、脖子里的那種刺癢,也讓人難以忘懷。倦了,就在歸鴉的聒噪中,懶懶地閉上眼睛,小寐。在草垛中睡覺,是頗有情趣的,那松軟熨帖的干草像柔嫩的玉指,輕輕地按摩著肌膚,癢絲絲、麻酥酥,一如飲了瓊漿玉液,通體洋溢著難以言表的愜意——四體綿軟,玉山將傾,心游萬仞,且夢莊生。
草垛是鄉村最終的歸宿。在北方的鄉村,老人作了古,都要埋在草垛旁或接近草垛的地方,墳頭上還喜歡放一把干草——不是逝者生前怕冷,而是一種風俗。這種風俗里蘊含著深深的寓意:與青草相濡以沫的農人,一代又一代,都不會離開青草,離開植物,這是一種宿命,更是一種繼承。先人走了,后人會主動接過先人的土地和農具,接過先人的性格和追求,把平凡如稻草的日子一層層堆高、碼實。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前不久回老家,一進村口,就看見了散落于街巷的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草垛,它們如一枚枚音符,歌唱著鄉村,歌唱著五谷輪回。公雞叫了,草垛醒了,灶膛亮了,炊煙高了,太陽紅了………多么樸素清新的早晨,多么寧靜溫馨的日子!在這如詩如畫的空間里,草垛,像一位將軍,指揮著鄉村風塵仆仆,一路向前——草垛前面,是一張張樸實的笑臉;草垛后面,是一片片和諧的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