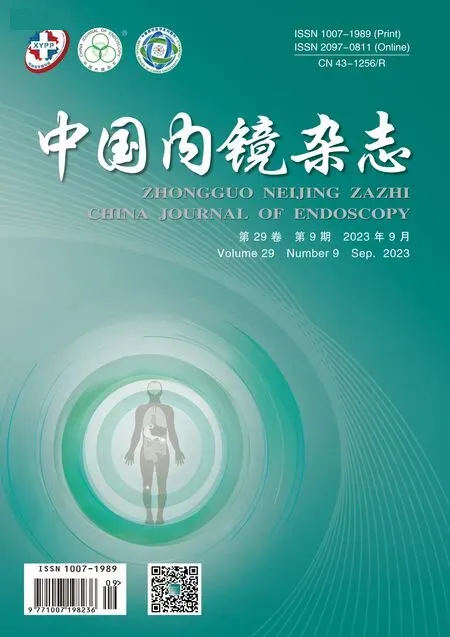超聲內鏡檢查術診斷消化道黏膜下病變的回顧性分析
鄒傲,王俊萍,楊莉麗,郭海,李曦,鄒兵
(北京大學深圳醫院 消化內科,廣東 深圳 518036)
消化道黏膜下病變(submucosal lesions,SML)經常在普通內鏡檢查中發現,但因其表面外觀與正常黏膜一致,普通活檢很難明確其性質,更是無法判斷其實際大小和起源。超聲內鏡檢查術(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EUS)通過觀察消化道管壁層次的回聲變化,分辨SML 與周圍組織的關系,確定病變的實際大小、起源層次、侵犯深度和是否為壁外壓迫,甚至可判斷其是否有潛在惡性變化等[1],聯合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或彩色多普勒能量圖一起使用,還可評估來自SML的血管信號,從而區分血管結構和囊腫,評估病變的血供[2]。本研究總結了病例在白光內鏡、EUS和病理等方面的特點,以探討EUS與病理診斷的符合率,旨在評估EUS在消化道SML診斷中的價值。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回顧性分析2020 年1 月-2021 年12 月在北京大學深圳醫院診治的142 例消化道SML 患者的臨床資料,包括:普通內鏡、EUS、病理報告和隨訪資料等。其中,男72例,女70例,年齡27~69歲,平均(46.3±11.5)歲。所有SML 均行普通內鏡和EUS 檢查,部分病例補充腹盆腔CT 或體外超聲檢查,根據患者意愿及病情,選擇內鏡或手術切除,并對術后標本行病理學檢查和免疫組化檢查。
1.2 EUS檢查
根據常規內鏡檢查結果,選擇性使用微型探頭(20 MHz)或線性陣列超聲探頭(6.0~7.5 MHz)。采用脫氣水充盈法確定病灶位置后,測量病灶大小,確定病灶的起源及回聲特征,并在多普勒模式下,使用超聲設備檢測血流、速度和方向。
1.3 治療方法
SML位于黏膜層、黏膜肌層和黏膜下層者,行內鏡下治療,如:冷切除、內鏡下黏膜切除術和內鏡黏膜下剝離術。對于瘤體>2 cm、位于固有肌層和向腔外生長者,行內鏡黏膜下腫物挖除術、胃鏡與腹腔鏡雙鏡聯合或腹腔鏡手術治療。
1.4 病理學檢查
所有病理組織在本院病理科行蘇木精-伊紅染色,采用鏈霉菌抗生物素蛋白-過氧化物酶連結法對相關標本進行免疫組化染色(CD117、CD34、DOG-1、SMA、Desmin、S-100、Syn、CagA和Vimentin)。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5.0 軟件統計數據。計數資料以例(%)表示,組間比較行χ2檢驗,P<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不同部位SML的一般情況
142 例SML 中,食管病變33 例(23.2%)。其中,上段5 例,中段17 例,下段11 例。胃部病變67 例(47.2%)。其中,胃底22例,胃體25例,胃竇18例,胃竇-胃角交界處及賁門-胃底交界處各1例。十二指腸病變17 例(12.0%)。其中,球部9 例,降部6 例,球降交界處2 例。下消化道病變25 例(17.6%)。其中,回盲部2 例,結腸6 例,直腸17 例。不同部位SML 患者的性別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年齡分布方面,本組病例40 歲以下患者的發病率為40.8%(58/142),41~60 歲患者的發病率為51.4%(73/142),60 歲以上患者發病率僅占7.7%(11/142),不同部位SML 患者各年齡段發病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不同部位SML病變起源于黏膜層和外壓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0.05),病變起源于黏膜肌層、黏膜下層和固有肌層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0.05)。見表1。

表1 不同部位SML患者的一般情況比較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SML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sites
2.2 EUS診斷
本組142 例SML 中,135 例實體 瘤,7 例壁外壓迫。實體瘤中,EUS 診斷黏膜層病變14 例,黏膜肌層病變20例,黏膜下層病變62例,固有肌層病變39例。其中,食管和胃部病變以固有肌層病變為主(26.7%,36/135),十二指腸及下消化道病變以黏膜下層病變為主(23.7%,32/135)。對于黏膜層病變、黏膜肌層病變、黏膜下層病變和固有肌層病變,EUS的診斷準確率分別為:100.0%、100.0%、95.0%和89.7%。EUS診斷平滑肌瘤30例(21.1%),間質瘤29例(20.4%),神經內分泌腫瘤25 例(17.6%),異位胰腺15 例(10.6%),息肉14 例(9.9%),脂肪瘤11例(7.7%),囊 腫9 例(6.3%),壁外壓迫7 例(4.9%),顆粒細胞瘤2例(1.4%)。
2.3 病變部位分布
142例消化道SML中,息肉平均分布于上、下消化道;囊腫好發于食管(5 例)和十二指腸(4 例);異位胰腺多見于胃(10 例)和十二指腸(5 例);平滑肌瘤多見于食管(19例)和胃(11例);顆粒細胞瘤僅見于食管(2例);脂肪瘤好發于胃(5例)和大腸(4 例),十二指腸次之(2 例);間質瘤好發于胃(25 例),食管(1 例)、十二指腸(1 例)和大腸(2例)較為少見;神經內分泌腫瘤常見于大腸(15例),胃次之(8 例),十二指腸(2 例)較為少見;壁外壓迫多見于胃(3 例)、食管(2 例)和大腸(2例)。
2.4 EUS回聲特點
息肉表現為:起源于黏膜層、突向腔內和邊界清晰的中高回聲光團。囊腫表現為:起源于黏膜或黏膜下層,單個或多房樣和薄包膜壁的無回聲光團。顆粒細胞瘤、脂肪瘤、異位胰腺和神經內分泌腫瘤大多起源于黏膜下層,顆粒細胞瘤和神經內分泌腫瘤均表現為:邊界清晰的低回聲光團,不同的是,前者可能回聲欠均質;脂肪瘤為厚包膜壁的均質中高回聲光團,異位胰腺亦可生長于黏膜層或肌層,為內嵌脈管樣結構的混合回聲光團。平滑肌瘤多起源于黏膜肌層或固有肌層,回聲低,質地均一,病變兩端可有“觸角”樣結構與肌層相連。間質瘤多見于固有肌層,回聲低,質地欠均質,無明顯包膜回聲。壁外壓迫可見消化道管壁結構回聲正常,病變起源于腔外。
2.5 術后病理
本組142 例消化道SML 中,107 例行內鏡治療或手術切除后送病檢,99例病理與EUS診斷相符,EUS總體診斷準確率為92.5%(99/107)。其中,息肉、囊腫、顆粒細胞瘤和脂肪瘤的EUS 診斷準確率為100.0%。25例神經內分泌腫瘤中,19例切除后送檢,病理診斷1 例異位胰腺,EUS 診斷準確率為94.7%(18/19)。15例異位胰腺中,9例切除后送檢,病理診斷1 例神經內分泌腫瘤,EUS 診斷準確率為88.9%(8/9)。30 例平滑肌瘤中,26 例切除后送檢,病理診斷1例錯構瘤,2例間質瘤,EUS診斷準確率為88.5%(23/26)。29 例間質瘤中,21 例切除后送檢,病理診斷1 例神經鞘瘤,2 例平滑肌瘤,EUS 診斷準確率為85.7%(18/21)。7 例壁外壓迫中,2 例EUS 診斷為縱隔占位,術后病理診斷為食管支氣管源性囊腫;另5例EUS 分別診斷為:脾臟外壓2 例,肝臟外壓1 例,子宮肌瘤2例,經其他影像學檢查輔助確診,EUS診斷準確率100.0%。
3 討論
3.1 EUS的臨床應用
EUS可以通過區分消化道管壁的層次,以確定病變的起源層次,有助于評估下一步的手術方式(內鏡手術或外科切除)[3]。EUS 可以通過顯示胃腸道SML的超聲特征,如:起源層次、大小、邊界、回聲均勻性和是否存在回聲等,診斷病變性質[2]。本組EUS診斷黏膜層病變14 例,黏膜肌層病變20 例,黏膜下層病變62 例,固有肌層病變39 例,EUS 對上述病變的診斷準確率分別為:100.0%、100.0%、95.0% 和89.7%。HERNANDEZ-LARA 等[4]認為,EUS 預測起源層次和組織學的總體準確率分別為:88.0%和96.0%。本組EUS 與病理診斷符合率為92.5%,與文獻[4]報道大體一致。美國消化內鏡學會[5]也認為,EUS是評估SML 起源層次、大小、內部回聲性、邊界和回聲紋理的最有價值的診斷方法。
3.2 EUS在消化道SML診斷中的價值
3.2.1 診斷SML 的起源層次 在區分消化道SML為壁內病變還是腔外壓迫方面,EUS的鑒別作用尤為突出。有研究[6]表明,EUS 高頻探針診斷SML 的準確率(92.6%)很高。R?SCH 等[7]研究顯示,EUS 對黏膜下腫物與腔外壓迫的鑒別診斷準確性明顯優于普通內鏡,兩者的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92.0%和87.0%、100.0%和29.0%。ZHANG 等[8]報道,在內源性病變及外源性壓迫的鑒別診斷方面,EUS(100.0%)明顯優 于體外超聲(22.0%)和CT(28.0%)。本組142例SML中,EUS診斷135例壁內腫物,7例壁外壓迫,鑒別壁內腫物和腔外壓迫的診斷準確率為100.0%。
3.2.2 評估病變性質 EUS除了可以判斷SML的起源層次外,還可以根據起源層次對病變性質進行評估。有文獻[9]報道,EUS 通過觀察病變的起源層次診斷間質瘤(固有肌層)和平滑肌瘤(黏膜肌層)的敏感度為94.4%,但特異度較低(< 60.0%)。有文獻[10]對比了EUS 與盆腹腔CT 對SML 的診斷準確性,結果顯示:EUS對胃腸道間質瘤、平滑肌瘤和異位胰腺的診斷敏感度明顯優于盆腹腔CT,EUS 誤診的病灶多為固有肌層病變(如:胃腸道間質瘤)。本組EUS 對黏膜肌層和黏膜下層病變的診斷準確率較高,考慮原因為:EUS的高頻探查,在微小SML及鄰近消化道表面病變診斷中具有優勢。而固有肌層病變的內鏡超聲特點,存在一些共性和非特異性,是造成EUS對此層病變的診斷準確率較低的主要原因。PARK 等[11]研究發現,71.0%的胃神經鞘瘤可表現出與固有肌層相似的回聲特點。本組EUS對第四層病變出現了誤診,也是由于病理診斷出2 種少見的固有肌層病變所致,如:神經鞘瘤和錯構瘤。
3.2.3 判斷SML 的性質 EUS 對SML 的大小、邊緣、回聲及是否有囊性或鈣化性改變的判斷,可縮小鑒別診斷的范圍,還可通過顯示病變的典型超聲特征來判斷SML 的性質[12-13]。CHU 等[14]以異質性、高強度、腫瘤內高回聲斑和腫瘤周圍邊緣高回聲暈等4個EUS特征,評估黏膜下腫物的性質,EUS診斷的靈敏度達89.1%。一項EUS引導下的鑒別診斷評分系統研究[15]顯示,間質瘤大多位于胃底和胃體,賁門病變大多是平滑肌瘤,脂肪瘤、異位胰腺多見于胃竇。一項針對709 例上消化道SML 的回顧性研究[16]提示,EUS對上消化道SML起源層次的診斷準確率為88.2%,與病理診斷的符合率為80.1%,其對脂肪瘤和異位胰腺的診斷準確率(97.0%和96.8%)最高,但對間質瘤的診斷準確率僅為63.0%。本研究以EUS特點為判斷標準,評估SML時,EUS對脂肪瘤和神經內分泌腫瘤的診斷準確率稍高于平滑肌瘤和間質瘤,原因可能為:相較于普遍呈低回聲改變的固有肌層病變,SML的EUS特點更具特異性。胃腸道間質瘤作為固有肌層病變中最易誤診的一種病變類型,因其具有較高的惡性轉化潛能,如何進行鑒別診斷,就顯得尤為重要。KIM等[17]認為,異質性、非賁門部位病變和高齡是胃腸道間質瘤的獨立預測因素。利用年齡、性別和4個EUS因素(同質性、腫瘤位置、回聲間隙、凹陷或潰瘍)建立的預測模型,有助于鑒別胃腸道間質瘤與平滑肌瘤,此方法可在不獲取病理標本的情況下,對SML的性質作出一定判斷[17]。有研究[18]顯示,以回聲不均勻、大小 > 3 cm、邊緣不規則等3個超聲特征為判定標準,EUS診斷惡性胃腸道間質瘤的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80.0%和77.0%,如出現吞咽困難、胃腸道出血、疼痛和體重減輕等4個臨床表現,提示間質瘤有惡變可能。KIM 等[19]認為,出現異質性、高強度、高回聲斑點和腫瘤周圍邊緣暈4種超聲特征中的2 種,EUS 診斷胃腸道間質瘤的靈敏度和特異度可達89.1%和85.7%。這種高敏感度強調了EUS 對指導手術選擇的重要性,而部分間質瘤即使完成了病理組織學和免疫細胞化學檢查,也無法完全鑒別[18]。另有文獻[2]報道,固有肌層病變如存在下列EUS 特征,如:病變較大(r ≥ 20 mm)、低回聲、異質性、分葉、鈣化和局部囊性變等,需考慮有惡變傾向。
綜上所述,EUS 在消化道SML 的診斷中意義重大,尤其是微探頭超聲(頻率12~20 MHz)對胃腸道微小病變(< 5 mm)的探查優勢明顯。在分辨病變與周圍組織的關系、鑒別壁內腫物或壁外壓迫方面,EUS 明顯優于腹部CT。EUS 對SML 病變起源及深度的判斷,能為病變選擇合適的治療方案提供指導。但EUS對操作者有一定的技術要求,EUS特點的判斷有時受操作者主觀因素的影響,超聲波對組織穿透性的局限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EUS 診斷的準確性。因此,SML的最終診斷還需結合患者的臨床表現、其他影像學檢查及病理特征等,以進行全面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