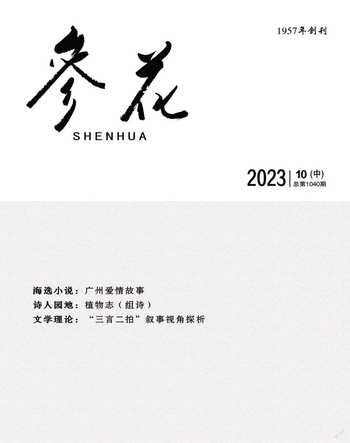與老屋重逢
回鄉辦事前,父親再三叮囑我路過老屋時一定要多拍點照片。于是我頂著盛夏的烈日,回到了相隔將近兩千公里,且離去已有十多年的故鄉。
夏日的鄉間小道上,知了在枝頭頻頻叫著。烈日炎炎,我不免有些心焦氣躁。站在山坡上朝下一望,遠處幾個蕭索的村落就那樣落在正午炙熱的陽光下,它們好像也被這太陽曬得毫無半點生氣。眼中的場景與兒時的記憶相撞,我愣了好一會兒才想起回鄉的路。
村里人影稀疏,走了很久也看不到熟悉的面孔。終于走近那間老屋時,我遲疑地停下了腳步。恍恍惚惚間,十余年過去了,這間老屋的身上長滿了爬山虎,遠遠望去,就像是一道長滿皺紋的綠墻。原來我長大了,它也老了。
我躊躇向前,生銹的門鎖被我拉開,低頭邁進大門,曾經覺得無比高聳的房屋,如今再看竟也沒那么高了。而那些被關在門內的記憶,也隨著這扇大門的打開把我撞得踉蹌。我太久沒看到它了,以至于我與它重逢時,那些心底的故事連帶著十幾年的漂泊感全部在心間洶涌奔騰。
就是這間屋子,父親在這里結婚,我在這里出生,祖父在這里終老。我們一家三代人在這間老屋里度過了無數個日月。
記憶里,農家人很是重視節氣,他們總是按照節氣有條不紊地進行著一年的勞作。幼時的我卻把這些日子簡單地分為抉擇的春天、等待的夏秋,以及重逢的冬日。春天的到來不僅代表著莊戶人家一年的勞作要開始了,同時也把新一年的抉擇帶到了家家戶戶的面前。
是去遠方開拓,還是在故鄉留守?這樣的抉擇問題,在每年春節后,都會如期來到祖父與父親面前。而祖父與父親之間似乎有著默契,他們并不用商量,于是每到春天來臨時,祖父握住手中的種子,灑向無邊的原野,父親則背上行囊,走向遙遠的他鄉。他們在春天里總是很快找到自己守候或者開拓的位置。
至于我,我在春日的這場抉擇里默選了守候。我總在春日里與祖父在故鄉的一隅,望著父親遠去的背影。那時,我還來不及體味離別,便要明白守候的故事。祖父比我更懂得如何去排解因守候而到來的孤獨,他撫摸著我的鬢角告訴我,只需到冬日春節,他們便會再次回來。
我問他,冬天要多久才能來呢?他說,要經過夏秋兩季的等待與守候。
我還是不解地追問,如何去等待與守候呢?
他為我抓來了幾只小鴨子,他說:“你看啊,等這些小鴨子長大,他們就回來了。”我低頭不語,沒有回答。他繼續說:“你看啊,這院子里的樹長出柿子的時候,他們就快回來了。”我掃了一眼院中柿子樹上的新芽,念念有詞:“還有呢?”祖父指了指門后那無邊的田野:“你看啊,這田野里的稻子被大雪蓋住的時候,他們就回來了。”
從此,我的守候有了故事。
相比我的守候,祖父總是沉默著低頭勞作,恨不得將自己的全部身子埋進這一方水土之中。老屋的后面是他開辟出來的一大片菜地,因為臨河,每到夏日,河面上的風拂過菜園時,會給老屋帶來滿園清香。清晨的菜園里,祖父的身影似乎蒼老得像匍匐的樹根,銀發隨著他的動作飄揚在那片青山綠水之間。當清晨的煙霧散盡之時,祖父便走向他的田野。他勞作累的時候,就會站在田埂之上,笑望著土地哼起他的黃梅調,他干涸的臉上露出的那長長的皺紋,儼然融入了腳下的黃土地里。
秋日,祖父又去原野里打草。他揮舞著長長的鐮刀,將那牛尾草斬斷。隨著他的動作,被鐮刀斬斷的,還有時光。他知道秋日已至,離家的孩子們可以細數歸期了。于是他將那些牛尾草拿回老屋,在落日斜陽里,用他粗糙的手做出一把把掃帚。
到了冬天,他走向山丘,迎著陣陣冷風凝望遠方。他在看那通往縣城的馬路上是否有他歸家的孩子們。祖父干枯的手托著和他一樣蒼老的煙袋,他的雙手在寒風里靜默細數這一年中最后的時光。那手上布滿的裂紋,是守候的歲月贈予他的年輪。這些年,他與這土地融為一體,他的身體里有著這片土地上的一切,那些傳奇故事,那些鄉間小調,那些東南西北風,都是祖父低頭守候的一生。
歲月流轉向前,我在這間老屋里選擇開拓。我不記得守候的日子有多久,久到我也慢慢地適應將自己的身心全部投入這片土地,久到我以為我會像祖父一樣在這片土地上長出根芽。后來祖父摸著我的頭,他告訴我,我該走出去了,我們的家族應該有一個大學生。隨后,我懵懂地從春日里的老屋出發,去往了新世界。身后的老屋就像當年望著父親離去那樣不言不語。
開拓不需要沉默與等待,它意味著勇氣。當我走出那片土地時,新世界的風從我面前呼嘯而過。我抬頭隨風望去,便只見高樓大廈、五彩繽紛、人來人往。而我卻像脫離了蛋殼的雛鳥一般,惶恐地看著嶄新的世界。
邁出故土后,還有更遠的路要去前行,這些都要勇氣:學會普通話、融入新世界、咬牙堅持。我曾將那些怯弱化作課本上的習題、作文本上的文章、考試時的成績,但也在變化之間迷惘。偶爾走在城市里,看著繁華之景只剩悵然,滿目高樓卻沒有一間屬于我,更覺得自己是一只迷茫的孤舟,在陌生的城市里寂寞地漂泊著。
我思索起開拓的意義,在深陷痛苦準備退縮離去之際,卻看見父親在這里佇立很久的模樣。他不再年輕,卻依舊用自己的滿身力氣鑄造起繁華城市里的一座座高樓大廈。他那烈日下的汗珠、高空中搖晃的身影、鋼筋水泥里磨出的老繭……都在深刻地告訴我開拓的意義。他掄起那大錘,一錘一錘地開拓著我們這些后輩們的人生。
與他一樣的父輩們也走在開拓的路上,他們有的爬上火車去往未知的遠方,他們有的帶上故鄉的漁網翻山越嶺去往異邦,他們有的在北方的寒風里咬牙堅持,有的在南方的潮濕里埋頭耕耘。他們比誰都堅信只要努力便能看到收獲。他們像是故土吹來的蒲公英,風吹到哪里,他們便在哪里拼命扎根,風把他們帶到哪里,他們便在哪里用余生去開拓。
此去十余年,我與父親都奔走在開拓的路上。我埋頭求學,為實現祖父想讓家族里出個大學生的愿望用盡力氣。父親則昂頭沖進時代的浪潮里,努力讓他的后輩們可以在他親手筑造的城市里長出名叫留下的根苗。我們身后是千千萬萬個從故土走出的孩子們,一代又一代地從故鄉的老屋出發。他們要學會開拓,他們慢慢接過父輩肩上的開拓使命,成了從老屋里出發的新主角,努力演繹著屬于自己的新人生……
“喵——喵——”庭院里的貓叫聲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定睛一看,那是祖父生前養的貓。自祖父離去后,它像隨著祖父離開一般消失不見。我以為它早已不在這世間,如今我竟在老屋的舊庭院里再次看見了它。四目相對的一瞬,一種再見故人的唏噓感油然而生。我看見它,呆愣片刻后,不免懷疑這屋中的歲月是否還停留在過去。它看見是我,也愣住了,片刻后便認出我來。它穿過老屋的庭院朝我跑來,在我腿邊蹭了蹭又離開了。它鉆進庭院深深的綠草里,我透過那綠色,隱約看見它身后跟著三只小貓。
庭院里似有風來過,綠草輕輕搖曳著那些往昔的歲月。那棵我曾經數了又數的柿子樹,它再次抽出的新芽也在風中擺動。這風就那樣橫沖直撞地在我心里穿過。它將我年少時的回憶不講道理地甩在我的眼前。兒時用來釣龍蝦的棍子就豎在門后,它告訴我,這離去的十余年好像什么都沒變。可那院中祖父生前常坐的竹椅上卻爬滿了不知名的小花,它又在提醒我,我并不是當年的小孩子了,這里也早已時過境遷。
恍惚間,在外奔波的這十余年就如一場大夢,醒來后,整個人還徘徊在回憶里。我也終于懂得,守候是一種老屋教給我們的溫柔,開拓則是老屋給予我們的希望。
我們三代人,在這老屋的歲月里,不停地做出守候與開拓的選擇。卻不知這間老屋,在這一年又一年的歲月流轉里,可看懂了這人世的匆忙呢?我的心里好像有了一個答案,可我不敢輕言時光給的謎題。或許等我滿頭白發,再回來探望這老屋時,又會有一個新的答案。
人生還要繼續,老屋的抉擇也還會繼續。一代又一代,守候或開拓的抉擇與四季時光一樣從不停歇。這間老屋如今又有了新的守候者:那只貓兒帶著它的孩子們在老屋里繁衍生息。而我轉身離開,從老屋往人生深處出發。
我們匆匆一面,我們默契無言。它像祖父一樣留下,我如父親一般遠去。
作者簡介:丁思曉,筆名孫伯研,作品散見于《中國青年作家報》等報刊。
(責任編輯 劉冬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