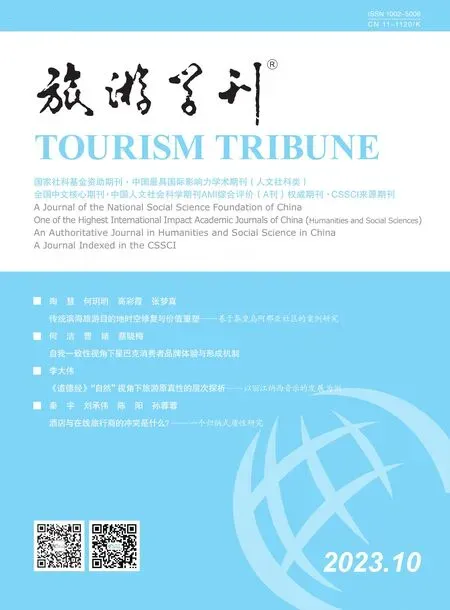紅色記憶對紅色旅游動機的影響研究
康曉媛,白 凱
(1.陜西師范大學地理科學與旅游學院,陜西西安710119;2.安康學院旅游與資源環境學院,陜西安康725000;3.陜西文化資源開發協同創新中心,陜西西安710119;4.陜西省旅游信息化工程實驗室,陜西西安710119)
引言
《2016—2020 年全國紅色旅游發展規劃綱要》公布以來,紅色旅游進入快速發展階段,其規模和增速已成為我國旅游市場中的一抹亮色[1]。紅色旅游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發展模式,其客源市場受到政府的大力引導和支持[2],因而市場結構以學生和中共黨員群體為主[3],客源群體相對單一。如何有效改變單一市場結構,深度挖掘紅色旅游資源和產品的特殊價值與內涵,增加旅游者在此類旅游活動中的幸福感和獲得感,進而明確紅色旅游產品與旅游者內心需求的關鍵契合點,發現紅色旅游動機的核心誘發因素,也已成為持續推進紅色旅游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任務之一。
以往的研究指出,記憶是誘導人們參與文化遺產類旅游活動的重要因素[4-5]。這種誘導作用表現在兩個層面:個體層面,記憶促使個體尋覓和前往那些被“渴望”的地方,并通過一系列的相關活動來修復、維持和捍衛自我一致性[6-7];群體層面,集體記憶在內化為個體心理特質的過程中,也催生了民族凝聚、群體歸屬感、群體認同等共同體意識與情感要素[6]。在此類因素作用下,旅游者往往樂意前往集體的“圣地”以鞏固自身與群體之間的聯系[8-9]。
在紅色認知和實踐背景下,記憶和旅游的關系同樣密切。現有研究指出,紅色旅游是構建紅色記憶的重要機制,是實現紅色記憶代際傳承和全球交流的重要媒介與載體[1]。然而,目前紅色記憶與紅色旅游的研究大多是從自上而下的視角考察紅色旅游地的記憶建構過程與記憶傳承功能[10-11],對紅色記憶、紅色旅游和潛在旅游者三者之間的聯系關注不足,并缺乏紅色記憶對紅色旅游動機影響的實證考察。
為此,本文將運用量化檢驗的方法探究紅色記憶對個體紅色旅游動機的影響作用。由于目前紅色記憶結構維度的相關研究仍處于理論探索階段,大多是通過定性訪談與理論推演的方式進行,現有成果或是在結構上難以自洽,或是對后續研究缺乏指導意義[12-13]。因此,本文將首先運用扎根理論的研究方法,構建紅色記憶的理論模型,并進行量化驗證。其次,再利用結構方程模型進行紅色記憶對紅色旅游動機的影響研究,以期為紅色旅游營銷管理提出針對性建議。
1 文獻綜述
1.1 紅色記憶
紅色記憶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成員對紅色歷史的記憶建構和意象體現[12],其核心內涵與中國社會建設與發展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它是一種情感、態度乃至認知的移入過程,是個體的一種社會化學習歷程,也是個體價值觀與中國革命價值觀整合統一的過程。在我國,紅色記憶具有集體性,是社會穩定的必要基礎,是一個基本的且普遍擁有的信仰、模范及價值綜合[14]。紅色記憶經歷個體的認同和內化,能夠幫助個體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國的歷史與現狀,繼而形成與中國社會集體規范或社會期待趨向一致的行為思想[15]。
紅色記憶具有宏觀建構的過程與特征,其主要包括喚起、重構、固化和刻寫4 個邏輯順序[16]。其中,喚起是激發個體對革命戰爭、事件、人物以及時代精神的回憶,它是主體對紅色歷史記憶和信息進行選擇和吸收的最基本條件;重構是對喚起階段形成的記憶體系進行重新包裝和新內涵注入的過程,是多種力量不斷博弈的結果;而固化則指對重構后的記憶進行保持和鞏固的過程,此過程有利于合法性的重構和認同感的強化;刻寫是以上3個關鍵步驟的重要價值承載,它通過社會符號建構和個人行為習慣規范實現紅色記憶的生產與再生產。經由以上4個建構過程,紅色記憶實現由抽象到具體、由平面到立體以及斷層到連續的發展過程,并對核心價值認同、政黨認同、文化傳承等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17]。
紅色記憶不僅是一種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同時也是個體自下而上的意義建構過程。在紅色記憶自下而上的建構過程中,記憶主體從個體的心理機制出發,運用感官系統對紅色歷史與遺產等信息進行主動接收和選擇性存儲[16];紅色記憶由局部和微觀向外延展,并通過人際之間的交流與分享活動使群體成員產生內容與形式趨近一致的紅色記憶圖式[18-19]。自下而上的記憶過程不僅關注現存的記憶與歷史,更著眼于群體成員之間的分享行為[20]。在這種記憶圖式的影響下,個體的文化依戀和歷史認同增強,并在紅色旅游、紅色紀念儀式等行為與活動中得以呈現[21]。
1.2 紅色旅游動機
動機問題是心理學研究的核心論題之一,它涉及人類行為的基本源泉,最能反映人類行為的目的性、能動性特征[22]。作為一種典型的社會性動機,旅游動機是激勵個體進行旅游活動的動因[23],它是個體在其心理潛能和先天傾向的基礎上,通過廣泛的社會實踐活動形成的。旅游動機具有鮮明的歷時特征,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社會文化背景和個體心理機制下都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性,該特征在相關研究中也得到充分說明[24]。
作為社會性動機和旅游動機的延展與組成類型,紅色旅游動機是個體為了滿足自身高層次需求而前往紅色旅游地進行觀光游覽的驅動力[25],是自我調節將外在誘因轉化為內在需要的產物[22]。在長期的父母教化、學校教育和紅色旅游地宣傳等作用下,個體對紅色革命歷史文化有了基本的了解和領悟,并產生了紅色旅游利于個人素質提升的價值研判。在此情況下,外在誘因(紅色物質資源與紅色精神文化)助推了內在需要(瞻仰偉人、提升自我等)的加速形成,內在需要被激發并獲得了朝向紅色旅游地這一目標的能量,最終促成了紅色旅游動機的產生[26]。
在紅色旅游動機的影響因素研究中,學者們主要將影響因素分為主觀和客觀兩類。主觀因素主要是指年齡、興趣、職業以及受教育水平相關的因素;客觀因素主要包括地方革命文化、旅游目的地資源價值等[27-28]。整體而言,現有對紅色旅游動機產生的影響因素研究尚且停留在對個體社會人口統計特征和目的地屬性等變量的簡單梳理,缺乏對變量內部結構和關系作用機理的深入剖析,研究仍需深入和完善。
2 研究一:紅色記憶理論模型構建、量表開發與模型選擇
2.1 理論模型構建
2.1.1 研究方法與數據收集
為了探索個體紅色記憶的生成與結構維度,筆者于2019年8月1—8日和10—17日進行了為期16天的訪談調研。首先,根據質性研究的資料飽和原則,調研之初暫不擬定訪談人數,當訪談信息重復出現且資料分析不再呈現新的內容和主題時,便停止訪談[29]。其次,根據質性研究的目的性抽樣原則,本文采取強度抽樣的策略,選取具有較高信息密度和強度的個體作為研究對象。在此指導下,本文以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和延安革命遺址群兩個典型紅色文化地為核心調查區域,通過隨機偶遇的方式,以掌握紅色史實基本脈絡、了解豐富的紅色文化歷史事件以及對于紅色中國有著較為深入思考與判斷的個體為訪談對象,發掘訪談對象有關紅色記憶的深刻認知與見解,形成本文的一手資料。最終,在對兩個典型案例地先后訪談14 人和12 人后,訪談數據達到理論飽和,訪談停止。同時,由于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公民紅色記憶的異質性,本文在訪談過程中盡量保證受訪對象在年齡、職業、學歷、政治身份、地域上的層次性和均衡性。
本研究選取了26個訪談樣本,訪談時長基本保持在30~120分鐘之間,訪談總時長達29.5小時。受訪對象人口統計特征如下:性別上,男性和女性分別為12 人和14 人;年齡上,50 后、60 后7 人,70 后、80 后10 人,90 后、00 后9 人;職業上,國企及行政事業單位公職人員6 人,私企員工7 人,農民、工人及自由職業者5 人,學生8 人;受教育程度上,高中及以上19人,高中以下7人;政治身份上,中共黨員和共青團員共15 人,群眾11 人;地域分布上,受訪對象分別來自陜西、山西、河南、江蘇、浙江、內蒙古、甘肅、貴州等地,受訪對象社會文化背景各異,具有代表性。本文按照訪談對象的先后順序進行了數字編碼,最終形成了編碼X01~X26 的32 萬余字的訪談文本。在26個訪談樣本的基礎上,本研究繼續進行了5組深度訪談以備理論飽和度檢驗。
2.1.2 編碼過程
(1)開放式編碼
本文依據Corbin 和Strauss 的三級編碼方法對訪談資料進行扎根理論分析[30]。首先進行開放式編碼分析,對資料進行概念化和范疇化處理,并按照“原始語句-初始概念-初始范疇”的方式逐字逐句進行編碼。經過對訪談資料的反復整理與分析,本文得到68個初始概念和25個初始范疇。
(2)主軸式編碼
主軸式編碼是在開放式編碼的基礎上,通過對相近的概念和現象加以歸類和集聚,發現與建立各類別之間關系的編碼過程。紅色記憶的結構特性與集體記憶相融相通,因此副范疇的識別與提取借鑒了集體記憶的相關理論成果。本文對開放式編碼的25 個初始范疇加以“聚斂”,歸納出6 個副范疇和3 個主范疇(表1)。6 個副范疇為自我關聯符號記憶、社會象征符號記憶、歸屬認同情感記憶、懷舊反思情感記憶、習慣記憶和模仿記憶,3個主范疇為符號記憶、情感記憶和實踐記憶。

表1 主軸式編碼Tab.1 Axial coding
集體記憶具有高低不同的層次,當記憶與事件原始發生的時間和空間距離越遠時,它的層次越高,越體現集體層面的意識,相對抽象與客觀。反之,它的層次越低[31],越反映個體生活經歷與內心情感,相對具象與主觀。自我關聯符號記憶就是相對低層次的記憶,特指個體對家族成員革命時期親身經歷的紅色革命歷史的記憶,具有較高的鮮活性。社會象征符號記憶則是相對高層次的記憶,指個體對代表紅色歷史與精神的社會象征體系及其內涵的認知與把握,是相對抽象的、無所不在的記憶。
集體記憶不僅是公開的符號和意義系統,而且還蘊含了特定個人的實際思維過程與情感狀態[19]。歸屬認同情感記憶指個體經過感受、體驗并內化于心的對紅色過去的情感認同與記憶歸屬;懷舊反思情感記憶則指個體對紅色革命年代的情感寄托與對現代社會批判性思考的集合,二者代表了個體不同的紅色情感傾向。
每個集體都試圖將最亟須保存的范疇和價值融入個體身體的自然動作中,并以習慣記憶的形式保存和傳承下去[32]。因而,習慣記憶指個體在紅色儀式活動中所重復與保留下來的身體習慣性動作、姿勢、行為等記憶。此外,集體記憶不僅局限于記憶主體的習慣性身體行為,也是記憶主體和社會互動作用的結果,通過模仿他人來進行社會行事是集體記憶生成的模式之一[33]。模仿記憶指個體通過對革命先烈的外顯行為或內隱思想采取主動學習、模仿等實踐行為而產生的記憶。
在進一步對副范疇進行邏輯聯結與關系推演的基礎上,本文發展了符號記憶、情感記憶和實踐記憶3 個主范疇,并對其進行了內涵界定。具體而言,符號記憶指個體頭腦中的關于黨紅色革命時期、建設時期和改革時期歷史與事件符號系統;情感記憶是紅色情感體驗的記憶儲存,是個體對紅色事件、歷史與人物的整體評價與態度;實踐記憶是個體在紅色記憶傳承過程中親身實踐獲得的記憶。
(3)選擇式編碼
選擇式編碼要求提煉出核心范疇,并用故事線的形式描述現象。通過對主副范疇的持續比對和反復論證,本研究提煉出“紅色記憶具身建構”這一核心范疇。圍繞這一核心范疇,故事線為:我國公民生來就存在于一個紅色文化框架或情境之中,紅色記憶建構首先是從紅色符號的認知與辨別開始的。沒有過多生活經歷的小孩子在看到毛主席雕像時激動地大喊“毛爺爺,您好”便是例證。心智是身體的心智,認知是身體的認知[34]。在這個過程中,個體運用身體的重要武器——頭腦對符號進行系統學習并將符號儲存在大腦中,形成紅色“常識”。但紅色記憶不僅僅是抽象的符號體系,更是一種自豪與驕傲的情愫,一種“感動到想哭”的情感體驗。情感以身體為建構的場所[35],并在整體的身體震顫中客觀體現[36]。在年長者直接的情感過渡和個人價值理性判斷的基礎上,伴隨著身體的情緒性運動,個體形成了不同的紅色態度和情感傾向。此外,行動和操演的身體實踐是保存和傳承記憶的重要手段[37]。個體會有意識或無意識、主動或被動地運用身體實踐進行紅色記憶的再現,將紅色記憶內化為身體的自動化程序,并用于指導自身的意識體系建設和行為實踐發展。
總體而言,紅色記憶的建構過程就是身體與“紅色世界”的互動過程。在不同的情境中,符號記憶、情感記憶與實踐記憶以不同的方式組合在一起,并相互影響、相互交融。紅色符號的深刻認知有助于增加個體的情感強度、規訓個體的實踐行為;紅色情感的持續發酵有助于強化個體的符號辨別能力與記憶實踐動力;而紅色實踐則在記憶復現與書寫過程中完成符號的具象化再現與紅色情感的喚醒。三者的互動統一共同減少了時空距離帶來的記憶疏離與不真實感,使紅色記憶成為個人“真正的”記憶。
(4)理論飽和度檢驗

圖1 紅色記憶具身建構理論模型圖Fig.1 Theoretical model of embodied construction of red memory
編碼過程完成后,本文進行了理論飽和度檢驗,5個樣本的概況統計如下:性別上,男性兩人,女性3人;年齡上,80后、90后4人,00后1人;職業上,學生2人,企業人員2人,家庭主婦1人。經整理,發現相關內容均在已得到的核心范疇之內,主范疇之間也未發現新的因子。因此,可以認為,紅色記憶具身建構的理論模型已經達到飽和,范疇發展可以停止。
2.2 量表開發與模型選擇
2.2.1 量表編制與數據收集
研究設計問卷為結構式調查問卷,由兩個部分構成:(1)紅色記憶的測量維度;(2)調查對象的社會人口結構特征。紅色記憶的測度上,本文基于扎根理論分析所開發的紅色記憶理論模型,編制出含有29個測項的原始量表,測項的表述基本來自訪談內容。社會人口結構特征方面,主要涉及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和家庭/個人年收入等。
數據收集方面,考慮到研究對象為全體國家公民,故而樣本的選取不受地域限制。因此,本文借助“問卷星”調查平臺,以網絡調研的形式考察個體的紅色記憶建構情況與結構維度。預調研于2019年9月進行,收集問卷145份,回收有效問卷130份,問卷有效率89.7%。預調研完成后對數據進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最終刪除了6 個題項,形成具有23個題項的正式問卷。
正式調研于2019年10月進行,共收集問卷396份,回收有效問卷379 份,有效率達95.7%。樣本構成中,性別上,女性受訪者199 人,男性受訪者180人,男女比例基本適宜。年齡上,80后居多,107人;70后和90后次之,151人,占39.9%;其他年齡段的被調查者121人。政治面貌上,中共黨員和共青團員占比53.5%,群眾占比46.5%。受教育程度上,被調查者大多都接受過高中以上的教育,其中,大專及本科以上占到78.6%。
2.2.2 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 26.0 對回收數據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首先,檢驗量表是否適宜采用因子分析。因子提取標準為:每個因子至少3個測項;旋轉因子載荷小于0.4 或交叉因子載荷大于0.4 的測項刪除;各維度因子特征值大于1。結果顯示,量表KMO值為0.868,方差近似值為5898.858,自由度df值為325,Bartlett 球形檢驗的顯著性水平p=0.000<0.05,表明研究所開發的量表通過適合度檢驗。經過3次因子淬煉,本文將交叉載荷高于0.4的6個測項刪去,最終保留了23 個測項,各測項的因子載荷在0.653~0.898 之間,各因子的Cronbach’sα系數在0.815~0.923之間,各因子特征值均大于1,說明得到較為切合的因素結構(表2)。此外,6個維度的方差累積貢獻率為71.14%,符合60%的提取界限。根據各個因子的測項構成,分別命名為:自我關聯符號記憶、社會象征符號記憶、歸屬認同情感記憶、懷舊反思情感記憶、習慣記憶與模仿記憶。經過探索性因子分析發現,扎根理論所構建的紅色記憶理論模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以進行下一步的驗證性因子分析。
2.2.3 驗證性因子分析與模型選擇
本部分旨在通過驗證性因子分析選出最為合理的紅色記憶測量模型,并對該模型進行效度檢驗。根據扎根理論所確定的紅色記憶具身建構理論模型,本文構建了3 種不同類型的測量模型。模型1是由紅色記憶單一維度涵蓋所有測項的一階因子模型;模型2是在紅色記憶維度之下,聚合相關副范疇構成的二階因子模型,模型3是高階因子模型,紅色記憶高階維度由3個二階因子和6個一階因子構成。
模型選擇主要是通過3個測量模型的擬合度比較,從中選出穩健性最高的模型[38]。利用AMOS 23.0對各模型構建、運行與修正后,結果顯示,除模型1有3 條路徑不合理外(p>0.05),模型2 和模型3 的各條路徑均合理且達到顯著水平。在對各模型適配指標值比較后發現,模型1 大多數指標都不達標(χ2=771.190,RMSEA=0.075,SRMR=0.100,GFI=0.870,AGFI=0.829,NFI=0.862,RFI=0.834,IFI=0.896,TLI=0.874,CFI=0.895,PGFI=0.662,PNFI=0.716,PCFI=0.743,CN=162(α=0.01),χ2/df=3.672),模 型2 部 分 指 標 不 達 標(χ2=511.260,RMSEA=0.052,SRMR=0.070,GFI=0.914,AGFI=0.895,NFI=0.909,RFI=0.897,IFI=0.947,TLI=0.939,CFI=0.946,PGFI=0.742,PNFI=0.805,PCFI=0.838,CN=258(α=0.01),χ2/df=2.282),模型3 所有指標均達標(χ2=469.118,RMSEA=0.049,SRMR=0.054,GFI=0.921,AGFI=0.901,NFI=0.916,RFI=0.904,IFI=0.954,TLI=0.947,CFI=0.954,PGFI=0.737,PNFI=0.800,PCFI=0.833,CN=278(α=0.01),χ2/df=2.123)。因此,可以發現模型3是紅色記憶最優測量模型。
效度檢驗方面,主要包括收斂效度和區分效度。其中,收斂效度包括平均方差萃取量AVE(average of variance extracted)值 和 組 合 信 度CR(composite reliability)值,AVE 值高于0.5,CR 值超過0.7,說明各測項之間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數據顯示,一階因子的AVE 值分別為0.528、0.645、0.633、0.607、0.671、0.731;CR 值 分 別 為0.847、0.916、0.896、0.822、0.891、0.890,二 階 因 子 的AVE 值 分 別 為0.530、0.623 和0.697;CR 值分別為0.941、0.930 和0.941,均大于標準值,說明模型的收斂效度均達到了最佳標準。在區分效度上,主要采用AVE值和相應構念間相關系數的平方值大小比較來檢驗。對因素間的相關系數進行運算發現,各相關系數的平方值(0.152~0.318)均低于上述平均變異萃取量(0.530~0.697),說明該模型能夠體現較好的區分效度。
3 研究二:紅色記憶對紅色旅游動機的影響
3.1 研究設計
3.1.1 研究假設與模型建構
為了驗證紅色記憶對紅色旅游動機的影響,本文將在紅色記憶結構模型和前文理論梳理的基礎上,提出下列研究假設。
Wirtz等研究指出,個體通常參考過往記憶確定未來心理及行為傾向[39],過往記憶屬性越積極,個體就越容易采取積極的行為,反之亦然。Marschall則在旅游和記憶關系的研究中指出,記憶在人與地方的聯結中起著特殊作用,往往是記憶而非其他的旅游實踐催發了人們的出行動機[4]。這種記憶既包括個人對過往獨特生活經歷的記憶,也包括集體層面對目的地的感知與印象。以此類推,具有豐富紅色記憶的個體會在過往生活歷程中與某些紅色旅游地有獨特聯結,抑或對紅色旅游地有深刻的感知與想象。在此基礎上,本文推想具有豐富紅色記憶的個體會產生前往紅色旅游地進行記憶實踐的強烈愿望與訴求。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1:紅色記憶對紅色旅游動機有顯著正向影響
卡西爾認為,人類是“符號的動物”,人以符號為媒介創造了文化與社會,同時用符號解釋世界的意義并指導自己的行為[40-41]。旅游過程同樣是一種符號化的過程,旅游目的地通過符號標識系統的打造,滿足了人們的心靈與精神追求,吸引著旅游者不斷前來,并進行符號實踐[42-44]。紅色旅游地是官方主導下,紅色符號記憶系統通過選擇、表述和重演3個環節構建而形成[11]。那么符號記憶對不同的紅色旅游動機是否有影響?有怎樣的差異性影響?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2:符號記憶對紅色旅游動機有顯著正向影響
H2a:符號記憶對求知教育紅色旅游動機有顯著正向影響
H2b:符號記憶對景仰朝圣紅色旅游動機有顯著正向影響
H2c:符號記憶對自我實現紅色旅游動機有顯著正向影響
情感是個體決策行為背后的重要動因。王克軍和馬耀峰指出,情感是激發個體出游的主要動機[6]。Swarbrooke 和Horner 認為,旅游動機包括情感因素,例如懷舊、浪漫、逃避、冒險和心理滿足等[46]。Marschall研究證明,與目的地的情感聯結會激發旅游者的旅游動機,比如鄉愁旅游、尋根旅游等[47]。然而,對于目的地的復雜情感,如珍視、懷念等反而會使旅游者產生避免破壞心中美好伊甸園的想法,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礙旅游者的出行[6]。紅色旅游情境下,紅色旅游地因承載了革命文化與精神從而使旅游者產生了崇拜、懷舊等情感[48]。那么這種情感記憶對不同紅色旅游動機是否有影響?有怎樣的差異性影響?綜上,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3:情感記憶對紅色旅游動機有顯著正向影響
H3a:情感記憶對求知教育紅色旅游動機有顯著正向影響
H3b:情感記憶對景仰朝圣紅色旅游動機有顯著正向影響
H3c:情感記憶對自我實現紅色旅游動機有顯著正向影響
過去形塑現在。任何過往經歷都會成為個人記憶之所,并深深影響個體的旅游目的地選擇[49]。過往的經歷和行為習慣與未來需求的匹配度越高,個體的旅游選擇意愿也越強烈[50]。實踐記憶是個體在親身實踐后形成的紅色記憶集合,其通過對過去的傳承和當下的建構,影響著人們的行為模式,并一定程度上成為未來實踐的摹本[51]。那么實踐記憶對不同的紅色旅游動機是否有影響?有怎樣的差異性影響?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是像我們親歷過的風吹草底見牛羊的呼倫貝爾大草原,還是鋪滿白色珍珠(羊群)長滿碧綠酥油草的巴音布魯克大草原?從友人所攝的卡爾梅克大草原照片看:遼闊無際、碧綠一片中盛開鮮艷的郁金香花,又是一番美景。
H4:實踐記憶對紅色旅游動機有顯著正向影響
H4a:實踐記憶對求知教育紅色旅游動機有顯著正向影響
H4b:實踐記憶對景仰朝圣紅色旅游動機有顯著正向影響
H4c:實踐記憶對自我實現紅色旅游動機有顯著正向影響
由此,形成了研究假設模型圖(圖2)。
3.1.2 量表編制與數據收集
研究設計問卷為結構式調查問卷,由3 個部分構成:(1)紅色記憶的測量維度;(2)紅色旅游動機的測量維度;(3)調查對象的社會人口結構特征,前兩個部分采用Likert 5點量表進行測量,第三部分采用單項選擇的方式調查。在紅色記憶的測度上,本文采用研究一設計并驗證的紅色記憶量表,該量表包含3 個維度23 個測項。在紅色旅游動機的測度上,由于旅游者動機的激發源于個體內心的選擇而非外在的吸引[52],本文重點借鑒了已有紅色旅游動機量表中的內在動機維度。具體而言,本文參考了Li等[53]、范春春[25]、Zhao和Timothy[26]的問卷量表,保留了求知教育和景仰朝圣的維度;結合Dunkley等[54]和劉紅梅[55]的研究內容以及Pearce和Lee[56]的量表,設計了自我實現維度。最后,結合本文的研究目的,對問卷進行了適當的修改,形成了本文的最終問卷。
3.2 探索性因子分析
在進行數據分析前,本文將收集到的478 份有效問卷隨機分為兩個子樣本,樣本一(n=178)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樣本二(n=300)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由于紅色記憶量表在前文量化研究中已得到檢驗,本部分直接進行紅色旅游動機的探索性因子分析。首先檢驗量表是否適宜采用因子分析。結果顯示,量表KMO 值為0.903,方差近似值為2968.683,自由度df值為66,Bartlett 球形檢驗的顯著性水平p=0.000<0.05,表明研究所開發的量表通過適合度檢驗。接著,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最大方差法,經過5次因子淬煉,刪除兩個交叉載荷大于0.4 的測項后,得到紅色旅游動機旋轉后的成分矩陣。該模型共提取出3 個公因子,分別命名為求知教育動機、景仰朝圣動機及自我實現動機。其中,各因子的Cronbach’sα系數分別為0.797、0.741及0.836,均大于0.7,各因子特征值均大于1,說明得到較為契合的因素結構。此外,整體因子方差累積貢獻率為68.25%,符合60%的提取界限,因子分析效果良好,可以進行下一步的驗證性分析。
3.3 驗證性因子分析
本部分通過驗證性因子分析對紅色記憶與紅色旅游動機兩個潛變量進行效度檢驗。效度主要包括收斂效度和區分效度。數據顯示,紅色記憶3個因子的AVE值分別為0.587、0.587及0.677;CR值分別為0.927、0.908及0.935,紅色旅游動機3個因子的AVE值分別為0.583、0.503及0.661;CR值分別為0.847、0.800 及0.886,均大于標準值,說明潛變量的收斂效度較好。在區分效度上,對因素間的相關系數運算發現,紅色記憶各相關系數的平方值(0.106~0.286)低于其平均變異萃取量(0.587~0.677),紅色旅游動機各相關系數的平方值(0.457~0.492)低于其平均變異萃取量(0.503~0.661),說明潛變量均能夠體現較好的區分效度。
3.4 結構模型分析與假設檢驗
3.4.1 結構模型分析
首先,本研究總體檢驗了紅色記憶對紅色旅游動機的影響作用(H1),由此形成了紅色記憶對紅色旅游動機的影響模型(模型1)。其次,為進一步探究紅色記憶各子維度(符號記憶、情感記憶及實踐記憶)對紅色旅游動機的影響作用(H2~H4),本文建立了符號記憶、情感記憶及實踐記憶對紅色旅游動機影響的3 個結構模型,分別命名為模型2~模型4。在驗證性因子分析的基礎上,本文采用極大似然法對上述模型進行估計,最終得到各模型的適配指標值。修正后的模型結果顯示,模型1~模型4 各項指標均達到良好的標準,可被用作檢驗本研究所提假設(表3)。

表3 假設檢驗結果及模型擬合指標Tab.3 Results of hypothesis and model fitting index
3.4.2 假設檢驗
相關研究證實,檢驗標準t值的絕對值大于2.58,則參數估計值達到0.01顯著性水平,若t值的絕對值大于1.96,則參數估計值達到0.05顯著性水平[57]。本文運用結構模型對研究假設進行驗證,結果如下。
紅色記憶正向顯著影響紅色旅游動機(γ=0.77,p<0.001),H1成立。集體記憶體現出整個群體較為深層的價值取向、情感表達以及心態變化等方面,為群體的態度、行為等方面提供更加一致的標準和方向[58]。紅色記憶作為一種特殊的集體記憶,同樣塑造著中國人民的家國情懷,影響著整個民族的態度、情感和行為傾向。旅游者層面,擁有豐富紅色記憶的個體往往具備強烈的革命情懷和家國意識,更加重視對紅色知識的索取,并以多種方式內化和踐行紅色精神。目的地層面,紅色旅游地作為典型的紅色記憶空間,具有豐富的紅色遺產和精神底蘊,其建構與開發過程中紅色記憶要素的合理搭配,如影像、雕塑、歷史物件等,正好滿足了具有深刻紅色記憶個體的精神追求,并深深吸引著個體前來感受革命歷史,體驗革命生活。
符號記憶正向顯著影響紅色旅游動機,H2 成立。細化而言,符號記憶正向顯著影響求知教育(γ=0.83,p<0.001)、景仰朝圣(γ=0.80,p<0.001)和自我實現(γ=0.77,p<0.001)紅色旅游動機,假設H2a、H2b、H2c 成立。其中,符號記憶對求知教育動機的影響更為顯著。符號具有能指和所指雙重含義,能指是外在形態和物質載體,所指是其背后蘊含的意義。對于個體而言,符號不僅是多維價值體系,同時能夠引起情感的發生發展[59],并導向一定的個體行為[60]。旅游者往往是在心中已有符號和印象的激發下,前往某地進行多種旅游體驗,因此,符號記憶對不同紅色旅游動機均有正向顯著影響。Culler在旅游符號學的研究中指出,旅游者是“符號軍隊”[61],旅游者前往目的地就是為了進行符號實踐。同時,由于符號具有認知特性[62],因而符號記憶對求知教育動機影響最大。具體而言,在長期的紅色文化、紅色符號浸染下,個體對紅色旅游符號系統認知越深刻,越容易被紅色旅游地承載的多維符號價值吸引,產生求知教育的出游動機與行為。例如旅游者不僅自行前往紅色旅游地,也注重帶領子女前往紅色旅游地接受思想教育,以期提高后代的文化素養和思想覺悟,實現紅色記憶的代際傳承[63]。
情感記憶正向顯著影響紅色旅游動機,H3 成立。細化而言,情感記憶正向顯著影響求知教育(γ=0.77,p<0.001)、景仰朝圣(γ=0.86,p<0.001)和自我實現(γ=0.79,p<0.001)紅色旅游動機,假設H3a、H3b、H3c成立。其中,情感記憶對景仰朝圣動機的影響最為顯著。涂爾干認為,集體情感是一種有序的、自覺的社會力量,它能夠規范社會行動,促進社會整合[64]。具體而言,在集體情感的指引下,共同體成員不僅會對傷害集體情感的行為做出抵抗,也會積極主動追尋集體步伐、推動集體延續和維持。在紅色情感記憶影響下,個體熱衷于前往紅色遺址地鞏固紅色集體身份,強化紅色集體人格。因此,情感記憶對不同紅色旅游動機均有顯著正向影響。此外,集體記憶具有維持關系和加強情感聯系的功能[65],情感記憶則在其中發揮著關鍵作用。故此,情感記憶豐富的個體更傾向于參與集體互動,增強彼此間的情感紐帶,產生情感共鳴,3種動機類型中也更有可能激發景仰朝圣旅游動機。
實踐記憶正向顯著影響紅色旅游動機,H4 成立。細化而言,實踐記憶正向顯著影響求知教育(γ=0.69,p<0.001)、景仰朝圣(γ=0.86,p<0.001)和自我實現(γ=0.74,p<0.001)紅色旅游動機,假設H4a、H4b、H4c成立。其中,實踐記憶對景仰朝圣動機的影響最為顯著。實踐記憶不僅受到傳統(過去)的規約而重構過去,而且通過當下記憶影響未來的實踐[51]。在日常生活和儀式活動中,個體形成了一種紅色記憶實踐的“慣性”,這種慣性使其定期進行記憶實踐,并從中學習提升、尋找歸屬感以及建構自我生命意義。因此,實踐記憶對于3 種紅色旅游動機都有顯著的影響。實踐記憶包括習慣記憶和模仿記憶,在一定程度上,二者分別代表了被動和主動的紅色記憶實踐。一般而言,作為操作性的紅色記憶維度,實踐記憶會更有自我指向性,在此記憶影響下,個體會更易激發自我實現紅色旅游動機。但由于模仿記憶(γ=0.67,p<0.001)對自我實現動機的影響較強,習慣記憶(γ=0.50,p<0.001)對自我實現動機的影響偏弱,使得整體上實踐記憶對自我實現動機的激發較弱。同時,由于個體情感的易觸發性,景仰朝圣動機成為實踐記憶影響下最顯著的出游動機。
4 研究結論與啟示
4.1 主要結論與討論
本文采用質性與量化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對紅色記憶的結構維度進行了扎根理論分析和量化檢驗,并驗證了紅色記憶及其子維度符號記憶、情感記憶及實踐記憶對不同紅色旅游動機的差異性影響,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第一,提出了紅色記憶的結構維度和理論模型。典型的集體記憶研究主要從較宏觀的空間維度和時間維度兩個層面論證了集體記憶的建構過程與功能作用[66]。除Connerton 強調紀念儀式中人的自身操演對集體記憶形成的重要作用之外[32],少有學者探究個體中心觀下,集體記憶的生成乃至其結構維度。本文運用扎根理論,探索出紅色記憶具身建構高階理論模型。該模型包括符號記憶、情感記憶、實踐記憶3個主范疇以及自我關聯符號記憶、社會象征符號記憶、歸屬認同情感記憶、懷舊反思情感記憶、習慣記憶和模仿記憶6 個副范疇,以及“紅色記憶具身建構”這一核心范疇。本文突破了傳統的集體記憶研究視角,呈現了意識主體能動的紅色記憶建構過程與結構維度。
第二,開發了紅色記憶量表,并進行了實證檢驗。已有的紅色記憶多為質性研究和理論推演,鮮有量化實證研究。本文運用結構方程模型,對紅色記憶的結構維度進行了量化測定,形成了具有3 個二階維度、6個一階維度、23個測項的量表。數據顯示,紅色記憶具有符號記憶、情感記憶、實踐記憶3個二階維度,其中,實踐記憶對紅色記憶的標準化回歸系數高于情感記憶和符號記憶。這是由于實踐記憶是在一定的場域環境下形成的,對紅色記憶的塑造更加多元鮮活,因此,在紅色記憶形成中發揮著更為重要的作用。6 個一階維度中,社會象征符號記憶、懷舊反思情感記憶和習慣記憶對二階維度的回歸系數分別高于自我關聯符號記憶、認可歸屬情感記憶以及模仿記憶。符號記憶方面,由于時空距離的加大,革命親歷者的不斷逝去[14],自我關聯符號記憶逐漸淡化,個體更多是通過學校教育、影視作品、紅色研學活動以及社會宣傳等途徑獲得紅色記憶,因而社會象征符號記憶更為顯著。情感記憶方面,當今社會,個體不是記憶接收的機器,而是能動的記憶實踐者,經由自身長期觀察與深刻反思后形成的情感風格才是奠定情感記憶的重要基調。實踐記憶方面,目前,我國公民組織參與下的習慣記憶較為豐富,自發形成的模仿記憶相對薄弱,因而,習慣記憶在實踐記憶中占據更為主要的地位。
第三,量化分析了紅色記憶對紅色旅游動機的影響作用。實證結果顯示,紅色記憶及其子維度符號記憶、情感記憶及實踐記憶均對紅色旅游動機有正向顯著影響。首先,紅色旅游動機的激發與個體紅色記憶密切相關,這說明紅色旅游動機的激發受到個人過往的紅色經歷、經驗的首要影響。其次,整體上,情感記憶對紅色旅游動機的影響作用更為顯著,符號記憶和實踐記憶次之。正如休謨所言,快樂和痛苦等情感是人類心靈的主要動力[67],同時也是欲望、意愿和行為產生的重要源泉。對旅游者而言,在其前往異地旅游的過程中,無論是追求愉悅,還是追求身心自由體驗,都離不開情感這一要素[68]。本文的研究結論呼應了該論斷,說明即使是富有教育和精神色彩的紅色旅游情境下,追求情感體驗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再次,紅色記憶對景仰朝圣紅色旅游動機有更強的激發作用,這一結果是紅色記憶本質屬性與紅色旅游屬性契合的結果。紅色記憶的客體來源為革命史實,具有一定的神圣化色彩;而紅色旅游區別于其他旅游形式的重要標準也正是基于社會現實的神圣性[10]。二者的對接使得旅游者期望通過追尋先烈足跡、憶苦思甜等方式在紅色目的地獲得“朝圣”般的精神體驗。因而,紅色記憶不僅是建構紅色旅游地的重要手段,同時也是吸引旅游者的重要動力之一。
4.2 管理建議與不足
當今社會,多元文化不僅嚴重沖擊著人們的觀念和價值體系,更對民族精神傳承、文化生態和國民的身份認同造成了威脅。而以紅色旅游、紅色教育等多種形式為載體的紅色記憶,已成為刻畫時代精神底色、匯聚強大發展動能的重要支撐。因此,掌握紅色記憶的結構維度,抓住紅色記憶脈搏,有利于建立紅色歷史與當下存在之間“活的聯系”,使得后代從被動接受記憶的客體轉變為能動的記憶實踐者,并主動前往紅色記憶之場追溯過去或反觀當下。基于此,本文對紅色記憶實踐和紅色旅游營銷管理有如下建議。
(1)創新話語體系與表達機制,激發紅色記憶傳承動力。Halbwachs 曾說,集體記憶是基于當下需要而建構的[69],即如果脫離現實社會和文化土壤,集體記憶就會不再生動、鮮活,并失去規范個體行為和促進社會凝聚的強大影響力。因此,紅色記憶需要不斷更新,在政府引導下創新話語體系與表達機制(如融合數字實踐),塑造適應社會生活的、具有現實指導意義的“新紅色記憶”,從而實現紅色記憶的主動交流和有效傳承。
(2)加強紅色記憶要素辨別與情感激發,針對性地制定紅色旅游營銷戰略。雖然個體的紅色記憶內容各有不同,但具身建構下的紅色記憶大體都包括符號、情感與實踐3 個維度層次。這3 種記憶類型,尤其是情感記憶對紅色旅游動機有著顯著的影響。管理者在構思紅色旅游地形象時,應提取出與旅游者認知契合度最高的符號與情感要素,使紅色旅游地意象與個體心中趨于一致,吸引旅游者主動到訪。
(3)打造革命記憶場域,增加紅色旅游特色主題活動。紅色旅游管理者應根據自身資源特點,以多種主題活動為記憶觸發點,設計互動式旅游產品與體驗,激發旅游者的到訪動機,并推動其進行更有效的紅色記憶實踐。
紅色記憶的形成過程是微觀與宏觀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本文僅從微觀層面探討了紅色記憶建構,而未涉及更廣闊的社會層面(如大眾媒體影響下),這些都需要后續的深入探討。此外,本文著重探討了紅色記憶對紅色旅游動機(游前行為傾向)的影響,而未考察個體到達或離開紅色旅游地后,紅色記憶會怎樣影響其心理和行為傾向,這也是未來值得探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