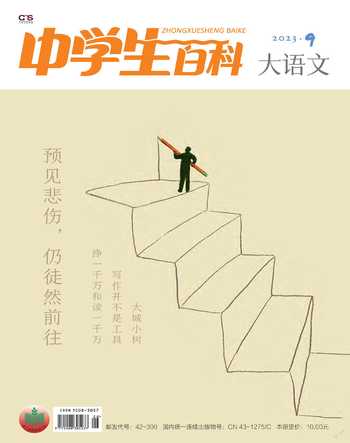紙質書的電子困境
朱歡
在霸主地位被電子書動搖之前,紙質書于人類閱讀史上已經走過了漫長歲月。公元105年,東漢蔡倫改進造紙術,傳統制紙技術不斷精進,紙這一信息載體得以代代傳承。從抄寫到印刷,中國人手捧一本本由紙裝訂而成的滿載光陰的書籍度過了漫長歲月。今天,隨著更加系統可控的造紙工藝的出現及廣泛應用,紙早已從珍貴的資源變為隨手可得的書頁,承載著無形的思想,傳播著文明的火種。
然而,電子媒介的出現使傳統的紙質閱讀方式出現轉折。1995年,電子百科全書的銷量超過紙質百科全書的銷量——盡管在當時這件事還鮮受關注。隨著電子媒介的興起,人們獲取信息與經驗的途徑逐步發生改變。電子墨水屏技術的出現和電子閱讀器不斷地更新換代,引發了持續的數字化出版熱潮。
與此同時,紙質書銷量開始下滑,電子書迅速占據人們的視線。易于檢索、易于記錄、易于管理、不易損壞……電子媒介讓人們看到了閱讀書籍的另一種形式。數字技術變革之下,即時獲取的海量圖書資源令人無比欣喜。比起曾經在街角的書店辛苦地尋尋覓覓,如今人們只需動動手指,閱讀隨時隨地可進行。
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兼媒體實驗室主任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曾說:“我們無法否定數字化時代的存在,也無法阻止數字化時代的前進,就像我們無法對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樣。”新舊媒體的更替確實是難以逆轉的時代力量,然而,僅在閱讀領域而言,紙質書或許還有更加深遠的意義與價值。
無論電子書如何盛行于世,我們的生活似乎總有某個角落留給心儀的紙質書。紙質書如深海般包裹住原本浮躁的思緒,用墨香書寫美好,用工藝詮釋匠心。紙質書對于生活的意義早已超越單純的信息傳遞,為我們帶來更多附加享受。
閱讀需要靜心,需要沉浸,對于篇幅長、信息量大的著作而言更是如此。在這方面,紙質書自有其魅力。研究表明,相比紙質閱讀,電子閱讀器中的內容在人腦海中只能留下短暫印象。翻動紙質書就像在小徑上行走,留下一個又一個腳印;而在看電子書時,數字設備會干擾人們在腦海中形成完整的閱讀流程。從某種意義上說,紙質書不僅能緩解“屏幕倦怠”,也是大腦的偏好。
《大英圖書館書籍史話》的序言有云:“如果書籍存在的理由純粹是承載文本,那么它們的消亡指日可待。”事實也確乎如此,書籍對于人們而言,遠不只是一份信息載體,閱讀除了意味著學習、思考,還是一種獨特的感官和情感體驗。我們在閱讀紙質書的過程中調動多種感官系統,企圖尋找生活的美好與浪漫。相比之下,電子書只有堅硬光滑的屏幕,毫無溫度,也毫無熱情。
書,不僅僅是文字與紙張的結合,還滿含審美與收藏意義。借助科技的先進性、優質多樣化的材料、更專業的藝術手段,每一本書都有可能做成一件精美的藝術品,從而具備獨特的收藏價值。德國有一項已經舉辦了近百年的評選活動,叫作“世界最美的書”。中國出版界也同樣有“中國最美的書”評選活動,其入選作品,內容與形式相得益彰,件件都可稱為藝術品。
毫無疑問,數字化極大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電子書的出現為閱讀提供了另一種便捷的選擇——我們不再只依賴厚重的書本獲取知識,隔著小小的屏幕,萬千世界都將展現在我們眼前。對于數字原住民而言,紙質書的整體可視化或工藝性或許并沒有那么重要,但無可否認,它仍然是許多人的精神食糧和情感寄托。我們無法舍棄手捧書籍的感覺,就好像是在凝望一個陪伴了好久的老友。
或許現在,我們可以嘗試回應紙質書的電子困境了:電子閱讀媒介的興起,與其方便信息傳遞而迎合快節奏生活不無關系,但對于紙媒來說,正是其在傳遞信息之外的特質決定了它不會就此消亡。目前,同時使用紙質書與電子書是許多人的選擇。其實,不管是對于“兼收并蓄”者、紙質書的誓死捍衛者,還是對于電子書的堅實擁躉而言,閱讀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正如村上春樹在《我的職業是小說家》中所說:“紙張也好,畫面也好,媒介和形態怎樣都無所謂,只要喜歡書的人好好地讀書,就足夠了。”
(摘自南京大學《南大青年》,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