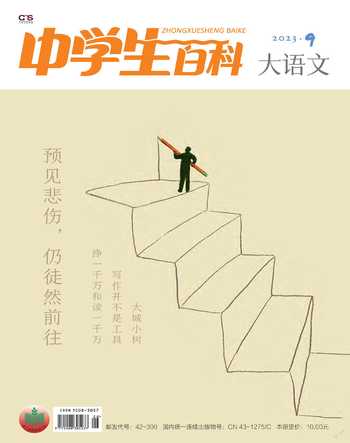我們向唐老師學什么
張建慶
我們不妨把教學理解為一場“漫游”和“遠行”,這是一次充滿好奇的、以發現的目光去探究新世界的旅程。
關于教育,梅貽琦先生有過一段經典的論述:“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這段論述的關鍵詞是一個“游”字。“游”既是一種技能訓練和知識習得的過程,也是一次不斷展開的充滿驚奇發現的旅程。
教師的使命就是引導學生去探索、去發現、去體驗,去迎接一次一次的挑戰,在有限的生命時空中追求無限的可能性。這讓我想起了《西游記》。
吳承恩的《西游記》,為什么不取名為《西行記》或《取經記》?這個“游”字是有深意的,“游”既包含了“行”的過程,也蘊含著“取經”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它讓我們感受到這段艱辛的、漫長的、充滿曲折和風險與挑戰的旅程,其實是很“有趣”很“好玩”的。
《西游記》之所以被譽為成年人的童話,就是因為它很“好玩”。
蔣勛先生說:“我覺得游戲的觀念很重要,因為生活中有很多好玩的東西……我們發現,在過去的青少年的生活中,充滿各種有品格的游戲,這些游戲看起來像在玩,事實上都是教育。”“德國的美學在講到游戲的時候,認為人類的文明創造力很重要的一個動機是‘玩,他們提醒我們千萬不要看不起兒童的游戲跟玩,所有的學習都是在游戲跟玩當中出現的,有目的性的教育只有壓迫的感覺,人只有在玩的時候學東西才是最好的,因為那個時候人完全放松,完全自由。”

陳省身在2002年的世界數學家大會上給少年兒童的題詞就是“數學好玩”。但為什么現在的教育很不好玩呢?
《西游記》里的取經團隊,在唐老師的帶領下開啟了一場“快樂的、好玩的學習之旅”。唐老師其實并沒有什么過硬的本事,肩不能挑重擔,也沒有一身好功夫可以打妖怪,但他能夠帶領三個本領高強的學生一路西行取回真經,這就很值得我們學習了。他好像什么都不會,在這個團隊中是最“無用”之人,但整個團隊中又離不開他,他是真正的核心和“定海神針”。作為一個老師,我以為他不僅是合格的,而且是足夠優秀的。
首先,他不僅自己有堅定的信仰、明確的目標、堅韌的意志,而且也知道要把徒弟們帶到哪里去。這幾個徒弟,本事都很大,來頭都不小,可他們身上都隱藏著逾越規矩的沖動。人在成長的特定階段(青少年時期)總是有很強烈的叛逆心理,同時又往往擋不住外部世界的種種誘惑,在這個階段能夠遇到一個好老師是幸運的。教育最重要的功能是為成長預設目標,因為好的教師知道“我要帶學生去哪里”。處在成長中的學生,往往并不明了自己的未來在哪里,不清楚自己要往哪里走,不知道腳下的路可以通向何處,因為這個世界誘惑太大又太多了,所以教育就要承擔引導學習者面向成長走向遠方的責任。
其次是要規劃好行動路線和方式,然后有效落實。唐老師帶著徒弟們一路向西。這條路,是要靠自己的雙腳走出來的。這一路上,“你挑著擔,我牽著馬,迎來日出,送走晚霞”,走過千山萬水,歷盡千難萬險,嘗遍千辛萬苦,但是也有千萬重柳暗花明和四季輪回中的綠水青山。越是有危險的地方,越是有奇異的風景,風餐露宿也是別樣的體驗。這一路前行,其實就是不斷地吸收日月精華,滋養生命閱歷,豐富精神世界。因此,這條路不能一個筋斗云就翻過去,當然也不可能乘飛機坐高鐵,而是要腳踏實地地走下去。我們的生命唯有在“行動”中才能真正“活起來”,活出生命的光彩,活出人生的高度,活出人性的偉大。
最后是教無定法,貴在得法。一路上,唐老師面對各種各樣的妖魔鬼怪一點辦法都沒有,但換一個角度從教學上看,他又是很有辦法的。他的高明之處可以說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其妙處有三:
一是“無為而治”。他知道如何讓每個人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特長。三個徒弟分工明確,而且平時唐老師對他們的工作不加干預,每天只要完成任務(走完一段行程)就可以,既不布置什么作業,也不安排各種各樣煩瑣的考試和檢查。
二是“團隊合作”。他從來不在團隊內部搞競爭,不鼓勵相互之間爭強斗勝,每一次遇到困難徒弟們都會“一起上”,實在解決不了也會想辦法去找外援,集中力量解決現實問題和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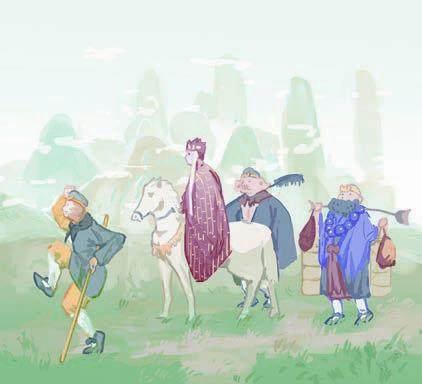
三是“慎用懲戒”。教育是需要懲戒的,唐老師雖然會念緊箍咒,但一般情況下不會輕易使用。在徒弟們信心動搖準備打退堂鼓的時候,他絕不嚴厲批評,也不會在上級領導和家長面前打小報告,只是自己給徒弟們做出示范,讓他們自己做出選擇。雖然“三打白骨精”中唐老師確實有些不分是非,但他的底線原則是很明確的,妖怪可以打,但是人命不能害。
這一路上,唐老師帶著三個徒弟,在游山玩水中豐富了經歷,在風餐露宿中品味了艱辛,在斬妖除怪中提高了技能,完成了學業,取到了真經。而唐老師這一路上堅定前行的身影,正合我心目中的那個“大先生”形象。
(作者系湖州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