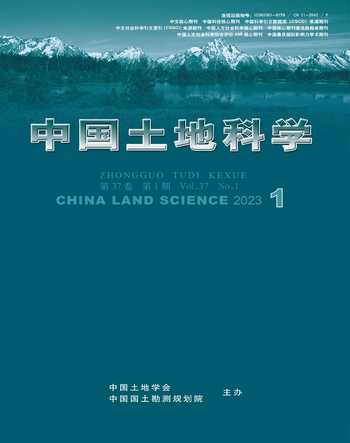國土空間規劃支撐城鄉融合發展的邏輯與路徑
戈大專 孫攀 湯禮莎 孫東琪 湯爽爽



摘要:研究目的:國土空間規劃落實城鄉融合發展戰略是高質量空間治理體系的核心目標之一,解析國土空間規劃支撐城鄉融合發展存在的現實困境及其內在機理,進而提出可行的破解路徑,為國土空間規劃支撐城鄉融合發展提供破題思路。研究方法:歸納演繹法和邏輯推演法。研究結果:多尺度交互的空間網絡不暢通和城鄉空間多元價值難交換成為阻礙城鄉融合發展的現實困境;國土空間規劃與城鄉融合發展在措施手段和目標體系的關聯性上搭建了二者的銜接邏輯,空間一致性和互動性決定了二者銜接的現實可行性;優化城鄉空間網絡體系、創新空間用途管制體系、統籌城鄉空間治理體系成為國土空間規劃支撐城鄉融合發展的可行路徑。研究結論:統籌協調國土空間規劃“發展、公平與生態”三維目標和城鄉“要素、結構與功能”融合的內在關系,落實城鄉要素有序流通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將有利于完善國土空間規劃支撐城鄉融合發展的內在機制。
關鍵詞:國土空間規劃;城鄉空間治理;城鄉融合發展;鄉村空間治理;鄉村振興
中圖分類號:F301.2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8158(2023)01-0001-09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42271205,41901204);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19YJCZH036)。
城鄉空間統籌治理為落實城鄉融合發展戰略創造空間支撐。《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與政策體系的意見》指出需要促進城鄉要素自由流通與平等交換,推進公共資源有序配置,落實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戰略。“多予少取放活”的農村政策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挖掘農村發展的內生活力,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是新時期城鄉關系演進的必然趨勢[1-2]。城鄉空間差異化所有權實現方式和管控模式,決定了城鄉空間權屬體系及其價值分配體系存在顯著差異,導致城鄉空間價值流動不平衡,進一步抑制了城鄉關系的有序改善。城鄉發展不均衡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體現,暢通城鄉要素流動,協調城鄉基礎設施配置,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是我國高質量發展的應有之義[2]。城鄉分治模式不適應新的發展形勢,城鄉空間共治推動城鄉融合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城鄉空間治理逐漸從空間權力分割轉向空間權利均衡分配,從“自上而下”主導向“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轉變[3-4]。
國土空間規劃體系推進城鄉空間治理體制機制融合的研究仍相對欠缺,新時期、新技術、新訴求對國土空間規劃支撐城鄉融合發展提出更高要求[2,5-6]。城鄉空間差異化用途管制體系和價值實現路徑決定了國土空間規劃打通城鄉統籌發展的路徑仍存在眾多困難,“五級三類”國土空間規劃體系,對城鄉空間統籌治理缺乏頂層設計,不論是多級傳導的用途管制體系,還是多類規劃體系中城鄉空間聯動的規劃技術都尚缺乏有效實施路徑[7]。《市級國土空間總體規劃編制指南(試行)》圍繞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產城融合等戰略落實城鄉空間融合目標,推進城鄉三生空間有機互動。學者們從城鄉規劃、鄉村規劃、城鄉統籌規劃等視角嘗試分析城鄉空間統籌治理的可行方案[8-9]。當前,城鄉割裂發展、城鄉價值分配不均、城鄉轉型不充分、城鄉聯動不通暢等系統性城鄉治理問題,仍然是我國邁向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障礙[10-11]。
推進城鄉融合發展戰略需要國土空間規劃制定有針對性的支撐體系和落實路徑。構建面向城鄉融合發展的一體化空間治理體系,需要深化對城鄉空間差異管控模式,偏向性價值流向、失衡性配置邏輯[4,6]的體制機制研究。國土空間規劃通過重構城鄉發展要素流動趨勢、城鄉經濟空間布局、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城鄉公共服務配置、城鄉生態環境保護格局,進而重塑城鄉關系,提升空間治理水平,保障高質量發展。以縣域為載體的城鎮化發展新路徑,要求以縣域為基本單元,統籌城鄉發展宏觀布局。立足國土空間治理體系優化,如何在多級多類的空間規劃體系中,優化以縣域為載體的城鄉關系需要新思路,亟需在國土空間規劃體系中進行綜合考慮。立足城鄉空間統籌治理目標,建立國土空間規劃支撐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有利于完善空間治理體系,提升空間治理能力,服務國家現代化的現實訴求。
因此,本文以國土空間規劃支撐城鄉融合發展存在的體制機制困境為線索,系統總結推進城鄉融合需要破解的核心問題。以多目標國土空間規劃與城鄉關系轉型為抓手,嘗試解構國土空間規劃支撐城鄉融合發展的內在邏輯,并進一步探索可行的支撐路徑,進而完善分析框架。下文分別從現實困境、邏輯體系構建和路徑探索幾個方面展開論述。
1 國土空間規劃與城鄉融合發展的內在聯系
1.1 國土空間開發與城鄉融合進程的現實困境
城鄉發展的國土空間載體結構紊亂阻礙了城鄉關系的有序疏解。現階段,城鄉融合發展的國土空間載體缺乏遠景謀劃,制約了國土空間規劃支撐城鄉有序轉型的現實能力和潛力。城鄉空間網絡體系不完善,導致城鄉空間割裂進一步加劇,限制了區域城鄉空間的融合與統籌[6]。此外,差異化的城鄉空間管控體系,進一步撕裂了城鄉空間的融合進程,并強化了空間用途管制的城市價值取向,鄉村空間管控與限制力度進一步強化,鄉村空間開發利用潛力與活力可能被削弱,城鄉融合發展的空間支撐載體并未得到有效確認。城鄉空間體系動態遠景謀劃不足與多尺度協調機制紊亂,使得城鄉融合發展的空間支撐持續性不足。當前,城鄉空間遠景布局彈性空間不夠,城鄉空間邊界的動態調整機制不完善,城鄉空間多尺度結構體系不協調,難以應對城鄉發展的尺度差異性和空間異質性訴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空間開發與管控中存在明顯的利益“博弈”,多尺度城鄉空間結構的科學體系并未得到足夠重視[12]。
多尺度交互的空間網絡不暢通限制了城鄉發展要素的高效流通。城鄉發展要素有序流通與公共服務一體化配置是完善城鄉多尺度交互的前提,也是保障城鄉有序轉型的無形推手[13]。然而,城鄉空間差異化治理體制成為新時期阻礙城鄉共治,抑制城鄉發展要素高效流動的制度屏障。“自上而下”的空間管控傳導對落實國家安全底線做出突出貢獻的同時, “自下而上”反饋機制不暢通,城鄉發展要素自由流動的潛力和動力可能被抑制,進而帶來鄉村發展的要素短缺,鄉村非正規用地欲望進一步抬頭[14]。城鄉空間規劃事權劃分與治理不明晰,不能有效完善城鄉公共服務網絡體系。此外,城鄉市場鏈接體系和產業聯動體系的空間載體不匹配,資本、勞動力、技術等城鄉市場發展的核心要素難以在城鄉市場銜接網絡中高效運轉。鄉村空間開發與運營難以適應鄉村產業用地的靈活性、鄉村空間用途的復合性、鄉村空間管控的強彈性等訴求,不適應鄉村產業發展的現實需要,難以支撐鄉村產業發展的長遠目標。
空間多元價值實現渠道受阻抑制了城鄉價值的有序交換。城鄉空間發展權的不均衡配置,阻礙了空間多元價值的交換,成為限制城鄉深度融合的核心障礙之一[15-16]。以生產性價值為核心導向的自然資源價值評價體系難以適應城鄉深度融合的需求,國土空間的多元價值認知體系、評價技術、實現渠道尚未得到有效關注。國土空間產權體系不健全進一步阻礙了自然資源資產化和資本化的轉化道路,自然資源主體不明確,產權不明晰,交易不明朗,直接導致城鄉空間價值流動渠道不暢通,多元價值培育難以形成社會共識。城鄉空間已經形成固化的價值傳導鏈、市場供應鏈、主體參與鏈,進而塑造了城鄉空間的價值分配鏈[17]。城鄉空間價值因差異化市場化軌道的割裂而不斷加深,甚至發展成為城鄉二元發展的核心特征。城鄉空間差異化的所有權制度及其實現方式,逐漸成為塑造城鄉空間價值異化的制度缺陷[18],城鎮化帶來的土地增值收益絕大多數被城市發展所占據,鄉村空間價值顯化渠道和路徑不通,鄉村發展空間需求呈現行業性和社會性失語[19-20]。鄉村空間集體化組織方式和模式創新,鄉村全民所有的自然資源資產管理的制度化和法律化,精英化集體組織成員同現代鄉村經營主體的培育等治理體系仍待完善。
1.2 國土空間規劃與城鄉融合發展的銜接邏輯
國土空間規劃與城鄉融合發展在措施手段的相關性和目標體系的對應性等方面搭建了二者的銜接邏輯。國土空間規劃以國土空間的開發保護為綱領,形成對國土空間“要素—區域”的布局與動態優化,實現國土空間的綜合管控,服務國家空間治理現代化。因此,國土空間規劃體系是空間開發戰略落實的載體,尋求全域、全要素、全過程的一體化治理方案。從安全底線思維出發,國土空間規劃建構面向生態文明的空間布局方案,形成多層級聯動的空間管控體系,破解多部門空間規劃相互制肘的現實困境。城鄉融合發展從破解城鄉中國二元發展軌道的現實邏輯出發,需求建構城鄉聯動、城鄉互動、城鄉協同的發展性規劃愿景。此外,鄉村發展不充分、城鄉發展不協調、發展要素難流通、鄉村價值被弱化等現實問題,正是城鄉融合發展亟需破解的現實問題,而這些問題又同國土空間規劃的實施與成效密切相關。因此,國土空間規劃是推動城鄉融合發展落地的空間載體,國土空間規劃的管控與傳導邏輯也是確立空間發展權配置和發展要素流通的關鍵措施,面向城鄉高質量有序發展的共同目標是國土空間規劃與城鄉融合發展的銜接基礎。
國土空間規劃與城鄉融合發展的空間一致性和實施效應的互動性決定了二者深度銜接具有現實的可行性。當前,國土空間開發與城鄉融合進程呈現出的現實困境,與二者銜接體系不暢通、互動關系不明確緊密相關。國土空間規劃對空間資源的配置作用、多層級空間管制邏輯、多目標實踐機制,同城鄉融合發展亟需打破的城鄉發展體制機制障礙密切相關。此外,國土空間規劃決定了國土資源發展權的初次配置格局和城鄉空間發展權轉移的趨勢,一定程度上國土空間規劃及其實施策略決定了城鄉融合發展進程。因此,建構面向城鄉融合發展的國土空間規劃目標和實施路徑,需要打破城鄉分治的制度障礙,進而服務于城鄉高質量發展。
2 國土空間規劃支撐城鄉融合發展的邏輯體系
2.1 面向“發展—公平—生態”的國土空間規劃與城鄉融合作用
統籌協調經濟發展、社會公平與生態保護三者之間的關系是保障城鄉關系持續向好轉型的關鍵環節。城鄉關系問題與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的城鄉發展政策密切相關。因此,面向高質量發展也應從城鄉發展視角尋找突破口,“不發展型增長”“不發展型保護”“不發展型施策”均難以真正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中國的城鄉問題因發展而生,也將在發展中得以緩解。現階段國土空間規劃仍應以保障“發展”為核心導向,以保障實現現代化為根本目標。“發展才是硬道理”,在邁向第二個百年目標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然具有現實意義。國土空間規劃促進“發展轉向”可作為支撐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手段,變“低質低效發展”為“高質高效發展”,變“無序失衡發展”為“有序均衡發展”,變“短視脆弱發展”為“持續韌性發展”。唯有高質量發展才能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建設。我國剛解決絕對貧困問題,鄉村發展任重而道遠,鄉村內生發展動力不足,鄉村持續性發展基礎不牢,農業生產現代化、農民生計體面化、農村生活便利化、城鄉服務均等化均面臨重大現實挑戰[21]。現階段,解決城鎮化質量不高,工業化層次較低,農業現代化水平待提升等問題,需要在發展上找到突破口。國土空間規劃應以破解國家發展的核心問題為目標,為創新發展提供空間與機遇,為重塑城鄉發展格局提供戰略保障。
國土空間規劃體系中城鄉空間權利公平配置需要在體制機制上找到突破口。城鄉空間差異化用途管制體系決定了城鄉空間發展權初次配置存在顯著的差異,以城鄉建設用地差異化所有權實現方式為例,城市國有土地市場配置機制已逐步完善,而鄉村建設用地仍處于集體所有的供給配置狀態,城鄉割裂的建設用地管控模式和用途管制體系直接導致空間價值的巨量差異[22]。鄉村公共服務供給的長期短缺,已然成為當前城鄉發展不公平的重要障礙,教育和醫療等公共資源配置的城鄉差異,進一步導致城鄉發展差異的代際傳遞。城鄉空間價值市場配置現狀成為抑制鄉村空間價值實現的重要障礙,鄉村市場發育程度低,鄉村產品銷售網絡組織程度低,進一步固化了城鄉發展的不公平[3]。面向城鄉發展權利的公平配置,激發鄉村空間潛在價值,突破城鄉市場網絡的阻隔效應,破解城鄉空間發展權初次分配的制度缺陷,進而建構城鄉公平發展的空間管控體系。
面向高質量發展,生態友好型城鄉關系構建既是國土空間規劃亟需落實的目標,也是推進鄉村優先發展的重要保障。建設生態友好型城鄉公平的發展渠道,將是打破城鄉發展困境的有效路徑,為重塑城鄉空間價值創造條件[6]。鄉村空間作為生態型自然資源富集區,為平衡生態系統做出突出貢獻,科學核算城鄉空間生態價值,為生態產品的價值交換與交易創造條件。新一輪國土空間規劃“三區三線”劃定,從底線視角出發建構生態空間安全格局體系,有效支撐了城鄉空間生態網絡。
生態文明是建構城鄉關系的遠期根基,城鄉空間權利公平配置是城鄉關系優化的中期基礎,高效優質發展是統籌城鄉關系的近期條件。處理好“經濟發展”“社會公平”“生態保護”的時序進程和邏輯關系有利于明確城鄉融合發展的階段目標和工作重點(圖1)。通過國土空間規劃開辟鄉村發展的新增長點,完善農村公共服務配套,改善農民生產生活條件,全面推進農業現代化,將鄉村持續良性發展始終作為現階段解決“三農”問題的核心工作,將有助于擺脫運動式鄉村治理帶來的潛在危機。國土空間規劃在明確空間開發用途管制的基礎上,統一自然資源開發與保護,協調空間開發時序與發展權公平配置關系,統籌自然資源收益分配體系,有利于挖掘鄉村空間價值增值潛在手段和實現方案,進而推進城鄉空間公平發展[23]。以城鄉空間生態價值核算為基礎,探索城鄉空間發展權配置與交易體系,明確鄉村生態空間價值的歸屬和分配方案,進而落實城鄉生態文明建設的現實目標[1]。
2.2 國土空間規劃與城鄉“要素—結構—功能”融合體系建構
國土空間規劃作為“發展性”和“管控性”相結合的綜合性規劃,明確了國土空間管制的事權體系和監管主體,推動了城鄉空間剛性管控與彈性引導相結合。落實多目標國土空間規劃有利于城鄉發展要素的有序流通。鄉村發展要素流失、空間結構紊亂和功能衰退是城鄉地域系統動態變化的階段狀態[24],城鄉融合發展需要破解的難題多與鄉村空間承載的社會經濟狀態和權屬關系組織密切相關[25]。國土空間規劃立足于地域承載能力動態配置國土空間,以“三區三線”要素類管控為抓手強化空間地域功能的分區管制,利用“一張圖”突出底圖底數統一,提升國土空間數字治理能力[23]。城鄉發展要素自由和高效流通是保障城鄉融合發展的基礎動力,離開城鄉發展要素的跨尺度和跨地域流通,城鄉二元格局難打破,城鄉融合發展難推進。城鄉發展要素有序流動有利于緩解鄉村地區人地矛盾,進而重塑城鄉地域承載格局[26]。生態文明建設進一步強化了鄉村空間的生態功能屬性,城鄉空間生態價值流動有利于推動城鄉格局轉變。國土空間規劃體系下落實城鄉發展要素流動,需要在渠道疏通、補償激勵、管理保障等層面強化體制機制建設。全面放開多級城鎮落戶的限制條件,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應能力,重構城鄉土地發展權配置體系(如鄉村產業用地指標傾斜),探索靈活可控的鄉村國土空間用途管制模式。通過國土空間規劃的傾向性制度設計,吸引城鎮發展要素“入鄉回流”,落實城鄉發展要素雙向流動,進而推動國內城鄉大市場的聯動,推動城鄉空間要素發展的融合。
城鄉空間結構互通是打通城鄉空間價值交換和城鄉空間治理互饋的有效手段,也是構建國土空間治理體系和傳導路徑的重要環節。城鄉空間結構在物質空間結構(三生空間結構、土地利用結構、聚落體系結構等)和空間關系結構(空間組織結構、空間價值結構、空間權屬結構等)等層面改變城鄉融合發展進程[26]。以三區(城鎮空間、農業空間、生態空間)三線劃定為代表,國土空間規劃對城鄉三生空間結構從全局性統籌到局部性安排,成為城鄉三生空間結構優化的頂層設計。國土空間規劃對城鎮村聚落體系的結構性安排,決定了村鎮建設格局、城鄉空間布局、聚落體系等級的演化趨勢,成為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的關鍵力量。國土空間規劃作為分級分類實施的系統性規劃,重構了城鄉空間治理的組織模式,突出信息化和數字化技術在空間管控中的作用。城鄉國土空間一體化統籌,強化城鄉空間融合治理,將有利于打破長期以來形成的城鄉二元權屬結構特征,破解農村集體土地權能被抑制、市場化配置體系不健全(鄉村土地轉用的低補償與低成本)、多元主體參與度不高等問題。
城鄉功能融通在空間特征、時間特征、尺度特征等層面決定了城鄉融合發展的方向。國土空間規劃在規劃體系、規劃目標、規劃技術等方面將主體功能區劃融入其中,試圖通過多級尺度和多類目標實現國土空間綜合功能和主體功能的銜接,尤其在國家宏觀尺度的地域主體功能布局,成為塑造國土空間開發格局的重要依據,也是城鄉空間功能格局的主導因素之一[27]。城鄉空間功能定位的初次配置,決定了地域空間開發利用的未來趨勢,塑造了城鄉空間開發權利的價值流向(圖2)。國土空間規劃的城鄉地域功能定位和差異化管控模式決定了城鄉轉型發展的動力源,只有打通城鄉功能融合的渠道,推動城鄉空間價值交易與流轉,才能真正落實城鄉融合發展目標[28]。新時期,城鄉空間鏈接網絡化和城鄉空間治理數字化驅使城鄉空間功能,可以在更大尺度上實現交互影響,更大空間范圍內實現互動,城鄉空間功能融合渠道和價值流通通道也更具可能性。
面向“發展—公平—生態”的國土空間規劃為城鄉“要素—結構—功能”融合提供有效支撐。國土空間規劃通過優化城鄉空間要素流動、結構聯動和功能互動支撐城鄉融合發展的現實訴求。多目標國土空間規劃通過強化城鄉融合發展的空間支撐作用,破解空間利用存在的結構性和功能性問題。城鄉“要素—結構—功能”融合對國土空間規劃的多元目標實施提出更高要求,促進要素平等交換和自由流動,突出空間價值的公平配置,強化空間發展權和空間價值分配權的城鄉均等化,落實城鄉公共資源的均衡配置體系。生態文明體系下建構的國土空間規劃體系,將城鄉空間融合內嵌入生態文明的建構邏輯,服務城鄉融合發展的內在要求。
3 國土空間規劃支撐城鄉融合發展的路徑探索
國土空間規劃支撐城鄉融合發展的可行路徑需要破解上述核心障礙,探索多目標國土空間規劃的落實措施,推進城鄉空間治理現代化。城鄉國土空間結構功能體系優化,城鄉國土空間用途管制體系創新,城鄉國土空間統籌治理為落實上述目標提供依據。從城鄉國土空間地域發生規律出發,探索基于用途管制的發展權城鄉配置體系,推進城鄉發展要素流動與公共服務均衡配置,謀劃城鄉空間統籌治理的系統性架構。
3.1 優化城鄉空間網絡體系,保障空間有序高效開發
城鄉社會經濟發展要素的雙向流動,需要改變城鄉地域系統的結構功能狀態,進而破解城鄉國土空間交互作用的內在障礙,重塑城鄉互動格局[29],重構城鄉空間網絡體系,以城鄉空間網絡聯動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目標落實。現階段城鄉融合發展需要突破的問題仍需從二元軌道的城鄉國土空間管控不互通,城鄉國土空間價值分配不均衡,城鄉空間權利配置不對等入手找到突破口。“三區三線”的格局與動態調整是否能夠適應城鄉轉型的科學規律,適應階段性城鎮化的目標,仍需進一步論證和科學調試。研究差異化的城鄉空間結構轉型過程,探索城鄉發展要素雙向流動對城鄉空間結構功能的影響機制,進而分區調控城鄉空間結構功能體系,打破城鄉空間結構功能不協調、城鄉互動不通暢、城鄉價值難流通的現實問題。針對大都市區、傳統農區、典型牧區、綠洲地區等類型區,優化城鄉空間結構功能的主控要素,建設城鄉空間網絡體系,服務多目標發展導向的城鄉轉型趨勢。
新時期,城鄉空間網絡化、聯動數字化、互動跨尺度化趨勢為城鄉空間網絡建構創造機遇,基于空間網絡化的國土空間規劃實施體系為城鄉融合發展創造條件。當前,城鄉空間網絡化交互作用頻繁,尤其在信息技術和現代交通網絡綜合作用下,城鄉空間跨尺度作用成為跨越城鄉鴻溝的重要渠道,為打通城鄉空間治理障礙,疏通城鄉發展要素流通通道創造條件。因此,強化跨尺度作用對空間結構功能的優化作用,擴充地域承載力的內涵體系,進一步明確城鄉遠程耦合作用的價值體系,為城鄉空間功能交換和價值交易提供理論和實踐渠道[30-32]。以城鄉空間網絡化為平臺,科學評價空間流動性對國土空間承載力和開發適應性理論與實踐的擴展作用。從城鄉空間結構的連續性和功能的多樣性出發,以城鄉空間網絡和空間流動系統為突破,建構面向城鄉高質量發展、城鄉空間聯動開發、城鄉空間多層級流動的空間開發邏輯,突破當前限制開發與僵化保護的線性空間開發思維,服務城鄉融合發展訴求。
3.2 創新空間用途管制體系,促進空間價值公平流動
構建面向城鄉空間均衡發展的土地配置聯動體系,進而完善國土空間用途管制初次發展權配置失衡和城鄉差異化用途管制體系帶來的現實問題,推動城鄉空間價值公平流動,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的機制創新。國土空間規劃試圖建立協調與平衡的空間管控體系,平衡空間發展差異的重要工具。剛性約束有利但彈性管控措施不足將成為限制國土空間規劃實施成效關鍵環節,為了緩解剛性管控機制缺陷,需要探索城鄉空間跨區域聯動管控路徑,突破區域空間用途管控的制度障礙(如建設用地指標跨區域交易,虛擬耕地保護指標等)。此外,因地制宜探索城鄉國土空間用途管制聯動激勵制度,破解當前城鎮化過程中低效擴張和鄉村建設失序等現實問題。以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制度為基礎,創新開展城鄉國土空間用途管制的聯動實驗,突破現有指標交易的空間置換邏輯,從發展權配置視角出發,突出城鄉土地市場與用途管制的互饋機制,建立“土地用途管制→住房制度改革”的城鄉聯動制度創新鏈條。創新交易手段和市場配置方案,探索城鄉建設用地市場化運轉平臺,開辟城鄉融合發展特殊用途區(或城鄉融合規劃試驗區),發掘城鄉國土空間用途的差異化價格形成機制,發掘農村建設用地價值實現的新渠道和新路徑。
完善城鎮空間、鄉村空間和生態空間的用途管制體系,以城鄉空間價值公平為導向創新用途管制模式,開辟面向城鄉公平發展的國土空間規劃實施路徑。城鎮空間重點關注剛性指標傳導與分區管控的結合,推動城鄉網絡結構的互聯互通,讓渡土地發展收益向農村傾斜。鄉村空間治理探索在組織層面打破城鄉要素雙向流動的障礙,在權屬層面更多地給予基層和村民發展權,進而落實鄉村產業發展訴求、公共服務配給要求和基礎設施完善等目標。以實用性村莊規劃為突破,以產業發展為動力,以用途管制為手段,統籌建設鄉村基礎設施,開辟鄉村產業發展空間,提升鄉村生態保護與文化傳承能力,提高城鄉融合發展中要素互動與結構互通的水平,落實鄉村優先發展戰略。推動生態空間治理,細分生態空間劃分方案,挖掘自然保護區和自然公園的休憩娛樂和生態涵養功能,推動一般生態用途區的價值開發,創新生態空間價值實現與轉化機制,以城鄉空間網絡交互為基礎探索城鄉生態空間價值的公平交易。
基于多元主體有效參與,多級市場尺度交互,多種組織方案融合,推進城鄉國土空間用途管制體系建設,建設城鄉主體公平參與的空間規劃實施機制[33]。以土地征收改革、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改革為基礎,打破城鄉空間利益不均衡配置壁壘。以鄉村空間資源資產運營市場化改革為切入點,研究鄉村國土空間價值轉化的可行方案,探索城鄉國土空間用途轉用的市場化運轉機制。在管控落實層面,創新多元主體力量參與空間管控的有效機制,減少行政管控“成本高而成效低”等問題。開辟鄉村空間組織化和集體組織制度化模式,通過農村集體組織法人制度化、農村集體組織協調現代化、農村集體資產管理規范化、農村集體事權參與多元化等手段,落實鄉村空間用途管制的多元監督和議事制度,完善鄉村空間用途管制成效[34]。
3.3 統籌城鄉空間治理體系,搭建全域生態安全底線
城鄉國土空間統籌治理是完善全域生態安全底線的基礎,現有治理邏輯和技術體系需要新的突破,服務城鄉融合的空間安全支撐體系。城鄉分割的治理體系在現有國土空間規劃體系中仍較為明顯,保護耕地、修復生態、保障發展在不同城鎮化階段體現出的矛盾綜合體具有差異化特征,不能“顧此失彼”,更不能“因噎廢食”[30]。因此,需要從城鄉轉型規律出發,通過城鄉空間統籌治理落實生態文明目標,探索面向“發展—公平—生態”多目標的城鄉空間治理邏輯體系,突出城鄉空間聯動邏輯,以城鄉空間共治為核心目標,將國土空間規劃與城鄉融合發展的共同目標在統籌治理得到落實。從生態系統發生演化規律出發,結合城鄉生態空間差異化地域特征,制定全域生態治理方案,打破條塊分割和城鄉分離的生態治理思維,在國土空間規劃編制與實施過程中落實城鄉統籌的生態治理方案,探索全域生態安全底線協調方案,服務城鄉融合發展目標。
構建城鄉國土空間資源資產統籌配置的多元實現渠道,拓展城鄉空間治理價值流通的技術通道,完善城鄉空間統籌治理的現實邏輯。滿足城鄉公共服務統籌目標,積極推動城鄉公共服務供給一體化、基礎設施配套一體化和社會保障機制一體化,促進城鄉公共服務融合發展[30]。城鄉公共服務配置的統籌治理需要在技術層面進行科學的模擬,預測城鄉公共服務配置的時序階段和空間布局,提升空間治理配置效率[31]。統籌國土空間技術體系應對接前沿數字信息技術,將智能空間調控預測與國土空間信息數據庫對接,研發國土空間信息系統智能治理平臺,提升城鄉空間統籌治理的技術水平和預測能力,服務全域生態安全治理的定量測度與科學預測。
4 結論與討論
本文從城鄉融合發展的現實訴求出發,研判國土空間規劃支撐城鄉融合發展存在的現實和邏輯困境,從多維目標國土空間規劃入手,嘗試建構國土空間規劃支撐城鄉融合發展的實踐體系,進而探索了國土空間規劃支撐城鄉融合發展的可行路徑。
(1)國土空間規劃支撐城鄉融合發展的現實困境主要包含城鄉融合的國土空間載體結構紊亂、城鄉多尺度交互的空間網絡不暢通、城鄉空間多元價值融合的渠道受阻等方面。
(2)統籌協調國土空間規劃“發展、公平與生態”三維目標之間的關系是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關鍵。國土空間規劃應以保障“發展”為核心,兼顧城鄉空間權利公平配置,構建生態友好型城鄉關系。
(3)多維目標國土空間規劃推進城鄉發展要素的有序流通,國土空間治理體系和傳導路徑激發城鄉空間結構互通和城鄉功能融通,決定了城鄉融合發展的空間特征、時間特征、尺度特征。
(4)優化城鄉空間網絡體系,創新用途管制體系,統籌城鄉治理體系,搭建全域生態底線促進城鄉空間,為支撐城鄉融合發展提供有序高效開發保障、價值公平流動保障和全域生態安全保障。
本文以國土空間規劃支撐城鄉融合發展的現實困境為線索,基于國土空間規劃多目標體系與城鄉融合發展的內在關系建構,分析了國土空間規劃支撐城鄉融合發展的內在邏輯體系,并嘗試從空間地域網絡思維、城鄉空間統籌治理思維、城鄉空間用途管制創新思維出發,探索其可行路徑。由于國土空間規劃編制與實施尚在完善過程中,規劃目標與實施成效仍待評估,國土空間規劃支撐城鄉融合發展的創新機制和政策設計仍存在理論和技術上的限制,這些也是后續值得深入研究的內容。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 戈大專,龍花樓.論鄉村空間治理與城鄉融合發展[J].地理學報,2020,75(6):1272 - 1286.
[2] 劉彥隨.中國新時代城鄉融合與鄉村振興[J].地理學報,2018,73(4):637 - 650.
[3] 戈大專,陸玉麒.面向國土空間規劃的鄉村空間治理機制與路徑[J].地理學報,2021,76(6):1422 - 1437.
[4] 曹小曙,歐陽世殊,呂傳廷.基于用地分類的國土空間詳細規劃編制研究[J].經濟地理,2021,41(4):192 - 200.
[5] GE D Z, ZHOU G P, QIAO W F, et al. Land use transition and rural spatial governance: mechanism, framework and perspectives[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20, 30(8): 1325 - 1340.
[6] 林堅,武婷,張葉笑,等.統一國土空間用途管制制度的思考[J].自然資源學報,2019,34(10):2200 - 2208.
[7] 龍花樓.土地利用轉型的解釋[J].中國土地科學,2022,36(4):1 - 7.
[8] MACKINNON D. Rural governance and local involvement: assessing state community relations in the Scottish Highland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2, 18: 307 - 324.
[9] ANDRIJEVIC M, CRESPO CUARESMA J, MUTTARAK R, et al. Governance in socioeconomic pathways and its role for future adaptive capacity[J]. Nature Sustainability, 2019, 3: 35 - 41.
[10] 吳桐,岳文澤,夏皓軒,等.國土空間規劃視域下主體功能區戰略優化[J].經濟地理,2022,42(2):11 - 17,73.
[11] 龍花樓,屠爽爽.鄉村重構的理論認知[J].地理科學進展,2018,37(5):581 - 590.
[12] 嚴金明,陳昊,夏方舟.“多規合一”與空間規劃:認知、導向與路徑[J].中國土地科學,2017,31(1):21 - 27,87.
[13] 劉彥隨,王介勇.轉型發展期“多規合一”理論認知與技術方法[J].地理科學進展,2016,35(5):529 - 536.
[14] 顧朝林.論中國“多規”分立及其演化與融合問題[J].地理研究,2015,34(4):601 - 613.
[15] 賀艷華,譚惠敏,康富美.大都市邊緣區城鄉融合發展模式及效應評價——以長沙市望城區為例[J].經濟地理,2022,42(5):156 - 164.
[16] 葉超,于潔.邁向城鄉融合: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結合研究的關鍵與趨勢[J].地理科學,2020,40(4):528 -534.
[17] KOOPMANS M E, ROGGE E, METTEPENNINGEN E, et al. The role of multi-actor governance in aligning farm modernization and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8, 59: 252 - 262.
[18] 黃賢金.論構建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體系——兼論“同地、同權、同價、同責”的理論圈層特征[J].中國土地科學,2019,33(8):1 - 7.
[19] 曹智,李裕瑞,陳玉福.城鄉融合背景下鄉村轉型與可持續發展路徑探析[J].地理學報,2019,74(12):2560 -2571.
[20] 岳文澤,鐘鵬宇,王田雨,等.國土空間規劃視域下土地發展權配置的理論思考[J].中國土地科學,2021,35(4):1 - 8.
[21] 張英男,龍花樓,馬歷,等.城鄉關系研究進展及其對鄉村振興的啟示[J].地理研究,2019,38(3):578 - 594.
[22] 郭杰,陳鑫,趙雲泰,等.鄉村空間統籌治理的村莊規劃關鍵科學問題研究[J].中國土地科學,2020,34(5):76 -85.
[23] 張京祥,夏天慈.治理現代化目標下國家空間規劃體系的變遷與重構[J].自然資源學報,2019,34(10):2040 -2050.
[24] GE D Z, LONG H L, QIAO W F, et al. Effect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on rural production transformation in Chinas traditional farming area: a case of Yucheng City[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0, 76: 85 - 95.
[25] 龍花樓,屠爽爽.論鄉村重構[J].地理學報,2017,72(4):563 - 576.
[26] 葉超,于潔,張清源,等.從治理到城鄉治理:國際前沿、發展態勢與中國路徑[J].地理科學進展,2021,40(1):15 - 27.
[27] 岳文澤,王田雨,甄延臨.“三區三線”為核心的統一國土空間用途管制分區[J].中國土地科學,2020,34(5):52 -59,68.
[28] 周敏,林凱旋,王勇.基于全鏈條治理的國土空間規劃傳導體系及路徑[J].自然資源學報,2022,37(8):1975 -1987.
[29] 谷瑋,王夢婧,吳次芳,等.統籌發展與安全戰略下的國土空間規劃:范式、學理和實踐邏輯的反思與回應[J].中國土地科學,2022,36(6):11 - 20.
[30] 崔樹強,周國華,戴柳燕,等.基于地理學視角的城鄉融合發展研究進展與展望[J].經濟地理,2022,42(2):104 -113.
[31] LONG H L. Land Use Transitions and Rur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M]. Singapore: Springer, 2020: 519.
[32] 賈克敬,何鴻飛,張輝,等.基于“雙評價”的國土空間格局優化[J].中國土地科學,2020,34(5):43 - 51.
[33] 張曉玲,呂曉.國土空間用途管制的改革邏輯及其規劃響應路徑[J].自然資源學報,2020,35(6):1261 - 1272.
[34] 盧新海,王洪政,唐一峰,等.農地流轉對農村減貧的空間溢出效應與門檻特征——省級層面的實證[J].中國土地科學,2021,35(6):56 - 64.
The Logic and Path of Supporting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rough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GE Dazhuan1,2, SUN Pan1,2, TANG Lisha3, SUN Dongqi3, TANG Shuangshuang1,2(1. School of Geograph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2. Jiangsu Center fo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Nanjing 210023, China; 3.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practical dilemma and internal mechanism of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to support the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o propose the feasible solution,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to facilitate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s one of the core objectives of a high-quality spatial governance system. The research methods are inductive deduction and logical deduc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unimpeded multi-scale interactive space network and the difficult exchange of multiple spatial values have become realistic difficulties that hinder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easures and target system of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and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stablishes the cohesive logic of the two. The consistency of space and interaction effect determines the practical feasibility of their connection. Optimizing the urban-rural spatial network system, innovating the space use control system, and coordinating the urban-rural spatial governance system have become feasible paths to support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In conclusion,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coordinate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dimensional goals of “development, equity and ecology” for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and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factors, structures and functions”. Moreov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rderly transfer of urban-rural factors and the balanced allocation of public resources can improv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between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and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Key words: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urban-rural spatial governanc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rural spatial governance; rural revitalization
(本文責編:陳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