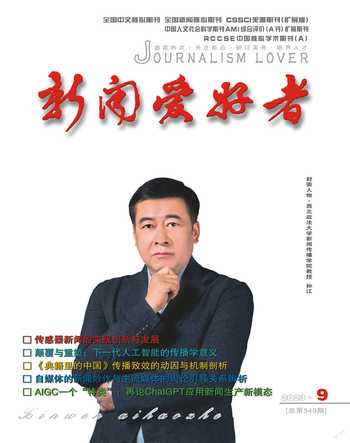AIGC一個“特類”:再論ChatGPT應用新聞生產新模態
郝雨 文希
【摘要】人工智能不但顛覆了傳統新聞生產傳播的方式,而且將催生全新的新聞產品和樣態。人工智能從算法程序處理大數據的基礎層,到多模態識別模擬人類體感知覺的感知層,到現在演進為自然語言理解自動生成的認知層,讓新聞生產傳播朝著智能化、人性化、個性化的方向發展。ChatGPT的出現為探索“人機對話新聞”提供了無限可能,未來在人機互嵌中共塑智能新聞業。
【關鍵詞】人工智能;新聞生產;對話新聞
在不斷迭代的智能媒介化浪潮中,新聞傳播業態將如何被改寫值得學界持續關注。本文之所以把ChatGPT新聞生產稱為AIGC特類品種,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其他任何AIGC都是依賴數據庫已有資源加以自動生成內容,而ChatGPT新聞生產則必須從現實世界和場景提取素材,因為“新聞是最新發生的事實報道”。對新聞事實第一手資料的現場獲取以及深度訪談調查報道等特殊生產方式,是對ChatGPT的特別考驗和挑戰。
一、在顛覆中推進:無可抵擋的人工智能作用于新聞生產
(一)以計算機為視角,萬物皆可編程
在智能新聞中,萬物皆可被編碼為抽象數據。智能技術抓取信息主要通過信息采集、數據判斷、結果執行三個基本單元完成,信息采集單元負責搜羅計算機可識別電子數據信息,之后傳遞給數據判斷單元進行歸類,最后由結果執行單元進行取舍。這樣的方法避免了重復采集數據,提升效率的同時確保數據的準確性。智能技術除了利用人類現成的數據庫,也有自己的信息采集方式。其一,無人機采集新聞影像。當現場環境極其危險,記者無法靠近時,無人機實時捕捉現場環境影像,傳回更加全面高清的視頻。比如客機事故、森林火災、化學品爆炸等緊急危險事件,無人機能實時跟進災難新聞報道。其二,智能傳感器延伸人的視覺、聽覺、觸覺感官,為全景式新聞提供24小時的新聞素材。封面新聞打造的“智慧內容平臺”每日可采集的數據達上千條。傳感器技術實現了傳統由人趕往事件現場到事件現場向人實時傳送的轉變。信息采集的智能化大大削減了記者重復勞動的工作量,使記者能夠投身到更具創造性的深度報道中去。
(二)計算可能性的窮盡,AI預測新聞強勢突圍
如何從海量數據中挖掘出有價值的新聞線索是新聞生產的第二個重要環節。傳統的新聞生產方式是依靠具備豐富社會經驗和知識儲備的資深新聞從業人員日積月累的新聞敏感度,人工智能則是利用算法洞察大數據的趨勢與異常,美國西北大學教授Nicholas?Diakopoulos將其稱為“計算發現新聞”。人工智能透過多維數據處理工具預測事件潛在的發展趨勢,強大的分析與預測功能推動“AI預測新聞”的強勢崛起,這也是對人類分析力、提煉力和預測力的模仿。因為人工智能是對已有資料的挖掘,由于新資料的注入、環境的變化,預測也可能會出現偏差失靈的情況,因此需要人的參與和監督。
數據分析處理過程是AI的機器學習過程,算法模型在分析處理中不斷修正完善,數據庫由此不斷充實。整體而言,數據處理過程是對數據庫文本內容的先解構再重構,如此循環往復生成更多新聞故事和擴容數據庫的增殖過程。以ChatGPT為例,它的技術信息處理大致也分為三個層次,分別是預料體系、預訓練算法模型和微調算法模型[1]。首先,OpenAI公司將從網絡渠道搜集到的海量無標注數據利用開源代碼爬取、搜集、加工成有標注的優質文本。接著,用預訓練算法模型訓練ChatGPT,從2018年初代版本GPT-1的5GB訓練文本,到GPT-3的45TB訓練文本,正是因為OpenAI研發了可以處理巨量訓練文本的預訓練大模型,才使得ChatGPT-3脫穎而出,甚至引發白領人群的飯碗恐慌。預訓練算法模型具備自然語言理解、生成和聯系上下文內容的能力,能夠根據人類的提示(Prompt)結合特定場景,捕捉語義相似性和關聯度特征,輸出準確的高質量文本。最后,在預訓練基礎上,OpenAI公司進一步研發出微調算法模型,賦予GPT-4更強的代碼理解、修改、生成能力。ChatGPT是人工智能數據處理技術的卓越進步。
(三)輸出大于輸入,AIGC的創造性生成
傳統新聞的生成,在獲取新聞線索后,記者需要投身采訪、寫作中,而今網絡將地球聯結成一個村落,人工產出新聞的數量難以滿足受眾的信息需求,新聞寫作智能化大大緩解了新聞供小于求的問題。AIGC不同于傳統搜索引擎基于互聯網上已有的內容調取預設答案,智能內容生成會根據用戶的提問生成新的內容。目前AIGC的類型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使用預先埋入模板模型,輸入素材輸出固定模式的規格化新聞類型。中國地震臺網的地震報道就是典型的模板模型寫作,它的優勢在于成稿速度快,不到30秒便能生成分發。另一類是自然語言處理模型,可將采集到的數據轉化為“類人話”語言,此技術可對機械化報道進行語言潤色,減少機器寫作的生硬僵化。ChatGPT采用的是大語言訓練模型(Large?Language?Mode,LLM),并且創造性地運用了人類反饋強化機器學習(RLHF),以至于ChatGPT能快速產出符合人類用語習慣,符合大眾基本認知和具有普世價值觀的內容。自然語言處理模型是MGC向AIGC轉變的結果。有網友試用后批評ChatGPT生成的是“正確的廢話”,其實ChatGPT的回答遵循的是類似黑格爾辯證法的邏輯。我們以“AI是否會取代人類及工作”的問題為例讓ChatGPT生成一篇“人機關系”的論文大綱,ChatGPT列出的核心主干部分是“AI如何取代人類工作,AI無法取代人類”,各從三個方面論述,最后得出結論“AI與人類合作才是未來”。從這個框架背后可以明顯看出ChatGPT正是運用了黑格爾辯證法“正反合”的思維方法。學者張生將此邏輯方式稱之為“褶子”,此說法引自法國后現代哲學家“有機體褶子”理論。即論證總是從正反、內外、現象本質等方面同時展開,它們是密不可分的一體[2]。這恰是ChatGPT的優長之處,既保持了內容的相對客觀性,又拓展了語言思維的表達方式。
如今AI主播、聊天機器人、語音識別播報助手、數據可視化短視頻等智能新聞呈現形式日新月異。文本方面,寫稿機器人已經突破前1.0的生成簡要通訊類信息的階段,進入可以依據語法邏輯、算法關聯生成帶有一定分析的長新聞稿的2.0階段。圖片方面,AI能為報道自動配圖,二維圖、3D模擬動畫等元素的加入增加了新聞報道的生動性。音頻方面,已經出現了閱讀機器人,自動為視頻內容創作音頻。視頻方面,將抓取的數據生成可視化視頻內容,用AI主播播報。如《新京報》用3D動畫還原了韓國梨泰院踩踏事故,生成名為《血色萬圣節》的動新聞。《人民日報》的AI數字主播任小融出鏡了全國“兩會”報道。人工智能不但豐富了新聞形式,同時人機的交互性也越來越強。用戶對新聞事件的觀點、時評也會被抓取成為AI新聞的素材。AIGC的智能是“集成的智能”,用一個公式來表達就是AIGC=UGC+PGC+OGC+MGC,以此建構了新的媒介內容生產格局。
二、“把關”與“使用”的雙重精準:人工智能內嵌于新聞分發
(一)“擬主體性”充當“把關人”,賦能AI審核
社會心理學家盧因認為,只有符合群體規范和把關人意見的信息才可流向大眾。智能時代把關機制由人向機器轉移。用魔法打敗魔法,用技術監管技術,開發出人工智能信息核查系統為新聞生產助力。學者吳飛提出記者編輯的把關應該設置三道關卡:事實觀、政治關、辭章關[3]。這三道關卡同樣也適用于人工智能為智能新聞把關。政治方面,過濾掉敏感詞;辭藻方面,語料算法模型自動糾錯。這兩關比較容易通過,而真實是新聞的生命,事實核查是新聞把關的基礎和核心要義。
對于新聞事實的核查有以下四種方式。第一,算法能夠追蹤一個事件的全過程,同樣也能追溯同一新聞不同的信源,將不同信源的信息進行交叉驗證便能迅速辨別出新聞的真假。第二,基于圖像識別系統對抗虛假信息。圖像識別系統可以在海量的圖像、影像中快速定位新聞事件的人物信息,從源頭阻斷不實信息。第三,版權檢測系統打擊知識侵權行為。版權檢測系統的核心技術是區塊鏈,原創作者將作品加密上傳到區塊鏈網絡,每位作者的作品都有唯一的區塊鏈,如此便將原創文本、影像納入監管范圍之內。第四,輿情仿真系統研判新聞走向。輿情仿真系統是在新聞作品還未發表出來之前,模擬新聞作品可能產生的社會輿論,預判新聞的大致輿論走向,為記者寫作內容、角度提供參考。總體而言,事實核查是對新聞質量的把關,AI運用到事實核查中有利于生產出優質新聞。
(二)算法思維介入內容分發,激活長尾效益
傳統報紙的新聞生產和分發是相互獨立和分離的,智能新聞的生產和分發實現了時間上的同步、空間上的分離。在時間上,智能新聞程序不但能實現自動分發,而且還能依據算法精準匹配需求,從以前的“我找新聞”到現在的“新聞找到我”(news find me)。算法分發提升了用戶黏性的同時激活了新聞內容的“長尾效應”。以“今日頭條”APP為代表,采用協同過濾算法,一方面搜集用戶足跡,多角度描摹用戶個人畫像,推送符合用戶喜好的信息。另一方面搜集用戶的社交信息,多維度描摹用戶社交地圖,在興趣相投、經驗相同的圈子中投放熱點新聞。社會網絡科學發現,社會廣大民眾成為網絡中的節點,以“己”為中心聚散著新聞信息。人類學家羅賓·鄧巴認為自然狀態下,人的大腦決定一個人所能連接的社交網絡上限是150人。人工智能則拓展了人類的社交連接能力,算法將共同愛好的人聚合在一起形成虛擬社群,實現精準分發。
在空間上,新聞生產系統和分發系統分離,媒體擁有眾多發布新聞的渠道。首先,媒體自有的平臺自產自銷。其次,門戶網站、搜索引擎充當搬運工。然后,基于人際關系的社交媒體觸發新的分發方式,集直播賣貨、興趣交流、快捷資訊多功能服務為一體。最后,分發平臺以算法為媒介連通用戶與內容,新聞生產者用算法解讀用戶需求,用戶用算法陳述“我的訴求”。在人—機—內容機制對話下,增強了生產者對受眾的理解力,提升了受眾“使用與滿足”理論下的地位升級,讓媒體可以向用戶提供私人定制化服務,帶領新聞生產傳播走進TOC運作模式,也就是生產內容面向個人用戶,注重用戶的個人體驗,這是智媒趨于人性化的體現。聊天機器人的出現,讓用戶以對話的方式獲取新聞成為可能。此外,從用戶消費新聞的角度來看,智能移動設備的泛化致使用戶無時無刻不處在自由流動的新聞場景中,加拿大學者赫米達將這種始終在線的新聞景觀稱之為“彌漫新聞”。移動化、場景化、個性化成為智能新聞的代名詞。
三、智能化再造:ChatGPT催生人機對話新聞新模態
縱觀人類傳播史,技術革新不但會帶來新聞生產傳播流程的變革,而且還會催生出新形態,為新聞業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比如微博、Facebook等社交平臺催生了自言自語的“私語式新聞”[4]。各類直播平臺催生了演員以線上直播表演的方式向受眾展示事件發生過程的“劇場新聞”[5]。如今,ChatGPT對內是可以結合上下文語境與人類進行持續對話的聊天機器人,對外是基于千億級別參數量訓練出來的生成式AI,為人類提供信息服務。自20世紀80年代“信息”這一概念被新聞學引入后,信息實現了與新聞的融合,甚至有學者提出“新聞是新近信息的媒介互動”[6],強調了新聞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向受眾提供信息,這與人機對話在于獲取信息的根本目的不謀而合,從此路徑出發,ChatGPT將可能催生出“對話新聞”新模態。
(一)智能工業中雙向度的人,人—機“對話新聞”
對話(Dialogue)來自希臘語“Dialogos”,意為兩個或以上主體之間的談話、交流。國外蘇格拉底采用問答式對話開啟教育實踐,國內經典著作《論語》用語錄體的寫作方式闡述儒家思想。學者奧倫·索弗認為“對話”是新聞民主的體現,是相對于長久以來客觀新聞規范的另一種思維方式,于2009年提出“對話新聞學”。學者蔣曉麗和李瑋認為“對話新聞”崇尚平等協商、相互交流、彼此糾正的精神是對19世紀末實證主義倡導客觀、公正原則的反思。李希光教授從國際傳播的角度提出對話新聞旨在減少或避免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民族之間溝通交流的屏障與誤解[7]。史安斌教授認為新聞是記者與采訪對象對話的產物,與“客觀新聞學”目的是傳遞信息給受眾的首要功能不同,“對話新聞”旨在引發具有建設性的公眾對話[8]。總體而言,對話新聞提倡建立平等多元的公共對話平臺。記者扮演著推動社會進步的參與者角色;受眾不是“讀新聞時代”被動接收信息的“單向度的人”,而是擁有充分表達權、生產權、傳播權的“雙向度的人”。從技術可供性視角來看,對話新聞對應的是數字媒體主導的“人人都是記者”“多音齊鳴”的新聞傳播生態。當智能技術賦能新聞,新型媒介聊天機器人突破“人人對話”模式轉向“人機對話”模式,新聞傳播理念也需要跳出傳統的“以人為中心”的客觀反映論視角,走向“人機共生”的主動對話觀視角。
ChatGPT面世以來,用戶陷入與它持續對話的互動狂歡之中,ChatGPT與人的對話何以產生?ChatGPT有賴于生成式預訓練的Transformer模型和對比預訓練的Embedding模型。Transformer模型的核心組件是編碼器和解碼器,解碼器的功用是詞預測(Next?Word?Prediction),也就是基于給定文本序列,無監督地預測后續文本,這是ChatGPT能自動生成文本的根源。Embedding模型原理是關聯相近文本,推開不相似文本,以完成聚類、分類、搜索等任務。ChatGPT能生成高質量的“人類語言”得益于人類反饋強化學習(RLHF)微調技術,標注者對生成的N個答案進行排序,讓ChatGPT的輸出文本接近人的表述。關于人機的“對話新聞”實踐在ChatGPT引發輿論爆點之初就已出現,多家媒體與ChatGPT實戰對話,連篇累牘的報道將ChatGPT推上頂流之路。
(二)ChatGPT震蕩新聞傳播生態
美國媒介理論家保羅·萊文森提出媒介進化的終極目標是人性化的觀點。ChatGPT擬人化的持續對話引發人們對AI未來是否會擁有意識和情感的終極想象,帶來“人機”關系的新思考。運用到新聞傳播領域,除了可能催生人機“對話新聞”這一新樣式之外,還會對整個新聞傳播業態產生結構性的沖擊。
在新聞生產主體方面,生產簡單化、扁平化新聞信息的“勞工型”記者面臨被具備計算機知識,精通算法原理的“技術型”記者所取代的風險。技術型記者需要熟練操作人工智能生產傳播新聞,同時還能及時處理人工智能故障的問題。ChatGPT介入新聞生產能快速調查被采訪者的背景信息,依據被采訪者的特性列出采訪提綱,甚至加入到采訪過程中,同步記錄采訪者的回答并整理出新聞線索。但是AI目前還存在算法偏見和新聞失實的情況,記者需要承擔起幕后監管AI的職責。聯合機器人公司首席營銷官塞西莉亞·坎貝爾認為大語言模型(LLM)會無差別引用互聯網所有可訪問的文本,GIGO問題明顯,嵌入新聞中加劇深度造假風波[9]。這就需要記者著重把關內容,修正錯誤的事實和帶有偏見的觀點。硅基智能體看似給記者職業帶來了危機感,實則仍是碳基智能體的產物,從“機之為人”的角度看,人類的主體性不但沒有削弱反而增強了。
在生成新聞內容方面,場景化構建得到格外重視與強化,《即將到來的場景時代》一書中揭示未來25年互聯網將進入全新的場景時代。各大主流媒體結合智能技術打造智媒應用場景。5G以高速率、大連接、低時延優勢解決場景化應用視頻卡頓、無法交互和延時加載的問題。新華社建立了“新立方智能化演播室”,在全國“兩會”中推出兩個真實空間場景虛擬跨屏訪談系列報道。聊天機器人從專注文本對話進階成文本、圖片、音視頻等多模態的互動,ChatGPT支持輸入圖片輸出描述,文心一言支持輸入描述輸出圖片。AI接入音響系統打開語音聊天機器人的窗口,接入VR可穿戴設備延伸觸覺感官,接入搜索引擎開啟智能問答,微軟已將ChatGPT接入搜索引擎Bing中,知乎應勢發布了“知海圖AI”,AI智能問答場景應用將成為新的流量風口。
在算法分發方面,用戶提問破除信息繭房。個性化推送算法應用以來,信息圍城的問題日益凸顯。正如心理學著作《象與騎象人》中所描述的那樣,騎象人以為是自己決定了前進方向,但實際上是由大象80%的潛意識和騎象人20%的顯意識所共同決定的,如今人工智能就是大象,在人類自主決策中隱性地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不同于平臺算法靜態精準推送的方式,ChatGPT生成內容的分發包裹在一個不斷人機交互的動態對話之中,用戶最后所獲取的信息不是由平臺單方面決定,而是在用戶自主思考和算法模型計算的雙重作用下決定的。這意味著算法判定用戶喜好的做法將被逆轉,用戶自身代表著一種主動選擇的機制,以提問的方式反向制約AI完全聽命于算法,用戶媒介素養的提高還將幫助ChatGPT補充信息,還原事實,平衡觀點。在人機多輪對話中,個體加深了對新聞的理解。就用戶角度而言,聊天機器人讓用戶從傳統單向度的離身新聞接收轉化為雙向度的具身人機交互,在對話體驗中加深用戶身體和情感的卷入程度,凸顯人工智能的人性化陪伴功能。
四、結語
人工智能技術的可供性極大擴展了新聞的應用場景,豐富了新聞的表現形式。聊天機器人引領的人機對話新聞,無疑表現出媒介技術與受眾本位視角,重視人工智能和用戶全程化參與到新聞采集、處理、寫作、審核、分發各個流程中去,注重在媒體—人工智能—受眾之間建立一個三腳架的多元循環交流關系,增強了媒介、媒體、用戶三者之間的理解力、關聯性和互動性,全面提升了新聞傳播的效能。新聞生產傳播業態中,各個環節均可見人工智能的身影。大數據賦能記者腳力,圖像處理賦能眼力,機器自動化寫作程序賦能筆力,算法模型賦能腦力,全方位延伸了新聞生產者的感官,開啟了人機共生共存的智能傳播時代。
參考文獻:
[1]錢力,劉熠,張智雄,李雪思,謝靖,許欽亞,黎洋,管錚懿,李西雨,文森.ChatGPT的技術基礎分析[J/OL].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0.1478.G2.20230324.1112.002.html.
[2]張生.ChatGPT:褶子、詞典、邏輯與意識形態功能[J].傳媒觀察,2023(3):42-47.
[3]胡尊櫳.人工智能在新聞傳播中的應用研究[D].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2020.
[4]王建磊.社交型媒體與變形的新聞[J].新聞記者,2010(9):65-69.
[5]田浩,常江.回歸社區與重構真實:劇場新聞的理念與實踐[J].中國編輯,2023(Z1):105-112.
[6]寧鵬莉,王建磊.作為“對話”的新聞:ChatGPT帶來的新聞業態變革可能[EB/OL].https://mp.weixin.qq.com/s/Nz3DAyBxrbEFMJ5QvLV
MyQ.
[7]蔣曉麗,李瑋.從“反映論”到“對話觀”:論多重語境下新聞的轉向[J].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6):141-145.
[8]史安斌,錢晶晶.從“客觀新聞學”到“對話新聞學”:試論西方新聞理論演進的哲學與實踐基礎[J].國際新聞界,2011(12):67-71.
[9]張建中.面對ChatGPT,新聞記者不應該有身份危機[EB/OL].https://mp.weixin.qq.com/s/eLyLLV0dkWpS3qph_8-bAw.
作者簡介:郝雨,上海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上海 200444);文希,上海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生(上海 200444)。
編校:董方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