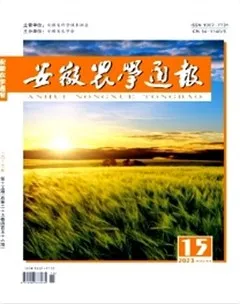新鄉(xiāng)賢助力鄉(xiāng)村振興的內(nèi)在邏輯及其實現(xiàn)路徑
于恩洋
(廣西師范大學(xué)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廣西桂林 541004)
1 問題的提出
新鄉(xiāng)賢是脫胎于傳統(tǒng)鄉(xiāng)紳的、具有一定知識技能、高尚的道德品行、較好的經(jīng)濟基礎(chǔ)的人才,在鄉(xiāng)村振興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人才振興是鄉(xiāng)村振興的基礎(chǔ)和關(guān)鍵,要把人力資本開發(fā)擺在鄉(xiāng)村人才振興的首要位置。鄉(xiāng)村人才困境仍是掣肘鄉(xiāng)村發(fā)展的重要因素,學(xué)界為此也做了大量研究,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鄉(xiāng)村人才缺失的原因、鄉(xiāng)村人才隊伍建設(shè)的途徑。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鄉(xiāng)村人才振興政策的實施,但是不能忽視社會資本的缺乏給鄉(xiāng)村人才振興政策實施帶來的阻力。目前鮮有研究立足社會資本視角探討破解鄉(xiāng)村人才振興困境之道,社會資本存在于每個人和他們的社會關(guān)系中,并作為個體及其組織擁有的社會結(jié)構(gòu)資源(信任、規(guī)范和網(wǎng)絡(luò)),能夠?qū)︵l(xiāng)村人才振興產(chǎn)生深刻的影響。社會資本概念最早是由布爾迪厄于1980年提出,社會資本就是個人在社會結(jié)構(gòu)中的社會網(wǎng)絡(luò)聯(lián)系以及成員資格、身份。隨后科爾曼將這種社會網(wǎng)絡(luò)聯(lián)系總結(jié)為權(quán)威關(guān)系、信任關(guān)系以及作為社會規(guī)范基礎(chǔ)的關(guān)于權(quán)利分配的共識。帕特南在科爾曼的基礎(chǔ)上進一步完善了社會資本的概念,并最終形成了關(guān)于社會資本的普遍認知,即社會資本包括互惠的規(guī)范和公民參與的網(wǎng)絡(luò)[1],它是指社會組織的特征,如任人唯賢、交往規(guī)范、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等。
目前,鄉(xiāng)村人才總量不足、鄉(xiāng)村人才素質(zhì)不高以及鄉(xiāng)村人才結(jié)構(gòu)不優(yōu)是制約鄉(xiāng)村人才振興的因素之一[2]。新鄉(xiāng)賢作為新時代背景下的農(nóng)村經(jīng)濟文化“能人”,自身具備雄厚的社會資本以及濃厚的鄉(xiāng)土情懷,學(xué)界認為新鄉(xiāng)賢能夠遵循鄉(xiāng)村人才振興的價值規(guī)律,助力鄉(xiāng)村人才振興。一方面是因為作為傳統(tǒng)社會精英的“鄉(xiāng)村能人”群體都呈現(xiàn)出相似的特征,即擁有雄厚的社會資本,能夠利用社會資本參與鄉(xiāng)村治理;另一方面是因為當今鄉(xiāng)村人才振興缺乏社會資本的注入,導(dǎo)致主客體之間信任度低、人才管理制度不完善以及治理網(wǎng)絡(luò)薄弱,而作為“新型社會精英”的新鄉(xiāng)賢,自身也是人才群體的組成部分,并且也具有雄厚的社會資本的特征,可以在鄉(xiāng)村振興中引發(fā)模范效應(yīng)、增加鄉(xiāng)村人才振興社會資本、解決鄉(xiāng)村人才振興困境。
2 新鄉(xiāng)賢助力鄉(xiāng)村人才振興的內(nèi)在邏輯
2.1 新鄉(xiāng)賢能夠提升鄉(xiāng)村人才振興主客體之間的信任度
新鄉(xiāng)賢提升鄉(xiāng)村人才振興主客體之間的信任度主要體現(xiàn)在2個方面。一是新鄉(xiāng)賢自身與鄉(xiāng)村主體之間的高信任度,新鄉(xiāng)賢作為人才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自身的高信任度能夠有效填補其他人才與鄉(xiāng)村之間的信任“空缺”。這種高信任度從古代一直延續(xù)至今,這種信任來源于血緣關(guān)系帶來的親緣信任,特指內(nèi)生鄉(xiāng)賢;同一地方帶來的地緣信任,特指生于斯的外在鄉(xiāng)賢;治理合作帶來的業(yè)緣信任,特指政策招引或自發(fā)下沉的農(nóng)村精英,他們以服務(wù)鄉(xiāng)村為本位、突出公益性,為鄉(xiāng)村經(jīng)濟發(fā)展注入大量資源,因此獲得了村干部和村民的普遍信任。
二是新鄉(xiāng)賢能夠?qū)崿F(xiàn)鄉(xiāng)村人才振興主客體之間信任度的積累和強化。社會信任作為社會資本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來自個體間互動和使用的積累,新鄉(xiāng)賢作為某一領(lǐng)域內(nèi)的精英,自身有著過硬的領(lǐng)導(dǎo)、協(xié)調(diào)和溝通的能力,他們對于組織成員人際關(guān)系的運作有著豐富的實踐經(jīng)驗,能夠利用自己的領(lǐng)導(dǎo)能力和管理知識消除人才群體之間因交流溝通產(chǎn)生的不和諧,從而加強彼此的互動與合作。這是因為新鄉(xiāng)賢在人才群體中有著超越他人的威望,所以大部分人才愿意相信新鄉(xiāng)賢的領(lǐng)導(dǎo),同時新鄉(xiāng)賢比政府更加了解下鄉(xiāng)人才的需求,懂得如何協(xié)調(diào)、滿足群體和個體的需求,避免沖突產(chǎn)生的信任危機。此外新鄉(xiāng)賢能夠利用地方性知識有效化解下鄉(xiāng)人才和村民之間因地域、文化以及價值觀沖突等造成的信任危機,推動雙方在統(tǒng)一規(guī)范、包容和諧的鄉(xiāng)村秩序下實施治理活動、加強雙方的信任。社會信任也是對于社會制度、規(guī)范和網(wǎng)絡(luò)的信任,隨著鄉(xiāng)村人才振興主客體之間信任度的積累與強化,鄉(xiāng)村人才振興的規(guī)范將更加完善、治理網(wǎng)絡(luò)將更加優(yōu)化,三者并非此消彼長而是相互促進的關(guān)系,進而形成良性循環(huán)。
2.2 新鄉(xiāng)賢能夠完善鄉(xiāng)村人才振興實施規(guī)范
制度是政策執(zhí)行的重要載體,制度的運行能夠為實施鄉(xiāng)村人才振興政策提供保障,新鄉(xiāng)賢在促進正式制度的確立和非正式治理條約的成立方面發(fā)揮著積極作用。首先是在人才管理制度方面,新鄉(xiāng)賢自身就是優(yōu)秀的管理人才,大多數(shù)憑借多年在外經(jīng)商的實踐具備一定人力資源管理的知識和經(jīng)驗,而且作為人才群體中的一員,新鄉(xiāng)賢比地方政府更加了解不同人才的自我需求,因此收集人才群體的需求信息會更加全面和高效,有利于政府不斷完善人才管理制度,推動人才管理的制度化、規(guī)范化。其次是在非正式治理條約的制定方面,新鄉(xiāng)賢能夠促進村規(guī)民約的形成與完善。非正式的治理條約是人們基于一套共享的價值規(guī)范體系所打造的行動準則和行事標準,它是鄉(xiāng)村人才振興社會資本體量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人才群體的行為規(guī)范起到約束作用、能夠促進人才群體間的合作、增加彼此信任。新鄉(xiāng)賢憑借自身權(quán)威以及對地方性知識的掌握,在制定非正式治理條約時能夠獲得普遍信任,而且新鄉(xiāng)賢以身作則的影響力能夠為非正式治理條約的約束力提供保障。
2.3 新鄉(xiāng)賢能夠優(yōu)化鄉(xiāng)村人才振興治理網(wǎng)絡(luò)
新鄉(xiāng)賢在優(yōu)化鄉(xiāng)村人才振興治理網(wǎng)絡(luò)時主要通過拓寬人才振興治理規(guī)模和提高人才振興治理網(wǎng)絡(luò)密度來提升人才振興治理網(wǎng)絡(luò)質(zhì)量,進而增加鄉(xiāng)村人才振興社會資本存量。首先社會網(wǎng)絡(luò)規(guī)模越大,越能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參與治理,促進彼此間信息、資源等共享。新鄉(xiāng)賢憑借自身成就積累了大量的人脈關(guān)系,自身社會網(wǎng)絡(luò)比較發(fā)達,加上近年來國家和地方對于鄉(xiāng)賢文化的弘揚以及一大批新鄉(xiāng)賢典型人物的樹立,使得新鄉(xiāng)賢在社會上具有很高的認可度,其行為選擇能夠成為他人行動的標桿,大部分本土人才更是將鄉(xiāng)賢榮譽視為家族榮譽。因此,新鄉(xiāng)賢下鄉(xiāng)必定會引發(fā)模范效應(yīng),吸引更多的賢能之士和本土人才參與到鄉(xiāng)村振興的建設(shè)中來,進而開拓鄉(xiāng)村人才振興治理網(wǎng)絡(luò)的規(guī)模、強化本土育才網(wǎng)絡(luò)功能,為鄉(xiāng)村人才振興提供持續(xù)的動力。其次,由于新鄉(xiāng)賢身份的影響力和他們自身的社會網(wǎng)絡(luò),使得他們一直處在鄉(xiāng)村人才振興治理網(wǎng)絡(luò)的重要“結(jié)點”位置,處于特殊網(wǎng)絡(luò)位置的新鄉(xiāng)賢能夠有效聯(lián)結(jié)已有網(wǎng)絡(luò)中的不同類別的網(wǎng)絡(luò)節(jié)點,增加人才振興治理網(wǎng)絡(luò)的密集度、增強各個網(wǎng)絡(luò)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性。對于在外鄉(xiāng)賢來說,成功的創(chuàng)業(yè)經(jīng)歷使他們擁有多個行業(yè)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這些多元化行業(yè)網(wǎng)絡(luò)的嵌入極大地提高了鄉(xiāng)村人才振興治理網(wǎng)絡(luò)的多樣性和網(wǎng)絡(luò)密集程度,促進鄉(xiāng)村人才振興治理網(wǎng)絡(luò)升級。
3 新鄉(xiāng)賢助力鄉(xiāng)村振興面臨的現(xiàn)實困境
3.1 鄉(xiāng)村人才振興主客體之間的信任度有待提升
對于實施鄉(xiāng)村人才振興政策來說,信任不足降低了人才群體參與鄉(xiāng)村振興的意愿。實施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必須從根本上樹立“人才是第一資源”的理念,充分認識農(nóng)民在鄉(xiāng)村振興中的主體地位,農(nóng)村社會是地緣血緣認同度高的社會,與鄉(xiāng)村社會聯(lián)系不密切的外來客體突然參與到鄉(xiāng)村治理中,很容易引起本地村民的非議、甚至是部分村干部和本地人才的排擠[3],在這種情況下很難建立起人才群體與鄉(xiāng)村的信任關(guān)系。其次,通過政策招引下鄉(xiāng)的精英來自五湖四海,且層次不齊,陌生感和價值觀的不同也會造成人才群體之間的信任危機,這也是鄉(xiāng)村留不住人才的主觀原因之一。最后,很多下鄉(xiāng)人才并沒有把服務(wù)鄉(xiāng)村作為本位,而是將其視作晉升的跳板,導(dǎo)致這類人才實際上對于鄉(xiāng)村發(fā)展并無作為,與當?shù)卮迕衤?lián)系很少,辦實事的能力不行,自然難以讓百姓信服,這與鄉(xiāng)村人才監(jiān)管評估制度的不完善也有著密切關(guān)聯(lián)。以上矛盾和可能破壞信任關(guān)系的行為,導(dǎo)致鄉(xiāng)村人才振興整體信任度較低。
3.2 鄉(xiāng)村人才振興實施規(guī)范有待完善
規(guī)范不僅是社會的游戲規(guī)則,也是人與人彼此行為的約束,社會規(guī)范能夠產(chǎn)生人的合作行為提升社會效率。對于鄉(xiāng)村人才管理來說,目前尚未出臺具體法律、條例等對鄉(xiāng)村人才管理進行規(guī)范,有且僅有一些政策性、會議性的說法和少數(shù)發(fā)達地區(qū)為數(shù)不多的指導(dǎo)資料。鄉(xiāng)村人才管理制度的缺位易使鄉(xiāng)村人才振興過程處于失序狀態(tài)。由于部分地區(qū)鄉(xiāng)村人才引流機制和管理服務(wù)的漏洞,加之不同人才群體對于自身所需要滿足的利益追求的不一致也給鄉(xiāng)村人才管理制度的確立增加了難度,使得鄉(xiāng)村人才的引進和管理變得混亂,不免出現(xiàn)一些利用漏洞為自己謀利益和“打擦邊球”的違法行為,給鄉(xiāng)村人才振興政策帶來負面影響,打擊那些真正為鄉(xiāng)村謀復(fù)興的人才的信心與斗志,更不利于鄉(xiāng)村人才振興信任度的積累。除此之外,鄉(xiāng)村社會中延續(xù)的村規(guī)民約是鄉(xiāng)村社會中由村民塑造的文化和精神、內(nèi)生的價值觀念和生活規(guī)范[4],是鄉(xiāng)土社會治理秩序、話語權(quán)和自主性的非正式體現(xiàn),也是鄉(xiāng)村開展非正式合作的基礎(chǔ)規(guī)范,有利于激發(fā)人才群體的主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但是由于下鄉(xiāng)人才缺乏一定的社會聲望和地方性知識,無法制定一套統(tǒng)一的價值體系和治理條約指導(dǎo)非正式治理合作的開展。
3.3 鄉(xiāng)村人才振興治理網(wǎng)絡(luò)有待優(yōu)化
當下鄉(xiāng)村人才振興面臨著治理網(wǎng)絡(luò)薄弱的困境,進而限制了鄉(xiāng)村人才振興合作的規(guī)模與質(zhì)量。作為社會行動者及其關(guān)系的集合,網(wǎng)絡(luò)給予它的成員們足夠的歸屬感和認同感,網(wǎng)絡(luò)成員會因為某些共同的目標、利益與期望而保持著頻繁的互動。當前鄉(xiāng)村人才振興政策的推進被外部視為國家主導(dǎo)下的社會改造運動,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制度設(shè)計。因此,鄉(xiāng)村人才振興治理網(wǎng)絡(luò)建構(gòu)以外在的行政力量為主推動,加之鄉(xiāng)村內(nèi)生制度的薄弱,使得鄉(xiāng)村人才振興治理網(wǎng)絡(luò)通常欠缺內(nèi)生開拓性,造成本土育才和汲取人才的能力不足,延緩了鄉(xiāng)村人才振興治理網(wǎng)絡(luò)規(guī)模的拓展和升級。另外,地方政府對于鄉(xiāng)村人才引進規(guī)劃設(shè)置的不合理也會導(dǎo)致治理網(wǎng)絡(luò)缺少高質(zhì)量和重點領(lǐng)域的人才節(jié)點,從而降低整個治理網(wǎng)絡(luò)的質(zhì)量。
4 新鄉(xiāng)賢助力鄉(xiāng)村人才振興的實現(xiàn)路徑
4.1 立足新鄉(xiāng)賢提升鄉(xiāng)村人才振興主客體之間信任度
首先,提升新鄉(xiāng)賢與鄉(xiāng)村社會主體之間的信任度。第一,深化血緣信任,政府借助傳統(tǒng)節(jié)日、地方紀念日等活動契機,以親情血緣為紐帶,組織新鄉(xiāng)賢開展“尋根問祖”活動,通過認祖祭祖活動,深化與當?shù)厝罕姷难壭湃巍5诙瑥娀鼐壭湃危瑢τ谠谕馊〉贸删偷男锣l(xiāng)賢,政府要加強與他們的溝通交流,通過鄉(xiāng)賢理事會將在外鄉(xiāng)賢組織起來,積極宣傳鄉(xiāng)賢文化,吸引有鄉(xiāng)村情懷的鄉(xiāng)賢回鄉(xiāng)交流分享,厚植新鄉(xiāng)賢的鄉(xiāng)土情懷,增強鄉(xiāng)村社會對于新鄉(xiāng)賢的地緣信任。第三,強化業(yè)緣信任,政府要加強與鄉(xiāng)賢理事會等鄉(xiāng)村社會組織的合作,支持新鄉(xiāng)賢參與“造橋鋪路”“村容改造”和“移風(fēng)易俗”等鄉(xiāng)村項目建設(shè),讓新鄉(xiāng)賢積極主動投身鄉(xiāng)村建設(shè),增強鄉(xiāng)村社會對于新鄉(xiāng)賢群體的業(yè)緣信任。其次,以新鄉(xiāng)賢為主導(dǎo)增強人才群體與鄉(xiāng)村社會的信任關(guān)系,推動鄉(xiāng)村人才振興信任度的積累與強化。一方面,政府可以利用新鄉(xiāng)賢對于地方性治理知識的了解,采用民主協(xié)調(diào)等非正式治理機制處理人才群體之間的矛盾糾紛,加強人才群體的鄉(xiāng)規(guī)民約教育,使之更好地融入鄉(xiāng)村文化體系,推動各方主體在統(tǒng)一的價值觀引導(dǎo)下開展合作,有利于增強彼此的認同、增加彼此的信任;另一方面,發(fā)揮新鄉(xiāng)賢在形成社會規(guī)范中的作用,幫助地方政府完善鄉(xiāng)村人才管理考評規(guī)范,加強對下鄉(xiāng)人才的監(jiān)管和考評,遏制下鄉(xiāng)人才違法亂紀和無所作為的情況發(fā)生,建立以村民滿意度為導(dǎo)向的人才考核與獎懲機制,以此增加村民和村兩委對于下鄉(xiāng)人才的信任。
4.2 依托新鄉(xiāng)賢完善鄉(xiāng)村人才振興實施規(guī)范
首先,政府應(yīng)當明確新鄉(xiāng)賢在制度制定階段所承擔(dān)的職責(zé)與功能,積極聽取新鄉(xiāng)賢關(guān)于人才管理制度制定方面的意見和建議,同時依托新鄉(xiāng)賢在人才群體中的社會信任和社會網(wǎng)絡(luò)傳達政府的政策意志,反映人才群體的不同訴求。在制度實施階段,可以安排新鄉(xiāng)賢作為負責(zé)人負責(zé)制度的實施,并且新鄉(xiāng)賢以身作則的影響力能夠增加鄉(xiāng)村人才群體對制度的接納程度。同時憑借新鄉(xiāng)賢自身通達的社會網(wǎng)絡(luò),在收集人才群體關(guān)于制度規(guī)范實施的意見方面能夠更加全面和高效,有利于政府及時改良實施細則,減少損失。其次,政府應(yīng)當支持新鄉(xiāng)賢與村兩委共同制定非正式的治理條約。非正式的治理條約對人才群體的行為規(guī)范起到約束的作用,同時也為人才群體提供了大量合作交流的機會,增進了彼此間的信任。最后,政府應(yīng)當按照鄉(xiāng)賢理事會的組織框架和運行規(guī)范,協(xié)助新鄉(xiāng)賢建立鄉(xiāng)村人才自我管理與服務(wù)的非正式合作組織,改善原本鄉(xiāng)村人才處于分散、缺乏交流的不利局面,使其轉(zhuǎn)化為鄉(xiāng)村人才振興組織體系的后備軍。
4.3 憑借新鄉(xiāng)賢優(yōu)化鄉(xiāng)村人才振興治理網(wǎng)絡(luò)
首先,為新鄉(xiāng)賢下鄉(xiāng)鋪平道路,保證新鄉(xiāng)賢“干事有平臺、生活有保障”,進一步加強鄉(xiāng)賢理事會等鄉(xiāng)村社會組織的建設(shè)、完善鄉(xiāng)賢理事代表制度,為新鄉(xiāng)賢實施鄉(xiāng)村治理提供物資和制度保障,以此推動更多鄉(xiāng)賢參與鄉(xiāng)村人才振興。其次,當?shù)卣畱?yīng)當著手構(gòu)建“鄉(xiāng)賢文化”的傳播機制和“鄉(xiāng)賢典范”的激勵機制,如利用現(xiàn)代網(wǎng)絡(luò)社交平臺積極宣傳新鄉(xiāng)賢參與鄉(xiāng)村振興的光榮事跡,以此推動鄉(xiāng)賢文化的傳播,對先進典型進行表彰,頒發(fā)鄉(xiāng)賢榮譽證書,并將個人事跡寫入鄉(xiāng)賢文化館,提升新鄉(xiāng)賢參與鄉(xiāng)村振興的成就感,帶動更多本土鄉(xiāng)賢和人才參與,提升鄉(xiāng)村人才振興治理網(wǎng)絡(luò)規(guī)模。最后,政府可以憑借新鄉(xiāng)賢發(fā)達的行業(yè)網(wǎng)絡(luò)資源,構(gòu)建以新鄉(xiāng)賢為紐帶的“多元人才引進”機制,加快制定鄉(xiāng)村人才振興高層次人才需求規(guī)劃和出臺豐厚的獎勵政策、吸引鄉(xiāng)村振興緊缺型行業(yè)人才的加入,如經(jīng)濟、文化、醫(yī)學(xué)、教育、法律等領(lǐng)域的“能人”,這些都是當下鄉(xiāng)村振興亟須的高層次人才。同時憑借新鄉(xiāng)賢的資源、能力培養(yǎng)內(nèi)生人才,作為鄉(xiāng)村人才振興內(nèi)生動力的重要補充,構(gòu)建鄉(xiāng)村本土育才網(wǎng)絡(luò)機制,提升鄉(xiāng)村人才振興治理網(wǎng)絡(luò)的質(zhì)量和多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