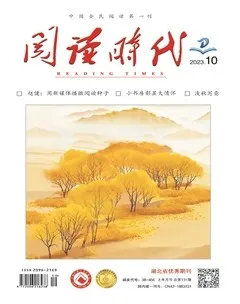竹溪書院
蔡達斌
南宋紹興年間,在張氏族人的殫精竭慮、苦心經營下,沿河司北部橫空出世了一家書院,它就是竹溪書院!竹溪書院和鑾塘書院、鶴鳴書院,在思州大地形成三足鼎立之勢,如旗幟或明燈般,成為肩負起思州文明拓荒、傳播和燎原的舵手。在那個年代新建一所書院,尤其是在邊鄙思州,實乃石破天驚的壯舉。
竹溪書院的面世,開創了思州地域文明的先河,讓生于斯長于斯的畢茲卡(沿河土家人自稱畢茲卡),終于迎來了心中渴慕已久的文明的曙光。在思州眾多文明的源頭活水中,竹溪書院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
翠竹林中書聲瑯瑯,黃土地上清溪湯湯。這便是水墨竹溪,風雅竹溪,人文竹溪。竹溪書院的由來,充滿著行板的雅致,浪漫而傳奇。《古色古香竹溪書院》一文中云:相傳,張氏祖公,南宋年間,從鐘嶺山遷徙而來。幾經輾轉,幾次擇址,才在一處巖矸生長的仙域圣地,安營扎寨。因為這塊風水寶地半山有個洞,像馬一樣常年冒熱氣,故叫“馬出氣”。但這名字土俗不雅,又見四周荊竹成林,溪水長年累月地蜿蜒流瀉。于是,人們詩意地變音為“麻竹溪”。張家憑借著馬路途經的便利條件,開店做生意,攢錢辦書院,以培養子嗣后代。起初,叫竹溪勝院、竹溪書屋,后改為竹溪書院。
隨著生意越做越大,張氏家業也就與日俱增地殷實、富足起來。到鼎盛時期,張氏祖公竟有十多只商船,每天進進出出上百號人,沿河縣城黑巷子的半條街都是他們家的門鋪。如此說來,竹溪,簡直就是張氏族人發家致富、揚名立世的旖旎家園、夢幻水鄉!張家老小,完全可以把他們自己的幸福、夢想和未來,靜靜地在這里愜意、穩妥和婉美地安放。故在竹溪修建一座城,供族人居住。在城旁左下角設立書院,且在四周筑城墻,要道處設關卡,于高處建鼓樓,又在山頂架起了大炮,以好貼身護衛。
如今,城破,鼓不存,炮已啞,徒留一些隱隱約約的古城址遺跡,讓人對過往的真相,不斷地胡亂猜測。
話說一天夜里,張氏祖公夢見一位白頭老翁對他說:爾辦書院,方便周圍子弟入學,是件大好事。行善積德,終有好報,爾家子弟定會連中三元,九代儒生……
歷史上,張家子弟果真連中三元,九代儒生,官至六七品,在省城和地方做官的,都為舉足輕重的名流。為此,官府在寨上樹三圍子以熱情嘉獎,高度禮贊,希望再接再厲,層樓更上。從某種意義上說,竹溪書院堅實了沿河人的文明傳播之路,揚起了思州人生命夢想之帆,為后來貴州文化的發展、文明的傳承,奠定了基礎。
竹溪書院系木房,長五間,有四合院、吊腳樓,雕窗廂房,華美精致,堪稱一絕。書院環境幽靜,空氣清新,伴著鳥語、水聲、蛙鳴和墨香,以及寺廟箴言禪味,各自的鴻鵠志向,虔誠捧書汲取古人智慧營養,領悟人生真諦,尋求報國為民、澤被萬世的道路和真理,該是多么賞心悅目、心旌搖曳的快事!學子有此書院,分分秒秒都是人間四月天。竹溪有此書院,日日夜夜沐浴詩畫般的光輝歲月。思州有此書院,年年歲歲都浸在江南詩畫中。遙想當年,多少莘莘學子慕名而來,如饑似渴地博覽圣賢書,聆聽先生至真、至善、至理的教誨,定有數不清的鮮活掌故、風花雪月……
時光,凝固成一道瑰麗的風景線;人事,走失在歷史的岔路口。可惜,風生水起的竹溪書院,彈指一揮間便夭折了。落紅凋零成護花新泥,唯有多情者,還在一味地喟嘆曾經花開時節的那份嬌美與馨香。一如流星雖然短暫,卻照亮過之前的暗夜。竹溪書院也命途多舛,幾經磨難,因為主人的家大業大,人丁興旺,而樹大招風地遭人嫉恨與排擠。加上兩次烈火的肆虐蹂躪,尤其是1965年那場大火的無情焚燒,到現在已面目全非。以至于有關它的身世經歷,是那么深沉莫測,雋永成謎。如今插三圍子的石器,還遺棄在一家屋基之一隅。在一座高墻大院外,石工精心雕刻的朝門,仍巍然屹立,昭示著昔日的輝煌,不朽的傳奇,別樣的芳華。它上面的對聯,頗耐人尋味:金鑒家聲綿世澤,竹溪山色煥文章。橫額:孝友流傳。另外,一塊斷碑,似乎還在饒有興趣地憶念曾經書院的人聲鼎沸和氣象萬千。水墨潑成的竹溪書院,為這片熱土文明的傳承,文化的積淀,英才的孕育,經濟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據《貴州古代教育發展述略》中介紹,竹溪書院培育了宋時孝廉朱可熹兄弟,明進士陳景蓍、田景新,舉人張紳、田景猷等眾多賢達鄉紳。正可謂世代皆有通儒,而名揚省內外。
由此可見,竹溪書院,仿佛一條圣潔璀璨的星河,哺育和澆灌著思州這片神奇的土地,催生了叢叢文明森林,盛開了朵朵文明仙葩,釀制了累累文明金果。思州文化,也因有它而豐富多彩了許多。曾經,有無數人都把竹溪書院,作為他們夢泊的精神棲息地。可以想象它在讀書人心中的威望與地位,可以想象它在沿河人眼中的威武及雄壯。竹溪書院從問世起,就燃成竹溪、沿河文明的燎原之火,甚至譜寫成思州文化婉美馨香的華章,以及壯大成后來貴州文化的核心精華。
(源自“文史天地”)
責編:王曉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