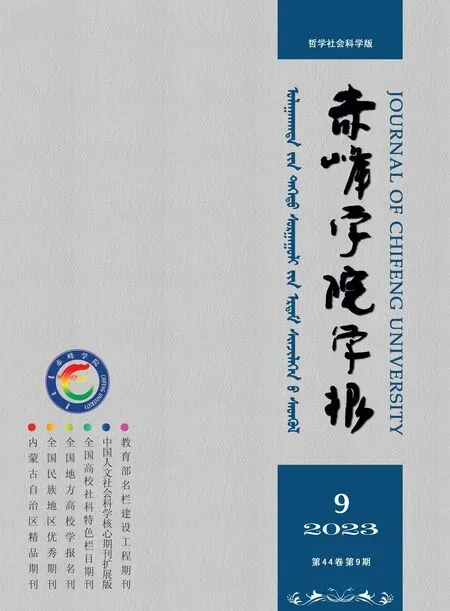“美第奇效應”視域下開放性試題的多向度闡釋
——以2022年文綜全國乙卷第42題為例
劉建榮,吳合文
(陜西師范大學 教師發展學院;陜西教師發展研究院,陜西 西安 710062)
全國卷歷史試題中的開放性試題,“一直是最奪人眼球的試題”[1],最能見證高考命題改革的方向和力度,既承載著“參酌核心素養,強化國家意志”[2]的使命,又擔負著打破試題的封閉性,“適當提升學生創新能力”“加強對學生獨立思考和歷史思維能力的考查”[3]之重任,還要阻擊題海戰術、機械刷題、思維定勢和經驗主義的流弊,落實“雙減”目標。可以說集涵育核心價值、考查高階思維、應對靈活創新三大高層級考查要求于一身,既“攻”且“防”,既“破”且“立”,既“考”且“導”。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完成如此多元化、高難度的使命?綜合性、跨學科、交叉性就成為高考命題人在命制此題時的重要參考標準。這既是本輪課程改革的主流趨勢,也是學業評價的改革方向;既是高考評價體系“綜合性”的考查要求,也是普通高中歷史學業質量的高層次要求。這里的“綜合性”不僅是指學科內部的綜合,更是指學科與學科之間的綜合與交叉。
“美第奇效應”是指通過不同學科、領域、文化的“交叉”而產生的創新思維。源自美國學者弗朗斯·約翰松對創新靈感和交叉思維的研究,顯然受到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佛羅倫薩美第奇家族成功的啟發。依據已有的2022年文綜全國乙卷第42題——“猛虎過界”題的研究成果,結合高考實際考情,筆者發現,無論是考生還是教師,囿于學科本位、視野邊際和思維局限等,大多從歷史學科單向視角對此題進行思考和闡釋,陷入同質化和單向度困境不可自拔。要想走出困境,高質量解答此題以及此類開放性試題,必須進行多向度思考和闡釋,而這需要實現“破壁”與“升維”,養成跨學科思維,形成“美第奇效應”,即高階的創新思維。
一、困境:單向度局限
2022年高考結束之后,許多教師已經對2022年文綜全國乙卷第42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有不少成果發表于多家業內專業雜志。為方便詮釋,錄原題于下。
42.閱讀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分)
解讀史料,獲得歷史認識,探尋史料表象背后的意蘊,是歷史學的魅力所在。下表為史書所載東漢時期幾位良吏的事跡。

姓名 任職地事跡劉陵 安成(今屬江西) 先時多虎,百姓患之,皆徙他縣。陵之官,修德政,逾月,虎悉出界去,民皆還之。

姓名 任職地事跡(郡)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為所害者甚眾。雄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民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禽)走(獸)……其毀壞檻阱,不得妄捕山林。”是后虎害稍息,人以獲安。劉平 全椒(今屬安徽) 縣多虎為害,平到修政,選進儒良,黜貪殘,視事三月,虎皆渡江而去。法雄 南郡(今屬湖北)童恢 不其(今屬山東)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咒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為之歌頌。
——據《后漢書》等
闡述從上述材料中發現的歷史現象,并得出一個結論。(要求:現象源自材料,結論明確,史論結合,表述清晰。)
部分教師從新課標所倡導的核心素養角度進行解讀。董振華認為應該先“以‘史料實證’素養目標為基解析史料”,然后“以‘歷史解釋’素養目標為軸解讀歷史現象”,最后水到渠成“以‘唯物史觀’素養目標為綱做出客觀結論”[4],將三大核心素養目標統籌為一體,以唯物史觀為引領,對歷史現象進行科學解釋,一定程度上展現了高校教師的史學理論水平和實證研究素養。韓金華立足“歷史解釋”[5]核心素養,兼論時空觀念與唯物史觀。趙啟佳認為“本題主要考查史料實證素養”[6],主張對學生的“史料實證”素養培養應該“內化于心、外化于行”。韓、趙二位教師代表了中學年輕教師對開放性試題素養考查目標的普遍認識,還有部分教師不滿足于僅從核心素養視角進行解讀,而是深入歷史思維的深度去探尋新高考命題的方向。曾金海、王生二位教師通過分析解讀此題得出結論:“新高考歷史命題的總體方向,就是以高階思維為導向,以核心素養為立意,以知識演繹為支撐。”[7],這一研究頗具慧眼,很有深度。也有教師高度肯定此題所體現的歷史學魅力。陳小軍從“理政原則”“生態文明”“宣傳教化”“整飭吏治”“地理區域”[8]等五個角度進行解讀,深度探尋史料表象背后的意蘊,并分別提供了自擬的答案示例,既彰顯了“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價值取向,也比較全面地反映了中學一線教師對本題答題思路的實戰化回應。
應該說教師們的研究已經基本觸及本題考查方向和命題意圖,提出的一些策略、案例和教學建議也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和參考價值。但也集中暴露出兩大問題:
1.同質化。這并非在最近的開放性試題研究中才出現的新問題,其實每年高考結束后對此題的研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同質化、套路化問題。其基本的結構無非是四部曲:此題有何新變化——體現了何種素養導向——有何解題思路、技巧、策略——有何教學建議。
2.單向度。即囿于學科本位和視野邊際,大多局限在單一歷史學科視閾下進行解讀,沒有觸及此題所體現的綜合性、跨學科、交叉性教育改革方向和育人導向。這種局限難免導致對歷史現象的過度解讀甚至曲解,有教師將材料中的老虎解讀為“豪強的爪牙或豪強自身”[9],認為這些良吏“在抑制地方豪強的過程中體現了王朝中央的威權,維護了王朝的尊嚴。因此才被作為王朝代言人的史官群體記錄與傳揚”[10]。看似結合東漢時代特征,實則牽強附會,違背常識,是典型的偽唯物史觀。
單向度與同質化兩個問題相互纏繞,因為視域的單向度而加劇同質化,因為結構的同質化而局限于單向度,從而陷入一種解釋“困境”。
二、破壁:跨學科思維
要解決開放性試題這樣的綜合性、復雜性、高階性、創新性問題,就不能只用單一學科思維和方法,必須要實現“破壁”,即要打破學科與學科之間的壁壘,拆掉束縛思維的“墻”,以歷史學科思維為主體,運用語文、地理、政治等多學科的知識、方法與思維分析和解決問題。質言之,就是要養成跨學科思維。這里強調的跨學科思維并非多學科的“拼盤化”,也非單向度的,而是多學科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化學反應”。
(一)歷史學科思維
1.史料閱讀與史料運用的方法
有學者認為,歷史學的本質是史料學,史料閱讀方法猶如磨刀之于砍柴。在對比國內外歷史教育中史料運用的目標要求的基礎上,首都師范大學唐朋指出二者在史料運用的層次方面存在共性,認為:“歷史教育中對史料運用的評價可大致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理解地讀’,其核心任務是讀懂史料,包括提取史料信息、區分史料類型、判斷史料價值等;第二個層次是‘批判地讀’,其核心任務是批判性地運用史料,包括辨別史料的真假和意圖、比較不同觀點的史料、運用史料進行推理論證等。”[11]這一分層方法簡單、實用、高效,是將“史料實證”素養的落實策略化、方法化的路徑探索,極具推廣和應用價值,非常適合作為對本題史料閱讀和史料運用的實操指南。首先,對本題史料應該“理解地讀”。本題四則史料摘編自《后漢書》,屬于研究東漢歷史的一手史料,具有較高史料價值,由四則材料中的 “修德政”“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 (禽)走(獸)”“修政”“天生萬物,唯人為貴”等共性信息、關鍵信息,并結合所學知識可知,東漢時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已經更加穩固,并深刻影響了官員們的執政理念,因而可以得出“東漢時儒學思想影響官員執政理念”的歷史結論。其次,對本題史料應該“批判地讀”,即“批判性運用史料”。四則史料在解釋“虎悉出界”“虎害稍息”“虎皆渡江”“垂頭服罪”的因果關系時,皆用官員“修德政”、行“仁”政作為原因解釋,此處學生若產生思考“這二者之間真的存在因果關系嗎?”“這一解釋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嗎?”,那么學生就已經具備一定的唯物史觀、批判性思維和發現問題的能力。在此基礎上再進一步“辨別史料的真假和意圖”“運用史料進行推理論證”,或者基于課標要求“運用史料就是理解歷史,需要秉持大膽懷疑、多源互證等原則”[12],可以發現這四則史料存在虛構現象,其真實性是存疑的。《后漢書》雖然是研究東漢歷史的一手史料,而且是屬于史學界公認的史料價值較高的 “前四史”之一,但作為文獻史料,也難免存在主觀性;作為正史,則更是具有較強的政治性,情節的虛構滲透著當時的主流思想。
2.從“歷史現象”到“結論”的歷史思維過程
掌握史料閱讀與史料運用的基本方法,并不足以完全解決本題所提出的問題,從 “歷史現象”到“結論”,還有一段距離。這距離看似近在咫尺,卻又遠在天邊。要彌合這段距離,需要完成“三步曲”。
第一步要厘清“歷史現象”的概念和特點。歷史本質上是人的活動,歷史現象是指歷史運動的表面特征和外部聯系,是歷史本質的外部表現。陳先達教授強調 “歷史現象具有相似性”[13],并且普遍存在。對歷史現象相似性的認識比對單一歷史事件的認識更進一步。本題四則材料反映的歷史現象即具有相似性,雖不同于古今中外歷史現象的相似性,但也是在同一歷史時期歷史現象的相似性,反映了當時的時代風貌。有相似性才可能從中發現規律,從歷史現象相似性中發現規律是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方法。此外,因為歷史現象是外在的、表層的、感性的,所以具有迷惑性。四則史料共328字,信息量不少,如何透過紛繁的現象洞察本質,需要具備較高的歷史學科素養。
第二步要廓清“結論”的內涵。如何理解本題設問中“得出一個結論”中的“結論”?它僅僅是指歷史結論嗎?如果是,為什么設問中不明確要求得出一個“歷史結論”?如果不是,那么它涵蓋了什么?回歸試題原文,本題材料引言部分有一個非常重要但容易被忽視的信息就是“探尋史料表象背后的意蘊”,意蘊不僅僅是歷史的結論,還應該包括規律、本質、內涵等。這也是前文強調關注歷史現象的相似性和迷惑性的目的所在,由相似性而總結其規律,由迷惑性而洞悉其本質。
第三步要運用歷史思維。作為一種認識活動,歷史思維具有思維的普遍性,也具有歷史學科的特殊性。根據趙恒烈先生對歷史思維的概念定義,歷史思維的特殊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歷史思維的內核是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就歷史唯物主義而言,本題重點是要以“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映社會存在”的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觀點為指導進行歷史解釋,作為文獻史料的史書本質上屬于社會意識的范疇,是當時社會存在的映射。因此,在闡述歷史現象時,不能只有“是什么”這樣的事實性知識,更要有“為什么”這樣的解釋性知識。就辯證唯物主義而言,本題涉及唯物辯證法的聯系觀,以及現象與本質、原因與結果等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范疇。
其次,歷史思維的外顯表現為時空觀念,即“在時序中思考”[14]。本題四則史料的時間定位為 “東漢”,空間定位為山東等黃河中下游地區和江西、湖北、安徽等長江中下游地區。本著重視時空的思維方式,聯想時代背景,調動和運用所學知識進行歷史解釋,可關聯的知識包括兩漢儒學的政治化、漢代儒學的讖緯化或漢代緯學對經學的影響、吏治與古代地方治理、虎患與苛政之間的關系、歷史時期老虎分布地域、老虎活動與生態環境、虎患與地方社會經濟發展關系等。
最后,歷史思維的內化表現為歷史意識。歷史意識既是一個哲學概念,也是一個歷史教育學概念。徐賜成博士在梳理了古今中外相關的觀點和表述后,總結出“歷史意識”的內涵“是人類對自然、人類自身在時間長河中發展變化現象與本質的認識,是思維主體了解自身所認知的過去是什么,所要傳達的概念是什么,體現的是人們對過去事物的感受力”[15]。歷史教育的過程就是培養、建構學生的歷史意識的過程。要想讓學生像歷史學家一樣思考問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在平時的課堂中不斷進行浸潤式的滲透。本題即需要作為“思維主體”的學生對歷史的“現象與本質”進行基于時代背景和社會環境的“感受”。
3.歷史敘事的模式化問題
前文述及歷史思維的核心是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形式與內容的關系也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之一。一般而言,作為歷史思維主體的學生主要觀察到的是史料呈現的內容,而忽視史料呈現的形式。本題四則史料的呈現形式屬于“并列式連接排比”,其敘事方式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同質化、模式化。
有學者研究發現,由于西漢中期以后災異祥瑞論的盛行以及漢王朝對循吏的褒崇等原因,東漢史籍中出現兩種良吏書寫的常見模式——“猛虎渡河”和“飛蝗出境”,即用一種超經驗、超自然的書寫模式來構建、形塑地方良吏形象,將良吏形象讖緯化、神學化。“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史書的真實性,并使得史事記載類型化、程式化,缺乏個性描述。”[16]這種類型化、程式化的書寫模式也體現在孝子、儒生、文士等形象的塑造上。因此,本題可得出結論:東漢史書同類人物敘述存在模式化現象。
從高考實際考情來看,只有屈指可數的考生能答出諸如“關于良吏的歷史敘述具有相似性”的結論。因此,不得不反思我們關于史學理論的教學工作。《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標準 (2017版2020年修訂)》的“課程內容”部分,除了兩冊必修和三冊選擇性必修之外,還設計了兩個模塊的選修課程——“史學入門”與“史料研讀”。兩門課程各7個專題,是在必修課程和選擇性必修課程基礎上的進一步延伸,也服務于高校歷史專業的人才選拔。這兩個模塊目前只有課標要求,沒有統編教材,在實踐中往往以校本課程的形式開設,而是否開設以及授課質量取決于一線教師的重視程度與理論水平。無論是“歷史現象”與“結論”之間的辯證關系,還是歷史敘述的模式化問題,都涉及史學理論的相關知識,這是目前中學歷史教學中亟待補齊的短板。
(二)語文學科思維
俗話說“文史不分家”,語文學科以其獨特的學科思維為史料閱讀、歷史理解、歷史解釋以及闡述論證提供能力和方法支持。
《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2017年版2020年修訂)》設計了18個學習任務群,其中第6個學習任務群為“思辨性閱讀與表達”。雖然這一學習任務群的學習內容主要是閱讀古今中外論說名篇而非歷史史料,但其所培養的閱讀能力、思辨能力、推理能力、實證能力和表達能力,對學生在開放性試題的史料中“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卻大有裨益。事實上,論說類文章閱讀理解能力較強或者議論性文章寫作能力較強的同學,回答開放度試題的水平也更高。坦率地講,就閱讀理解的技能而言,語文學科為中學其他所有學科都提供了基礎性的支撐作用。
歷史高考開放性試題的材料呈現形式具有多樣性,但大多以非連續性文本形式呈現。方智范、李亮和潘文彬三位教授認為:“所謂非連續性文本,是相對于以句子和段落組成的連續性文本而言的閱讀材料,多以統計圖表、圖畫等形式呈現,如數據表格、圖表和曲線圖、圖解文字、憑證單、使用說明書、廣告、地圖等。”[17]再結合其他學者觀點:“大家比較一致的看法是把非連續性文本按類型分為表格類、圖表類、圖畫類以及圖文結合類。”[18]這正是自2011年全國卷開放性試題正式獨立成題以來的主要呈現形式,為便于研究,筆者將2011—2022年全國卷開放性試題的文本呈現形式按照上述概念和分類總結如表1。

表1 2011—2022年高考全國卷開放性試題文本呈現形式
由表1可知,2011—2022年一共27道開放性試題,其中有20道都是非連續性文本,占比高達74%。閱讀非連續性文本是現代人必須具備的重要能力,主要指向主旨內容的深刻理解、抽象思維能力的提升和語言文字的實踐運用。由于非連續性文本具有“非線性”“直觀性”“概括性”[19]等特點,其與連續性文本在組織形式、邏輯形式、閱讀方法、信息淬煉等方面都有很大差異,對學生的多元智能維度、閱讀理解能力、概括能力和轉化能力要求也更高。這便是學生在解答這道題時得分較少的原因之一。
自2011年非連續性文本作為一個新的亮點正式進入語文課程標準以來,語文學界對非連續性文本的概念、特點和閱讀策略進行了持續研究,取得了諸多成果,初步形成了針對性的方法體系,對解決歷史學科的開放性試題具有重要借鑒價值。歷史教師,應該打破學科壁壘,學習、借鑒、推廣語文學界的研究成果。
(三)地理學科思維
地理學是研究地理環境以及人類活動與地理環境關系的科學,兼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性質。《普通高中地理課程標準》強調加強“生態文明”教育,“地理課程旨在使學生具備人地協調觀”等地理學科核心素養,“使學生強化人類與環境協調發展的觀念”“懂得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道理”,從而形成關注“可持續發展問題的意識”,突出地理學科的育人價值。
本題四則史料中的“虎患”,可能是指真實的虎患,也可能是喻指“苛政”或者其他。如果是指真實的虎患,從人地關系的視角來看,就需要索證東漢時期究竟有沒有虎患的記載以及社會歷史背景。
首先,東漢時期的確存在虎患。這在范曄的《后漢書》以及李昉的《太平御覽》等相關史書中均有大量記載[20]。
其次,東漢時期也存在虎患出現的社會歷史條件。老虎被稱為“森林之王”,森林是老虎賴以生存的環境。秦漢時期生產發展、社會進步,加之封建統治階級大興土木,廣建宮室,造成了對森林資源的過度消耗和嚴重破壞。植被破壞進而導致水土流失加劇,水災、旱災、蝗災頻發,與先秦時代相比,自然災害發生的次數明顯增多。人類活動也影響了“森林之王”老虎的生存,而東漢虎患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
也許有人會質疑,當時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的破壞應該主要是在黃河流域,北方地區是當時政治、經濟的中心區域,為何材料中的虎患發生地不僅包含北方地區的山東,而且還涉及江西、湖北、安徽等南方地區呢?這體現了在老高考模式下貫徹新課程理念和考查新教材內容,從而“著眼新舊課程過渡,助力改革穩步推進”[21]。秦漢時期,隨著封建統治者對江南地區有效控制的建立與完善,江南地區的農業得到次第開發。中原的人口、技術、工具等要素逐漸進入包括今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安徽、江蘇、浙江等長江中下游以南的廣大地區。“因此,進入東漢以后,江南農業經濟已漸呈現出迅猛發展之趨勢,中國經濟重心轉移之萌芽逐漸顯露。”[22]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東漢虎患是社會經濟發展,人地關系緊張,老虎原有生存環境受到人類活動破壞的結果。
(四)政治學科思維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課程標準》把“科學精神”作為思想政治學科四大核心素養之一,即“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能夠對個人成長、社會進步、國家發展和人類文明作出正確的價值判斷和行為選擇”。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其核心要義是必須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這固然也是歷史學科“唯物史觀”的核心素養要求,但若以政治學科的哲學思維來分析這四則史料,則可以得出“東漢良吏事跡敘事體現了唯心主義天命觀”或者“東漢良吏事跡敘事具有唯心主義色彩”的結論。因為官員行仁政,行德政,則“猛虎過江”“垂頭服罪”,這種對因果關系的附會,猶如古希臘相信迷信的伯羅奔尼撒人把海嘯視為兇兆而非地震引發,顯然違背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違背了科學精神。如果學生能從哲學高度來分析和認識這四則材料所共同反映的歷史現象,無疑是非常具有穿透力的洞見,可以同時反映學生的歷史學科和政治學科核心素養達成程度。從思維角度而言,這四則史料對虎患消弭的解釋是一種常識性思維,具有表面性和直覺性,并非科學性思維。在高中階段要引導學生實現從常識性思維到科學性思維的飛躍。
當然,政治學科思維對歷史學科的影響不僅限于科學精神,還包括政治認同、學科思政、政策思維、歷史哲學等。
三、升維:美第奇效應
愛因斯坦說“問題不能在發生的同一層面得到解答”。這就是說,問題不能僅在產生問題的維度得到解決,解決問題要跳出既定的思維框架,進入一個更高階、更深刻、更廣闊、更長遠的維度,找到不同維度之間的 “交叉點”,形成深度洞察力和解釋力,產生非凡的創新思維,只有這樣才能創造性解決問題,這就是所謂“美第奇效應”。當我們思考問題的視角、層次和維度不同,所得到的結論也并不相同。升維思考,才能對問題實行降維打擊。
那么,如何實現“升維”,多向度闡釋開放性試題?筆者認為,與其被動地從政策執行者的低階維度思考問題,不如從政策出臺者的高階維度思考問題。具體而言,應該從以下三個方面著力:
(一)站在高考命題人及高考評價體系的維度思考問題
開放性試題主要落實的是高考評價體系中“綜合性”“創新性”等高階考查要求。綜合性包括學科內部和學科之間的綜合,主要強調融會貫通、觸類旁通。因此,不能以單一的學科知識和學科思維去解決“綜合性”問題,“升維”是應對“綜合性”的必然選擇。創新性則強調創新意識和創新思維,包括獨立思考、發散思維、逆向思維等,要“鼓勵學生擺脫思維定勢的束縛,積極主動探索新方法、解決新問題”。可見,不能以傳統思維、定勢思維去解決“創新性”問題,必須走出題海戰術,減少“機械刷題”,擺脫固化思維,以靈活思維應對高考的“創新性”。
(二)站在課程標準制定者及課程標準的維度思考問題
作為 《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標準 (2017版2020年修訂)》的主要制定者之一,徐藍教授指出:“2017版《課程標準》最突出、最重要的新理念是提出了歷史學科核心素養。”核心素養目標對歷史學科的育人價值進行了概括性和專業化表述,被普遍認為是對三維目標的發展和深化、繼承與創新。根據這一概念并結合本題,有如下兩個方面值得重點關注:
1.知識為基。核心素養的培養和發展是以歷史知識的習得為基礎的,否則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本題所蘊含的基礎知識包括董仲舒創立新儒學、漢武帝“罷黜百家、尊崇儒術”、漢代儒學對政治文化的影響、東漢儒學正統地位的加強、經學與緯學的關系等。這是本題正解的邏輯出發點。
2.素養導向。從正確價值觀角度來看,本題是想要發揮歷史學科的以史育人價值,引導學生“禮敬、自豪地對待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23],學習中國古代治國理政的政治智慧和生態觀念。從必備品格角度看,本題主要是想引導學生形成求真精神和批判思維,學生既要看到史料中的真實性部分,也要看到史料中的虛構性部分。這對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要求相當高,顯然已經不是知識立意,而完全是素養立意。從關鍵能力角度來看,本題對“獲取和解讀歷史信息的能力、分析歷史問題的能力和歷史探究能力”三大關鍵能力均有考查,尤其是考查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允許學生多維度、跨學科分析和解決問題,對同一歷史現象得出多元的、合理的結論,增強探究意識,發展學生個性。
當然,如前文所述,多向度分析和解決問題,不僅要研究歷史學科的課程標準,還需要研究諸如語文學科、政治學科、地理學科等相關學科的課程標準。
(三)站在教材編寫者及統編歷史新教材的維度思考問題
當前高考處于新舊交替時期,即便是在老高考模式下,也注重貫徹新課程理念和考查新教材內容。因此,與教材編寫者對話,深研統編新教材,有助于我們更深刻地理解、更準確地把握高考命題的考查方向和素材選擇。就本題而言,我們要關注統編歷史新教材的兩個突出特點。
一是,統編歷史教科書作為國家意志的集中體現,特別強調以唯物史觀為指導。人民教育出版社歷史編輯室主任、編審李卿在解讀統編高中歷史教科書的編寫思路時明確指出:“教材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精選基本的、重要的史實,對人類歷史發展進行科學的闡釋。”[24]唯物史觀既是教材編寫的指導思想,更是高考命題的考查重點。特別是開放性試題,其核心要義就是考查在唯物史觀指導下的歷史解釋素養。因此,在闡述本題史料所體現的歷史現象并得出結論時,必須自覺運用“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映社會存在”的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觀點,以及唯物辯證法的聯系觀、“現象與本質”“原因與結果”“形式與內容”的辯證唯物主義基本理論。
二是,統編歷史教科書特別注重發揮以史育人功能,重視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反對文化虛無主義。歷史教育的真正價值是發揮其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以史育人功能。李卿認為:“教材是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最基本、最主要的依據,師生都要認真研讀教材。”[25]只有吃透教材,充分領會編者意圖,正確解讀教材內容,才能挖掘教材育人價值。從文化視角來看,統編教材注重“引導學生辯證、客觀地理解歷史事物”“認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自覺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26]。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是教材編寫的重點,也是高考考查的重要內容。漢代儒學在中國儒學發展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中外歷史綱要(上)》第4課“西漢與東漢——統一多民族封建國家的鞏固”中“西漢的強盛”一目論及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時重點強調“思想上,接受董仲舒的建議,尊崇儒術。此后,儒學成為我國封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在述及東漢開國之君劉秀開創“光武中興”時強調“重視儒學”。實際上,“兩漢歷史即儒家思想之推行史也”[27]。儒學的正統地位雖然是在漢武帝時期確立的,但其鞏固卻主要是在東漢時期。司馬光稱:“自三代(指夏、商、周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梁啟超稱:“東漢尚氣節,崇廉恥,風俗稱最美,為儒學最盛時代。”因此,近年來的高考開放性試題考查儒家文化,常以東漢時代入題,不獨2022年全國乙卷第42題,2018年全國Ⅲ卷第42題以“東漢史學家班固所撰《漢書·古今人表》中的部分人物及相應等級”為材料入題,也是考查東漢儒學。只有以聯系的觀點看待兩漢儒學之間的關系,才能正確解讀東漢儒學對政治理念、史書撰寫以及人物評價的深刻影響。
四、結語
單一的視域、低階的維度、傳統的思維是不可能真正解決綜合性、高階性、創新性的復雜問題的。我們必須運用系統論的觀點,以歷史學科思維為主,同時打破學科本位主義,綜合運用語文、地理、政治等多學科的知識、方法與思維,實現“破壁”與“升維”,養成跨學科思維和創新思維,形成“美第奇效應”,多向度地進行闡釋,才能真正破解2022年全國乙卷第42題,這對我們以后解決同類型問題也具有普遍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