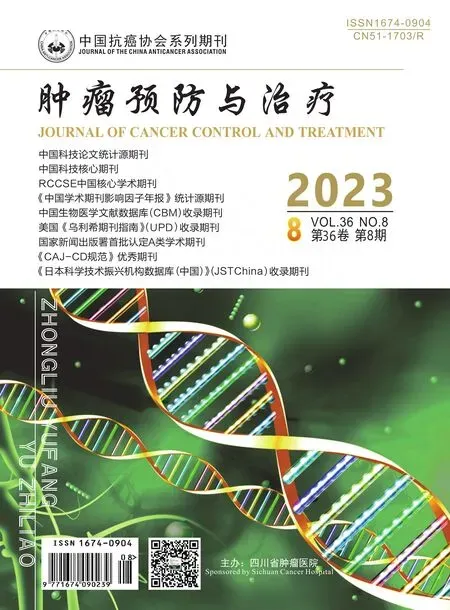外泌體在肺癌免疫治療中的作用*
曾娟,馬士淇,張璐,張雨陽,朱桂全 ,曹邦榮
610041 成都,四川省腫瘤臨床醫學研究中心,四川省腫瘤醫院·研究所,四川省癌癥防治中心,電子科技大學附屬腫瘤醫院 放射腫瘤學四川省重點實驗室(曾娟、馬士淇、張璐、張雨陽、曹邦榮);
610041 成都, 四川大學華西口腔醫院,國家口腔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口腔疾病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 頭頸腫瘤科(朱桂全)
根據2020 年全球癌癥統計數據,肺癌已成為第2 大常見癌癥,但仍然是癌癥死亡的主要原因,估計每年有180 萬人(18%)死于肺癌[1]。近年來,除了傳統的放療和化療外,出現了靶向治療及免疫治療等多種新的治療方法。靶向程序性死亡受體1(programmed death 1,PD-1)/程序性死亡配體1(programmed death ligand 1,PD-L1)的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已被批準用于晚期非小細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患者的治療,與傳統化療相比,這不僅顯著提高了總生存期,而且減少了治療相關的不良事件[2]。然而,通常只有20%~30%的患者有效,仍有大部分患者對其產生治療抵抗[3]。此外,缺乏預測性生物標志物也限制了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進一步臨床應用[4]。因此,尋找其他免疫治療方式迫在眉睫。
外泌體是由多種細胞分泌的脂質雙層膜磷脂囊泡[5]。最初,外泌體被認為只參與細胞代謝廢物管理,但隨著研究的深入,研究人員發現外泌體在免疫應答、細胞增殖、炎癥、代謝和神經功能中發揮著重要作用[6]。值得注意的是,腫瘤來源的外泌體(tumor-derived exosome, TDX)通過與腫瘤微環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 TME)中的多種免疫細胞相互作用而誘導免疫逃逸,是肺癌免疫治療失敗的原因之一[7-9]。目前,靶向外泌體的腫瘤免疫治療策略已引起研究者的關注,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有望為肺癌患者的治療提供新的思路,本文就外泌體在肺癌免疫治療中的研究進展進行綜述。
1 外泌體與TDX
多種細胞可釋放不同類型的細胞外囊泡,根據其大小、生物發生和分泌方式分為3 類:微泡、凋亡小體和外泌體[10]。其中外泌體是一種納米囊泡,直徑為30~150 nm[11],浮力密度為1.13~1.19 g/mL[12]。外泌體起源于細胞內體,發生過程包含3 個階段。首先,質膜內凹形成早期內體。然后,內體膜向內出芽形成多個腔內小泡,轉變為含有眾多小囊泡的多泡體(multivesicular bodies, MVBs)。最后MVBs 將有兩種宿命,與胞質內溶酶體融合導致MVBs 降解;或者與質膜融合,將MVBs 內的囊泡釋放到細胞外間隙,形成外泌體[13-14]。外泌體形成主要依賴轉運所需的內體分選復合物(endosomal sorting complex required for transport,ESCRT)途徑[15]。然而,有研究表明當4 種ESCRT 復合物的關鍵亞基被耗盡時,仍可形成MVBs,提示存在不依賴ESCRT 的外泌體形成途徑[16]。據報道,神經酰胺可以誘導外泌體的生物發生,促進神經酰胺合成的中性鞘磷脂酶2 能夠調節外泌體形成[17]。此外,Rab 家族成員Rab5、Rab7、Rab27a、Rab27b 和Rab35 在外泌體的生物發生、運輸和分泌中發揮著重要作用[18]。另外,外泌體的生物發生和分泌受外部刺激的影響,如熱休克、氧化應激、化療、輻照、缺氧和低溫[19]。
外泌體攜帶了多種質膜和胞質相關分子,如蛋白質、核酸及脂質。在釋放到細胞外環境后,外泌體可能通過3 種機制與受體細胞相互作用。一是配體-受體相互作用,即外泌體表面分子與靶細胞質膜上的分子相互作用;二是內吞,外泌體可通過網格蛋白依賴和網格蛋白不依賴的內吞作用被受體細胞吸收,如胞飲作用、大胞飲作用和吞噬作用;三是直接膜融合,外泌體直接與質膜融合,將其內容物釋放到受體細胞質中[20]。因此,外泌體成為了細胞間信息交流的重要媒介。
TME 由癌細胞、成纖維細胞、免疫細胞、內皮細胞、細胞外基質和基質組織共同組成,是癌細胞賴以生存的復雜環境[21]。TME 中TDXs,通過誘導血管生成[22]、上皮-間質轉化[23]及耐藥性[22],在腫瘤的發生、侵襲和轉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 TDXs 通過影響TME 中的多種免疫細胞的免疫功能發揮腫瘤免疫調節作用,主要誘導免疫逃逸效應,在肺癌免疫治療失敗中發揮關鍵作用[23]。
2 TDX 與腫瘤免疫微環境
2.1 TDX 調控T 淋巴細胞分化及功能
研究發現,TDXs 可通過抑制效應T 細胞功能從而發揮腫瘤免疫逃逸作用。一方面,TDXs 可通過多種機制直接作用于T 細胞,抑制其增殖及功能。來自肺癌的外泌體可攜帶PD-L1,與T 細胞PD-1 結合后,可抑制T 細胞活化和促炎細胞因子的釋放[24]。另外,Wang 等[25]發現肺腺癌來源的外泌體circRNA-002178 通過增強CD8+T 細胞PD-1 的表達,誘發T 細胞衰竭。TDXs 可影響TCR-CD3 復合物的相互作用,從而抑制CD4+和CD8+T 細胞激活[26]。TDXs 釋放ULBP 和MICA,與細胞毒性T 細胞上NKG2D 結合,阻斷了后者的腫瘤裂解作用[27]。TDXs 可通過線粒體通路及死亡受體通路誘導T細胞凋亡[28]。此外,TDXs 通過靶向有絲分裂原活化蛋白激酶1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1,MAPK1)及Janus 激酶(Janus kinase,JAK)/STAT 途徑抑制T 細胞的增殖[29]。另一方面,TDXs 可通過調節調節性T 細胞(regulatory cells,Tregs)誘導腫瘤免疫逃逸。Huang 等[30]發現肺癌細胞外泌體的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pi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可誘導幼稚的CD4+T 細胞分化為Tregs。TDXs 通過TGF-β和 IL-10 依賴機制增強Tregs 增殖[23]。此外,TDXs 攜帶細胞因子CCL20 可招募Tregs,發揮免疫抑制作用[31]。同時,TDXs 可調節Tregs 表面CD39 和CD73 的表達及腺苷產生,后者與T 細胞受體A1,A2A,A2B 和A3 結合可抑制T 細胞功能[23]。
2.2 TDX 抑制NK 細胞的腫瘤殺傷作用
NKG2D 是NK 細胞表面的一種刺激性受體,當其與表達于腫瘤細胞表面的NKG2D配體(NKG2DL)結合后,可被激活而發生脫顆粒作用,介導腫瘤細胞死亡。而TDXs 可攜帶可溶性NKG2DL(sNKG2DL)如MICA 及MICB,導致腫瘤細胞逃避NK 細胞的毒性作用[32]。Berchem 等[33]發現肺癌細胞系來源的外泌體通過傳遞轉化生長因子β1,降低NKG2D 表達,從而抑制NK 細胞的細胞毒功能。TDXs 也可能通過其他機制減弱NK 細胞活性。TDXs HSP70 與表達TLR2 的MDCSs 相互作用誘導免疫抑制因子的產生,從而損害NK 細胞的活性[34]。外泌體miR-92b 可抑制NK 細胞表達CD69 及損害NK 細胞的細胞毒性作用[35]。 腫瘤外泌體circUHRF1 可抑制NK 細胞分泌IFN-γ和TNF-α及其細胞毒功能,同時還與TME 中NK 細胞數量下降有關[36]。Wan 等[37]發現來自晚期惡性胸膜間皮瘤患者的TDXs 能抑制IL-2 誘導的NK 細胞增殖。另外在小鼠模型中,TDXs 降低了肺內NK 細胞的百分比[23]。
2.3 TDX 促進巨噬細胞向M2 型極化
作為免疫系統的關鍵成分之一,腫瘤相關巨噬細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 TAMs)在腫瘤免疫調節中發揮著重要作用。TAMs 可極化為抗腫瘤M1 表型或促腫瘤M2 表型[32]。TDXs 可通過多種機制促進M2 型極化。多種外泌體RNA 可促進TAMs 向M2 型極化。腫瘤外泌體miR146a 通過SALL4-miR146a 軸促進了M2 的極化[32]。來自p53突變的癌細胞外泌體miR-1246 可以誘導巨噬細胞極化為促腫瘤M2 表型[38]。M1 型主要通過糖酵解獲得能量,而M2 型更依賴有氧代謝,肺TDX 通過改變巨噬細胞能量代謝途經誘導巨噬細胞向M2 表型極化[39]。細胞骨架蛋白重排是巨噬細胞活化及成熟的原始特征[40]。腫瘤干細胞來源的外泌體可通過改變單核細胞的形態和肌動蛋白骨架,促進單核細胞向M2 表型分化[41]。有趣的是,低氧條件可增強外泌體誘導巨噬細胞向M2 型極化的作用。Hsu 等[42]發現低氧肺癌細胞的外泌體miR-301a 通過下調巨噬細胞極化蛋白PTEN 表達誘導M2 表型。
2.4 TDX 與樹突狀細胞及髓源性抑制細胞(myeloid derived suppressor cells,MDSCs)
樹突狀細胞(dendritic cell,DC)是來源于骨髓干細胞的特異性抗原呈遞細胞,通過處理抗原并將其呈遞給T 細胞,在免疫反應中發揮著重要的功能[29]。多項研究發現TDXs 可抑制DCs 的抗原呈遞功能。TDXs miR-212-3p 通過抑制DCs 表達MHC-II 發揮免疫耐受功能[43]。Huang 等[30]發現超過80%來源于肺癌的外泌體攜帶EGFR,傳遞給DCs 后誘導其分化成耐受性DCs,從而促進CD4+T細胞分化成Tregs。
MDSCs 是一種異質的不成熟骨髓細胞,可介導免疫抑制性TME[44]。TDXs 可加強MDSCs 的免疫抑制作用并調節其豐度。Alipoor 等[23]證明了TDXs 表面的HSP72,以TLR2/ MyD88 依賴的方式激活STAT3,增強了MDSCs 對T 細胞的抑制作用。此外,體外培養的B16 腫瘤細胞釋放的外泌體能夠以TLR2 依賴的方式誘導MDSCs 增殖[44]。同時,Ren 等[45]報道TDXs 通過傳遞miRNA-107 可促進MDSCs 增殖。
3 外泌體在腫瘤免疫治療中可作為潛在的生物標志物
腫瘤免疫治療旨在增強人體固有防御以消除腫瘤細胞,它的出現使腫瘤治療發生了革命性改變。腫瘤免疫治療主要包括溶瘤病毒治療、腫瘤疫苗、細胞因子、過繼細胞移植治療和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Is)。而目前NSCLC的免疫治療主要指以PD-1/PD-L1 抗體為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代表性藥物[46]。以下提到的免疫治療特指PD-1/PD-L1 抑制劑。
近年來,PD-L1 表達、腫瘤浸潤淋巴細胞、腫瘤突變負荷、某些驅動基因突變和微衛星不穩定性/缺陷錯配修復等生物標志物,被提出用于預測免疫治療的療效和預后[47],但它們都不能很好地用于對免疫治療有反應的NSCLC 患者。例如,一些研究揭示了PD-L1 表達與PD-1/PD-L1 靶向劑的潛在效益之間呈正相關[48]。在另一項隨機研究中,PD-L1 表達水平不能預測生存獲益[49]。總之,PD-L1 的表達并不總是與免疫治療的潛在好處一致,這可能源于腫瘤的時空異質性[50]。外泌體PD-L1 可以動態顯示PD-L1 的平均表達水平,可能作為免疫治療的潛在生物標志物[51]。Yang 等[52]發現,在ICIs 治療2個月時外泌體PD-L1 的變化高于基線時的NSCLC患者有更好的無進展生存期和總生存期。然而,Del 等[53]研究表明,血漿來源的外泌體PD-L1 在治療有效的NSCLC 患者中顯著下調,而在疾病進展的受試者中則升高,這也被另一項研究證實[54]。此外,Shimada 等[55]發現基線外泌體PD-L1 可以很好地區分應答者和非應答者。外泌體PD-L1 的預測價值有待進一步研究。此外,hsa-miR-320 家族的3個miRNA 被鑒定為潛在的生物標志物,以選擇患者接受晚期NSCLC 的免疫治療,其中外泌體miRNA miR-320d 被認為是進展性疾病和部分緩解患者之間最顯著的差異表達miRNA[56]。此外,基于外泌體的液體活檢比組織活檢具有更小的侵入性和更低的成本[57]。隨著液體活檢技術的發展,外泌體有可能成為免疫治療的潛在生物標志物。
4 外泌體作為靶點在肺癌免疫治療中的潛在作用
4.1 阻斷外泌體上的免疫檢查點
CD47 是一種免疫檢查點,通常在腫瘤細胞上高表達,通過與吞噬細胞上的信號調節蛋白α(signal regulatory protein α, SIRPα)結合,抑制巨噬細胞的吞噬作用[58]。阻斷CD47/SIRPα 相互作用已作為一種治療策略,包括以CD47 或SIRPα 為靶點的單克隆抗體和拮抗相互作用的重組SIRPα 蛋白[59]。例如,Zhang 等[60]發現一種新的靶向CD47 的融合蛋白SIRPαD1-Fc 可以增加巨噬細胞對NSCLC 細胞的吞噬和細胞毒活性。然而使用重組SIRPα 蛋白雖然可以通過阻斷抑制信號增強體外吞噬能力,但體內治療效果只有與其他抗癌藥物結合才能實現[61]。此外,Liu 等[62]在免疫缺陷小鼠肺癌細胞異種移植模型中發現抗CD47抗體可使巨噬細胞吞噬肺癌細胞,從而抑制腫瘤生長,提高荷瘤動物的生存。然而,有限的特異性導致抗CD47 抗體與正常(非腫瘤)細胞結合,導致貧血和白細胞減少。為了克服這些限制,Koh 等[63]開發了一種基于外泌體的免疫檢查點阻斷劑,即表面含有SIRPα 變異體的外泌體,顯著提高了其對CD47 的親和力。靜脈注射SIRPα 變異體-外泌體后增強了巨噬細胞的腫瘤吞噬能力,引發了有效的抗腫瘤T 細胞反應,提示SIRPα 變異體-外泌體具有巨大的阻斷免疫檢查點的潛力。盡管這項研究基于結腸癌,但CD47 是所有腫瘤細胞的主要抗吞噬信號[59]。這為SIRPα 變異體-外泌體用于肺癌治療提供了思路。
4.2 外泌體分泌抑制劑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聯合應用
外泌體PD-L1 結合抗PD-L1 單克隆抗體(mAbs)從而釋放了腫瘤細胞的PD-L1,或外泌體PD-L1 直接與效應T 細胞上的PD-1 結合,抑制抗體的阻斷作用,允許PD-L1 介導持續的免疫抑制反應[18]。Yang等[64]發現BALB/c 4T-1 荷瘤小鼠經外泌體分泌抑制劑GW4869 和抗PD-L1 單克隆抗體處理后,原代腫瘤負荷降幅最大,表明外泌體分泌抑制劑與免疫檢查點抑制聯合治療顯示出協同效應。另一方面,外泌體circUHRF1 可能導致抗PD-1 免疫治療的耐藥性。Li 等[65]證明敲除外泌體cirUHRFI 可導致抗PD-1 治療的敏感性提高,并提高了總生存率。本研究團隊前期研究發現低氧TDXs 通過miR-21/PTEN/PD-L1 調節軸增強MDSCs 對γδT 細胞的抑制作用。同時,在口腔鱗狀細胞癌小鼠中,通過聯合抑制外泌體miR-21 和免疫檢查點PD-L1/PD-1 顯著抑制了腫瘤細胞的增殖。由此可見,聯合外泌體抑制劑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是肺癌患者治療的新方向。到目前,外泌體抑制劑主要通過靶向RAB27A 及SMase 實現[66]。盡管聯合外泌體抑制劑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在肺癌患者免疫治療中具有巨大的潛能,但仍需進一步的研究。
4.3 外泌體作為腫瘤疫苗
研究表明樹突狀細胞來源的外泌體(dendritic cell-derived exosomes, DEXs)及TDXs 有可能開創肺癌疫苗研制的新時代。DEXs 攜帶MHC-肽復合物和共刺激分子,具有強大的抗原呈遞作用[5]。本質上,外泌體在腫瘤免疫治療中具有新型細胞游離疫苗的功能[67]。目前,DEXs 已經歷經第一代及第二代的發展。第一代的臨床試驗開始于2005 年,該研究利用DEX 治療晚期肺癌患者,結果只有30%的患者中效應T 細胞功能輕微增加[68]。而后為了改善DEXs 誘導的有限的T 細胞反應開發了第二代DEXs,使用LPS 或IFN-γ 促進DCs 成熟后,再從成熟DCs 中獲得外泌體,增強了T 細胞的抗腫瘤活性[69]。但在一項II 期臨床試驗中,NSCLC 患者在一線化療后接受了IFN-γ-DEX 治療,患者無進展生存期為50%,未見顯著的免疫反應性[70]。在體外和體內動物模型中,TDEs 也可誘導腫瘤特異性T 細胞反應。然而,單純TDEs 不能誘導強的抗腫瘤活性,必須對其進行修飾。目前已有幾項研究表明改進TDXs 后可增強抗腫瘤反應。例如,超抗原修飾的TDEs 可誘導更強的免疫原性反應;來源于表達 IL-18+TDEs,可增強細胞因子釋放及DC 細胞成熟,從而可誘導更強的特異性細胞毒性反應[16]。但尚未有TDEs 進入臨床試驗階段。由此看來,目前外泌體疫苗在肺癌免疫治療的療效不盡人意,原因可能是TME 中的T 細胞多處于功能障礙狀態,由此引發的免疫反應較弱[71]。急需尋求一定的聯合治療方式來增強DEXs 或TDXs 對T 細胞的激活作用,提高腫瘤患者的免疫治療效果。值得一提的是,Choo等[72]通過擠壓方式獲取M1 巨噬細胞的外泌體模擬納米囊泡(exosome-mimetic nanovesicles derived from M1 macrophages,M1NVs),他們發現向荷瘤小鼠注射M1NVs 可抑制腫瘤生長,并且聯合應用M1NVs及aPD-L1,比兩者單獨應用能更有效地抑制腫瘤生長,并進一步揭示MINVs 主要通過將M2 巨噬細胞復極化為M1 巨噬細胞發揮作用,上述結果提示外泌體類似物可作為一種潛在的新型腫瘤疫苗。
5 結 語
目前肺癌免疫治療在晚期肺癌的治療中占據著重要地位,但由于免疫抑制性TME 的作用,削弱了免疫治療的療效。免疫抑制性微環境的形成涉及多種機制,外泌體是近年來廣受關注的機制之一。基于外泌體在腫瘤免疫逃逸中的作用及對外泌體的生物學特性方面的研究,開發靶向外泌體的腫瘤免疫治療方案成為了研究熱點。但目前外泌體是否可作為未來免疫治療的生物標記物或作為癌癥疫苗,均缺乏系統研究。癌癥疫苗雖然已經進入臨床試驗,但目前未顯示出良好的療效,并且實驗多基于小樣本,癌癥疫苗是否能使肺癌患者獲益仍存在爭議。此外,基于外泌體的其他癌癥免疫治療顯示出了較好的療效,但研究停留在動物模型階段,這些治療方案是否能使肺癌患者獲益仍不清楚,需要開展更多實驗研究來進一步推動外泌體在肺癌免疫治療的臨床應用和轉化。
作者聲明:本文全部作者對于研究和撰寫的論文出現的不端行為承擔相應責任;并承諾論文中涉及的原始圖片、數據資料等已按照有關規定保存,可接受核查。
學術不端:本文在初審、返修及出版前均通過中國知網(CNKI)科技期刊學術不端文獻檢測系統的學術不端檢測。
同行評議:經同行專家雙盲外審,達到刊發要求。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文章版權:本文出版前已與全體作者簽署了論文授權書等協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