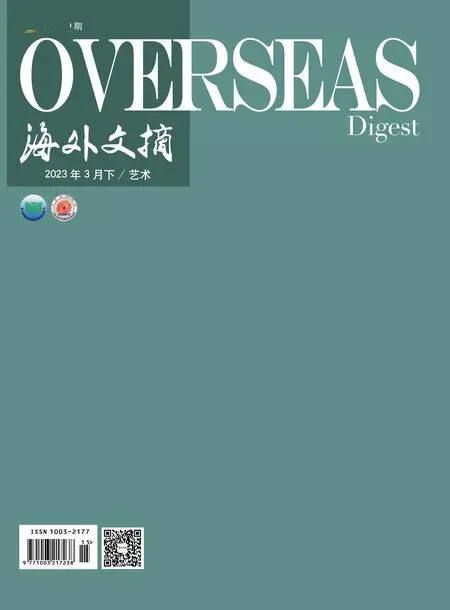敦煌樂舞壁畫中的“對稱美”及其活態化呈現
□武迎輝 寇亮/文
莫高窟存有壁畫洞窟492個,其中含有樂舞壁畫的洞窟有328個,樂舞壁畫占據較大部分。在敦煌石窟中占據一席之地的樂舞壁畫,承載著自十六國(304年—439年)時期以來的樂舞審美特征——華夏文化視域中的“對稱美”。本論文通過分析敦煌樂舞壁畫的“對稱性”規律,在探究樂舞壁畫所體現的審美認同的基礎上,把握如何在舞蹈作品活態化呈現“對稱美”的實踐方法與應用路徑,幫助相關從業者在敦煌樂舞中汲取靈感,更好地進行創作與表演。
1 “對稱性”規律相關概述
1.1 概念界定:敦煌樂舞壁畫之“對稱性”
“對稱”的概念源于中國傳統思維方式之一,太極思維中的“置陣布勢”。“均齊和諧,平衡對稱”是太極圖的一個顯著特征。“對稱”內涵豐富,象征著中庸、平衡、和諧的中正之美;莊重、穩健、大方的傳統之美;寧靜、安和、穩定的意境之美。“對稱”以一條線或點為中心,使得事物的顏色、結構、格局在兩側形成和諧一致的象,從而構建協調、勻稱的空間現象,以一種對等的形式給人帶來視覺上結構整齊、協調統一的美的感受。
“對稱”的概念分類中有絕對對稱、相對對稱(相似對稱)等,而在哲學范疇以及更大的平衡法則中又有不相似對稱這個概念。局部不對稱的相對對稱賦予“對稱”一種可變量的美,表達著中國人在物的造物表現上對“對稱美”的獨到追求。
聚焦于敦煌樂舞壁畫中“對稱”的應用,強調整體與局部的和諧,壁畫局部的內容遵循著“相對對稱”與“絕對對稱”的原則,而從石窟整體的呈現效果上來看,石窟貫徹了不相似對稱的美學追求。具體體現在從洞窟整體布局來看,敦煌壁畫嚴格遵循了對稱法則。一般說來,主要是以洞窟西壁為中心,南、北兩壁相向的壁畫之面積、位置等呈對稱均衡狀。如南壁中央有一幅說法圖,在北壁相應位置也有一幅同樣大小的說法圖;如南壁有幾幅經變畫,北壁也就有幾幅經變畫,并且大小、位置也相對應。但是,其畫面中的局部布局、人物造型、建筑背景以及色彩等等卻存在著很多差異。這是它的不對稱性的體現[1]。
1.2 審美認同:“對稱美”寓于敦煌樂舞壁畫之中
所謂審美認同,是藝術類型與社會群體的文化結盟,借助這種結盟,群體就會感覺到某種藝術類型是代表了“我們的”或者“他們的”藝術、音樂和文學。古語有云:“夫美者,上下、內外、大小、遠近皆無害焉,故曰美。”中國文化始終追求著對稱美,無論是建筑中所追求的工整、宏偉,如北京市東城西城呈東西對稱布局,而故宮正好在中軸線上,飛檐翹角紅墻黃瓦也如鵬鳥雙翼,呈現出對稱之美;還是詩詞中所追求的對稱和諧,如“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月照人,人觀月,物我相望;還是服飾中所追求的剪裁得當,如旗袍盤扣的對稱美學,都體現了中國人對對稱美的認同。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說“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在“對稱美”形式背后的,是民族成員對敦煌樂舞壁畫所承載的文化的認同,是其情感歸屬和紐帶所在。
2 敦煌壁畫中“對稱”樂舞形式分析
2.1 藻井中的飛天伎樂
敦煌壁畫中的藻井圖案是以點為中心的相對對稱結構。四方形的藻井圖案中,方形或圓形的飛天花紋圖案由內而外層層疊加,從而形成了典型的旋轉式對稱圖案。敦煌壁畫中現存的最早的藻井圖案是第272窟頂的北涼時期的泥塑彩繪套斗式藻井(圖1),該藻井邊框為方形,飛天伎樂(東魏成書的《洛陽伽藍記》中記載:“有金像輦,去地三尺,施寶蓋,四面垂金鈴七寶珠,飛天伎樂,望之云表。”伎樂天,是專司散花施香、歌舞伎樂的佛陀侍從,飛天造像之一,不能完全等同飛天。由于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初傳,在中國發展還不成熟,概念釋義有模糊重疊的地方,飛天伎樂、伎樂天、飛天指同一神,即伎樂天)處于外層的四角內,有不同表現形式的忍冬紋作邊飾,岔角飾有火焰紋等花紋。在井心向上凸進形成的側壁,還畫出垂角紋樣,中央繪制圓形蓮花。值得注意的是藻井中的飛天伎樂服飾、飄帶的顏色均有不同,從整體結構來看卻顯現出對稱統一之美。藻井中一位位飛天伎樂姿態造型各異、方向順逆結合,以靜制動,以旋轉對稱營造出飄逸飛翔的動態之美。總的來說,敦煌樂舞壁畫既呈現出了均齊和諧的靜態的對稱之美,同時也以飛天伎樂的不同服飾造型、樂舞姿態的變換表現出一種動態的效果,方圓相疊、動靜相宜,體現出濃郁的東方美學。

圖1 272洞窟藻井
2.2 宮門中的天宮伎樂
天宮伎樂作為敦煌石窟中最早的石窟樂舞圖像,每一個樂伎都由二方連續的宮門隔開[2],呈現出交錯復雜的視覺效果。由于這些樂伎大都位于洞窟壁畫上端的天宮樓閣中,因此被稱為天宮伎樂。最早出現在北涼時期的洞窟里的門的形狀為半圓拱序式,是西方的建筑形式。而到了北魏時期,方形的門上方帶有小小的屋檐,有明顯的漢人的建筑形式特點,這種門稱為宮門。從門的建筑形式的發展變化來看,這一時期佛教文化初傳,并逐步對中原文化產生影響,故門的建筑構造有明顯的西域文化與中原文化融合交流之美。
在諸多的洞窟中,天宮伎樂或出現在洞窟的一面墻,或出現在四壁,有時也出現在人字坡上。在形式上具有橫向排列、人數眾多、一人一宮門、半身居于各中的特點,這種單一、限制、傳統且格式化的表現形式使其在整體布局上更顯現出強烈的對稱美學。
北魏時期的莫高窟251窟(圖2)中出現了天宮伎樂以全部舞姿形態呈現在樓閣中的較為少見的特例。他們姿態各異,或雙手合十作冥想之態或衣袂翩躚欲乘風歸去。由此可以看出,天宮伎樂相關的樂舞壁畫在整體布局上有序排列,形成對稱之勢,此為形式上的對稱。細化到樓閣中,天宮伎樂樂器演奏與舞姿形態相互呼應,態勢形象逼真,暗示著樂伎音樂節奏與舞姿韻律的相互配合,就內在調度而言,也形成了樂舞相接、樂律響應的動態效果。敦煌莫高窟在不變的樓閣中表現了萬般變化的樂舞者形象;在不變的形式中呈現了萬變的樂器鳴奏、舞姿韻律。舞與樂互為補充、融為一體。

圖2 莫高窟251窟局部
2.3 經變圖中的樂舞場面
所謂經變圖,經是“佛經”,變是“變相”或“變現”,也就是形象化的意思。換句話,經變圖就是以圖像的形式來說明某部佛經的思想內容。敦煌莫高窟中的經變圖像依據佛經中的故事情節繪制相應的樂舞場面,高德祥先生將這類壁畫統稱為“經變樂舞”[3]。經變圖中的樂舞場面形式統一、排列有序、樂舞相依。這樣極具美感的樂舞畫面與唐代兼收并蓄、充滿包容性的文化風氣緊密相依。經變樂舞將唐代宮廷宴樂中最高級的樂舞配置——坐部伎(坐部伎是唐玄宗時期宮廷燕樂中的一種演奏形式。在堂上坐奏時稱為坐部伎,而在堂下立奏時稱為立部伎)應用其中,以此演奏制式表達人們對西方“極樂世界”盡善盡美的美好想象。經變樂舞壁畫中,中間是姿態各異的舞伎,旁邊是單排或多排式進行演奏的樂伎,且左右人數對等。經變樂舞壁畫中除了樂伎、舞伎的對稱排列之外,還有舞臺、服飾顏色的對稱。
較為經典的經變樂舞是中唐時期莫高窟第112窟中的金剛經變(圖3)。該壁畫從舞臺的構建到樂隊的布局再到樂器的使用以及各個樂伎形態各異的舞姿,都顯現出隋唐宮廷宴樂制式的特點。壁畫中左側樂隊與右側樂隊人數均等且制式相同,左側樂伎演奏的樂器由前到后,依次為橫笛、法螺、篳篥、拍板;右側樂伎演奏的樂器由前到后依次為笙、豎箜篌、羯鼓、琵琶。置于舞臺正中的舞伎在雙手執巾、雙臂展平的同時,左腳立姿,右腳后掖,身體與眼神似乎與樂伎多有交流,因此成向前傾倒的態勢。這種位置排序固定但舞伎姿態風流隨意,體現出唐代宮廷樂舞儀式性和娛樂性兼具的特點。坐部伎位置的固定強調了唐朝等級制度下坐部伎的尊貴性。宮廷樂舞中具有較高地位的樂舞制式強調固定人數、固定樂器、固定排列方式,這種程式被再現于敦煌壁畫的樂舞場面之中,可以說經變樂舞壁畫是唐人對于“對稱性”審美觀念的獨特表達的載體。

圖3 莫高窟第112窟金剛經變局部
3“對稱美”于敦煌舞的活態化呈現
3.1“對稱美”于舞蹈構圖的形式呈現
黑格爾說過:“只是形式一致,同一性的重復……把彼此不一致的定性結合為一致的形式,才能產生平衡對稱。”敦煌樂舞壁畫在“平衡對稱中蘊含著調和對比,從而達到多樣統一的美感配置”[4]。
當代舞蹈實踐中,學習運用敦煌樂舞壁畫所承載的“對稱美”構圖進行舞蹈創作的代表有高金榮先生。他創作的舞蹈作品《千手觀音》,構圖以中間舞者為中心,左右兩側演員形體上存在差異,但大體上相當,位置固定,體現出平衡之美。舞者縱向對齊,在固定化的垂直關系基礎之上以“千手”多樣化的聚合與分離營造出真善美的千手觀音形象。舞者身體的靜態處理與手臂的動態變化,構成對稱形式,從而達到了以靜制動、動靜結合,以不變應萬變的韻律之美[5]。
3.2“對稱美”于舞蹈姿態的內容表達
敦煌舞蹈屬于中國古典舞的范疇,它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各家之精華,是中國自古以來樂舞一體的藝術形式的傳承與繼續。敦煌壁畫中的樂舞種類繁多,但均凸顯著敦煌樂舞壁畫中獨有的“S”形姿態動勢,承載著敦煌樂舞的共性規律。樂伎雖有造型差異,但在整體步調上顯出協調、統一的特點。
敦煌舞姿的“對稱美”呈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呈現在由身體的勁力對抗而形成的人體對稱結構:敦煌樂舞壁畫中的人體姿態有著獨特的舒展與曲屈的弧度。從局部來看,舞伎們手姿豐富,腳指、腳踝的勾繃力度具有彎曲又有勁力的特點。身體局部關節的彎曲協調至全身,頭、腕、肘、臂、胸、肋、腰、胯、膝、腿、腳各個部位互相配合,整體上形成了一條自然的“S”形曲線。敦煌壁畫中的舞伎以身體的不同部位發力向外延伸,形成了榫卯結構一般力與力對抗的關系[6]。例如,莫高窟中晚唐時期114窟經變畫中的舞伎,她提肘、挽綢、側身、擺胯、盤腿、儈腳、彎膝,形成了一個“S”型曲線。這些身體部位,失去任何一個發力點,便會出現人物傾倒的現象,但舞伎卻實現了一種平衡,這進一步說明了敦煌樂舞中身姿的勁力對稱。
另一方面,呈現在由舞姿造型所形成的對稱態勢,例如,敦煌莫高窟初唐時期第220窟中的樂舞壁畫(圖4)是借鑒《對影胡旋》創作的。畫面中舞伎的舞姿成對稱態勢,相互推動,神態交流,身體形態與彎曲飄逸的綢帶彼此配合,給人以鮮明活躍的審美感受。

圖4 莫高窟第220窟局部
3.3“對稱美”于舞蹈表演的審美意境
敦煌樂舞壁畫的“對稱美”審美規律應用于舞蹈藝術中,呈現的是平衡對稱、陰陽相諧的審美意境。
敦煌壁畫中所描繪的佛國世界中的伎樂以不同的身份,如伎樂天、伽陵頻迦(佛教詞匯,佛教里的一種妙音鳥)等形象出現,他們或身姿如旋或反彈琵琶,造型各異,多變的形象與豐富的肢體語言相互配合,在給人以鮮明活躍的視覺感受的同時,又以形、質、勢的融合,樂舞一體畫面的呈現,動靜結合的審美意境的營造,創造出非凡的氣象。
當代舞蹈創作實踐中,有相似意境的作品有北京舞蹈學院胡元圓、馬路瑤編創的舞蹈作品《伽陵頻迦》,舞蹈中舞者四人縱向于舞臺之上,以中段固定配以四肢在不同空間的對稱姿態,在展現靈巧多變的手姿的同時,塑造了人首鳥身的妙音鳥形象,表現出其形象于對稱之中體現的千變萬化、萬象歸一之美。該舞蹈以靜制動、動靜結合,凸顯出舞者以不變應萬變的主體意識。該作品舞臺結構也是對稱的。舞者在表演時節奏、神態、氣力、情感相互統一,在流動中求“合”,合并中求“異”,傳遞出一種“真、善、美”的意境。
4 結語
敦煌樂舞壁畫所體現的“對稱美”的審美規律,承載著中國傳統文化思維中對中庸之道的追求,凸顯了“陰陽相合,主從有序”的內在特征:樂伎既為壁畫中的個體,主體為陽,也為壁畫中的群體,配體為陰,在對稱之勢中彰顯了樂舞一體、動靜結合的審美意境。這種審美意境同樣也是中國樂舞藝術自誕生起就一以貫之的追求。■
引用
[1] 胡同慶,胡朝陽.試論敦煌壁畫中的于對稱中求不對稱美學特征[J].民族藝術,2004(03):81-82.
[2] 汪雪.敦煌莫高窟壁畫樂舞圖式研究[D].蘭州:蘭州大學,2022.
[3] 高德祥.敦煌古代樂舞[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8.
[4] 呂藝生.舞蹈美學[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1.
[5] 高金榮.敦煌石窟樂舞藝術[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 2000.
[6] 夏瑩瑩.關于敦煌舞美學特征的探索[D].蘭州:西北民族大學,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