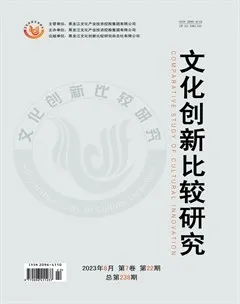以風景為敘事媒介
——《烏拉尼亞》中的“理想”空間
劉碧原
(長江大學 文理學院,湖北荊州 434020)
《烏拉尼亞》講述了位于墨西哥河谷,在紅燈區、貧民區和不斷擴張的富人區包圍之下,兩個 “理想的”空間從創建到失敗的故事。“理想的城市”坎波斯追求“自然原始”[1]、人人平等的生活狀態,與現代文明持久斗爭,最終被迫遷移、尋找新的出路;“理想的學院”朗波里奧期待不同膚色、種族、階級的人自由交流、豐富知識,也沒能實現。現有評論常常將前者視為“自由國度”[2]“返歸自然”的代表[3],與現實世界對立,而忽略了后者,或將之簡單歸入“現代文明”。如果以風景意象為線索,就能清晰地看到兩者的內在關聯和故事的發展脈絡。
1 以風景為敘事媒介
1.1 烏托邦想象與風景再現
勒·克萊齊奧明確表示,《烏拉尼亞》是一部“現代版的《烏托邦》”。烏托邦概念一開始就與“地方”緊密相連,意為“快樂之地”(eutopos)和“烏有之地”(outopos);并且這一想象之地是被實踐了的場所,包含列斐伏爾所說的 “被感知的空間”(perceived space,人們在場所中隱含了社會空間的表現與活動)、“構想的抽象空間”(conceived space, 通過數字與文字符號表現的人們對特定地方的再組織方式)和“日常空間”(lived space,亦即“再現的空間”,由“圖像和象征物”做媒介傳述給想象,進而改變和占用空間)[4]。
風景(landscape)一詞,源于荷蘭語landskip。美國學者W·J·T·米歇爾指出:作為“一種文化意象,圖畫式的再現、建構,或周遭環境的象征”[5],風景首先和場所有關;其次,在創造和欣賞風景的過程中包含各種權力的對抗與妥協,風景本身則顯示了拉康稱之為“象征系統”的法律、社會監控等,是一個被管理、被規劃的地帶。在烏托邦文學傳統中,風景往往作為“圖像式”媒介再現有關理想社會的想象,如《理想國》的洞穴之喻、《烏托邦》中的荒海孤島、《巨人傳》中的森林烏托邦、傅立葉的工業化城邦;《一九八四》中無處不在的鐵幕講述人如何被監視,《我們》以玻璃及玻璃透視的景象展現劇情的轉向,《美麗新世界》中的印第安保留地和海島則是不同人物命運的轉折點與終點……風景將場所從“固定的位置”中抽離,在人的行為過程中與社會組織結構結合,揭示被場所隱藏起來的主體身份,顯示創造和欣賞風景過程中的各種社會關系,并承擔不同程度的敘事功能。
1.2 《烏拉尼亞》與墨西哥城
國內有關評述大多注意到小說中風景描寫得優美細膩,部分論述將烏托邦式的坎波斯“走向自然”的理想與桃花源相提并論[6]。但是這一理想與“烏拉尼亞”(“天上的國度”)有何關聯,又為何崩塌卻不得而知;其敘事性和現實性更是在未知中被消解,成為一種“政治幻想”,“只可能是一個審美虛構的存在”[7]。
勒·克萊齊奧指出,“《烏拉尼亞》中,有兩個烏托邦……一個是理想的學院,一個是理想的城市”[8]。“理想的城市”融于自然,夢想建立不同民族、文化、宗教與生活方式和諧共存的理想社會,追求人的平等自由;“理想的學院”立于山崗,希望“砸爛社會等級與偏見的枷鎖,讓農民和普通老百姓也能登上大雅之堂”,追求智識的平等自由。“結果兩個理想都沒有實現,都有問題。”優美的風景指向對現代社會語境下理想生活的反思,這是桃花源式的幻想所不具備的。
在《烏拉尼亞》中,風景作為敘事媒介完成對真實或虛構的事件與狀態的講述。故事發生在“當代墨西哥一個極具代表性的地方”河谷中,完全不同于烏托邦文學傳統中的“烏有之地”,也因此有了更具象的現實意義。“以物質世界原本的方式描繪這個世界”是勒·克萊齊奧作品的一大特點;以無比清晰的筆觸描寫不同社會群體對風景的依戀。“與美洲印第安文化的邂逅、對墨西哥文明的書寫向我們展示出他介入行為的另一面。”[9]在邊境之地設置各種彼此對立又相互依存的河谷社會,風景成為社會,權力、經濟權力和知識權力的“圖像和象征物”,既展現對理想生活的想象,也講述了權力掌控者如何改變和占有空間。
2 “理想的城市”
不同于烏托邦分為赫然對立且保持距離的城市和鄉村[10],“理想的城市”融于田園,不僅看似修正了“現代社會的弊病”,還兼具城市滿足居民 “群體需求、倫理和美學”的功能。但是,當這一切建立在被當作可蹂躪的“地”的貧民和原住民身上時,坎波斯是否真的“安樂和諧”,它的失敗是否僅僅因為“過于理想”?
2.1 “自然生活”中的方塔
“理想的城市”保有良好的自然生態景觀,其生產方式、教育體制、日常生活組織也“自然原始”(沒有現代時間度量,人人平等,人人議事)。然而,“城市……是人類社會權力和歷史文化所形成的一種最大限度的匯聚體”[11]。作為“理想的城市”,坎波斯自有其歷史文化,并非完全“自然原始”,這一點由城市的中心——一座紀念碑式的方塔所揭示。它標志著原屬于耶穌會會士的坎波斯教堂遺址,承載關于這個集體及其理想的記憶。
勒·克萊齊奧特意指出:1540年西班牙修道士曾建立保護印第安人 “免受政府軍欺凌”的自治村莊,“采用的是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模式。那是一次建立理想社會的嘗試,致力于消除等級與貧富差別,使每個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展現各自的手藝和學識”。同時,神父也常常是當地反殖民斗爭的重要領導者,如“多洛雷斯呼聲”。這也是坎波斯教堂中被政府軍槍殺的普羅神父形象的意義所在。
“理想的城市”與作者記憶中的自治村莊具有高度相似性。坎波斯居民庇護逃難者,“想要恢復耶穌會會士的事業,建立一個理想社會”,試圖以耶穌會教堂遺址中的歷史文化內涵為“理想社會”的真實性和合法性提供無聲佐證。方塔的聳立即是為了完成這一敘述,并處于新的敘事中心。
2.2 田野上的金錢共同體
坎波斯在極具象征意義的土地上重組空間,流浪者得以改變身份成為城市居民。它并非桃花源,更不能等同于“天上的國度”[12],而是與“現代城市”“現實世界”共同構成河谷景觀,彼此有無法割斷的聯系。
坎波斯以租賃形式獲得合法性 (參事賈迪從富人處租賃土地并注冊坎波斯),與河谷城市有緊密的貿易來往。土地作為商品,以租金為媒介實現資本化,并形成所有權(房地產商)、使用權(賈迪)及連帶使用權(坎波斯其他居民)的三層經濟依附關系。“伴隨著商品的普遍化,土地成為商品,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的空間,也投入了買賣中。”基于使用權,賈迪決定生產生活方式、教育方式和收入支配方式等的“理想”模式,有權驅逐叛逆的居民,并居中將集體生產和房地產商對價值的占有聯系起來。從這一點上來看,賈迪更像是一名企業經理。
同時,“美國商品”及其貿易規則控制了河谷的經濟命脈。坎波斯既依附于現代經濟關系,更直接從投資中獲利 (居民勞動收入被參事安東尼存入高利活期賬戶)。土地作為商品的本質隱藏在城市的田園風光之下,資本運作也藏匿于財富共有的美好圖景之中。實際上“金錢共同體取代了所有社會聯系的紐帶關系。多元、流動、零碎是新的人文特征”。在環環緊扣的經濟鏈中,坎波斯無法獨善其身。它的“理想”植根于對貧民和原住民的榨取,并非“獨立于外界發達物質文明以外的烏托邦”[13];其居民本質上是無意中成為新殖民工具的外來移民。
2.3 回不去的半月島
烏托邦理想和空間不可分割,在大衛·哈維的論述中又和身體政治緊密相連。自1798年以來,“共和國身體政治不僅被表現為女性形象,而且還被賦予了強而有力的母性特征……這種養育性的身體政治版本深植在1840年代的左派社會主義和烏托邦計劃中”[14]。《烏拉尼亞》繼承了這一思想傳統。
小說著意刻畫了一位被囚禁在紅燈區的印第安女孩,并在革命者的演講《土地的面貌》中將河谷的土地比喻為 “一個充滿活力的印第安女人的身體”,懇請人們不要讓“貪婪和大意糟蹋了這個美麗、高貴的女人的身體,把它變成一個膚色暗淡、干癟瘦弱、風燭殘年的龍鐘老婦”。這一呼吁顯然失敗了。不僅如此,連遠在海洋之中的“理想城市”的雛形半月島也未能幸免。
法語“月亮”和“島嶼”都是陰性詞匯,半月島孕育了賈迪對“天上國度”的想象,隱喻人回歸本原的理想,和包括坎波斯在內的城市形成對比;另一方面,坎波斯人被迫離開“理想的城市”,半月島成為新的目的地。但是,等他們真正抵達時,卻發現完全無法在“自然原始”的環境中生存下去,只能離開。就連半月島本身,最后也遍布 “粗俗的野餐者留下的垃圾”。物質文明的觸角和新殖民勢力一直伸到這座珊瑚小島上,附近的海域逐漸變為休閑度假的療養區、“自然”風景區和現代文明的垃圾場。
盡管如此,坎波斯人在新的女性領導者奧蒂帶領下重踏追尋之路,預示著半月島孕育和象征的本原生活仍然能夠成為新的起點。正如勒·克萊齊奧所說,“書中對坎波斯的描寫,有理想主義的層面,也有現實的層面,雖然最后失敗了,但,還是給人希望的”。
3 “理想的學院”
與“理想的城市”相對應的,是“人類學家的山崗”上的“理想的學院”朗波里奧。不同于直接進入坎波斯的視角,勒·克萊齊奧在特寫它以前首先設置了背景——不斷擴張、不斷驅趕貧民、不斷占據和改造新的風景的河谷富人區。接著,又描繪學院的前景——被工具化的下層社會所寄居的傘兵區,以及作為遠景的紅燈區。與坎波斯位于廢墟之上不同,這樣一座思想的燈塔立于河谷制高點,“一夜之間為他們(人類學家們)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生活。可以夢想擁有一幢自己的房子,有花園、內院,還有噴泉池”。然而,在以學問換取理想生活的人類學家眼里,本應是他們研究對象的貧民和原住民終究只是 “移動的影子”“一群幽靈”。
3.1 “混血”景觀與新殖民
建立在南美土地上,“理想的學院”中卻處處可見古希臘、古羅馬風格與南美風格混雜的建筑,形成一種“混血”景觀。學院代表唐·托馬斯本身即是混血兒,其學術理想也是混血式的——既崇尚古希臘雅典學派,又渴求為本土印第安人立學。景觀、身份與話語的雙重性,都暗喻了這個理想空間的“混血兒”身份。
這種身份在文本中實則隱喻學院的依附性。為了維系發展,學院必須依靠河谷中上層社會的贊助資金,將來自“美國大學”的人類學家充作研究員。在經濟政治權貴和西方知識體系的雙重壓力之下,南美獨立運動只不過是“人類學”龐大體系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印第安人似乎變成了齷齪行為的象征”,“印第安人的歷史甚至無法在自己祖國的百科全書上占有一席之地”,印第安學者也受到排擠。最終,知識成為新殖民的道具,新興階級成為新時期剝削的中間人,混血的矛盾之處就在于,這一身份無法歸屬,也無法獨立于任何一方。在空間組織、經濟基礎和知識體系上均無法正視這一矛盾的 “理想的學院”名存實亡。
3.2 花園、柵欄與權力對抗
在《烏拉尼亞》中,“理想的城市”和“理想的學院”看似開放——坎波斯收留逃難者,朗波里奧對所有求知者開放。但實際上,它們具有不可避免的封閉性,是被圍墻和柵欄圈起來的居所和花園。圈地的緊閉空間和土地私有化使風景成為顯貴的標志,花園悄無聲息地被定性為占據自然以后的“自然”空間,在再現“自然”、欣賞“自然”的每一行為中都暗藏權力和社會身份的對抗。
《烏拉尼亞》對這種對抗的描寫很含蓄,被“西班牙柵欄”圍繞的羅馬式花園仿佛只是欣賞美麗風光的場所。事實上,學院創建者希望在這里實現“文化自由化、平民化、流動化”。但是,對人類學家們來說,出生、成長在這樣一片土地上,很可能自身就帶有殖民的印記,這印記在新的話語體系下被刻意忽視:革命者的抗爭可能“導致政治后果”,是不合時宜的研究對象;身為被殖民者的后裔,又因資本和學術受制而變為新的殖民和被殖民者,且必須依靠此身份才有可能擁有一座花園。花園和花園里的人們依附外界又害怕外界,只好對真實的人和生活視而不見,從而維護交流的“平等”、學術的“自由”。
對貧民和原住民來說,花園是伊甸園式的禁地。貧民窟的孩子們敢闖入山崗,卻不敢闖入花園,只能默不作聲地站在圍欄外遠觀。富人區、坎波斯和山崗之外的人被迫生活在一種麻木的狀態中,不會有欣賞自然之美的眼睛和閑暇;紅燈區的女人們也只關心生計,生命如同她們寄居的廢棄花園一樣荒蕪。因此,不僅在物質生活方面,在生活志趣和審美上,花園也是一處雙向的禁閉之地。“理想的學院”是財富與權力的象征空間,和圍墻環繞的“理想城市”一樣具有封閉性,沉默地宣告了人類學家和印第安人、貧民、妓女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通過占據“自然”、美化“自然”掩蓋知識、身份、經濟、社會地位的不平等。新殖民與新資本混合成迷藥,“資本榨取個體的自由,用以實現自我增殖:在自由競爭中,并非個體獲得自由,而是資本”[15]。這就是封閉表象的根源所在。
在作者看來,“理想的城市”和“理想的學院”都不是“烏拉尼亞”。小說結尾處明確指出,“從某種角度來說,朗波里奧與坎波斯有著某種邏輯聯系”,“由于自身的缺陷,所有的努力都歸于失敗”。兩個烏托邦的背后都是土地殖民和話語壟斷,河谷內各個社會群體相互隔絕、漠視、侵占。如此,各社會等級之間的矛盾焦點不僅是“羊吃人”式的生產資料所有權,更表現為通過經濟力量、政治手段和知識體系搭建的社會空間,因此不可能成為真正的理想社會[16]。
4 結束語
勒·克萊齊奧多次強調《烏拉尼亞》的現實性,利用對稱式風景敘事將一切打開給讀者自己看。在他的筆下,普通的地理環境、建筑風格、城市結構都具有自身特點和特殊內涵,在流動的畫面中利用明暗對比賦予景物以生命,引導人們從“烏托邦”自身反思其不足,說明烏托邦不僅是因為“過于理想”或者“人類社會的圍攻”而失敗。崩塌的根源深藏于烏托邦的內在矛盾——居民、生產生活和土地如何平衡?早在《理想國》中,柏拉圖就曾以“城邦之間的戰斗和正義”為題對此進行討論,并沒有得出“理想的”解決方案。而托馬斯·莫爾則是直接用占據新的殖民地來解決:“在鄰近無人的荒地上建立殖民地……烏托邦人通過所采取的步驟,使雙方都有維持生活的土地,而這種土地先前是被當地人認為荒蕪不毛的。對于不遵守烏托邦法律的當地人,烏托邦人就從為自己圈定的土地上將他們逐出。”勒·克萊齊奧說他“不相信烏托邦,相信未來”,就是在表達對這一內核的思考。
就《烏拉尼亞》而言,作者直言“這是一部沒有結局的小說”。“沒有人指導我們是否會實現一個完美的社會,達到長治久安、人類的一切愿望得到和諧的實踐這一目標。但是,這種理想并不荒謬。”其中包含“與都市空間相對立的外部自然”,是在文明的沖突中,以“揭露”和“見證”式的介入,“端正人的生存態度,發現人的生存智慧,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時不間斷的行動,這也是勒·克萊齊奧的主人公不停流浪、不懈追求的意義。因此,“烏拉尼亞”作為意象而存在,顛覆“自然原始”與“現代文明”的二元對立,將追求自由平等的美好理想從具體的烏托邦城邦、政治形態中解放出來。在閱讀這一圖景時,如果沒有深入辨明小說的現實意義,而用“遠離現代文明大地的自然原始”一言蔽之,或將坎波斯居民視為“高貴的野蠻人”的升級版,則很可能造成誤讀。“無論如何,這是一個永遠面向未來的創新過程,所有強加于它的圖示、概括、范式都是不同形式的對它的歪曲,不同形式的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