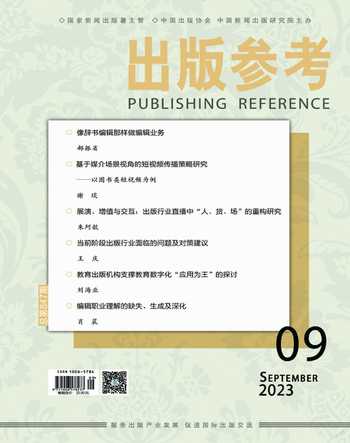展演、增值與交互:出版行業直播中“人、貨、場”的重構研究
朱珂歆
摘 要:在移動網絡日益融入日常生活、人們與紙質閱讀漸趨疏離的當下,圖書營銷順勢而為積極入局短視頻直播平臺,已經成為出版行業的一種共識。而在出版業的不斷摸索中,出版直播中“人、貨、場”三大核心要素的內涵與外延也在悄然發生變化。本文通過網絡田野調查對其進行了觀察與探究,總結出當下出版直播主播IP化、商品符號化以及場域動態化的發展趨向,并針對不足之處提出了相應建議。
關鍵詞:出版直播 人貨場理論 圖書直播 出版營銷
在移動技術與社交網絡的推動下,直播電商成為一種新的營銷方式,通過吸引用戶和實現流量變現從而達成理想的交易額,成為了各行各業電商直播所追逐的目標。隨著市場逐漸從商業主導轉向興趣引導,許多行業改變了自身的“玩法”,以短視頻、直播為載體,透過優質、有趣的內容傳播,進而引發興趣和購買,用有深度的內容沉淀用戶的消費行為。
當下,利用短視頻、網絡直播平臺開展圖書營銷活動已然成為出版行業的“標配”,而作為以內容為核心優勢的行業,其直播中的“人、貨、場”三大構成要素在內容電商的大趨勢下也發生了嬗變,突破了傳統商業直播模式的桎梏。起初出版行業隨著直播電商的火爆逐步入局圖書帶貨,由專業的網紅主播或知名作家來對書籍進行講解和銷售,然而低價銷售、網紅提成使得直播利潤一再壓縮。但是,東方甄選在2022年卻依靠差異化的內容營銷在其直播間帶火了一部又一部圖書,“賣空”“緊急加印”成為直播間的常態,這無疑為出版行業帶來了新的思考。
由此,本文旨在通過對短視頻平臺中的出版行業直播間進行網絡田野觀察,以歸納、總結當下出版直播營銷中的“人、貨、場”較以往傳統直播帶貨具體發生了哪些變化,分析這些變化將會如何賦能出版行業,并針對其目前的困境和存在的不足提出建議與優化進路。
一、“人、貨、場”理論與出版直播
“人、貨、場”是2017年由阿里巴巴CEO張勇所提出的概念,這里的“人”指的是重構用戶認知,“貨”是指重拾產品創新,“場”則是指持續動態經營。[1]當下,傳統零售中的“人貨場”理論在出版行業直播日漸火熱的大環境下演化出了新意義:從銷售方面對圖書消費者轉向主播吸引用戶流量;從簡單的展示圖書向全方位講解轉變;從線下零售向線上銷售轉變。而針對“人、貨、場”這三個不同維度,學界也對出版行業的直播營銷進行了相關研究。
首先在“人論”層面,出版行業直播涉及的主體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在前臺展演中占據核心地位的圖書主播,在直播電商的特定環境中,“人論”已不再局限于對消費者的研究,而是延展到了能夠吸引用戶注意力的主播身上。例如學者崔青峰和艾娟基于準社會交往理論,探討了圖書主播構建自身媒介形象的策略,他們認為圖書主播的孵化與培育是出版機構運營私域流量、優化圖書直播營銷的關鍵,主播應以受眾需求為基準,從內容、個性和價值三個維度去優化自身的形象建構。[2]另一類主體則是觀看直播和購買圖書的用戶,現有研究大都以模型或相關理論對用戶在直播間的消費行為進行了探析,學者隗靜秋和陳晶指出消費需求轉型升級之際,出版直播營銷正逐漸邁入堅守“以人為本”價值導向、契合用戶心理情感消費需求的全新階段。[3]
其次在“貨論”層面,相關研究聚焦于直播的產品——圖書展開了不同層面的討論,從圖書的選品到銷售策略,并隨著研究的深入逐漸延伸到如何提升圖書的附加價值、如何創新圖書的講解話術和展示方式。由此可見,出版直播中“貨”的核心開始從物質層面偏向了價值和意義層面。
最后在“場論”層面,有研究基于場景理論和互動儀式鏈理論對直播中主體間的互動實踐進行了解讀:學者王海玉認為圖書直播間構建的新場景重構了導購員與消費者間的信息交互行為,在虛擬現實技術的加持下,現實社交場景被還原,呈現出親切而真實的“社會臨場感”;[4]而陳俊和江玉則指出,人們基于共同關注的焦點聚集在虛擬的場(直播間)內,對“場外人”(直播間以外的人)設限,能夠形成共享情感體驗。[5]因此,“親切”“信任”“情感”逐漸成為出版直播場域內必要的構成要素。
二、出版直播中“人、貨、場”的重構
為了更好地了解當下出版行業直播間中“人、貨、場”的具體設置,本研究采用了網絡田野調查的方式,選擇直播平臺中處于頭部的抖音,在圖書直播榜中選擇銷量、評分較高的8個賬號(其中包括與出版機構合作的圖書KOL賬號和出版社自營賬號),并對其直播進行觀看、記錄與分析。自2023年2月10日至2023年3月19日,筆者在下列出版直播間中進行了38天的線上觀察,對其直播間背景板、前景道具以及畫面清晰度進行了解,隨后考察了主播講解的話術與風格、產品的價格設置、選品思路與營銷重點、直播間互動頻率與整體氛圍等(見表1),此外筆者還通過申請加入粉絲群等方式對出版直播的私域維護進行了考察。
(一)“人”的重構:主播展演與受眾追隨
出版行業入局直播電商是在“書業寒冬”和“直播爆火”的背景推動下而做出的被動選擇,起初出版社大多與平臺的頭部KOL進行合作,利用KOL的成熟帶貨模式和巨大流量解決銷量難題,因此以往出版直播中的“人論”幾乎圍繞著平臺KOL和受眾展開。而當下,出版行業直播不再執著于通過“網紅流量”“低價吆喝”尋求與受眾需求的契合點,而是將“聚光燈”轉移到了專業圖書主播身上,基于行業屬性打造對受眾構成吸引力的媒介形象,從而刺激和帶動直播觀看和消費活動。此外,出版行業的幕后人員等也紛紛以圖書主播的媒介形象出現,從“幕后”走向“臺前”進行展演,并對出版直播中的“人論”進行了重構。
在一個多月的網絡田野調查中,本研究將當下出版行業直播中的主播媒介形象建構大致分為以下兩類:第一類從話語內容和知識儲備著手,該類圖書主播大多呈現出學識豐厚、思維開闊以及溫暖治愈的媒介形象,將圖書的精華最大程度呈現在受眾面前,并通過圖書這一媒介將自己豐富的精神世界和人生感悟傳遞給觀眾,與屏幕前的讀者形成了“想象中的共同體”[6],讓其感受到了閱讀與知識的魅力所在,最終促成圖書消費;此外,主播的知識儲備不止于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文本信息積累,還涵蓋了特定閱讀圈層中的“黑話”與“術語”,在青春文學、言情小說以及二次元漫畫等小眾圖書直播中,當直播間的觀眾通過夾雜著“黑話”的彈幕評論表達自身訴求時,主播能夠憑借自身的知識儲備——與受眾共通的意義空間對其評論進行“解碼”,并迅速作出反應。例如在磨鐵圖書旗下的“鐵鐵的書架”直播間中,面對評論區與言情小說情節內容相關的問題,主播鐵鐵能迅速理解這些話語的含義,并且根據粉絲的問題進行劇情解說和小說推薦,因此在讀者心目中成功構建起親切、知心的姐姐形象,獲得了大批讀者的追捧。第二種類型則注重主播氣質與身份的建構,使之與出版社或者產品特色相匹配,例如在以漫畫與動漫作品為主的浙江文藝出版社直播中,主播以經典動漫EVA(新世紀福音戰士)中角色“明日香”的裝扮出現進行產品講解,一方面能夠將出版社品牌特色進行具象化呈現,與其他圖書直播進行區隔,另一方面則承載了漫畫愛好者對角色展開的愛欲想象[7],從而與讀者達成了心理契約。[8]
直播電商的日益普及和營銷手段的豐富使得消費者的購買決策越來越受到不確定因素的影響,然而新媒介技術的加持使得主播更多的性格特點、身份特征等社會線索嵌入直播電商之中。主播在用戶心中從隱匿的他者轉變為具有社會臨場感的在場者,這為更緊密的準社會交往提供了可能。[9]通過前文所述的兩種主播媒介形象建構與前臺展演,受眾都會在不同程度上對圖書主播產生情感聯系與信任。基于這種信任,消費者會認為主播所推薦的圖書對自己不會構成經濟上的損失,且能達到預期效果,因此推動了對主播的追隨和消費行為的產生。
(二)“貨”的重構:意義增值與內容細分
在傳統直播營銷中,“物美”與“價廉”是構成“貨”的兩個必要要素,商品的質量與價格直接決定了消費者的購買行為,因此有大量的圖書直播間在公屏上打出“清倉處理,打折優惠”等字眼,以此來刺激消費者購買。這一形式雖然在短時間內能迅速拉高圖書銷量,但長遠來看卻壓縮了出版行業的利潤空間,此外該形式還忽略了出版行業中“貨”的本質屬性——滿足受眾精神需求的文化產品。在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中,基于自我實現目的的精神需求居于最高層次,不同于只需要物美價廉就能滿足的底層物質需求,精神需求的滿足需要用更深刻、更有意義的內容來觸達受眾的內心世界,并構建起情感上的聯系。[10]
由此,當下出版直播電商中“貨”的內涵不再局限于圖書本身,而是轉向了多元維度的價值、意義延伸。鮑德里亞認為在居民消費社會發展中,人類消費的對象不止于物質自身,還有物質之上所附帶的符號價值,人類消費行為的目的也從實現根本需求轉化為符號價值的實現。[11]在本研究所考察的直播間中,主播在介紹產品時除了圖書內容,還側重于展示圖書的裝幀設計、包裝、獨家贈品周邊以及作者的限量簽名印章等,這些圖書衍生品在設計時將圖書中的意涵與主題提取出來進行具象化處理,與圖書主題、故事情節巧妙呼應,有利于迎合大眾在消費社會中的符號消費需求。直播間場域中所兜售的“貨”,除了具有可視性的實體書籍與衍生品,還囊括了基于圖書內容而創造的“意義價值”與“服務”。在東方甄選的圖書直播中,主播對書中的信息內容進行了發散化、個性化制碼,由某個段落或情節延展到相關詩詞歌賦、自身經歷與人生感悟,并將這種詩意與情懷作為商品售賣給觀眾;此外,主播還會兜售定制化的“服務”,根據受眾需求為其推薦適合的圖書。這些情懷與服務相較于實質性的產品更能夠觸達讀者的精神層面,并且構建起對主播和其推薦圖書的信任。
而在“貨”的類型方面,出版直播逐漸從多元、雜糅的全域類型“大賣場”轉向矩陣化、細分化的垂類直播,相較于先前讓觀眾感到無從下手的龐雜選品范圍,越來越多的出版社開始將不同類型的圖書直播分配到不同賬號進行矩陣式運營,根據賬號特色進行個性化產品選擇。例如浙江文藝出版社就專注于二次元出版領域,主要推薦經典的漫畫作品,而二十一世紀出版社基于自身近40年的高品質兒童圖書出版發行經驗,打造了官方自營的專業童書直播間。在細分化、差異化的出版直播中,受眾可在短時間內迅速找到所需“貨架”并進行挑選,同時差異化的定位也有利于出版機構在受眾心中留存深刻印象,從而驅動品牌持續發展。
(三)“場”的重構:書香氛圍與情感交互
在出版直播中,直播平臺形成了一個交互網絡,即布迪厄提出的“場域”,此時的“人”與“貨”等共存于該場域之中,在動態演進的場域之中發生交互與共振,場域的狀態也會隨著“人”與“貨”的卷入程度呈現不同的結果。[12]在該場域中,利益是聯系彼此的紐帶,出版方、主播、讀者、圖書等需要共同發揮作用,而作為“局外人”的非直播參與者則很難融入。
在以往的圖書直播中,圖書往往成為場域中的架構核心,整個空間由各式書籍堆砌而成,主播通常只是機械地重復產品的簡介與價格,幾乎沒有對圖書相關的深入問題的答復,在這樣的場域中觀眾無法產生社會臨場感來感知閱讀的吸引力,因此主播的講解成為單向度的傳播。從當下直播間的構造和布景來看,出版直播的空間場域開始融入與閱讀有關的元素,文化空間、營銷空間以及受眾空間交疊在同一場域內,實現“人”與“貨”的同時在“場”。例如與教輔圖書相呼應的黑板、輔之以暖黃色燈光的書房以及書架林立的圖書館等等,并且從線上虛擬背景不斷擴展至線下實體場地。參與者面對場域的動態性與未知性,不知道下一秒或下一次直播會是什么內容,這種機制也對場域氛圍的調動起到了正向作用。例如在《看見敦煌》的新書直播中,直播間場域就拓展到了作者謝水成先生的敦煌壁畫展館之中,雖然觀眾在直播中無法細致深入地品讀書中的文字與圖畫,但實景空間的視覺沖擊使觀眾仿佛置身展館場域之內,用身體感官去體會敦煌文化的魅力和書香氛圍。
而在互動層面,直播中的即時互動功能為場域中的他者賦權,使得原本占據主導的作者和出版方與觀眾處于平等地位。在直播過程中,直播間在彈幕功能的賦能下不再是“大賣場”,而是“聊天室”,對于讀者的提問與要求,主播與出版方能夠給以及時的反饋。在精心營造的沉浸式直播中,圖書館、書房、教室等具備閱讀屬性的功能化空間通過主播這一中間媒介,與屏幕前受眾所處的現實空間相聯結,讀者與圖書主播在你來我往的交互中建構共同記憶、激發共同情感,形成了更加緊密的群體認同,雙方同時共處的直播間成為儀式性場域。熱衷于閱讀的讀者和追隨主播的觀眾,將情感寄托在了這個虛實相交的場域之上,并且其場域卷入程度也隨著直播的推進逐步加深,情緒也沉浸在直播的意義空間之中。[13]
三、建議與進路
培養垂類人才,輸出專業內容。隨著出版直播中“貨”的細分化發展,圖書主播的媒介形象也趨于個性化,垂類人才能夠對自己所屬的圖書領域有更加深入、細致的理解,同時在直播中也能夠對“圈外人”設限,從而加強直播場域內部的群體認同與情感聯系。而出版機構自發培養垂類人才,一方面有助于搭建出版方與私域流量間的橋梁,另一方面也能將圖書主播的形象轉化為專屬IP,推動出版機構之間甚至是與其他品牌進行聯名、合作,賦能于出版機構的結構化轉型與可持續發展。出版機構可基于自身品牌特色,培養與其相契合的專業主播,并且注重塑造主播對特定圖書內容和圖書類型背后所蘊含的文化的理解,將講解話術、風格節奏與所屬領域的屬性進行融合。
優化定價策略,堅持內容為王。作為文化產物的圖書和其他商品有著很大的差異,這決定了叫賣兜售式的傳統直播電商會減損其文化屬性附帶的“光環”。盡管當下的出版直播已經逐漸發生了內容為主的營銷方式轉向,但在網絡田野調查的過程中,依然有直播間存在著圖書破價和內容深度缺失的現象。首先,圖書具有文化屬性,部分主播采用快節奏、多產品直播,很難讓受眾在爭分奪秒的短時間講解中領悟內容梗概和主題內涵;其次,圖書利潤整體較低,且定價以固定形態留存于書本封底,無法根據供求靈活調價,因此破價賣書無疑是對出版行業的“絞殺”;最后,除童書和教輔用書外,大部分的圖書不屬于剛需,且讀者看過一次后幾乎不會回購,傳統的“低價走量”并不適用于出版直播。出版業的使命是實現知識的傳播與傳承,因此圖書產品的宣傳重點在于對精神文化內涵的挖掘,需要主播的專業引導和深度交流。圖書直播應當堅持“內容為王”,只有優質內容才能持續不斷地吸引觀眾。同質化的模式和單一的內容,難以在出版業的文化土壤中生根發芽,當出版直播生態越來越多地被賦予文化內容和文化訴求時,背后的驅動將不再是商業化的喧囂,而是理性的回歸。
搭建私域流量,深化信任建構。在本研究的后期調查中,筆者申請加入了考察對象的官方粉絲群,但只有部分的申請通過了審核,其余并未得到回應,就可觀察的已經著手維護私域與經營社群的直播賬號來看,大多只是不定時地在粉絲群內發布直播鏈接和賬號視頻,由此可見出版行業直播的私域搭建與維護尚未完善。私域搭建一方面是基于對客戶售后權益的保障與維護,同時也為開拓新的產品渠道打開了通路,尤其是以兒童圖書、教輔用書等為主要產品的出版機構,其客戶群體多為學生家長和兒童家長,在后續推廣方面具有顯著的長線價值。出版機構應當在粉絲群中及時發布直播預告、粉絲福利等信息,并主動引導群內成員進行交流與互動,此外不定期舉辦線下活動也能夠進一步深化客戶對品牌的信任度。
四、結語
在不同的商業情境下,“人、貨、場”始終是營銷的核心,但將其置于出版行業特殊的文化屬性中“人、貨、場”的內涵及其三者關系發生了變化與演進。隨著出版機構的摸索,出版直播中“人、貨、場”的內涵與外延呈現出拓展與細化的趨勢,出版機構由外向內轉化,開始孵化自己的專業主播、打造自己的優勢產品以及構建自己的特色場域,三者形成了相互關聯又立體化融合的共生關系。無論營銷方式如何變化,出版行業都理應守住文化入心、內容為王的行業底線,鞏固自身高質量原創內容的優勢,在“人、貨、場”的共生關系中走向品牌化、專業化,讓出版物發揮自身的真正價值,賦能全民閱讀素質的提升與社會文化的高質量發展。
(作者單位系浙江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