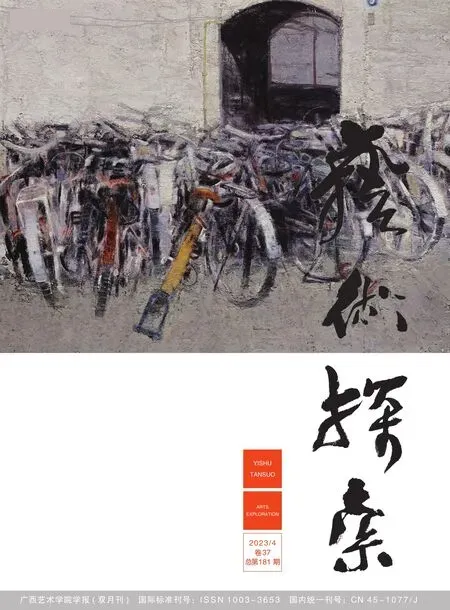瀛海遺珠:新加坡華人陳之初藏中國近現代書畫研究
劉康琳
(集美大學 美術與設計學院,福建 廈門 361021)
陳之初(1911—1983 年),原署兆藩,是20 世紀新加坡華人。他以經商起家,在遠離中國藝術創作中心的新加坡建立中國藝術收藏事業,于東南亞聲名遠揚。作為新加坡華人藏家,其收藏活動一定程度代表了南洋華人在特殊歷史時期的文化情結與審美傾向,也隱含著20 世紀中外美術交流的珍貴歷史片段,無論是對中國近現代美術史還是對文化史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價值。
陳之初出生于新加坡,4 至17 歲在家鄉廣東潮安接受教育,因而受中華傳統文化影響頗深。他自幼熱愛繪畫,在潮安小學會考時,國畫一科曾冠優全縣。①劉平衡《香雪莊主陳之初先生》,《雄獅美術》(臺灣)1982 年第12 期,第56-58 頁。青年時再次南渡,僑居星洲。初在林樹森店里任學徒,后自立門戶,經營南洋土產如咖啡、樹膠、胡椒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已資本雄厚。②陳家鵬《儒商陳之初傳略》,見潮安縣(今廣東省潮州市潮安區)政協文史委員會編《潮安文史》(第4 輯),1999 年,第91-92 頁。陳之初收藏起步于20 世紀30 年代末,堂號香雪莊,取“梅花清香”之意。③宋代張炎《疏影·梅影》一詞中有“做弄得、酒醒天寒,空對一庭香雪”,以“香雪”比喻梅之清香潔白。所藏包括書畫、陶瓷、端硯、印章、銅器、紫砂、竹刻、碑帖等,規模質量在20 世紀與百扇齋、虛白齋、袖海樓④百扇齋是黃曼士(1890—1963 年)藏齋,收藏約起步于20 世紀20 年代,因喜好收藏扇面而得名。主人黃曼士曾手寫過5 份《百扇齋藏畫目錄》。虛白齋是劉作籌(1911—1993 年)藏齋,收藏起步于20 世紀40 年代。其曾將所藏明清書畫借展上海博物館,日本二玄社為其出版有《虛白齋藏書畫選》。1989 年其將收藏悉數捐贈給香港藝術館。袖海樓是楊啟霖(1917—1998 年)藏齋,收藏起步于20 世紀50 年代。藏品由第二代藏家楊應群繼承。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新加坡國家美術館曾先后為袖海樓收藏舉辦展覽。齊名于星洲。收藏之余他亦研習書法⑤陳之初研習各體,曾自創“五色書”“彩墨書”。1979 年以香雪莊之名出版《陳之初書法》。1982 年3 月在新加坡國家博物院舉辦書法展覽后出版《陳之初書法》(二集)。同年11 月在中國臺灣歷史博物館展出其本人書法作品與香雪莊珍藏精品。現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中國臺灣華岡博物館均有陳之初書法作品收藏。。1976 年被新加坡中華美術研究會聘為名譽會長。⑥施香沱《會史》,見黃建斌等編《新加坡中華美術研究會四十五周年紀念刊》,新加坡中華美術研究會,1980 年,第4-7 頁。1982 年,作為新加坡中華書學研究會顧問,在新加坡國家博物院舉辦個人書法展覽。⑦新加坡中華書學協會編《新加坡中華書學協會二十年》,1988 年,第51 頁。新加坡中華書學研究會為今新加坡書法家協會前身。1968 年成立,名“新加坡中華書畫研究會”,1979 年改為“新加坡中華書學研究會”,1983年為“新加坡中華書學協會”,1996 年為“新加坡書法家協會”。1983 年去世。
在他40 余年的收藏歷程中,齊白石曾為其刻印。⑧1981 年陳之初香雪莊出版《香雪莊藏印》(非賣品),即有齊白石為其所刻“陳之初印”“香雪莊”等。現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亦收藏了這本印集。徐悲鴻多有贈畫,并與之保持通信。張大千、黃君璧到新加坡曾參觀其藏齋。劉海粟也曾表示:“陳之初先生精鑒賞,富收藏,囑畫當有以報命。”⑨劉海粟《劉海粟致劉抗函》(1980 年11 月20 日),見王欣、季曉蕙主編《劉海粟劉抗師友書信錄》(下),西泠印社出版社,2018 年,第249 頁。藏品質量獲得了多方認可,曾有《香雪莊書畫選輯》(1950 年)、《任伯年畫集》(1953 年)、《香雪莊藏砂壺》(1978 年)、《香雪莊藏印》(1981 年)等出版。⑩《香雪莊書畫選輯》為1950 年新加坡中國學會主辦陳之初先生珍藏古今書畫展覽會特刊,新加坡中國學會出版。《香雪莊藏砂壺》為饒宗頤編著,1978 年在新加坡出版。《任伯年畫集》《香雪莊藏印》均由陳之初香雪莊出版,為非賣品,后者收錄齊白石印章48 方。然陳之初去世后,香雪莊舊藏經過連續多年不斷釋出,已大量流散。?20 世紀80 年代開始,部分香雪莊舊藏流入美國紐約、中國香港等拍賣市場。2004 年前后,更有大量收藏回流到北京、上海、云南等拍賣現場。
2000 年起,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收到陳之初家屬的多次捐贈,總數累計130 余件。20 年來該館為這批藏品舉辦過4 次展覽,即陳之初書畫作品珍藏展(2002 年6 月19 日—2003 年9 月15 日)、香雪莊珍藏——陳之初捐贈書畫與陶瓷展(2003 年11 月18 日—2004 年4 月26 日)、香雪莊珍藏展——最新捐贈亞洲文明博物館(2006 年11 月15 日—2007 年3 月18 日)、水墨情——又逢香雪莊(2019 年11 月8 日—2020 年4 月26 日),陳之初收藏逐漸重回人們視野。實際上,除相關展覽圖錄出版外,新加坡華人藝術家劉抗、中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員劉平衡、日本學者西島慎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授衣若芬等已先后為陳之初香雪莊撰文,即劉抗《讀陳之初珍藏書畫歸來》(1950 年)、《東南亞名收藏家陳之初先生》(1977 年),劉平衡《香雪莊主陳之初先生》(1982 年),西島慎一《香雪莊主陳之初》(堀川英嗣、王亞峰譯,2018 年),衣若芬《陳之初香雪莊舊藏任伯年<八仙圖>的文圖學解讀》(2022 年)。但總體來說,學界對陳之初及其藝術收藏仍缺乏關注,對其收藏緣起、藏品規模及流轉情況等認識終不清晰,對其收藏動機與所反映的海外華人文化心理等分析不夠。基于此,本文聚焦于陳之初的書畫收藏,在考察其收藏面貌的基礎上,觀照南洋華人的特殊文化身份,以及其對中國文化的選擇與認同,進而揭示其藏品和收藏活動本身價值。
一、陳之初與徐悲鴻
徐悲鴻與星洲結緣極深。他曾一生7 次過星洲,4 次為途經,3 次作了或長或短的停留。?華天雪《一段確定與不確定的歷史——徐悲鴻在星馬》,見華天雪《徐悲鴻論稿》,山東畫報出版社,2014 年,第134 頁。1939 年初,徐悲鴻從中國香港出發,在新加坡、印度、馬來西亞等地游歷、避難三年,星洲一地即累計寓居17 個月之久。?1939—1941 年徐悲鴻動線:中國香港—新加坡(1939 年1 月9 日至11 月18 日)—印度(1939 年12 月6 日至1940 年12 月13 日)—新加坡(1940 年12 月13 日至1941 年1 月7 日)—馬來西亞(1941 年1 月7 日至6月下旬)—新加坡(1941 年6 月下旬至1941 年12 月)—緬甸(1941 年12 月太平洋戰爭爆發,經海路到緬甸)—中國重慶(1942 年夏經中國云南返重慶)。參見姚夢桐《徐悲鴻:從新加坡戰前(1939—1941)華文日報所刊載資料看其在海外的美術活動》,姚夢桐《新加坡戰前華人美術史論集》,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2 年,第98-108 頁。此時距離陳之初1927 年左右定居星島已逾10 年。在徐悲鴻到來前,諸多中國藝術家已陸續南來辦展。這使陳之初經商之余,獲得了不少中國名家真跡的觀摩機會,藝術鑒賞品位與收藏資本皆與日俱增。
據目前掌握資料,陳之初對中國書畫收藏的興趣可追溯到1939 年3 月徐悲鴻在新加坡舉辦籌賑展覽時期。為募集更多賑濟款,徐悲鴻在新加坡的展覽采用了出售籌賑畫券的形式,并為其“熱門”杰作——《九方皋》《廣西三杰》等印制畫片發售,得到了新加坡華人的踴躍認購。在1939 年3 月21 日《南洋商報》公布的一組認購名單中,即有陳之初的姓名。他購得徐悲鴻《田橫五百士》作品畫片,“一張叻幣五元”?《悲鴻大師籌賑畫展照片畫購者踴躍》,《南洋商報》1939 年3 月21 日。。二人緣分便從這一時期開始。
現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香雪莊舊藏中,屬徐悲鴻作品數量最多,質量上乘。9件書畫中,3 件有徐悲鴻為其上款。其中《柳鵲》一作題寫道:“之初先生雅教,廿八年中秋悲鴻寫。”可見3 月份展覽結束后,二人仍有來往。這批捐贈徐畫中,《雙馬圖》《受天百祿圖》2 幅為同類作品之佳作,陳之初鐘愛不已,曾并列書房左右(圖1)。另有精品收藏之《邊壽民書畫冊》顯示有徐悲鴻題跋。?現亞洲文明博物館香雪莊舊藏之《邊壽民書畫冊》,徐悲鴻題跋于1947 年。據跋文分析,應是徐悲鴻為當時書畫冊主人李時霖而題。最終該作轉入陳之初香雪莊,筆者推測應與徐悲鴻、黃曼士有關。以上可作二人交游之見證。
2004 年上海朵云軒春拍近現代書畫專場,上拍了一組徐悲鴻《任伯年評傳》手稿,附徐悲鴻致陳之初信札9 通。?這組拍品還包括徐悲鴻致蘇乾英信札1 通、廖靜文致陳之初信札7 通及相關信封5 幅。拍品經廖靜文鑒定為真跡。2004 年在上海朵云軒被成功拍下后,2008 年又出現在北京保利春拍“中國近現代書畫日場”,有相關拍賣圖錄出版。徐、陳二人交往的諸多細節,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塵封終展現于世人前。依書信內容判斷,其應寫于1950 至1951 年。通信期間,陳之初又至少獲得徐悲鴻畫作2 件。相關內容摘錄如下:
(1950 年10 月2 日)之初先生惠鑒……雅命作畫,現在太忙,精力亦不如前。先生又精賞鑒,不比尋常酬應。弟之作品十年前較勝今日。因從1943 起患病(血壓高),1946 做校長至今,進步既少而作畫時間又少,但較精之作因敝帚自珍關系,至今保存。貓、白鵝皆有佳幅,先生倘見愛,可以割去,照樣再畫不可能矣。向例一百美金一張,可合新加坡幣。古書畫在年關或新年可能有很多機會,最好先生存款于北京友人處,頗多麻煩。先生今日所藏已為大幸矣!?1950 年10 月2 日《徐悲鴻致陳之初函》,參見北京保利2008 年春拍“中國近現代書畫日場”圖錄。如無特別說明,本文所引《徐悲鴻致陳之初函》均出自該圖錄。
(1950 年12 月10 日)之初先生惠鑒,得手教,旋又得寄款港幣二千元。鵝尚在,雙貓則在上月為一外人購去,弟當另寫一幅以酬知己也(大約在一月以內)。
(1951 年1 月23 日)……群鵝一幅,另喜鵲梅花一幅(奉寄),皆托帶蘇乾英先生?蘇乾英(1909—1996 年),廣東潮州人。早年畢業于韓山師范專科學校,18 歲時曾往新加坡、印度尼西亞謀生,1929 年回國,就讀于上海國立暨南大學文學院歷史系,1933 年畢業后留校當助教,1944 年被聘為教授,主講亞洲史,從事文史有關方面的學術研究。見張玉春編《百年暨南人物志》,暨南大學出版社,2006 年,第315 頁。代轉(因超過一尺五寸不能寄且不得掛號)。又貓一幅,寒假內寫出送滬裱成,仍托蘇君轉奉。
(1951 年4 月23 日)……弟因忙尚未能將雅命之懶貓寫就,茲便中撿出舊日過滬與汪亞塵兄合作之小貓奉贈,候至五月內必為寫出,以贖吾延期之過。
(1951 年4 月29 日)……月前偶然試筆得奔馬一紙,尚不惡,□寄知己。?1951 年4 月23 日、1951 年4 月29 日《徐悲鴻致陳之初函》,內容由筆者根據信件圖片辨讀。
以上記錄充分說明,陳之初曾直接從徐悲鴻處購畫。因“雅命”難辭,陳之初又“精鑒賞”,徐悲鴻以港幣2000 元割愛“較精之作”,為陳之初轉去“群鵝”“喜鵲梅花”2 件。而“與汪亞塵兄合作之小貓”及“奔馬”2 件是否寄出,待進一步考證。從信中“古書畫在年關或新年可能有很多機會,最好先生存款于北京友人處”可以推測,陳之初可能也托徐悲鴻為其香雪莊搜尋古畫佳作。
徐悲鴻對陳之初最大的影響在于藝術審美的感染。徐悲鴻對任伯年推崇有加,曾表示:“近代畫之巨匠,固當推任伯年為第一”?徐悲鴻《論中國畫》,見王震編《徐悲鴻文集》,上海畫報出版社,2005 年,第95 頁。張安治在此文《后記》中曰:“此稿寫作時期應在1933 至1934 年”。。1939 年12月他在致星洲友人的一封信中還說道:“明年為任伯年入世百年祭,弟將在國際間為舉辦展覽與宣傳。”?徐悲鴻《致星洲友人》,見《星洲日報》1940 年1 月11 日。陳之初受其影響頗深,連年搜集任伯年作品。
1950 年左右,陳之初收藏之任畫已逾百件?據《任伯年畫集》(1953 年陳之初香雪莊出版)中《編后贅言》記載:“香雪莊主人陳之初,喜愛任伯年畫,連年搜求購買,得任畫逾百,經精賞鑒別,去蕪存華,集得真品百幀,影像付梓。”,有意將其付梓。徐悲鴻《任伯年評傳》(完成于1950 年冬)即特為此撰。他寫道:“今陳之初先生獨具真賞,力致伯年精品如許,且為刊印,發揚國光。吾故傾吾積蘊,廣為搜集附之,并博采史材,為之評傳。”?徐悲鴻《任伯年評傳》,見陳之初《任伯年畫集》,香雪莊,1953 年,第3 頁。最終《任伯年畫集》于1953 年出版(圖2),由陳之初自資刊印,徐悲鴻之評傳作為序文首次發表。

圖2 《任伯年畫集》封面、書名頁,1953 年,香雪莊出版
前文所述徐悲鴻致陳之初多通信札,其實主要是為聯系此集出版一事。從信札內容可知,徐悲鴻前后付出不少心力:
(1950 年12 月10 日)……伯年畫序文正在起草中,尚有伯年像乃弟二十年來尚未完工之作(像片借自伯年之子堇叔三十年前)將寫就,攝出奉寄。此文弟當精心寫之,為一中國近代第一畫家評傳。
(1951 年1 月12 日)之初先生,我現正寫任伯年評傳,匪止伯年畫集序。最近我尚得上海消息,伯年曾寫過一三友圖,己亦在內。現在設法求得一照片,恐須在寒假時,至少可得一伯年像臨本(吳仲熊君手臨,其繼祖母乃伯年之女雨華,尚有幾種照片亦須稍等時日,因為現在大家忙極)……伯年畫照片甚佳,所難得者是其山水。
(1951 年3 月9 日)……弟已寄上伯年評傳,來示未曾提及收函。念茲以弟藏伯年佳作攝出寄。另包奉滬上友好尚未寄來,因彼等不比吾人之熱心也。聞滬上可能遇有伯年佳作,但價皆在百萬以上為意。先看照片,然后定奪。
結合來信內容與畫集成稿,徐悲鴻不僅“為之評傳”,還多方聯系素材,特別完成了《任伯年畫像》,寄自藏“伯年佳作”之圖片(共11 幀?刊印于陳之初《任伯年畫集》的徐悲鴻收藏有11 幀,其中有8 幀來自同一花鳥冊。)供該集發表,為陳之初《任伯年畫集》出版給予了十分的支持。作為回應,陳之初請陳宗瑞協助編輯時,亦相當嚴謹認真。談及拍攝工作時,陳宗瑞表示:“翻印影像,為求清晰,幾倩名手”,“欲得顯具作品優點之照片,多經反復攝影”,?陳宗瑞《編后贅言》,見陳之初《任伯年畫集》,第9 頁。陳宗瑞(1910—1985 年),出生于廣東汕頭。1929年7 月畢業于汕頭私立友聯中學藝術科,1929 年9 月入學上海美專西畫科,因私曾兩度離開上海美專,其間在汕頭私立友聯中學執教,并與陳文希等人創辦春陽繪畫研究所。第二次回上海美專后不久,便離校轉學上海新華藝專。1931 年于新華藝專畢業后即赴南洋。1935 年與張汝器等人共同創立新加坡華人美術研究會,在南洋藝術學院任教20 多年。新加坡六大“先驅藝術家”之一,曾為楊啟霖藏品鑒賞顧問。側面反映出陳之初對任伯年收藏的珍視。
在二人交往中,徐悲鴻還時常對陳之初藝術收藏活動給予意見指導。在1951 年3 月11 日信(圖3)中,他寫道:
此函將發又得賜畫并照片六紙,欣知《伯年評傳》已收到,感慰之至。六畫中花鳥兩幅均是杰作,想先生近時收得允當稱賀。最近有友人自滬攜伯年大幅《五倫圖》及人物《天官》,均非精品,故未與收購。因既多矣,必須求精品,否則徒然自尋煩忙之,資不足取也。且大幅尤不便搬動,除非極精,不為羅致,報先生亦明意也。?1951 年3 月11 日《徐悲鴻致陳之初函》,內容由筆者根據信件圖片辨讀。1951 年3 月11 日《徐悲鴻致陳之初函》距離3 月9 日函只隔2 天。又根據文字內容“此函將發又得賜畫并照片六紙”可推斷,兩封不同落款日期的信為同一次寄送,因而3 月11 日信之開篇并未有“之初先生”之稱呼。
在這封信落筆前,徐悲鴻可能收到陳之初新入藏品的照片,請他過目鑒賞。“六畫中花鳥兩幅均是杰作”是其對陳“近時”收藏的肯定。“因既多矣,必須求精品”則是對“未與收購”?結合前文書信可知,陳之初曾托請徐悲鴻在中國為其搜尋古畫佳作。的解釋,也是他對香雪莊未來收藏的建議。類似囑咐在這批信中不止于此。??類似內容亦可見于1951 年4 月29 日《徐悲鴻致陳之初函》:“接得手書及任伯年畫影片□紙,狗幅甚好,若鴨幅、羊幅則不見精彩。以后如此等幅可以不收。因伯年終身賣畫,應酬之作當不下千萬幅,如不精選,將收購不盡,久則將厭倦。”因而,徐悲鴻可謂陳之初的收藏顧問,尤其對香雪莊任畫收藏給予了整體把關。
陳之初與徐悲鴻的交往,過去在相關研究中少有人關注,卻對陳之初收藏帶來了非凡的影響,也為中國藝術在新加坡的傳播帶來了實質性的推動。由相關文獻可見,徐悲鴻待陳之初并非一般買主,作品交易不是“一物一價”,性情所致的附帶贈畫也時有出現。他稱贊陳之初對藝術之“熱心”,肯定他的收藏品質,盡可能地給予支持。至于任畫收藏與出版工作,一方面許是徐悲鴻借陳之初財力,欲保存與善待大師精品,另一方面更是對陳之初為人的認可。最終造就了后來香雪莊任畫收藏之規模。
二、香雪莊書畫舊藏概況
陳之初香雪莊舊藏數量豐富,種類龐雜,無法窺其全貌。其中,書畫收藏數量始終在其他之上,這或許有書畫質輕之緣故,卻足見陳之初的審美旨趣。
談及香雪莊書畫,劉抗有言:“總數約1 400 余幀,其中三分之一是書法”,“任伯年計100 余幅,齊白石70 次之,徐悲鴻50 余又次之,溥濡、王一亭各50……吳昌碩、黃賓虹各10 余件,其他作家三五幀不等”?劉抗《東南亞名收藏家陳之初先生》,見《藝術家》(臺灣)1977 年總第23 期,第46-47 頁。,西島慎一則稱:“任伯年的畫達二百五十幅……吳昌碩書畫就有三十幅,齊白石五十幅”?西島慎一《香雪莊主陳之初》,堀川英嗣、王亞峰譯,見《書法》2018 年第12 期,第86-87 頁。,可想其規模體系之大。但二者描述存在明顯偏差,因此,擁有確切藏品名目的文獻著錄和捐贈信息就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1950 年在新加坡中國學會主持下,“陳之初先生珍藏古今書畫展覽會”義展開幕?該展覽為捐助馬來亞大學發展基金、新加坡防癆協會及同濟醫院而設。,作為展覽特刊的《香雪莊書畫選輯》出版,收錄其所藏宋元明清及近現代書畫共147 件。1953 年,《任伯年畫集》由香雪莊出版,收錄了時香雪莊百余件任畫收藏中的85 幀精心之作,合64 件(套)。?《任伯年畫集》共收錄任畫圖版100 幀,其中15 幀來自徐悲鴻、陳楷、黃曼士、陳景昭等的收藏,陳之初舊藏只85 幀。這85 幀,含1 套《八仙圖》四條屏,1 件花鳥冊頁(16 頁),1 件《江南風味》冊頁(4 頁),因此該集中陳之初收藏實際應為64 件(套)。此外,中國臺灣地區部分期刊如《藝術家》《雄獅美術》,早年也多次介紹和刊登了香雪莊收藏,為還原其舊藏面貌提供了重要線索。(表1?該表由筆者根據對應文獻整理編制。選擇標準為:確切著錄相關藏品的作者和具體名稱。若文獻只提及收藏數量,沒有摘錄具體作品名稱,則不在該表統計范圍。數量以實際件數為準,冊頁視為1 件。)

表1 陳之初香雪莊書畫舊藏的文獻著錄情況
根據表1 所列文獻,香雪莊書畫總體著錄數量已達到387 件,其中任伯年、徐悲鴻藏品著錄率最高。又有蘇漢臣《戲棗圖》,周臣《江廬遠眺》,陳洪綬《采蓮圖》,任伯年《八仙圖》《白石遺韻》《三羊圖》,倪墨畊《柳蔭系馬》,徐悲鴻《群鵝》《雙馬》《懶貓》,等等,均多次出現在不同的畫冊或文章中,屬香雪莊收藏精品。
1972 年起,陳之初及其家屬又陸續將香雪莊珍藏捐贈給新加坡與中國臺灣地區的文博機構。如今我們也能通過這些博物館認識香雪莊舊藏書畫。據不完全統計,這部分藏品共116 件。(表2?該表由筆者結合采訪,并依據新加坡南洋大學李光前文物館編印《文物匯刊》(創刊號,1972 年)、亞洲文明博物館編《陳之初香雪莊珍藏》(2006 年),以及新加坡國立大學博物館官網、新加坡國家文物局國家藏品數據庫、中國臺灣華岡博物館《數位典藏聯合目錄索引》等多方資料匯集整理而成。)

表2 香雪莊書畫舊藏捐贈信息表
新加坡國立大學博物館與中國臺灣華岡博物館的相關藏品雖為陳之初生前所贈,但受贈數量最多、品級最精的是目前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的相關收藏。這部分書畫藏品共52 件,是陳之初極其珍視之作,包括邊壽民的蘆雁,改琦的仕女,任伯年的人物、花鳥,徐悲鴻的馬,齊白石的蝦,黃賓虹、溥濡的山水,以及沈尹默所書“香雪莊”齋號,等等,皆為各藝術家最擅長之題材,或與香雪莊關系最緊密,十分具有典藏意義。
總之,結合文獻著錄與捐贈信息,經去重后統計,香雪莊書畫收藏至少還有430 件可以確定名目,包羅五代宋元以來180 位藝術家的作品,如董源、劉松年、盛懋、文征明、徐渭、惲壽平、鄭板橋、吳昌碩、高劍父、齊白石等。“有以筆法線條為主者,有以水墨變幻是尚者,或重形態,或講韻律,郁郁蔥蔥,不勝枚舉。”?劉抗《東南亞名收藏家陳之初先生》,第47-48 頁。其中宋院體畫家、元四家、清六家、四僧、揚州八怪及京派、海派、嶺南派等宗匠均匯集在內,規模體系趨于完備。通過文獻著錄獲取其藏品信息,終究是管中窺豹,但這一收藏數據已十分可觀。
三、對近現代海派之青睞
陳之初書畫收藏中,雖有不少明清古書畫,也不乏佳作精品,但其收藏重點及經典還在于近現代。目前所見,近現代藏品有274 件,占比最大(圖4?該圖由筆者以文獻著錄和捐贈信息為依據繪制而成。)。所有書畫收藏,以任伯年為最大宗,共108 件。其后依次是徐悲鴻、吳昌碩、齊白石等,藏5 件以上的藝術家共10 位,仍集中于近現代(表3?該表由筆者以表1 文獻著錄和表2 捐贈信息的相關數據為基礎匯編而成。)。這一收藏選擇,與新加坡人文收藏環境密切相關?新加坡社會中國藝術收藏起步較晚,約始于19 世紀末20 世紀初,又地處海外,古書畫缺乏有序的傳承,收藏條件有限,鑒定人才不足。適逢“當代藝術家”來往頻繁,為規避書畫贗品風險,“現當代”作品成為當時新加坡藏家的主要收藏方向。,但始終離不開陳之初個人審美意趣的影響。

表3 陳之初書畫收藏的藝術家分布

圖4 陳之初書畫收藏的年代劃分(以文獻著述和捐贈信息為依據)
近現代美術中,陳之初尤其青睞海派一脈,這一點在表3 中已有所顯現。除任伯年、吳昌碩、王一亭、謝公展外,香雪莊也有任熊、任薰、趙之謙、虛谷、吳湖帆等作品收入。甚至受任伯年影響的徐悲鴻人物畫,受吳昌碩影響的齊白石花鳥畫,受改琦、費丹旭影響的張大千仕女畫,均被囊括,其趣味偏好可見一斑。
海派書畫在中國近現代美術史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藝術家陣容浩大、風格紛雜,有“海派無派”之勢,但色彩華美、富于裝飾趣味的形式特點,尤受陳之初鐘愛。香雪莊藏品中,任伯年《花卉翎毛冊》(圖版著錄于《雄獅美術》1982 年第12 期《任伯年徐悲鴻精品展特輯》、吳昌碩《杏花春雨江南》(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藏)、王一亭《鸚鳥凌霄圖》(中國臺灣華岡博物館藏)、潘天壽《荷花》(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藏)等,乃至齊白石《花草神仙》《紫藤》《紅荷青蛙》(三作均藏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皆明顯反映了這種喜好。
從創作題材來看,香雪莊藏品大體以花鳥居多,其中包括了許多具有美好寓意的作品,也有不少清雅高潔的四君子圖。如:任伯年《桃花鴛鴦白頭》(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藏)象征有情人幸福美滿,《三羊圖》(圖版著錄于《任伯年畫集》,香雪莊出版,1953 年)寓意三陽開泰、吉祥亨通;吳昌碩《富貴圖》、《多子圖》(圖5)(兩作均藏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畫牡丹、石榴,寓意富貴如意、多子多福;諸聞韻、諸樂三、俞寄凡等合作之《五瑞圖》(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藏),畫端午時節菖蒲、艾葉、枇杷等,意在祈福避邪。相關藏品中亦可見謝公展《菊花》(中國臺灣華岡博物館藏)、潘天壽《蘭竹圖》(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藏)、吳湖帆《竹石》(圖版著錄于《香雪莊書畫選輯》,新加坡中國學會出版,1950 年)等,詠君子堅韌、淡泊之品格。可見,面對新興市民階層的崛起,海派藝術家在雅俗之間的搖擺與抉擇,于陳之初藏品中得到了充分的顯示。

圖5 吳昌碩《多子圖》,1889 年,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藏(香雪莊舊藏捐贈)
就單個藝術家而言,陳之初對任伯年作品的偏愛已于前文有所論述。這部分收藏中,《八仙圖》四條屏(圖6)?本文圖片出處:圖1、圖5、圖6,新加坡國家文物局官網;圖2,https://book.kongfz.com/199067/1899746297;圖3,北京保利2008 年春拍“中國近現代書畫日場”圖錄。可謂重中之重,在陳之初《任伯年畫集》編排中也居于首位。該作人物造型夸張,筆墨簡逸放縱,繼承發展了陳老蓮之法,又極富視覺張力。八仙各自有態,超然而獨立,是任畫中難得的成套人物畫。徐悲鴻曾表示:“計吾所知伯年杰作,首推吳仲熊藏之五尺四幅《八仙》中之韓湘、曹國舅幅……有同之初藏之《何仙姑》。”?徐悲鴻《任伯年評傳》,見陳之初《任伯年畫集》,第4 頁。陳之初長子陳玉燦也曾回憶,這套《八仙圖》“被先父視為珍寶”,在日本占領新加坡時期(1942—1945 年),“他把這套畫作埋在外公的橡膠園里,以防畫作遭到損壞”。?陳姍、袁惠蓮《陳之初香雪莊珍藏》,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2006 年,第7 頁。
《任伯年評傳》中,徐悲鴻有言:“能畫人像,方見工力”,強調了人物畫之難度和重要性。受其影響,陳之初搜集了不少任伯年人物畫精品。除《八仙圖》外,《鐘馗捉鬼》(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藏)、《射雉圖》、《白石遺韻》、《東坡操琴》、《羅漢人物冊》(四作圖版著錄于《雄獅美術》1982 年第12 期《任伯年徐悲鴻精品展特輯》)等,都十分精妙,突出呈現了任伯年人物畫筆法的爐火純青,或怪誕扭曲,或圓潤自在。并且,他由市井人物素材提取而來的寫生痕跡在這些藏品中已依稀可見。
除了大量以任伯年為代表的海派收藏,陳之初香雪莊還以徐悲鴻收藏而聞名。由于二人交往密切,這部分藏品大多質量精良、流傳有序,以人物畫、動物畫為多見。人物畫包括《晨汲》《觀音大士像》《鐘馗》(三作圖版著錄于《雄獅美術》1982 年第12 期《任伯年徐悲鴻精品展特輯》)等。《晨汲》以寫實主義技法入畫,描繪了婦人們井口取水、攀談的農村生活景象,人物立體,明暗對比分明。對比任伯年的人物畫創作,徐悲鴻明顯加重了對現實人物的觀看,并提供了一套現代人物畫新樣式。動物題材中,《雙馬》(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藏)神氣雄渾,《懶貓》《雙豬》(兩作圖版著錄于《雄獅美術》1982 年第12 期《任伯年徐悲鴻精品展特輯》)、《獅子與蛇》(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藏)皆動態天然,神色如真。
也許出于對中國近現代書畫收藏體系的整體性觀照,以及與個別藝術家的密切來往,陳之初也收藏了一批京派、嶺南派作品,其中以齊白石、溥濡與趙少昂作品最具代表,但總體數量遠不及海派。究其緣由,海派繪畫設色絢麗明艷,對雅俗共賞題材的描寫,對市井生活中通俗形象的關注,確實深得其心。而另一方面,海派藝術家為快速適應和滿足藝術市場需求,往往創作高產,隨著相關作品“市場份額”的逐漸提升,無形之間在供求關系中形成了一種市場導向。
總體來看,陳之初書畫收藏選擇與審美趣味更傾向于傳統,因此任伯年、吳昌碩等早期海派作品及齊白石等堅持傳統趣味的作品較多,而以西潤中、中西融合的革新派作品,則受其藝術交游影響頗深,僅個別藝術家作品較多。徐悲鴻、趙少昂作品的收藏即印證了這一點。香雪莊書畫收藏的特色面貌是主客觀條件共同作用的結果。從傳統到現代,從精英到大眾,從高雅到世俗,從本土到融合,陳之初建立的系列收藏尤其體現了中國近現代美術的重要轉型,可謂是百年書畫發展的歷史縮影。面臨西方文化的強烈沖擊,近現代中國藝術家對本民族藝術何去何從的艱難思考在陳之初收藏中能找到大量回應,這使其兼具藝術與學術價值,文化意義不言而喻。
四、收藏途徑與來源考
陳之初香雪莊收藏的這些書畫,有許多直接從藝術家處獲取。以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館藏為例,黃賓虹《山水》(1950 年),趙少昂《風荷》(1949 年)、《花鳥》(1951 年),潘天壽《荷花》(1964 年),等等,均有如“之初先生屬”“之初吾兄有道高論”之類落款。另趙少昂《松鳥》,有題跋道:
一九五四年余漫游英倫、法國、瑞士、意大利、荷蘭各地,故舉行畫展,備受歡迎。此作在巴黎畫展時,當眾揮毫,掌聲雷動。一九五四年三月返港選出,星洲檢贈之初先生為大廈落成志慶。少昂于星洲。?陳姍、袁惠蓮《陳之初香雪莊珍藏》,第121 頁。
跋文不僅清晰說明了該作創作、流轉及海外交流的歷史,也印證了陳之初收藏的來源途徑。通過這一方式獲取的藏品,無論是藝術家交誼性贈畫,還是藏家出資購買,基本來源可靠,這是香雪莊收藏的特色。
香雪莊另有一個特殊收藏途徑,即通過展覽購藏。由于南洋華人聚集,華商眾多,20 世紀30 年代前后,諸多中國藝術家赴南洋新加坡等地舉辦展覽,為宣揚文化、救濟難民、支援抗戰而售畫籌款。他們包括何香凝、高劍父、張善孖、王濟遠、徐悲鴻、劉海粟等?20 世紀30 年代前后赴新加坡展覽的藝術家主要包括李仲乾(1927 年1 月)、何香凝(1929 年11 月)、高劍父(1930年12 月)、張善孖(1935 年3 月)、王濟遠(1938 年4 月)、胡呈祥(1938 年8 月)、沈儀彬(1939 年1 月)、徐悲鴻(1939 年3 月)、翁占秋(1939 年6 月)、王靄多(1940 年9 月)、劉海粟(1941 年2 月)等。1937 年后,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成為大部分展覽籌賑的直接原因。,至少16 位。許多展品經此售出,直接豐富了南洋地區的中國美術收藏。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展覽除展示藝術家自身作品外,也展示其他古今作品,何香凝展覽即附展有于右任、蔡元培、譚延闿等人的書法?姚夢桐《何香凝在新加坡》,姚夢桐《新加坡戰前華人美術史論集》,第16 頁。,王靄多展覽有汪聲遠、張劍云等人作品,劉海粟展覽有徐渭、石濤、吳歷、沈銓、康有為、陳師曾、吳湖帆等人的作品?參見《巴城(今雅加達)現代中國名畫展覽籌賑大會特刊》(即劉海粟在印度尼西亞雅加達舉辦的籌賑展特刊)之《參放品目錄》。這部分展品原則上為非賣品,在印度尼西亞雅加達展覽后也在新加坡展出。然而,曾有新加坡藏家劉作籌收購其中非賣品的記錄。詳見杜南發《虛白齋中日月長——記明清古畫大藏家劉作籌先生》,《隔岸看山——書畫名家訪談錄》,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 年,第124 頁。。如此種種,為更多藝術家的作品流入新加坡提供了可能。
新加坡藝術市場體系尚未健全之時,此類籌賑、籌款性質的展覽作為特殊歷史時期的藝術交易場,具有當代藝博會的意味。據調查,該時期中國藝術家到南洋舉辦的展覽,無論數量、密度,還是地理覆蓋面、藝術家影響力等,都處于較高水平。當時新加坡的中國藝術收藏氛圍較為濃厚,陳之初亦通過這一渠道進行購藏。
得益于廣泛的文化交游,陳之初也從其他藏家處獲得藏品。他常舉辦雅集宴會,與藝術同好交流心得。就目前所見,香雪莊舊藏中至少有兩件作品,極有可能是陳之初經由藏家黃曼士收集而來。一件是徐悲鴻國畫《人物》(1926 年,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藏[香雪莊舊藏捐贈]),具“曼士珍藏”印款;另一件是《邊壽民書畫冊》(年代不詳,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藏[香雪莊舊藏捐贈]),有黃曼士、徐悲鴻等人題跋。后者于1948 年從中國流轉到新加坡,與李時霖?李時霖(1893—1980 年),字海霞,曾任中國駐外官員,與徐悲鴻為干親。1941 年春,李時霖、徐悲鴻及黃曼士夫婦曾同游馬來西亞金馬侖高原。有關。此類作品通過藏家之間轉贈或轉賣收集而來,是為陳之初又一收藏途徑。實際上,由于城市國家精小,新加坡中國藝術藏家大多彼此交好,藏品轉讓現象在當時新加坡收藏界十分普遍。后來袖海樓第二代藏家、楊啟霖之子楊應群也曾證實:“當時本地藏家像陳之初、劉作籌、郭木松等,彼此之間都會互相轉讓。”?杜南發《楊啟霖與楊應群的“袖海樓”故事》,見杜南發《隔岸看山——書畫名家訪談錄》,第231 頁。
此外,20 世紀六七十年代,通過中國外貿出口直接購藏,也成為陳之初的一個重要收藏來源。直到20 世紀70 年代以后,新加坡藝術品一、二級市場才逐漸完善。許多南洋藏家也開始通過畫廊、拍賣會購藏,其中即包括陳之初。中華書局新加坡分局在這一時期正式成立的中華畫廊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總之,中國抗日戰爭爆發使藝術家積極南來辦展,新加坡文人雅集與收藏熱潮的形成,20 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國外貿出口等,都促進了香雪莊古今書畫收藏面貌的形成。但是,無論通過哪種收藏途徑,客觀的歷史機緣都是陳之初收藏活動的外部條件,主導其收藏行為的內因,歸根結底來自他對中國藝術的熱愛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
五、藏品的社會影響及華人文化心理
陳之初香雪莊門口有一塊大石刻著“雅好筆墨,只自精賞”。“雅好筆墨”如前文所述,“只自精賞”卻不止于此。在幾十年收藏歷程中,陳之初積極展示藏品,為中華文化宣傳盡“使者”之力。
陳之初舉辦的藏品展中,1950 年在新加坡舉辦的“陳之初先生珍藏古今書畫展覽會”,及1982 年在中國臺灣歷史博物館舉辦的“任伯年徐悲鴻精品展”,最具影響力。前者陣容嚴整,質優量大,被劉抗稱為“南洋有史以來的空前偉觀”;后者一定程度填補了該時期中國臺灣地區任、徐二人真跡展覽的相對空缺,甚至以新加坡為起點促進了相關藝術的二次傳播。
在《讀陳之初珍藏書畫歸來》一文中,劉抗意將其1950 年展覽與1935 年“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相比較,突出該展在海外宣揚中華文化的意義。他認為,當時還是“文化沙漠”的南洋,雖“已漸次地發現了些許綠洲”,“仍不能不以目前的荒蕪景象而感到內心的凄涼”。此“古今書畫展”便是“太陽的光輝和云雨的甘露”帶來的一個盛舉。他還補充道:“搜羅一件藝術品,不是有了金錢便可濟事,還需要高雅的旨趣和深厚的涵養,始稱完畢,而這幾點陳先生是都具備的。……假如號稱他為中國駐馬藝術大使,想來是不會不妥的”,表達了對陳之初學養和藝術收藏的贊許,也指出其為中國藝術文化在新加坡傳播所做出的巨大貢獻。?劉抗《讀陳之初珍藏書畫歸來》,見蕭佩儀編《劉抗文集新編》,新加坡國家美術館,2011 年,第48-50 頁。
香雪莊藏品除獨立辦展外,也為其他展覽提供贊助。如新加坡中華美術研究會1976 年舉辦的“揚州八怪書畫展”、1977 年的“明清名家書畫展”、1979 年的“吳昌碩王個簃書畫展”(聯合新加坡國家博物院舉辦),均有展品來自陳之初收藏。?根據新加坡中華美術研究會《會史》記載:1976 年的“揚州八怪書畫展”,有44 件原作來自陳之初和陳文希、盧明德等多位藏家;1977 年的“明清名家書畫展”,展出了任伯年、黃賓虹、吳昌碩、溥濡等名家畫作,部分藏品由陳之初提供;1979 年的“吳昌碩王個簃書畫展”,作品均向收藏家征集,陳之初與楊啟霖、李氏基金、南洋商報共同捐助《吳昌碩王個簃書畫集》印刷費。陳玉燦有言:“先父致力于在新加坡推廣中華藝術……他有感本地年輕一代過于西化,深覺有必要讓中華藝術在這片土地上延續下去。”陳玉燦《前言》,陳姍、袁惠蓮《陳之初香雪莊珍藏》,第7 頁。也因此,對于自資刊印的藏品集,陳之初都免費分贈各地美術院、圖書館、大專學院及愛好藝術人士,廣為宣揚。
事實上,見過陳之初的人曾表示“這位商業巨子的身上,有著深濃的書卷氣”何恭上《收藏家陳之初訪問記》,見《藝術家》(臺灣)1977 年總第23 期,第53 頁。。“之初先生日常生活嚴肅而富雅趣,除博覽群書,賞玩字畫外,每日仍繼續數十年不輟之臨池工作,古碑今帖,輪回更替,寫來渾厚質樸。”“他對太極、舞劍,也頗有心得,曾在私邸招宴朋輩時,獻過身手,博得友儕的贊賞。”他“養魚、栽蘭”,庭院布置也頗有講究,“從開暢明朗的現代化客廳里向外眺望,可見到不太遙遠的峰巒起伏處,淙琤懸泉,穿巖過潭,蜿蜒而下,景色幽然,好一幅石谷的山水畫!陳列書畫的藝苑外邊,那綠茵的盡頭,插竹數叢,襯以嶙峋怪石,有的賦板橋之意,有的傳石濤之神”。劉抗《東南亞名收藏家陳之初先生》,第50 頁。
陳之初有一個60 多平方米的陳列室,玻璃櫥窗擺著瓷器、印章和紫砂壺,墻上掛著書畫。他經常更換這些作品,只要是樂意接待之人,他都會依其興趣擺出藏品。何恭上《收藏家陳之初訪問記》,第53 頁。1982 年,中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員劉平衡、華岡博物館館長陳國寧在香雪莊“飽賞歷代名畫達四日夜之久”劉平衡《香雪莊主陳之初先生》,第57 頁。。陳之初還曾為當地美術研究會會員、學者、藝術家等提供游園、雅集及藏品觀摩學習的機會,使諸多需要研究中國藝術技法、流派,甚至是分析歷代繪畫材質的相關人士,在香雪莊獲得幫助。可以說,在新加坡成立正式美術館之前,陳之初藏品一定程度上為藝術愛好者和研究者彌補了這份缺憾,也使香雪莊在短暫歷史時期內成為新加坡私人美術館一般的存在。
陳之初對中華文化藝術的熱衷,與其在特殊時期的特定文化身份是分不開的。首先,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是其華人身份的自覺體現。他常著中式長衫,練太極,舞劍,“數十年不輟之臨池工作”,都是對這份認同的最好證明。其次,對中華藝術的追求是其華人身份的一種需求。受中國教育影響,中華文化為其提供了一定的情感寄托。20 世紀是中外文化碰撞與交融之期,西洋油畫、水彩畫亦受新加坡華人追捧。>在陳之初收藏起步的20 世紀30 年代末,新加坡中華藝術研究會舉辦的五屆年展(1936—1940 年)總體以油畫展示居多,1938 年成立的南洋美術專科學校當時也以西洋美術教學為主,并沒有開設中國畫系。甚至與其關系密切的徐悲鴻亦不乏油畫創作,與其大量書畫收藏形成鮮明反差。而香雪莊卻見大量書畫、瓷器、紫砂收藏,幾乎沒有西洋藝術蹤影。這一情況普遍出現在當時新加坡同期藏齋中,說明這些具有強烈中華文化屬性的藝術形式能很大程度滿足他們的文化訴求。再次,陳之初還兼具華商身份。自古以來,中國封建社會的儒家思想長期壓抑商賈階層,富商大賈都希望以文化品位來提升社會形象。這種思想長期根植于海內外華人社會,也是陳之初收藏活動的另一心理寫照。他的這一身份就不僅表現在為其收藏提供財力支持,還表現在為他帶來商人的文化觀。可見,中華文化認同和價值判斷是陳之初積極宣揚中華文化的原因,也是他在海外建立中國藝術收藏的內在驅動力。
20 世紀陳之初在新加坡建立起香雪莊中國藝術收藏事業,是其自身的文化追求與多重歷史機緣交織的結果。特殊的文化身份和質與量兼優的藏品,為其藝術收藏增添了諸多價值意義。陳之初書畫收藏規模龐大,體系完備,以近現代繪畫為最大宗,又偏好于海派一脈,整體體現了中國近現代美術發展的重要轉型。尤其是他與徐悲鴻二人的交往,對任伯年作品收藏帶來巨大影響。無論是藝術收藏還是主動的文化宣揚,陳之初的行為動機都真切體現了該時期南洋華人對中華文化的強烈認同。其收藏活動作為相關領域的經典案例,對中國近現代美術研究、中外文化的傳播與交流、海外華僑文化心理的解讀等都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