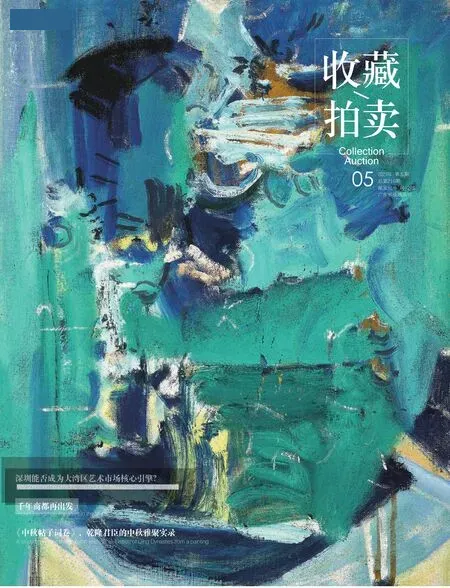照見古董珠寶的無形之美
文:柴曉 圖:李罡
大音希聲,大象無形。藝術(shù)殿堂中最稀有、彌足珍貴的,往往是那些看不見、摸不著,只能用心去感悟的部分。對于一件古董珠寶也是如此,無論它放在珠寶店還是博物館;無論是作為商品還是作為藏品,有一個重要的品鑒維度,可以超越其材質(zhì)、工藝之美,那就是珠寶如時光切片般對歷史人文的記錄,及其雋永且飽含的人類精神與情感的特質(zhì),這便是珠寶收藏價值的無形之美。

黃金祈禱書手鐲,19 世紀(jì)上葉手鐲設(shè)計精巧折疊后是一本書的造型,采用鏤雕、鏨刻等黃金工藝制作,書脊部分施以填色琺瑯并點綴鑲嵌野生珍珠。鏤空部分的字母是法語SOUVENIR,意為紀(jì)念、致意。

黃金琺瑯花卉手鐲,19 世紀(jì)70 年代法國珠寶師弗洛倫斯·穆里斯(FROMENTMEU RICE)作品。手鐲表面布滿精美的琺瑯彩圖案,花蕊交替鑲嵌藍(lán)寶石及珍珠,間隔部分裝飾鏤空渦卷造型,邊框上點綴紅寶石。
珠寶收藏的價值三原色
在參觀全球最知名的珠寶展廳——倫敦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珠寶廊時,筆者曾詢問展覽的策展人克萊爾最喜歡哪件展品,她繞過皇室珍寶和琳瑯滿目的各種寶石,把大家?guī)У揭幻娌荒敲挫拍康恼拱迩啊Kf這是自己經(jīng)常駐足的展區(qū),陳列著“從生到死的珠寶”,這里展示著先人們懷孕求安、狩獵祈福、婚戀示愛、逝者追思等各個生命重要時期所佩戴的寄托情感的珠寶。那一刻,我似乎突然領(lǐng)悟到什么,并由此得出一個古董珠寶收藏的“價值三原色”判定法,即一件珠寶作品的收藏價值,至少由其材質(zhì)、工藝設(shè)計、情感文化這三個維度綜合體現(xiàn)。
材質(zhì)維度最容易理解。各種寶石及貴金屬的稀缺性、穩(wěn)定性、美麗程度和人們的喜好程度,決定了珠寶的物質(zhì)價值。而珠寶設(shè)計師及工匠將各種材質(zhì)進(jìn)行創(chuàng)作構(gòu)思及加工組合的過程,反映了人類改變自然的一種能力,以及人類文明和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水平,這便是珠寶工藝與設(shè)計維度的價值體現(xiàn)。

古幣黃金胸針,19 世紀(jì)考古復(fù)興風(fēng)格作品。19 世紀(jì)70 年代,英國著名卡斯特拉尼(Castellani)金匠家族制作。邊框是其家族稱奇世界的金珠工藝,中間鑲嵌一枚約公元前1 世紀(jì)的阿波羅頭像古希臘銀幣。

圣喬治屠龍貝雕卡梅奧胸針,19 世紀(jì)中葉卡梅奧(Cameo)作者利用天然材質(zhì)顏色分層,讓主體造型浮現(xiàn)于背景上,畫面中的戰(zhàn)馬驚慌失措但神話人物圣喬治英勇淡定斬殺惡龍。
例如鉆石這一材質(zhì),19 世紀(jì)及以前的古董珠寶鑲嵌的老切鉆石與今天的“八心八箭”鉆石相比,不太規(guī)則且不夠閃亮,但其工藝價值卻體現(xiàn)了人類在有限的切磨技術(shù)下,為了制作珠寶努力改變這種自然界堅硬材質(zhì)的形狀,不惜耗費人力與生命的匠人精神。再如瑪瑙、海螺殼等材質(zhì),在現(xiàn)代采掘技術(shù)下已不算貴寶石范疇,但在古董珠寶中的Cameo(卡梅奧)中,可以見到當(dāng)時工匠巧妙的俏色設(shè)計和手工雕刻技術(shù),所以同樣被博物館和收藏家所珍愛。
珠寶,生命中的情感寄托
與前兩個“有形可見”的價值維度相比,情感與文化這一“無形之美”的感悟與發(fā)覺,就略顯困難。古董珠寶賣家和買家的段位,也多因此而拉開距離。其實這珠寶的“無形之美”是與生俱來的,公元前3 萬年,原始獵人們就開始佩戴動物的骨骼和牙齒制成的吊墜,他們相信這些吊墜可以保佑狩獵的成功。可見珠寶緣起,就并不是為了資產(chǎn)保值或彰顯財富,而是作為一種特殊的“媒介”承載了人類對某種精神的寄托。不僅遠(yuǎn)古時代如此,在當(dāng)今古董珠寶市場上常見的珠寶款式,很多也都如同情人節(jié)的玫瑰、母親節(jié)的康乃馨一樣,是寄托精神、傳情達(dá)意的重要載體,材質(zhì)和設(shè)計都是為了更好地表達(dá)特別的寓意而服務(wù)。
傳達(dá)愛意
珠寶制作的花卉,不僅可以流傳百年,而且其所傳遞的情感更為豐富。比如19 世紀(jì)60 年代,在英法流行的一種叫做“顫抖花”的珠寶,用金銀疊打工藝鑲嵌老切鉆石制作出一支或一簇花卉,工匠會用類似金屬發(fā)條的盤旋彈力裝置連接花頭與枝干。在那個燭火照明的年代,這種珠寶花卉佩戴在女性身上,花朵會隨著主人的動作微微顫抖,反射燭光搖曳生姿。顫抖花的造型會選擇一種叫“犬薔薇”的花形,因為這種花的每個花瓣形似一顆愛心圍繞的花芯,通常這樣的珠寶由紳士定制后送給心愛的女神,表達(dá)愛意。也有貴族沿襲狩獵的傳統(tǒng)并將獵物的骨頭取下,做成珠寶送給心上人,例如,用印度虎指甲和牡鹿牙齒制成的珠寶,這些珠寶聽起來有點血腥,但是也代表了人類原始的征服欲和情感的表達(dá)。
有形之美可以彰顯華貴,而無形之美充分體現(xiàn)出浪漫與文化品位。這些珠寶不僅珍貴華麗也傳遞著主人們的綿綿情愫,在它們主人的每個重要人生時刻,都有珠寶的身影參與其中。

金鑲牡鹿牙手鏈/吊墜,19 世紀(jì)雙色K 金鑲嵌打磨光亮的鹿牙,巧妙的制作出葉果顏色分明的橡果造型。

金鑲虎爪吊墜,19 世紀(jì)卷曲紋和勿忘我花卉造型的黃金飾片包鑲著一對印度虎指甲。

顫抖花胸針,19 世紀(jì)中期金銀疊打工藝的金屬枝干,鑲嵌老切鉆石。主花是當(dāng)時典型的犬薔薇造型,這件作品通過螺絲機(jī)關(guān)鏈接,可以拆分成4 種組合或分開佩戴。
勇氣與智慧的象征
不僅植物和花卉,動物造型也在珠寶的“無形之美”中占有重要的席位。1837 年,剛剛成年的維多利亞女王在參加加冕儀式的第一次議會上,就佩戴了一條蛇形手鐲,或許她希望在自己的重要人生時刻,通過這件珠寶鼓舞著自己的勇敢與智慧。蛇在歐洲古董珠寶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有一種說法是首尾相連的銜尾蛇代表著永恒,也有很多人認(rèn)為蛇是智慧與勇敢的化身。無論怎樣,蛇的造型被用在人們的愛情表達(dá)、信仰紀(jì)念上,這種寄情于物的表達(dá)延續(xù)了一個又一個世紀(jì)。

蛇形貼頸項鏈,19 世紀(jì)。黃金鑲嵌綠松石、鉆石、石榴石。
紀(jì)念與哀悼
在19 世紀(jì)70 年代的英國,還曾流行過用頭發(fā)搭配黃金寶石制成的發(fā)絲珠寶。有用嬰兒的胎毛制作祈佑小孩的平安健康;也有的人為遠(yuǎn)行的家人或朋友制作寄托思念的;新婚夫婦則將發(fā)絲做成最好的愛情見證。而更多的時候,發(fā)絲珠寶是用于紀(jì)念和哀悼逝者,哀悼珠寶通常有畫押字或鏨刻著逝者的名字。一枚小小的飾物就成了與親人心靈相通的媒介可以隨身相伴。這些發(fā)絲材質(zhì)上并不具備珠寶的屬性,但是經(jīng)過珠寶匠人的加工和擁有者的情感綁定,便成了特別的珠寶。

編發(fā)胸針,19 世紀(jì)黃金邊框內(nèi)嵌編織發(fā)片。透明封殼表面的英文黃金畫押字可能是主人家族的名稱縮寫。

編發(fā)手鏈,19 世紀(jì)上葉一對名叫喬治和路易斯的新婚夫婦用二人的頭發(fā)編織了手鐲,并在黃金接扣上鑲嵌了刻有兩人名字的紫水晶,作為自己的婚禮紀(jì)念信物。

微繪琺瑯胸針,19 世紀(jì)黃金琺瑯邊框,鑲嵌紅寶石。主題畫面是微繪琺瑯工藝再現(xiàn)的拉斐爾名畫《椅中圣母》,頭尾相銜的雙蛇邊框,寓意永恒。
珠寶,承載人類精神財富的容器
有人說,珠寶是讓回憶永葆青春的一種存在,也正是因為珠寶被賦予了人的情感才更加值得紀(jì)念與收藏。
一代代的珠寶工匠,將這些美好的情感元素,憑借巧思的設(shè)計,利用不同材質(zhì)的質(zhì)地、顏色,通過不同工藝的變換,最終制作出一件件有靈魂的珠寶,流傳百世。
透過珠寶價值三原色,感受到珠寶蘊含的情感與文化這一“無形之美”,在鑒賞古董珠寶的時候,會有更為奇妙的體驗。一頂冠冕擺在眼前,別人在計算鉆石金重的時候,我們可以感受到當(dāng)年的定制者和珠寶工匠,如何通過一件珠寶所表達(dá)的美好情感。星月造型與藍(lán)白配色是希望佩戴者如女神一樣美貌勇敢,有圣母的保佑和星辰的指引,閃耀的鉆石寓意著家族的傳承恒久綿延。

小冠冕,19 世紀(jì)金銀疊打冕架鑲嵌老切鉆石和天然綠松石。
說到底,古董珠寶的“無形之美”,是用心去感受一件珠寶作品所散發(fā)的歷史與人文之美,才是珠寶作為特殊的精神容器的意義,或許這也是珠寶流傳萬年跨越種族、地域與文化的魅力所在。
如果一個收藏者,不僅有傳承之心,同時可以穿越時空,感受到其創(chuàng)作初衷、傳遞之情,便離看到這“無形之美”更近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