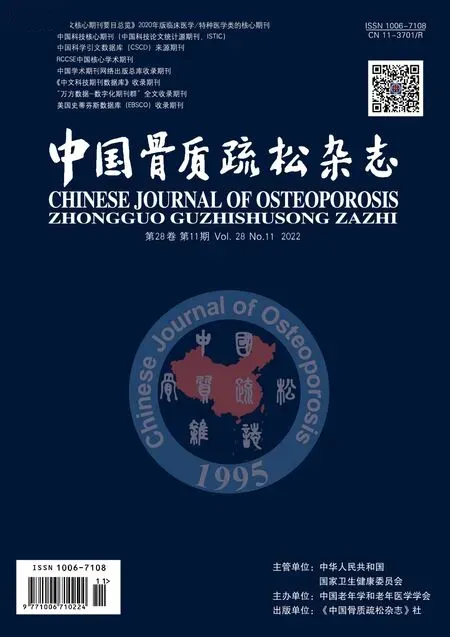不同中藥調控Wnt/GSK-3β/β-連環素蛋白通路治療骨質疏松癥的研究現狀
衛成軍 張智海 鄭琦 許燦 張振南 白楊 于潼 李玉彬
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骨科,北京 100053
骨質疏松癥(osteoporosis,OP)是隨著年齡增長,由各種原因導致的以骨量逐漸開始減少,骨組織的微細結構變細變小為特征,容易產生脆性骨折、嚴重影響健康的一種常見病。近年來圍繞其發生、發展及調控機制的研究越來越多。骨組織的代謝過程由不斷進行的骨形成和骨吸收共同維持,當破骨細胞造成的骨吸收比成骨細胞支持的骨形成明顯時,骨小梁含量降低,骨的脆性增加,導致骨質疏松。骨重建過程受到許多轉錄因子和細胞因子的調控,包括Wnt/β-catenin信號通路、TGF/BMP信號通路、Hedgehog通路等,其中最為經典的為Wnt/β-catenin信號通路。有研究表明當Wnt/β-catenin信號通路激活后,可誘導人體內成骨細胞的分化,提高成骨細胞的活性和礦化能力,最終使骨量增加,骨的機械應力增強。因此圍繞此通路的基因表達,便成為一些中藥治療骨質疏松的依據,也成為尋找高效的臨床治療藥物的突破點。
1 中醫藥治療骨質疏松癥的中醫理論基礎
臨床醫生越來越重視利用中醫中藥治療骨質疏松癥。傳統中醫文獻并無“骨質疏松”記載,但傳統醫學中的“骨痿”的臨床癥狀及其病因病機分析,與骨質疏松癥最為相似、關系最為密切。中醫理論中常見“腎為先天之本”的表述。如《素問·六節藏象論》云“腎者,主蟄,封藏之本,精之處也,其華在發,其充在骨,為陰中之少陰,通于冬氣。”明確指出腎主藏精,有生髓壯骨之功能[1]。《醫經精義》云:“骨者,腎之所合;髓者,腎精所生,精足則髓足;髓在骨內,髓足則骨強。”故“腎精虧虛”是骨質疏松癥的發病關鍵[2-3]。《靈樞·經絡篇》提出:“足少陰氣絕,則骨枯……”用中醫理論解釋,腎精氣不足,骨髓生成乏力,不能營養骨骼,最終導致“骨痿”。現代研究也提示“腎主骨生髓”,腎陽虛或者腎陰虛的患者臨床檢測骨密度,常常發現骨質疏松癥[4-5]。董萬濤等[6]認為,髓虛骨枯為其主要病機。故臨床一線常常以上述中醫思想及理論指導中藥使用,對骨質疏松癥進行相關治療。
2 Wnt/β-catenin通路治療骨質疏松癥的作用機制
Wnt 信號通路是一種作用廣泛的經典信號通路,在骨骼生長發育及骨髓干細胞轉化等多種過程起重要作用。該通路主要通過β-連環素蛋白(β-catenin)介導,進入到細胞核內,對基因進行一定調控來影響成骨細胞的功能。有研究發現Wnt/GSK-3β/β-catenin信號通路作用于骨的生長發育各個階段,激活Wnt/GSK-3β/β-catenin信號通路能促進骨髓中出現更多的成骨細胞增殖和分化,從而促進骨形成,增加骨密度[7-8]。Kim等[9]認為激活Wnt/GSK-3β/β-catenin信號通路誘導骨髓干細胞的同時,也能增加堿性磷酸酶的數量,促使成骨細胞分化趨勢增加,減少向脂肪細胞和軟骨細胞的分化趨勢;同時增加分泌胞外基質,骨細胞的礦化得到增強。
β-catenin進入細胞質中,其中一部分進入細胞核內,與轉錄因子作用后,便可促進成骨細胞的分化,并且抑制向破骨細胞的分化(圖1);多項基礎研究顯示Wnt/β-catenin信號通路主要涉及一系列蛋白表達,例如最常見的β-catenin、跨膜受體(frizzled、LRP5/6)、TCF/LEF及細胞外因子(Wnt)等[10]。無細胞外因子Wnt時,得到支架蛋白(axin)輔助,β-catenin與GSK-3β、APC基因表達產物形成某種復合體,并且開始一些磷酸化表現。而在有細胞外因子Wnt時,Wnt就會與兩種膜受體LRP5/6受體和frizzled結合,此時會抑制GSK-3β活性,β-catenin磷酸化過程和降解途徑被切斷,結果細胞質內β-catenin堆積,當堆積到一定量時,β-catenin進入細胞核調節靶基因的表達[9,11]。這個過程就解釋了β-catenin信號表達程度能夠影響骨的代謝[12-14]。經典的Wnt/β-catenin信號通路被激活后,可以抑制β-catenin降解,使β-catenin穩定并聚集于細胞核內,經過轉錄調控,促進成骨細胞分化,且抑制了破骨細胞分化[15]。當然,Wnt 信號還可以通過興奮 Runx2 來誘導成骨,屬于另外一條通路,其中Wnt10b 的過度表達以后,能夠抑制骨丟失并通過上調 Runx2驅動間充質干細胞分化[16],由此可見,隨著圍繞該經典通路基礎研究范圍的逐步擴大,也許會發現幾個“切入點”,通過對骨骼成骨與破骨之間的代謝調控進行人工干預,從而為骨質疏松癥的治療提供更多思路。

圖1 Wnt/GSK-3β/β-連環素蛋白信號通路作用機制示意圖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of Wnt/GSK-3β/β-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
3 中醫藥通過調控Wnt/β-catenin通路治療骨質疏松的研究進展
如何提高成骨細胞活性,促進成骨分化,繞不開激活Wnt/GSK-3β/β-catenin信號這條經典通路,研究表明一些中藥及相關成分能夠調控該通路,進而促進骨質疏松癥的有效治療。文獻報道[17-18]調控Wnt/GSK-3β/β-catenin通路的中藥有經典方劑右歸丸、左歸丸和金匱腎氣丸等,藥物及藥物成分有獨活、龜板、白藜蘆醇、淫羊藿苷、芝麻素、小檗堿、姜黃素、黃芩苷等,本文歸納總結了通過該通路起作用的單味中藥或有效成分及中藥復方,以及相關藥物在該領域的研究進展。
多項研究[19-23]表明白藜蘆醇、蛇床子素、淫羊藿苷及黃酮類化合物在細胞水平或在動物實驗研究水平能夠對成骨有明顯促進作用。
單味中藥獨活為毛當歸的干燥根,有特異香氣,味苦、辛、微麻。歸腎、膀胱經。《神農本草經》記載:獨活主風寒所擊,金創止痛……久服,輕身耐老。說明早在在東漢時期醫家就觀察到獨活的“抗衰老”作用。《中國藥典》收錄:獨活具有祛風除濕,通痹止痛的作用,主要用于風寒濕痹、腰膝疼痛等。現代藥理學研究顯示獨活可解痙止痛,抗血栓,提高免疫力。臨床上常用以獨活為主要藥物的“獨活寄生湯”治療骨質疏松癥患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姚琦等[24]利用高劑量獨活治療骨質疏松癥模型大鼠,發現其骨組織的GSK-3β、β-catenin表達量變化明顯,能夠增強成骨細胞骨形成,抑制破骨細胞,從而增加骨密度。
龜板具有益腎強骨的作用。余翔等[25]探討了補腎中藥龜板促進 BMSCs增殖和成骨分化的作用及let-7f 對TNFR2的靶向調控作用。分別以Western blot、qPCR 檢測TNFR2、β-cantenin、GSK3β的mRNA 表達,觀察到龜板可促進BMSCs增殖、成骨分化和礦化,let-7f-5p可靶向TNFR2調控Wnt/β-catenin通路,抗激素性骨質疏松癥。
白藜蘆醇是一種二苯乙烯類的植物雌激素,中藥藜蘆、虎杖以及食物花生和葡萄中均含有該成分[26]。劉兆平等[27]、Boyden等[28]研究已證實白黎蘆醇具有雌激素樣作用,還具有抗氧化、調節血脂、抗腫瘤和抗血小板聚集等生物活性作用。對去卵巢骨質疏松大鼠經含白藜蘆醇藥液灌胃3個月后,檢測到GSK3β mRNA的表達顯著降低,β-catenin mRNA的表達顯著增加,表明該藥物可能通過促進GSK-3β磷酸化,以及胞內β-catenin的集聚以致部分轉入到胞核中起作用,因此,認為白藜蘆醇促進成骨的作用可能與Wnt/β-catenin信號通路有關[29]。
姜黃素是一種姜黃屬植物(Curcumin longa L)根莖提取物,已被證實可以對抗激素誘導的大鼠骨質疏松。陳之光[30]運用熒光定量PCR技術,發現這種藥物可以干預到大鼠模型組骨組織和原代培養成骨細胞中Wnt/β-catenin信號通路關鍵蛋Wnt、β-catenin、LRP5等mRNA 表達情況,檢測到較多的成骨細胞分化和成熟相關蛋白如Runx2、Osterix、Osteocalcin的mRNA表達情況,因此發現該藥物是利用興奮成骨細胞中的 Wnt/β-catenin信號通路,誘導骨保護素(osteoprotegerin,OPG)的表達而抑制破骨細胞分化[31]。
在一些藥物成分常規研究中發現,如小檗堿、淫羊藿苷、黃芪甲苷、黃芪苷和骨碎補總黃酮等天然藥物均具促進成骨細胞分化達到抗骨質疏松的作用[32],并且該作用是通過經典Wnt/β-catenin 傳導通路來調整控制并最終實現的[33]。例如,Tao等[34]發現小檗堿可通過對氧化應激效應的抑制,降低炎癥因子和骨形成蛋白的生成,產生細胞外因子Wnt,從而刺激β-catenin向核內移動,抑制骨髓間充質干細胞向破骨分化,誘導其成骨分化,從而來改善大鼠骨的形態,提高骨密度,為臨床應用小檗堿來防治骨質疏松提供理論依據。陳廣明等[35]在用淫羊藿水提取液干預去卵巢骨質疏松大鼠后,從 Western-blotting 得到了部分驗證其能夠升高 Runx2 mRNA表達,升高β-catenin,說明該藥物同樣可激活此信號通路,進而影響骨保護素水平,從而達到控制成骨和破骨的平衡。
黃芪具有補氣固表,利尿托毒,排膿之功,用于氣虛乏力、表虛自汗、水腫癰疽等癥,現代藥理研究表明黃芪有強心、降壓、抑菌、抗疲勞作用。黃芪甲苷是從黃芪中提取的有效成分。成鵬等[36]通過對大鼠的絕經后骨質疏松模型灌藥觀察,發現黃芪甲苷能夠提高大鼠模型的骨密度,增強其生物力學強度,證明黃芪甲苷能夠有效抑制絕經后大鼠骨質疏松的進展。在實驗中同時檢測到Wnt2 蛋白和β-catenin表達都明顯升高,說明黃芪甲苷對骨質疏松的抑制有可能是通過Wnt2/β-catenin通路實現的。
中藥黃芩清熱燥濕,瀉火解毒,止血,安胎,臨床用于治療濕溫、暑溫、黃疸瀉痢等,現代藥理學認為,從黃芩中提取出的黃酮類化合物黃芩苷,具有抗炎、抑菌、解痙、鎮靜等作用。近來多項研究表明黃芩苷能夠提升堿性磷酸酶活性,提高β-catenin、Wnt10a的蛋白表達水平,促進骨髓干細胞向成骨細胞分化,因此黃芩苷對成骨細胞分化的影響并不是通過雌激素信號通路來實現的,而是激活了Wnt/β-catenin通道的信號蛋白完成的[37-38]。
中藥麻油味甘性涼,有潤腸通便,解毒生機的作用,用于治療腸燥便秘,皮膚皴裂等癥。天然芝麻素存在于芝麻油中,可從芝麻油中提取出來,也可人工合成。馬忠平等[39]對從大鼠分離出的骨髓間充質干細胞經芝麻素干預后,通過Western blotting檢測 Wnt/β-catenin通路表達情況,了解到β-catenin和LRP5 的表達明顯升高,而GSK-3b下降,并與芝麻素的濃度呈正相關。因此芝麻素能夠激活Wnt/β-catenin通路,誘導骨髓間充質干細胞的成骨細胞分化,阻斷骨質疏松的進展,可用于防治骨質疏松。
至于傳統經典名方治療骨質疏松癥的成方主要有右歸丸、左歸丸和金匱腎氣丸等,其中,右歸丸溫補腎陽,填精益髓,可用于治療腎陽不足的腰膝酸軟、肢節痹痛,方中運用菟絲子、鹿角膠、杜仲增強附子、肉桂的補腎陽之力,由熟地黃、山藥、山茱萸配合當歸、枸杞養血滋陰,充分體現了中醫“善補陽者必陰中求陽”的思想,現代醫學因其“填精益髓”,用來治療骨質疏松癥。章建華等[40]對右歸丸的研究發現,右歸丸能夠提升ALP、ERK1、ERK2 mRNA及β-連環素蛋白(β-catenin)蛋白的表達,促進成骨分化,可用來治療骨質疏松。顯然,這個過程是通過Wnt/β-catenin、ERK1/2信號通路來實現的。在這個研究中同時發現右歸丸對辯證為腎陽虛的骨質疏松作用更強,符合中醫辨證施治的原則。
左歸丸滋陰補腎,填精益髓,用于治療腎陰不足的腰膝酸軟等癥,運用龜板、枸杞子配合熟地黃、山藥、山茱萸滋陰補腎,牛膝、菟絲子強筋壯骨,鹿角膠溫補腎陽,奏“陽中求陰”的辯證思想。因歷代醫家用于治療腰膝酸軟,則在防治骨質疏松得以重視。多項研究[41-44]表明左歸丸能夠激活Wnt/β-catenin信號通路,GSK-3β活性降低,抑制了其對β-catenin磷酸化,β-catenin被降解減少,向細胞質內移動聚集,部分進入細胞核內部,誘導骨髓干細胞的成骨分化。研究還發現運用左歸丸后堿性磷酸酶活性明顯提高,證明了左歸丸的促進成骨作用。動物實驗中的組織樣本HE染色證實,左歸丸中、高劑量組和雌二醇組股骨骨細胞數量增加,骨小梁增粗,排列漸規整清晰。同時發現左歸丸對辯證為腎陰虛骨質疏松的誘導成骨基因表達作用更強。
金匱腎氣丸溫補腎陽,用于腎陽不足所致腰膝酸軟,畏寒疼痛等癥,方中重用六味地黃丸(地黃、山萸肉、山藥、茯苓、牡丹皮、澤瀉)輔助附子、桂枝陰陽并補,以求“陽得陰助生化無窮”,作為補腎的經典方劑,對歷代醫家運用補腎方劑具有深遠影響,宋朝以后就認為腎氣丸為陰陽雙補,能夠抗衰老、美顏、益壽。現代藥理研究表明腎氣丸具有改善微循環、抗衰老、增強免疫等作用,并且能影響蛋白、糖及脂肪代謝。金匱腎氣丸在臨床應用中,發現其改善消渴病癥狀的同時還可起到治療骨質疏松癥的功效。本藥中重用的“地黃”,其活性成分梓醇同樣起到如左歸丸類似的作用。相關文獻研究[45]提示金匱腎氣丸治療女性絕經后骨質疏松癥6個月,與治療前相比可以明顯降低骨硬化蛋白表達,提高骨密度。金匱腎氣丸治療基于消渴病引發的骨質疏松癥各種作用機制中,推測其可能通過激活Wnt/GSK-3β/β-catenin信號通路,調控自噬,抑制細胞內氧化應激水平,達到治療糖尿病性骨質疏松癥,此機制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
4 小結
上述研究表明,多種中藥成分都能夠通過激活Wnt/GSK-3β/β-catenin信號通路,抑制GSK-3β的表達,促使細胞胞質中有更多的β-catenin向核內轉移,進而誘導骨髓干細胞向成骨細胞分化,以達到增加骨密度的目的。這些中藥及其有效成分的積極作用,比目前臨床中經常使用的化學藥物如降鈣素、阿侖膦酸鈉、唑來磷酸鈉(抑制破骨細胞活性)等更勝一籌,也比甲狀旁腺激素(特立帕肽)等不良反應更小。這些中藥有效成分所起作用的機制類似治療艾滋病毒的“雞尾酒”藥物組,可以認為中藥在中醫理論的指導下同樣合成了天然的“雞尾酒”藥物組來治療骨質疏松癥。因此,開展中醫藥防治骨質疏松癥的科學研究具有更高的研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