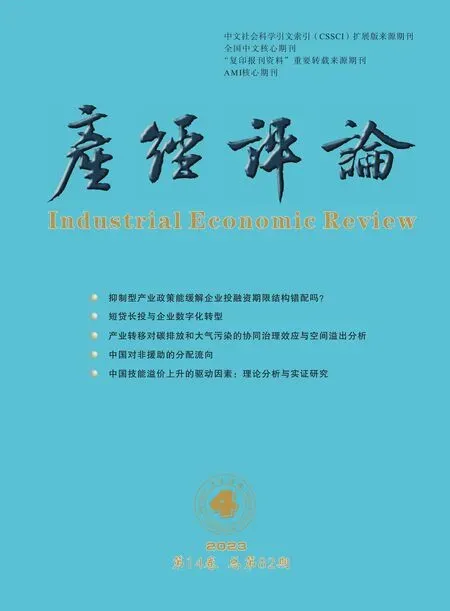中國對非援助的分配流向
——基于對非投資和經濟距離的視角
余林徽 李 瑩 武 巖
一 引 言
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發展最為迅速的新興經濟體之一。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非洲國家戰略地位的改變,中國對非洲的援助也呈現前所未有的高增長和高彈性,占全球比重不斷提高,與美國、日本等傳統援助國的相對差距不斷縮小,成為世界第四大對非援助國。盡管國際上一直將中國視為新晉的“援助者”,然而中國的對外援助活動實際可以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朝鮮戰爭后,中國首次向朝鮮的重建施予援助,之后又迅速對越南戰爭后獲得獨立的相鄰國家進行資助以確保其獨立的國際地位,并建立了合作友好的國際關系。OECD報告顯示,中國同美國的對外援助規模不相上下,但構成卻大有不同。中國對外援助中,官方援助(ODA)僅占25%,而美國對外援助中官方援助的比例高達93%(1)數據來源:http://aiddata.org/china。。政治、經濟、人道主義是傳統西方援助國關心的主要問題(Kuziemko和Werker,2006[1];Vreeland和Dreher,2014[2])。然而,中國的歷史和政治制度與西方傳統援助國截然不同,加之中國政府宣稱對外援助堅持互利互惠和一個中國原則,并強調援助無任何政治附加條件,這種差異使得中國對外援助的關注重點與傳統援助國也必然有所不同。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對非援助的分配動機和實際流向是什么?由于西方傳統援助國對外援助歷史悠久,因而國際上與援助相關的文獻大多關注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對外援助。同時,由于缺乏眾多新興捐助者(非發展援助委員會成員國)的全面援助統計信息,且中國政府對外援助和其他形式國家融資的地域與部門細目分類尚未公開,因此,對中國對外援助的系統研究相對較少。目前已有部分文獻指出,中國在非洲的援助活動與經貿活動密切相關(董艷和樊此君,2016[3];劉愛蘭等,2018[4];孫楚仁等,2021[5]),但多從對非援助產生的影響展開分析,對投資等經濟活動如何影響中國的援助分配進行研究的文獻鮮有。
鑒于此,本文采用AidData 中國對外援助數據庫,選取2000—2014年中國政府在非洲53個國家實施的援助項目信息,系統地論證和探討影響中國對非援助分配流向的主要因素。主要貢獻為:(1)以往研究中國對外援助的文獻大多集中于援助給援助雙方帶來的實際成效方面,本文著重考察影響中國對外援助項目分配的主要因素。(2)基于研究主題的特征,本文根據中國與非洲各國的貿易往來關系,構建全新的經濟距離綜合指標體系,測算中非間基礎設施建設、農業、制造業、能源、原材料五大類別行業的經濟距離,進一步分析經濟距離與中國對非投資的關系,對中國對非援助的分配進行有益的探索。(3)立足于“發展理論”,從受援國發展潛力、發展風險以及發展基礎三個方面剖析對非投資影響中國對非援助分配的作用渠道。
剩余內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為文獻綜述與典型化事實;第三部分為數據與方法;第四部分為實證結果分析;第五部分為機制探討與分析;最后為結論與啟示。
二 文獻綜述與典型化事實
非洲大陸歷來投資不足,援助可以幫助貧困國家擺脫貧困的惡性循環。一方面,援助可以通過為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和人力資本投資籌集資金,減輕發展中國家發展中所遇到的瓶頸,而私營部門則不會進行此類投資。另一方面,投資于有形資本的外國援助將會與其他類型的資本相互競爭(Selaya和Sunesen,2012)[6]。Kimura和Todo(2010)[7]認為,提供援助可能會產生積極的示范作用,吸引同一捐助國的投資,但對其他捐助國的投資沒有影響。Kilama(2016)[8]將G7國家的援助與中國援助聯系在一起進行研究時發現,G7 國家傾向在中國增加援助的區域投放更多的援助。
21世紀以來,傳統捐助者和國際組織的國際援助中,社會部門支出占援助項目總數的60%以上,而1970年代為30%(Frot和Santiso,2009)[9],傳統捐助者對經濟基礎設施的忽視為中國和其他新興捐助者在這些部門的援助開辟了道路,并有助于擴大他們在與非洲國家和其他低收入國家發展合作中的影響力。一般而言,中國傾向于援助體育館、水壩、鐵路或公共建筑等基礎設施項目,僅有少數西方捐助者繼續為這類項目提供資金(Hackenesch,2009)[10],這為中國提供了競爭優勢。但目前對國際援助分配流向的研究并未達成共識,關于中國對外援助的分配流向仍甚是模糊。
西方主流新聞媒體譴責中國政府將對外援助作為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經濟掠奪的工具,認為中國的對外援助主要流向那些能夠確保其獲取自然資源并進行海外市場擴張的國家,從而為中國企業創造更多的商業機會(Naím,2007)[11]。部分文獻認為中國在對外援助中扮演“流氓商人”的角色并在不斷弱化非洲國家的政權,中國的援助政策不符合傳統援助委員會制定的標準和規范 (Manning,2006[12];Naím,2007[11];Chileshe,2010[13])。Strange et al. (2017)[14]發現中國官方發展援助的分配主要是由外交政策考慮驅動的,而經濟利益則更好地解釋了中國官方融資優惠形式的分配。此外,隨著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經濟影響力的不斷提高,其更有能力利用經濟實力實現戰略和外交目標(Bhuvan et al.,2016)[15]。然而,一些研究對國際上關于中國對外援助的譴責也持有質疑態度。Dreher et al. (2011)[16]的最新證據證明了新老援助者表現相似,沒有理由指責中國等新興捐助者利用對外援助來獲得經濟利益,中國的援助策略并非“醉翁不在酒”。由此可見,國際上關于中國對外援助的動機爭論不停,且尚未達成一致意見。盡管那些夸張甚至帶有刻意“抹黑”性質的說法是不合理的(Dreher 和 Fuchs,2015)[17],但如何表征新興的中國發展合作模式仍然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通過梳理可以發現,國際上抨擊中國對外援助各種動機的文獻不絕于耳,此前因為缺乏有力的數據和證據而無力反駁。本文試圖從經濟視角考察中國對非援助的分配動機與流向,以期正面回應國際上諸多關于中國對外援助動機的說法,為促進國家區域協調發展,助力國內國際雙循環提供有益參考。
三 數據與方法
(一)數據說明
本文關于中國對非援助的數據來源于AidData數據庫,該數據庫使用“Geocode Methodology”的方法,搜集了2000—2014年間中國政府對非洲53個國家實施的援助項目信息,包括援助對象、金額和援助具體措施。為了考察中國對非援助的實際分配流向,本文構建的基礎模型如下:
aidi, t=β0+β1ofdii, t-1+β2ecodistancei, t-1+β3(ofdi×ecodistance)i, t-1+β4controli, t-1+εi, t
(1)
1.被解釋變量
AidData實際上只追蹤了援助項目的承諾數據,而援助項目實際支出并未給出,所以無法判斷援助項目承諾金額和落實金額之間的差距。Berthelemy(2006)[18]使用的是援助承諾數據,他認為援助承諾通常先于援助實際支出,因此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內生性問題。本文遵循這一思路,通過滯后解釋變量并使用援助承諾作為被解釋變量來克服內生性問題。對非援助的項目數量可以反映中國對非援助決策的傾斜情況,對于一些大型工程類的經濟援助項目,其援助金額與社會發展類援助項目而言差距較大,使用援助金額作為被解釋變量容易忽略不同類型援助項目的分配流向。因此,本文主要選用援助項目的總承諾項目數量(aid)作為援助績效的代理變量。同時注意到,只研究中國選擇進行援助的國家和地區的影響因素可能會存在樣本選擇偏差,援助項目多寡和是否進行援助實際上不能一并而論,為使結果更為穩健,在后文中將對非援助二元虛擬變量(aiddummy)作為被解釋變量納入考察框架。
2.解釋變量
國際上關于中國對外援助存在不同聲音,分析影響對外援助分配流向的相關因素(Broich,2017[19];Dreher et al.,2018[20];Marlène和Jacky,2020[21]),得到本文的關鍵解釋變量為:經濟距離(ecodistance)、對非直接投資存量(ofdi)。
經濟距離(ecodistance)表明兩國之間經貿距離的遠近。大量文獻表明中國的對外援助與貿易存在密切聯系,投資、貿易、援助之間呈現相輔相成的關系模式(顧振華和高翔,2019[22];劉愛蘭等,2018[4];米銀霞和余壯雄,2019[23])。一般而言,兩國之間的貿易往來越密切,越會拉近兩國經濟距離。然而僅用貿易來衡量兩國間的經濟密切程度并不全面,因此,為了測算國家間的經濟距離,本文構建基于援助雙方產業間貿易互補程度的經濟距離指標。首先需要說明的是貿易互補指數的測算方法。借鑒Drysdale(1969)[24]測量貿易互補性的方法,兩國貿易互補指數(CI)計算方法如下:
(2)
(3)
(4)
其中,i、j分別為國家i和j,本文中i表示中國,后文用c表示。Xki表示i國k商品出口額,Xi為i國的總出口額;Mkj表示j國k商品進口額,Mj為j國的總進口額;Xkw為世界k商品總出口額,Xw為世界總出口額;Mkw為世界k商品總進口額,Mw為世界總進口額。RCAx,i,k和RCAm,j,k分別表示k商品在i國的出口比較優勢和j國的進口比較優勢。CIi,j表示i、j兩國的貿易互補程度,CIki,j表示i、j兩國k商品的貿易互補程度。CIi,j越大表明兩國之間的貿易互補性越強。
當然,經濟距離的測算不僅取決于兩國間的貿易互補程度,還和地理距離、貿易成本等諸多因素息息相關。比如,運輸成本的變化會改變兩國的貿易和投資決策,兩國的語言距離、是否存在接壤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兩國經濟距離。本文參考邸玉娜和由林青(2018)[25]將石油價格引入到貿易成本中的做法,以及Arvis et al.(2016)[26]測算貿易成本的理論模型,構建經濟距離指標如下:
(5)
(6)
其中,tradecost的數據來自ESCAP數據庫,測算過程中考慮了地理距離、進入成本、語言、殖民關系、是否存在接壤等諸多因素,因此在構建經濟距離指標時不再加入同類變量(2)貿易成本數據來自ESCAP世界銀行數據庫。數據提供者Arvis et al.(2016)[26]選取殖民地、共同邊界、共同語言距離、入境成本、人均GDP、內陸虛擬變量、物流績效指數等諸多指標構建國家間貿易成本評估體系。。同時,考慮到石油價格是衡量運輸成本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選取代表美洲原油價格的WIT石油價格和代表歐洲原油價格的Brent石油價格的平均值oilprice來衡量國際運輸成本。ofdi代表當年中國對該國的直接投資存量金額,之所以選取OFDI存量而沒有選取OFDI流量,是考慮投資存在連續性且投資存量更能體現對外投資的規模。
其他控制變量包括:(1)臺灣問題立場(taiwan),表示一個國家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如果該國或地區與臺灣建立“外交”關系,則該指標為1,否則為0,數據參考Brautigam(2011)[27]的研究;(2)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成員國(unsc),表示該國是否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臨時成員,當一個國家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臨時成員時,該指標為1,否則為0,數據參考Dreher et al.(2009)[28]更新版本數據;(3)聯合國投票與中國一致性(pctagreechina),表示在聯合國大會上與中國在所有選票上的投票一致性,理論上該指標越大,在政治上的立場與中國越接近,數據參考Bailey et al.(2016)[29]版本數據;(4)礦產資源(minerals),表示中國從受援國進口礦產資源額與當年中國從世界進口礦產總額的比值,數據來自WITS數據庫;(5)人口數量(population),它既能代表當地的市場規模,一定程度上也能代表當地的勞動力數量,數據來自WDI數據庫;(6)自然災害(affected),表示受援國當年受自然災害影響的人數,用來衡量自然災害的嚴重程度,數據來自全球緊急災難數據庫(Emergency Events Database. EM-DAT);(7)法律規則(rlr),表示公眾對社會規則的信任和遵守程度,該指標分數越高,表明該地區的法治水平越高,制度環境越好,數據來自世界銀行WGI數據庫;(8)人均GDP(gdp_pc),代表受援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數據來自世界銀行;(9)其他援助國對非洲的援助(aid_dac),代表發展援助委員會成員國對非洲的援助金額,數據來自世界銀行。
考慮到中國政府在做出對非援助決策時往往是參考上一年的數據,同時貿易變量要滯后一年才能克服貿易與援助之間的反向因果關系潛力(Hoeffler和Outram,2011)[30],因此將本模型中的所有解釋變量做滯后一期處理,但自然災害一般具有即時性,故此變量仍然使用當年數據。其次,為減少因為數據統計口徑不同帶來的不準確性,對統計數據較大的數值取自然對數。同時也將樣本中所有用現價美元衡量的變量統一利用折算因子換算成2014年美元不變價。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見表1(3)為了更直觀地展示各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權重,本文同時計算了變量之間的beta系數,限于篇幅,文中未列示,感興趣的讀者可向作者索取。。
四 實證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分析
由于非洲國家的樣本數據存在大量零值,為了得到更為穩健的回歸結果,本部分將使用偽極大似然法(PPML)來估計,基準回歸結果見表2(4)Santos和Tenreyro(2006)[32]的研究表明,當樣本數據中存在大量零觀測值和存在異方差性時,PPML優于傳統的OLS和Tobit方法。Dreher et al.(2019)[31]指出,使用PPML回歸模型能更為準確地衡量各種因素對中國對外援助決策的影響。。列(1)—列(6)為逐步加入關鍵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被解釋變量為中國歷年對非援助的項目數量。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基準回歸中參照Dreher et al.(2019)[31]的做法并未控制時間固定效應和地區固定效應。由于探究的是中國對非援助的分配流向,因此需要對受援國之間不同屬性加以區分。政治制度、殖民史、官方語言等多重因素都可能會影響中國對其援助的分配,而控制地區固定效應容易將受援國之間的特質差異忽略。因此,為探尋中國對非援助的動機和流向,只控制了國家特定時間趨勢項,以期獲得更準確的結果。

表2 基準回歸結果
從表2列(1)—列(6)可以看出,對外直接投資(ofdi)的系數顯著為正,這表明中國的援助往往會根據中國前期與受援國之間的投資情況進行分配。以列(6)結果為基準進行分析,受援國前期來自中國的ofdi每上升1%,則該地區能夠獲得來自中國的援助項目上升3.9%。經濟距離(ecodistance)的系數同樣顯著為正,這意味著受援國與中國的經濟距離越大,即兩國的貿易成本越高,貿易互補性越小,該地區能夠獲得的來自中國的援助項目反而越多。對外直接投資和經濟距離交叉項(ofdi×ecodistance)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隨著經濟距離的不斷變大,對外直接投資對中國援助分配的吸引作用在不斷變小。
上述回歸結果表明,一方面,中國立足長遠照顧了經濟距離較遠的遠親關系,這種“舍近求遠”的援助范式與中國式“工業強國”脫貧發展理念同源,體現了援助的幫扶本質。因此,國際上一些關于中國通過對落后國家進行援助以此攫取經濟利益的說法顯然缺乏充足證據。另一方面,中國的援助兼顧當前利益,在根據實際投資情況進行援助分配的同時考慮了本國投資收益情況,通過對經濟距離較近且投資密切的國家進行援助強化了中非之間經濟距離較近的近鄰關系,有助于實現中非雙方合作共贏。此外,臺灣問題立場(taiwan)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中國在對非援助過程中也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與中國在對外援助時宣稱的各項原則基本一致。其他國家對非洲的援助(aiddac)也會顯著促進中國對該國家或地區的援助,這與已有研究結果基本吻合。
為了進一步分析經濟距離對中國對非援助決策的影響,本文對中國與非洲各國間的經濟距離進行了不同行業類型的劃分。根據WITS中給出的15個行業,主要分5大類別重新測算中國與非洲各國之間的經濟距離:(1)基礎設施建設類行業(ed_inf),主要包括交通運輸等行業;(2)制造類行業(ed_maf),主要包括紡織、鞋靴、機械和電氣等行業;(3)原材料行業(ed_raw),主要包括化工原料、塑料、橡膠、石料、木材等行業;(4)農業類行業(ed_agr),主要包括蔬果、畜牧、皮草等行業;(5)能源類行業(ed_eng),主要包括礦產、金屬、燃料等行業。表3分析了不同行業類別經濟距離對中國對非援助決策的影響,其中被解釋變量為中國對非援助項目數量。列(1)ed_inf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中國與受援國之間基礎設施建設部門的互補性越高,貿易成本越低,則這些地區相對能夠獲得更多的來自中國的援助。對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主要依賴于國內出口,由于需要大量鋼鐵建材以及大型基建設備,運輸成本較高,對受援國和中國之間的地理距離、運輸成本都有著較高的要求,因此只有選擇經濟距離較近的地區進行援助才能使援助更加高效。列(2)ed_maf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中國與受援國之間制造部門間的經濟距離越大,獲得的來自中國的援助項目越多,進一步論證了前文分析,即中國“舍近求遠”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是幫助當地發展,而這種以對外直接投資為主要形式的經濟援助帶有更強烈的“授之以漁”色彩。通過觀察列(3)—列(5)發現,原材料類行業(ed_raw)、農業類行業(ed_agr)以及能源類行業(ed_eng)的系數均不顯著,表明非洲國家與中國之間的能源、原材料和農業經濟距離并不會影響中國對非援助項目的分配,這與以往刻意抹黑中國對非援助是為了獲得原材料和自然資源的說法并不一致,也進一步論證了上文得出的結論,即中國對非援助并非自私自利,而是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互利方式,對非洲受援國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以幫助受援國的恢復與發展。

表3 不同行業經濟距離的回歸結果
(二)穩健性檢驗與分析
1.遺漏重要變量問題。實際上,影響中國對外援助決策的因素眾多,如果將它們全部一起引入可能會影響對相對均勻的受援國群體某些特征的關注,并且過多變量通常彼此共線,部分國家的數據也存在嚴重缺乏現象,因此無法將所有因素納入考察框架,而是選取具有代表性的控制變量以盡可能減少遺漏變量的問題,以此更加專注于經濟方面的援助動機。為了避免選取代理變量的主觀性而導致結果有偏,本部分進一步進行檢驗與探索。
(1)自然災害。選取自然災害中無家可歸人數(homeless)作為災害嚴重程度的代理變量,替換自然災害中總受災人數(affected)變量。表4列(2)結果表明自然災害程度與中國對非援助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2)政治動機。表4列(3)選取pctagreeus作為政治動機變量,該變量表示聯合國大會上與美國在所有選票上的投票一致性,理論上該指標越大,在政治立場上與美國越接近,結果表明其并不顯著。(3)自然資源。在表4列(4),參考現有研究的做法(Broich,2017[19];Dreher et al.,2019[31]),選取天然氣儲備(gas)作為非洲自然資源存量的代理變量進行分析,gas代表一個國家的天然氣資源稟賦,由天然氣租金占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計算得到,其中天然氣租金是以世界價格計算的天然氣生產價值與生產總成本之間的差額,數據來自世界銀行WGI數據庫。結果表明天然氣儲存量和中國對非援助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這意味著中國的援助往往流向那些天然氣資源匱乏的國家和地區,非洲國家的自然資源儲備并不是中國對非援助的重要考慮因素。(4)制度環境。已有大量文獻研究了制度環境與援助之間的關系(Broich,2017[19];王孝松和田思遠,2019[33])。表4列(5)和列(6)依次控制了代表制度環境的政府腐敗程度(ccr)和社會穩定程度(pvr)代理變量。ccr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對腐敗的控制,衡量了人們對公共權力在多大程度上是為私利而行使的看法,包括小腐敗和大腐敗,以及精英和私人利益對國家的“俘虜”,指數越高表明地區腐敗治理水平越高,則腐敗程度越低;pvr為社會穩定指標,衡量了政治穩定和包括恐怖主義的可能性在內的出于政治動機的暴力等因素,該指數得分越高,則社會越穩定,數據來自WGI數據庫,結果同樣不顯著。

表4 穩健性檢驗1:擴展基準模型
觀察表4可以發現,無論如何調整各種援助動機的代理變量,關鍵變量ofdi×ecodistance的系數依舊顯著為負,經濟距離ecodistance的系數和ofdi的系數與表2基準回歸保持一致,進一步說明本文結果的穩健性,也盡可能減少了因為遺漏重要變量而產生的偏差。
2.中國對非援助變量的穩健性檢驗。受援國是否能夠得到來自中國的援助和得到中國援助項目的多少的影響因素可能并不相同,選取中國對非洲援助的項目數量作為被解釋變量,是否會因忽視那些未能獲得中國援助項目的國家和地區的一些特征而導致回歸結果有所偏差?因此,本部分選取是否能夠獲得來自中國的援助項目二元虛擬變量(aiddummy)衡量中國對非援助,當年該地區獲得來自中國的援助項目數量大于等于1時,則該變量為1,否則為0。結果如表5 Panel A所示,在更換被解釋變量的代理變量后,關鍵變量ofdi×ecodistance的系數依然顯著為負,與基準回歸結果基本保持一致,進一步說明中國對非援助代理變量的合理性。為驗證本文模型的穩健性,更換估計方法和關鍵變量,選擇Logit估計方法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5 Panel B所示,關鍵變量系數符號與表5 Panel A和表2基準回歸結果保持一致,降低了因模型設定和估計方法選取主觀性而導致分析結果出現偏差的可能性,從而進一步論證結論的合理性。

表5 穩健性檢驗2:替換關鍵變量與估計方法
3.估計方法穩健性檢驗。Santos和Tenreyro(2006)[32]、Dreher et al.(2019)[31]對何時使用PPML回歸模型進行了大量的合理性闡述,此處不再贅述。為了進一步論證本文回歸結果的穩健性,參考Marlène和Jacky(2018)[21]的方法,使用Tobit方法進行回歸,結果見表6。研究結果表明,即使更換了估計方法,回歸結果也與表2基本保持一致,進一步論證了本文結論。

表6 穩健性檢驗3:更換估計方法
4.區分不同類型援助的穩健性檢驗。受不同類型對外援助特點的影響,不同類型援助的待估參數可能完全不同。為了進一步分析這些異質性,本文首先按照經合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的標準,將對非援助中的官方援助(ODA)與其他官方援助(OOF)區分開來。官方援助(ODA)包括:(1)由官方機構向發展中國家和多邊機構提供的交易;(2)主要目的是促進經濟發展和提高福利;(3)減讓性的交易,即它們有至少25%的贈款要素。其他官方援助(OOF)也由政府機構提供資金,但不符合官方援助的條件,因為這些資金主要不是用于受援國的發展,或者不夠優惠。本部分對不同類型對非援助的分配流向加以研究,結果見表7。列(2)官方援助中,關鍵變量ofdi×ecodistance的系數顯著為負,而列(3)其他官方援助中,關鍵變量ofdi×ecodistance的系數不顯著,這與預期相一致,由于官方援助的主要目的是促進經濟發展和提高福利,且由官方機構進行資助,因此其援助的特質更加顯著。

表7 穩健性檢驗4:區分不同類型援助
5.區分不同援助目的和方式的穩健性檢驗。根據AidData對援助目的的分類,將樣本按照援助目的劃分為發展目的(Development)和其他目的(Others)兩類。其中,根據AidData的定義,發展目的(Development)的援助是指援助國提供的不以追求經濟利益、旨在促進受援國長期經濟發展和提高福利水平的援助,其他目的(Others)的援助主要包括商業目的援助(Commercial)、特定目的援助(Representational)以及混合目的援助(Mixed),由于各類別在中國對非援助項目中所占比例甚小,因此并未對其進行細分而是劃歸到一個大類中,結果見表8列(2)和列(3)。為方便對比,將基準回歸結果置于表8列(1)。結果表明,以發展為目的的對非援助項目主要流向那些投資項目較少的國家和地區,而其他援助目的的對非援助并不關注經濟距離和在受援國前期的投資項目分布狀況。本文還按照不同援助方式對援助項目進行了劃分。古語云“授人以魚,不如授之以漁”,想要幫助發展中國家擺脫困境,相較于直接給予經濟往來的援助,技術援助等方法上的援助能夠對發展中國家產生更強大的發展動力。因此,按照援助的影響,根據AidData對援助方式的劃分,將債務免除、債務重新安排、撥款、貸款(不包括債務重新安排)等援助方式劃歸為直接援助(Direct),將出口信貸、免費技術援助、在捐助國的獎學金/培訓等援助方式劃歸為間接援助(Indirect),結果見表8列(4)和列(5)。可以發現,直接援助方式下ofdi的系數更加顯著,而間接援助方式則不明顯,這表明技術、培訓和教育為主的援助項目分配對ofdi的考量并不多。

ofdii, t=β0+β1IVi, t-1+β2ecodistancei, t-1+β3(IV×ecodistance)i, t-1+β4controli, t-1+εi, t
(8)
模型(8)的回歸結果見表9。根據Stock-Yogo弱工具變量檢驗,檢驗統計量均大于10%水平下所對應的maximal IV size值(7.03),拒絕了弱工具變量的原假設。上述結果表明,使用工具變量后的結果與基準回歸中的結果基本保持一致,從而進一步論證了本文結果的穩健性。

表9 穩健性檢驗6:內生性處理2SLS
五 “發展理論”機制探討與分析
研究中國對非援助的分配流向發現,對非投資尤其是制造業方面的項目會顯著地影響中國對非洲國家的援助策略。根據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援助發展理論,產業結構是援助國發展經驗策略的綜合體現(王釗,2020)[34],中國對非援助的部門分配恰恰反映了中國實現跨越式發展的理念。在推動非洲國家減貧發展的道路上,援助國會在援助中投射自我認知最為成功的發展經驗,提供自我認知最好的發展資源。中國政府一直強調工業強國,“要想富,先修路”一度成為口口相傳的脫貧致富口號,因此,交通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成為中國對非援助的部門分配重心具有必然性。那么,援助能帶來的實際增長與減貧可能性則成為驅動中國對非援助理性選擇需要考慮的重要環節。因此,中國援助策略的規范選擇和理性驅動雙重屬性使援助本身更容易脫離“道德綁架”式的束縛,回歸更加關注援助實際轉化效能的理性選擇。徐麗鶴等(2020)[35]的研究表明,“經濟相近性”會影響中國的對外援助。水利工程等類型援助項目建設周期比較長,雇用了大量當地勞動力,而這些勞動力可以模仿學習中國工程項目的建設過程以及中國工人的一些工作技能等,進而使項目建設完成后可順利交由當地管理。換言之,援助方與受援方的經濟發展水平越接近,援助對當地溢出效應越顯著,越有利于提高當地技術水平。因此,本文選取中非國家的技術差距作為發展潛力指標,用非洲各國工業年增長率與中國工業年增長率的差值進行衡量。Horn et al.(2019)[36]的研究表明,中國的對外援助,尤其是優惠貸款的部分基本是由企業所承接,對于風險較高的受援國,中國的政策性銀行不會將任何資金打入對方的政府控制賬戶,而是直接將資金支付給中國在該地的承建企業,這就使得海外承建企業成為獲得優惠資助閉圓中的必要一環。因此,本部分選用負債率來衡量受援國的發展風險。已有研究表明社會越穩定越能夠獲得援助,因此,本部分還選取國家脆弱指數衡量一個國家的發展基礎,該指數越高表明該國家或地區社會越不穩定。
本部分將嘗試在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援助發展理論框架下,將援助動因規范和理性選擇相統一,從發展潛力、發展風險和發展基礎三個方面構建機制變量來檢驗對非投資對提高援助實際轉化效能,從而推進中國對非援助理性選擇的作用機理。考慮到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條件也會對吸引投資產生反向影響,主要通過對ofdi變量滯后一期來減輕這種影響。表10展示了上述可能存在的作用機制回歸結果,即對非投資分別對發展潛力、發展風險和發展基礎等機制變量的影響。列(1)結果表明,對非投資能夠顯著影響中國與受援國之間的技術差距,從而激發受援國的發展潛力,提高援助的實際轉化效能,援助國與受援國之間適度的技術差距是實現援助技術溢出的有效保障,進而提高獲得更多中國援助的可能性。列(2)結果表明,對非投資能夠顯著影響受援國的抗風險能力,即改善受援國的負債狀況,降低受援國的發展風險。連續召開的中非合作論壇不斷強調重視中國外援項目的實際轉化效能,對非投資項目通過降低受援國負債情況,提高了其償債能力,為援助資金的償還和使用效率提供了保障,也為中非國家間基于援助項目以外的合作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列(3)結果表明,對非投資能夠顯著改善受援國的社會發展環境,即社會動蕩脆弱程度降低,為中國援助的有效轉化吸收提供更穩定的發展基礎,以此吸引更多來自中國的援助。

表10 機制分析檢驗
上述分析表明,發展潛力、發展風險以及發展基礎是援助實現有效轉化吸收的重要影響因素。中國對外援助的分配決策,不僅關注受援國需要獲得援助的實際情況,更加趨于規范選擇和理性邏輯自洽,通過援助海外基礎設施的對外投資項目來推崇工業體系在發展減貧中的核心地位,不僅符合非洲國家當前發展階段的增長和減貧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夠緩解我國國內產能過剩,有助于產業壓力的轉移,實現中非各國的“友好共生”。
六 結論與啟示
近年來,隨著貿易順差和國際儲備的不斷增加,中國正逐步成為全球資本供給國。中國不僅為工業化國家提供戰略資本,而且是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的主要投資國和援助國,并在那些不受西方投資者青睞、傳統意義上被認為風險最大的領域不斷增加對非援助,中國這種深入參與全球化的方式在國際舞臺上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開展對外援助過程中,中國政府強調無任何政治附加條件和一個中國基本原則,中國對外援助關注點與傳統援助國(DAC)的差異使得援助分配流向上必然有所不同。因此,中國對外援助的分配動機和流向是什么引發了廣泛思考。目前關于中國對外援助的研究還沒有形成共識,研究體系還不完善,且由于中國政府尚未公布官方援助的具體信息,此前一些學者的結論缺乏強有力的數據支持。鑒于此,本文基于AidData數據庫,選取2000—2014年中國政府在非洲53個國家實施的援助項目信息,試圖系統地論證和探討影響中國對非援助分配流向的主要因素。
研究結果表明,中國對非援助在首先考慮了受援國是否堅持一個中國基本原則之后,更傾向于援助那些與中國經濟距離較遠且亟需進行建設的落后國家和地區。中國的對非援助更關注受援國當地基礎設施建設與發展,這種“舍近求遠”的經濟形式援助與中國推崇工業體系在發展和脫貧中的核心地位密切相關,不僅符合非洲國家當前發展階段的增長和減貧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緩解我國國內產能過剩問題,是經過規范選擇和理性驅動后的“友好共生”目標導向。另一方面,中國的援助兼顧當前利益,在根據實際投資情況進行援助分配的同時還兼顧了本國的投資收益,通過對經濟距離較近且投資密切的國家進行援助強化了中非之間經濟距離較近的近鄰關系,有助于實現中非雙方合作共贏。此外,與國際上流傳的一種關于中國援助是自私的說法有所不同,本文結果表明受援國的自然資源對中國對非援助項目的流向不存在吸引效應,中國對非援助與受援國給予的政治選票支持也并無多大關聯。中國對外援助的分配決策,不僅關注受援國需要獲得援助的實際情況,同時還關注援助對于增長轉化的實際效能,使得援助分配更趨于理性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