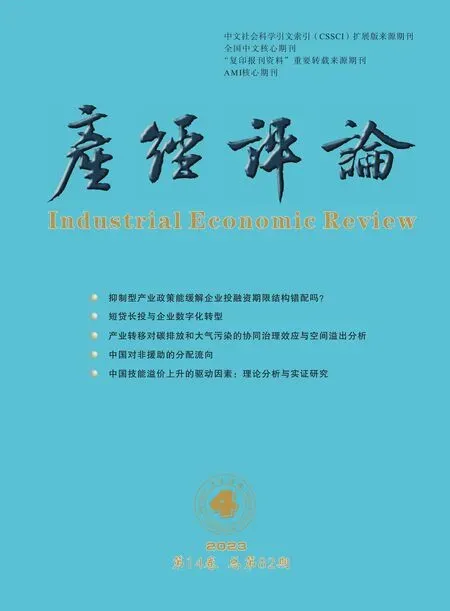中國技能溢價上升的驅動因素: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
盛衛燕
一 引 言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到 2035 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推動不同群體間的工資收入公平分配是其中應有之義。然而,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勞動市場上技能與非技能勞動之間存在的工資收入差距即“技能溢價”呈現明顯上升趨勢(1)技能溢價主要是指由于個體人力資本差異所導致的工資收入差距,實證研究中對高低技能的劃分主要包括高學歷與低學歷工資比、非生產性工人與生產性工人工資比以及高分位點與低分位點工資比。,技能溢價已成為決定個人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且其影響正在逐步擴大(郭凱明和王冰鈺,2022[1];李實和朱夢冰,2022[2])。技能溢價與勞動力個體特征密切關聯,其可能引起就業機會分布在不同群體間差異問題,隨之產生的特定人群失業以及收入分配不公平無疑影響著共同富裕遠景目標的實現,因此,技能溢價問題值得高度關注。
技能溢價問題的研究核心在于技能溢價變動的來源與機制。當前文獻主要從國際貿易(Acemoglu,1998[3],2002[4];Burstein 和 Vogel,2017[5])、信息技術與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引致的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視角進行分析(Autor和Dorn,2013[6];楊飛和范從來,2020[7];胡晟明等,2021[8]),然而,基于結構轉型視角解釋技能溢價的研究不多,且結論莫衷一是。例如,Berman et al.(1994)[9]研究指出,沒有證據表明結構變遷因素會顯著影響技能溢價,而Blum(2008)[10]和Rogerson et al.(2022)[11]基于美國數據、郭凱明和王冰鈺(2022)[1]基于中國數據的研究均顯示結構轉型是影響技能溢價變動的重要因素。理論上,即使不存在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或者國際貿易,只要不同部門技能密集度存在異質性,那么這種不同技能密集度部門間的結構變遷依然會影響技能溢價(郭凱明和王冰鈺,2022[1];Caron et al.,2020[12])。當前,中國正處于結構轉型的重要時期,信息技術、金融與教育等技能密集型服務部門(2)參考Rogerson et al.(2022)[11]技能密集型行業的分類方法,將信息傳輸、軟件與計算機服務、教育、金融、房地產等行業定義為技能密集型行業,并基于投入產出表中最終消費數據進行統計發現,技能密集型部門的需求占比顯著增加,由2000年的36%上升到2018年的58%。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提升,將重塑勞動市場的技能需求結構與工資結構。因此,有必要將中國技能溢價上升問題置于結構轉型背景下進行分析。
一般而言,技術進步水平與經濟結構轉型等宏觀因素對技能溢價的影響可能同時存在,但會在不同時期表現出階段性特征。例如,關于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的動態影響,Blum(2008)[10]基于美國數據研究發現,1970—1980年間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對技能溢價的影響并不大,但在1980—1996年間迅速增加,其可解釋技能溢價變動的50%;關于結構轉型因素對技能溢價的影響,Blum(2008)[10]的研究表明,經濟結構轉型可解釋美國1970—1996年期間技能溢價上升的60%,其影響貢獻率超過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與國際貿易因素的影響。然而,隨著美國經濟轉型日趨成熟,結構轉型因素的影響在減弱。Rogerson et al.(2022)[11]研究發現技能偏向的結構轉型效應可解釋美國1977—2005年間技能溢價上升的30%。因此,將技術進步、結構轉型等宏觀因素納入統一分析框架進行動態比較分析是合理且必要的。對于正處于轉型時期的中國而言,是否產業結構轉型因素對技能溢價的趨勢變動發揮著比發達國家更重要的作用?對該問題的回答亟待基于本國數據進行實證檢驗。
需要說明的是,不僅偏向性技術進步會影響技能溢價,不同要素密集度部門間的結構變遷使得中性技術進步也會影響技能溢價(Blum,2008[10];Rogerson et al.,2022[11])。然而,既有研究對技能溢價問題的考察多基于經濟整體或是部門內部,默認中性技術進步不影響技能溢價。雖然也有國內學者關注到中性技術進步對中國技能溢價的影響(宋冬林等,2010)[13],但其是基于中國1978—2007年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分析,仍沒有考慮到部門異質性影響,而是從中性技術進步的技能偏向性特征解釋技能溢價上升。顯然,當考慮不同部門間要素密集度與要素需求彈性異質性后,中性技術進步可以伴隨不同技能密集度行業間的結構變遷過程影響技能溢價(Blum,2008[10];Kaboski,2009[14];Rogerson et al.,2022[11]),因此,中性技術進步與偏向性技術進步對技能溢價的影響和作用機制可能是不同的,應充分考慮行業異質性將二者獨立分析。
綜上,對中國技能溢價問題的分析需要立足當前的結構轉型背景,同時考慮到各因素影響技能溢價的階段性特征,將結構轉型、不同技術進步與勞動供給等因素納入統一框架進行動態比較分析更具現實意義。為此,本文基于多部門Ricardo-Viner一般均衡模型,將結構轉型效應、Hicks中性技術進步效應、技能偏向技術進步效應以及勞動供給效應納入統一框架分析,運用中國行業面板數據與省級面板考察不同效應對技能溢價影響的階段性特征,以期形成對中國技能溢價變動來源、機制及動態演進的全面認識,進而為實現共同富裕的遠景目標提供現實依據與理論參考。
本文可能的創新之處為:(1)視角不同。不再局限于從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或國際貿易等視角研究技能溢價問題,而是立足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大背景下,基于Ricardo-Viner一般均衡模型分解技能溢價影響因素,豐富結構轉型視角下的技能溢價問題研究,同時,既有研究往往是基于經濟總量或單部門考察偏向性技術進步對技能溢價的影響,這也就決定其無法評估部門內部中性技術進步對技能溢價的影響,本文充分考慮行業結構性差異,補充了中性技術進步視角下的技能溢價問題研究。(2)方法不同。本文從整體性與歷史性視角出發,更加關注系統的動態比較分析。在對技能溢價進行分解的基礎上,基于行業面板數據與省級面板數據,綜合運用反事實分析法與GMM估計方法,考察各因素影響技能溢價的階段性特征,深化對技能溢價演進趨勢背后動力機制的全景認識,進而為縮小不同群體間工資收入差距提供參考。
二 理論模型與機制解釋
Jones(1965)[15]較早關注結構性因素對要素價格變動的影響,其構建了一個“兩要素(勞動與土地)—兩部門”一般均衡模型,借助要素替代彈性、要素需求彈性等深層參數,將要素相對價格分解為部門內技術進步效應、部門間技術進步效應和產品價格變動效應。在其基礎上,Blum(2008)[10]進一步將“兩要素—兩部門”模型擴展為“三要素(技能勞動、非技能勞動和資本)—多部門Ricardo-Viner”一般均衡模型(簡稱RV模型),將技能溢價分解為產品價格變動效應、中性技術進步效應、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效應、勞動供給效應和經濟結構轉型效應。相較于既有研究中分析單因素對技能溢價的影響,RV模型不僅可以考察部門結構性因素對技能溢價的影響,還可以將各因素納入統一框架進行比較分析。為系統考察中國技能溢價上升的驅動因素,本文運用RV模型對技能溢價進行分解,據此分析各類因素對技能溢價影響的階段性特征。
假設經濟總共由N個部門構成,其中,M個技能密集型部門,每個部門投入資本、技能勞動和非技能勞動三種要素。同時,假設產品市場完全競爭,勞動市場充分就業,規模報酬不變,消費者對技能密集型服務部門的需求滿足Cobb-Douglas偏好。那么,經濟均衡可用如下方程刻畫:
auiwu+asiws+akir=pi,i=1,2,…,N
其中,wu和ws表示非技能勞動和技能勞動平均工資,r為資本要素回報率,pi為部門i產品價格;U和S分別表示充分就業條件下非技能勞動數量和技能勞動數量。ci表示技能密集型消費的需求數量,I表示國民收入,τ表示總收入中用于消費的比重。


(1)
Φs和Φu分別表示技能勞動和非技能勞動供給的工資彈性,且滿足Φs<0,Φu<0,其表達式分別為:





第四,勞動供給效應。由式(1)可以看出,勞動供給效應對技能溢價的影響為ΦS?-ΦU,顯然技能勞動相對供給增加(?>)對技能溢價存在方向相反的兩種影響。情景一:當|ΦS|較小且|ΦU|較大時,ΦS?-ΦU>0,技能勞動相對供給增加,技能溢價上升;情景二:當|ΦS|較大且|ΦU|較小時,ΦS?-ΦU<0,意味著技能勞動相對供給增加,技能溢價會下降。對此,可用技能錯配理論予以解釋。以情景一中|ΦS|較小且|ΦU|較大為例,當勞動市場人力資本供給結構與工作崗位技能需求不匹配時,技能勞動工資對技能勞動供給的增加就會變得不敏感,即|ΦS|變得很小,遠遠低于非技能勞動工資對非技能勞動的供給彈性|ΦU|,以至于ΦS?-ΦU>0,此時技能勞動供給增加未必會降低技能溢價,甚至會出現技能勞動供給增加的同時技能溢價上升。反之,當勞動市場技能匹配性提高時,技能勞動工資對技能勞動供給的增加變得敏感,即|ΦS|變得很大,以至于ΦS?-ΦU<0,此時技能勞動相對供給增加可有效緩解技能溢價上升。
三 指標測算、數據說明與典型事實
基于技能溢價分解式(1),本文通過統計分解與計量回歸來檢驗中國技能溢價演進趨勢的動因機制。其中,統計分解部分以1990—2018年行業面板數據為研究樣本,采用反事實分解法量化分析各因素對技能溢價的動態影響;計量回歸部分則采用2003—2018年省級面板數據并結合GMM估計方法,考察各因素對技能溢價影響的階段性特征。
(一)基于1990—2018年行業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
參考Blum(2008)[10]的方法,將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的影響按照余值處理。需要測算的指標與參數包括:分行業技能勞動與非技能勞動工資水平、分行業技能勞動與非技能勞動就業人數、分行業資本存量、體現分行業Hicks中性技術進步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和相應要素需求彈性。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文并非按照《國民經濟行業分類與代碼》(GB/T 4754-2011)進行行業分類。這是因為,我國國民經濟行業的統計分類在2003年以后發生了變化,為和2003年前的行業分類數據保持一致,本文將2003年后部分行業進行合并以對應2003年之前的行業分類(4)具體地,將教育、衛生、文化體育和娛樂行業合并,將批發、零售和餐飲行業合并,將信息、租賃和居民服務行業合并為社會服務業。,按照類似1994年《國民經濟行業分類標準》(GB/T-1994)最終確定了14個行業類別,并將其按照技能密集度分為技能密集型行業組與非技能密集型行業組(5)技能密集型行業組包括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教衛文體行業,金融業,房地產業,社會服務業,國家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等6個行業;非技能密集型行業組包括農林牧漁業,采礦業,制造業,電力、熱力、燃氣供應業,建筑業,地質勘探業、水利管理業,批發、零售、住宿和餐飲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等8個行業。。

由此可以推導出技能勞動和非技能勞動工資水平表達式分別為:
(2)
由式(2)可得,如果已知分行業的平均工資與技能勞動占比,便可通過加權平均得到技能勞動工資與非技能勞動工資。歷年分行業職工人數、分行業就業人員受教育程度構成和平均工資數據均取自《中國勞動統計年鑒》。由于《中國勞動統計年鑒》只提供了2003年后的分行業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受教育程度構成數據,為保持數據一致性,本研究選擇城鎮單位為研究對象,選取分行業城鎮就業人員中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作為該行業技能勞動占比。借鑒雷欽禮和王陽(2017)[17]的處理方法,采用城鎮國有企事業單位分行業專業技術人員數,根據分行業單位負責人數比例進行修正,進而可得1990—2002年分行業技能勞動占比。最終測得1990—2018年技能溢價水平呈顯著上升趨勢(圖1),其中,1996—2002年是中國技能溢價快速上升的重要時期。

圖1 1990—2018年中國技能溢價變化趨勢
2.分行業資本存量。運用永續盤存法(PIM)測算1990—2018年分行業資本存量,采用PIM法估算資本存量的關鍵在于確定投資流量、投資價格指數、折舊率和基期資本存量等四個核心指標。此外,本文分行業資本存量測算還需要處理行業的歸并與重組問題。對此,參考楊軼波(2020)[18]的處理方法,首先估計2011年《國民經濟行業分類標準》(GB/T-2011)下城鎮單位分行業資本存量,然后將部分行業按照1994年《國民經濟行業分類標準》(GB/T-1994)進行歸并重組,從而得到與前文劃分口徑一致的分行業資本存量序列。
3.分行業Hicks中性技術進步。本文用全要素生產率作為Hicks中性技術進步的代理變量。既有研究常采用索洛殘差法測度全要素生產率,即在經濟增長要素貢獻中剔除資本和勞動要素貢獻后的余值。但索洛殘差法對生產函數形式假設過于嚴苛,且索洛殘差法測算中性技術進步會有時間趨勢,容易產生偽回歸問題。為了盡量規避中性技術進步索洛殘差法測度的局限,本文參考宋冬林等(2010)[13]的處理方法,采用DEA-Malmquist方法測度Hicks中性技術進步。

參考Blum(2008)[10]的估計方法,本文通過一個超越對數可變利潤函數方程估計各類要素需求彈性。設定在某一個時間上短期的利潤函數(π)取決于勞動價格(wu,ws)、資本存量(Kit)與技術狀態(Ti):
π(wu,ws,Kit,Ti)=max{Ui, Si}yi-(wuUi+wsSi)
(3)
lnπ(wu,ws,Kit,Ti)=ψ+ψulnwu+ψslnws+ψkilnKit+ψtTit+φu(lnwu)+φs(lnws)2
+φk(lnKit)2+φ1(Tit)2+ζus(lnwulnws)+ζuk(lnwulnKit)+ζsk(lnwslnKit)
+ζts(Titlnws)+ζtu(Titlnwu)+ζtk(TitlnKit)
(4)
利用謝潑德引理得到技能勞動與非技能勞動要素需求份額函數:
(5)

(6)
基于上述方法測算的要素需求彈性結果如表1所示。可以觀察到兩個特征:(1)所有行業技能對資本積累的交叉需求彈性均大于0,本文結果印證了Krusell et al.(2000)[16]提出的“資本—技能互補”假說,即隨著資本積累增加,企業對技能勞動的需求也會增加,而且對技能勞動需求的增加快于對非技能勞動的需求。(2)技能密集型服務部門資本與技能勞動互補性更強。表1顯示,金融、房地產、教育等技能密集型行業技能勞動對資本積累的交叉需求彈性均大于1,其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行業和教衛文體行業兩部門技能勞動對資本要素的交叉需求彈性達到2以上,遠高于制造業與農業部門技能勞動對資本要素的交叉需求彈性。表1呈現的關于要素需求彈性的兩個特征事實為基于“資本—技能互補”假說分析結構轉型因素對技能溢價的影響提供了現實依據。

表1 要素需求彈性特征
(二)基于2003—2018年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
進一步,本文通過GMM回歸方法檢驗結構轉型、Hicks中性技術進步、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以及勞動供給效應對技能溢價的動態影響,以期形成對技能溢價演進趨勢背后動因機制的穩健認識。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與統計口徑的一致性,選取樣本期間為2003—2018年。具體計量模型設定如下:
premiumqt=β0+β1Vqt+β2Zqt+δq+δt+εqt
(7)
其中,下標q表示地區,t表示年份;premium表示技能溢價水平;V表示本文重點關注的四個核心解釋變量,即地區中性技術進步、地區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地區技能勞動相對供給變量與地區結構轉型的代理指標;Z表示地區層面其他控制變量,包括地區外貿依存度和地區市場化水平;δq、δt分別表示地區固定效應與時間固定效應;εqt表示隨機誤差項。
1.分地區技能勞動、非技能勞動就業人數與技能溢價。與前文行業面板數據一致,將受教育程度在本科以上的勞動者定義為技能勞動,其他勞動者定義為非技能勞動,分地區就業人員受教育程度構成和分地區就業人員數據均來自《中國勞動統計年鑒》。用技能密集型行業與非技能密集型行業的平均工資之比表示地區技能溢價。具體地,將技能勞動占比超過70%的四個行業(金融、教育、科學研究和信息技術)歸為技能密集型行業,將非技能勞動占比超過70%的三個行業(農林牧漁、建筑業、住宿餐飲)歸為非技能密集型行業。
2.分地區結構轉型指標。鑒于本文更關注因行業技能密集度異質性而導致的結構變遷對技能溢價的影響,因此,選擇在行業層面構建結構轉型指標。根據“資本—技能互補”理論,資本要素在行業間的再配置過程會伴隨著技能勞動要素在相應行業間的再配置,進而可根據資本的行業構成變動判斷技能勞動要素的需求變化,用技能密集型行業的固定資本投資與非技能密集型行業的固定資本投資之比表示結構轉型。分地區分行業固定資本投資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
3.分地區Hicks中性技術進步與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 參考宋冬林等(2010)[13]的處理方法,采用DEA-Malmquist 方法測度地區層面全要素生產率(TFP),并以此作為地區Hicks中性技術進步的代理變量。現有研究對偏向性技術進步的測度普遍依賴于不變替代彈性生產函數(CES)假定,通過要素相對效率水平刻畫偏向性技術進步。本文認為超越對數生產函數更具靈活性,它允許要素替代彈性隨要素密集度而變化,放松了不變規模報酬假設,從而使總量生產函數更加接近于經濟現實,為此本文參考張月玲和葉阿忠(2014)[19]的研究方法,借助超越對數生產函數估計相關參數,利用估計得到的各要素替代彈性測度地區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相關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
4.地區外貿依存度與地區市場化指數。本文用外貿依存度(地區進出口貿易總額與地區生產總值之比)刻畫地區對外開放水平,相關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地區市場化指數相關數據來自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數據庫(6)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數據庫官網:http://cmi.ssap.com.cn。。
表2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初步顯示,隨著技能溢價由2003—2010年間的2.016上升到2011—2018年間的2.264,產業結構也呈現明顯轉型升級趨勢,由2003—2010年間的0.666上升到2011—2018年間的1.058;不同于既有研究結論,本文發現樣本期間中國的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演進特征總體呈現為非技能偏向性,并不構成技能溢價上升的主因;技能勞動相對供給由2003—2010年間的0.037上升到2011—2018年間的0.101,然而,技能勞動相對供給增加并未緩解技能溢價上升趨勢,這意味著簡單的教育擴張并不能緩解當前技能溢價上升的趨勢;此外,隨著國內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地區外貿依存度在樣本時期呈明顯下降趨勢,地區市場化指數呈顯著上升趨勢,表明中國市場化進程正在穩步推進。

表2 2003—2018年省級面板數據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
四 基于行業面板數據的反事實分析
本部分將基于技能溢價分解式(1),結合實際數據和要素需求彈性進行反事實分析,考察各因素影響技能溢價的階段性特征。圖2—圖5中,實線表示實際技能溢價水平,虛線表示反事實技能溢價水平,即剔除對應因素影響后的技能溢價水平。因此,當虛線高于實線時,表示剔除對應因素影響后技能溢價水平會更高,從而可以理解為該因素抑制了技能溢價水平。反之,當虛線低于實線時,表示剔除對應因素影響后技能溢價水平會更低,此時可以理解為該因素提升了技能溢價水平。接下來,本文將分別討論各因素對技能溢價的動態影響。

圖2 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的影響
1.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的影響
由圖2可見,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對技能溢價的影響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樣本早期(1990—2007年)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對技能溢價的影響并不顯著,直到2008年之后才開始明顯影響技能溢價,并在2014年后由抑制變為提升技能溢價,整體表現為“先抑制—后提升”的特征。本文研究結論與雷欽禮和王陽(2017)[17]的研究較為接近,其基于1990—2014年中國宏觀總量數據對技能溢價的分解顯示,技能—非技能效率效應(對應本文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效應)對技能溢價的抑制作用是逐年遞減的,且在2014年由負轉正。2008年以后偏向性技術進步效應開始顯著,這可能是因為金融危機以后,技能勞動整體效率增長緩慢,抑制了企業對技能勞動的相對需求,進而抑制了技能溢價的上升。2014年后技能勞動效率相對增長變快,企業轉而增加對技能勞動的相對需求,產生技能勞動對非技能勞動的替代效應,推動技能溢價上升。
2. Hicks中性技術進步的影響
由圖3可見,與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對技能溢價的影響類似,Hicks中性技術進步對技能溢價的影響也呈現“先抑制—后提升”的特征,不同的是Hicks中性技術進步影響技能溢價的轉折點出現在2008年。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在經歷了長期快速增長后,從2008年開始呈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尹向飛和歐陽峣,2019)[20]。樣本早期,隨著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勞動成本下降,企業雇傭更多的勞動,那些非技能密集度較高且非技能勞動需求彈性較大的部門受此影響更大,同時由于國民經濟中非技能密集型行業就業占比較高,經濟總體對非技能勞動的需求增加強于對技能勞動的需求,最終導致技能溢價下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后,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放緩,勞動成本上升,企業用資本替代勞動,此時,非技能密集度較高且非技能勞動需求彈性較大的部門受影響更大,從而導致總體上對非技能勞動的替代效應強于對技能勞動的替代,最終推動技能溢價上升。

圖3 Hicks中性技術進步的影響
3.勞動供給對技能溢價的影響
由圖4的反事實分析可以看出,技能勞動相對供給對技能溢價的影響與技術進步效應類似,表現為“先抑制—后提升”的趨勢,只是轉折的年份(發生在2002年前后)早于中性技術進步與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這與陸雪琴和文雁兵(2013)[21]的研究結論較接近,后者利用1997—2010年省級面板數據的結果也表明,技能勞動相對供給對技能溢價影響的轉折點發生在2003年左右。原因可能是,1999年高等教育擴招政策的實施在大規模提升技能勞動供給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加劇了勞動市場的技能錯配,使技能勞動工資對技能勞動供給增加不再敏感,乃至于出現技能勞動供給增加的同時技能溢價仍然上升的趨勢。對此,周敏丹(2021)[22]也曾指出,教育擴招后,勞動者人力資本結構與工作崗位技能需求不匹配的結構性問題突出。
4.結構轉型因素對技能溢價的影響
圖5對結構轉型效應的反事實分析結果顯示,長期以來,結構轉型效應都呈現為提升技能溢價的特征,特別是2001年以后,結構轉型因素對技能溢價的提升效應變得更為顯著。本文研究結果與郭凱明和王鈺冰(2022)[1]的分析結果相似,均表明不同技能密集度行業間結構變遷是技能溢價上升的重要驅動力。提及產業結構轉型的潛在動因,當前研究主要從需求和供給兩方面解釋:(1)以Kongsamut et al.(2001)[23]、Foellmi和Josef(2008)[24]為代表的學者從需求側消費者的偏好異質性解釋結構轉型,即隨著居民收入增加,消費需求會從收入彈性較低的生活必需品部門轉向收入彈性較高的享受型服務部門,生產要素也將隨之流向該部門;(2)以Ngai和Pissarides(2007)[25]為代表的學者指出,供給側全要素生產率差異是產業結構轉型的重要因素,生產要素從全要素生產率較高的部門向全要素生產率較低的部門流動是結構轉型關鍵因素。Blum(2008)[10]研究明確指出,雖然不同部門技術進步差異是推動要素由農業部門向非農部門轉移的重要因素,但沒有證據表明技術進步差異是引起要素由制造業流向服務業的決定因素。所以,對正處于轉型時期的中國而言,資本在不同部門間配置更可能是因為需求側消費結構向技能密集型服務部門轉型升級引致的產業結構向技能密集型服務部門轉型升級,從而技能密集度較高且資本與技能勞動更加互補部門的資本快速積累提升了技能溢價。
五 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回歸分析
上文采用反事實分析方法分析了各因素對技能溢價的動態影響,結果表明各因素均會顯著地影響技能溢價,且在不同時期表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本部分將基于省級面板數據,采用回歸分析法進一步檢驗上述結果的穩健性。
基于面板數據固定效應模型的基準回歸結果(表3)顯示,就2003—2018年整體而言,結構轉型因素與技能勞動相對供給對技能溢價影響較大且顯著為正,Hicks中性技術進步與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的影響較弱,甚至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的影響不顯著。分階段的回歸結果表明,結構轉型因素的影響在增強,2003—2007年間其影響系數為0.0656,2008—2013年間其影響系數為0.3248,2014—2018年間其影響系數上升為1.0597;Hicks中性技術進步對技能溢價的影響在2008—2013年間由負轉正,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的影響系數雖然也在同期由負轉正,但其影響系數較小且不顯著,直到2014—2018年,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的影響才顯著增強;技能勞動相對供給效應在2003—2007年間影響較大,此后有所下降但仍顯著為正,表明中國勞動市場技能錯配問題依然存在,雖然其影響在降低。上述各因素對技能溢價的影響方向和階段性特征與前文反事實分析法的結果基本一致。

表3 面板數據固定效應模型(OLS回歸)
考慮到技能勞動相對供給可能內生于技能溢價,即解釋變量技能勞動相對供給與被解釋變量技能溢價之間可能因互為因果關系而產生內生性問題,最終導致估計結果有偏不一致。本文選取技能勞動相對供給變量的滯后一期作為工具變量進行2SLS回歸分析。另外,考慮到地區間截面異方差的存在,本文還采用廣義矩估計(GMM)方法進行穩健性分析。
為檢驗2SLS回歸中工具變量是否為強工具變量,本文進行了不可識別檢驗與弱識別檢驗,LM統計量與Wald F統計量結果表明可以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工具變量識別不足和弱識別的原假設。為驗證工具變量的外生性,對工具變量進行過度識別檢驗,并報告了Sargan檢驗的伴隨概率,P值均大于0.2,表明無法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工具變量是過度識別的原假設。類似地,在GMM估計過度識別檢驗中,Sargan檢驗的伴隨概率與Hansen J檢驗的伴隨概率均大于0.1,無法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工具變量是過度識別的原假設。GMM估計中一般允許擾動項的一階差分存在自相關,即AR(1)的P值小于0.1,但不允許擾動項二階差分存在自相關,也就是AR(2)的P值應該大于0.1,顯然,本文結果滿足上述條件。表4基于2SLS和表5基于GMM的回歸分析中,各類因素對技能溢價的影響特征均印證了前文反事實分析的結論,表明本文研究結論較為穩健。

表4 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計結果

表5 廣義矩估計(GMM)結果
六 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從整體性與歷史性視角刻畫中國技能溢價上升的來源、機制和動態演進趨勢,得到的主要結論為:(1)各行業均滿足資本—技能互補條件,且技能密集型服務行業資本—技能互補性更強;(2)產業結構轉型長期提升了技能溢價,且其影響呈增強趨勢;(3)中性技術進步與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對技能溢價的影響均呈現“先抑制—后提升”的特征,其轉折點分別在2008年、2014年前后;(4)可能源于勞動市場的技能錯配,技能勞動供給增加并未有效緩解技能溢價上升,反而在2003年后顯著提升了技能溢價。綜合上述各因素對技能溢價的影響特征不難推斷:未來一段時期內,中國技能溢價仍將呈現上升趨勢,這與共同富裕的遠景目標明顯相悖。
當前,中國正處在劇烈的社會與經濟轉型過程中,技能溢價上升的驅動因素復雜多變。因此,政府部門應高度重視技能工資收入差距擴大趨勢,把縮小技能工資收入差距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之一。技術進步動態演進與產業結構轉型背景下,應兼顧勞動市場的需求側,逐步調整當前教育培養模式,注重對個體職業能力的培養,構建與勞動市場技能需求相適應的新人力資本積累體系。同時,積極推動要素市場化改革,以資本、技能密集型服務行業為重點,促進不同技能群體工資收入公平分配。具體而言:
(1)重視結構轉型升級對勞動技能需求結構的影響。產業結構變遷無疑將重塑勞動市場的技能需求結構。Deming(2017)[26]基于美國數據研究發現,那些密集需要社交能力和認知能力的技能型服務類職業(如管理者、心理咨詢師、教師等)無論就業數量還是工資增長都遠遠高于其他職業類別。因此,要切實提升勞動力自身應對經濟變革的根本能力,這既包括數據分析、演繹推理、書面表達等認知能力,同時由于產業結構轉型與組織方式變革,還需提升從業者的服務感知、社交協調等非認知能力以緩解不斷攀升的技能溢價,進而為實現高質量就業構建更加完備的人力資本積累體系。
(2)關注不同類型技術進步對技能溢價的動態影響。長期以來,以信息通訊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為代表的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引起各界對技術性失業的高度關注與熱烈討論,然而,本文研究顯示,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對技能溢價的影響并非單調,而是呈現“先抑制—后提升”的特征,總體而言并不構成中國技能溢價上升的主因,而隱藏在產業結構變遷中的中性技術進步可能發揮著更為重要的作用。因此,應當充分考慮不同部門內部中性技術進步對不同技能類型人才需求的影響,優化人力資本投資結構,完善技能培訓機制,改善部門技術進步與勞動匹配結構失衡,尤其需要重視提高非技能勞動對技術進步和高新技術應用的適應性。
(3)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并消除對職業教育的偏見。職業教育前景廣闊,大有可為。推動職業教育發展需要科學評估勞動市場技能需求變化,提高職業教育的財政支持力度,提升職業教育質量,完善職業資格證書和技能證書認證體系。此外,社會大眾對職業教育群體的重視和保障同樣不可忽視。國務院2019年印發的《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明確指出“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是兩種不同教育類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消除對職業教育的偏見,讓更多接受職業教育的人有更兜底、完善的保障,才能真正實現職業教育的目標。
(4)積極推動要素市場化改革,保障不同技能勞動者共享發展成果。加強對房地產、金融、科技等領域的監管,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嘗試通過引入資本利得稅以保障不同勞動群體分享發展紅利。壯大實體經濟,發揮資本在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過程中的引領作用。穩定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比重,增強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的就業帶動作用。破除勞動要素跨部門跨區域的流動壁壘(特別是戶籍制度),抑制要素市場分割趨勢,積極推進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提高勞動市場匹配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