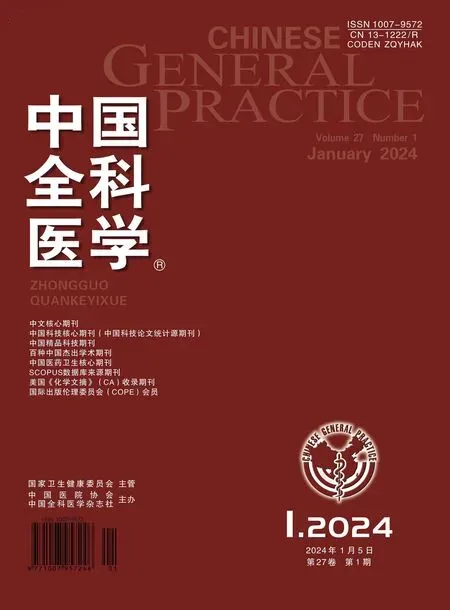將WHO《心理健康差距干預指南》應用于中國全科醫學服務:一項德爾菲研究
Kendall Searle,Grant Blashki,Ritsuko Kakuma,楊輝,呂淑榮,李寶琪,肖瑩瑩,Harry Minas
1.VIC 3010 Global and Cultural Mental Health Unit,Centre for Mental Health,School of Population and Global Health,University of Melbourne,Parkville,Australia
2.VIC 3010 Nossal Institute for Global Health,University of Melbourne,Melbourne,Australia
3.WC1E 7HTE 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London,England,UK
4.VIC 3168 Monash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ducation,School of Primary Health Care,Monash University,Notting Hill,Australia
5.518107 廣東省深圳市,中國科學院大學深圳醫院(光明)
1 背景和立題依據
作為中國最早的經濟特區之一,人口接近1 800 萬的深圳市以其先進的社會經濟發展和改革聞名全國,乃至世界[1-4]。深圳市穩步建立了龐大的社區健康服務中心(CHC)網絡,全科醫生作為居民醫療服務的第一接觸點,發揮著重要作用[5-7]。鑒于總體上精神障礙流行率的增加及重點、脆弱人群抑郁障礙患病率的升高[8-16],衛生行政部門在發展全科醫學服務的過程中,要求加強對常見精神障礙的識別和預防[17]。具體做法之一是提升全科醫生的心理健康工作技能水平[18-20],每個CHC至少有1 名具有心理健康認證的全科醫生[21]。但在對深圳市全科醫學中層負責人的質性研究中發現,隨著工作的深入推進,全科醫生需要更好地獲得抑郁障礙服務的診斷指南和方案[22]。
指南是證據的合成,以建議的形式呈現給服務提供者,從而讓患者得到“獲得最高服務質量”的機會[23]。把指南信息從一個環境分享到另一個環境,可以避免重復研究工作,并可以在資金不足的情況下優化資源使用[24-25],這已經成為被全球醫療保健領域廣泛接受的方法[26]。WHO《心理健康差距干預指南》第2 版(mhGAP-IG.v2)[27]中關于抑郁障礙的指南,為深圳市CHC 提供了一個經過嚴格開發并獲得國際批準的資源[28-29],其可以支持經過培訓的全科醫生開展對抑郁障礙和其他主要心理健康問題患者的評估、管理和隨訪[30-31]。mhGAP-IG.v2 納入了基于循證和經濟上可負擔的治療方案,適合在社區和資源不足的環境中使用[32]。
mhGAP-IG.v2 是一個通用工具,需要根據中國特色的初級衛生保健環境和文化背景進行調整。部分國家的全科醫生可以獨立使用篩查量表,可以獨立對抑郁障礙做出診斷并開展藥物治療[33-36]。但在中國,只有精神病學專家才具有診斷抑郁的法律權力[37]。醫院或專科機構負責開具治療方案和藥物處方,初級保健醫生的治療獨立性有限[7]。此外,過往事件也會影響居民目前的態度和行為,成為抑郁障礙表達和尋求服務的障礙[38-40]。雖然mhGAP-IG.v2 與國際分類系統[如《國際疾病分類》第10 版(ICD-10)、《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4 版(DSM-Ⅳ)]高度一致,但最初是根據西方醫院場景中臨床表現開發的,因此可能與其他文化背景不夠契合,并難以在社區環境下識別隱約難辨的抑郁表現。
規范化調整mhGAP-IG.v2 的方法仍在開發中[41],咨詢mhGAP-IG.v2 最終使用者的建議才能確保指南的適用性,促進指南的實施[30,42-43]。由于中國初級保健代表并未參與mhGAP-IG.v2 的起草,mhGAP-IG.v2 可能會忽略中國初級保健的實際做法或轉診方面的信息。本研究提出的問題是:為了提高mhGAP-IG.v2 的適用性,CHC 全科醫生認為要對其中的抑郁相關表述做哪些調整?
本研究旨在對mhGAP-IG.v2 進行調整,使其對中國全科醫生具有知識相關性和實際可接受性。本研究采用德爾菲法[44-47],希望能獲得深圳市全科醫生是否需要對mhGAP-IG.v2 中相關表述進行調整的共識,以及全科醫生對mhGAP-IG.v2內容和結構調整的具體建議。本研究在指南適應性研究中的獨特性,是關注國際指南對中國基層醫療中抑郁障礙診治的適用性[30,43,48-50]。這是第一項在中國進行的基層醫療指南適應性研究。
2 對象與方法
2.1 招募參加者
全科醫生自愿參加本研究。7 位在深圳市5 個區工作的全科醫生負責招募,通過所在區的基本醫療系統傳播研究信息,根據倫理學要求分發簡明文字聲明,并分發和回收知情同意書。本研究主持人給每名同意參與的全科醫生安排參加者注冊,并提供受密碼保護的在線調查鏈接。
2.2 納入與排除標準
被邀請醫生在CHC 承擔基本醫療工作,每星期至少給50 位患者看診。醫生需自述對心理健康感興趣,或有初級保健心理健康服務證書。分別在深圳市城區、郊區和邊界區的CHC 招募醫生,以增加參與者的異質性。調查材料用中文形式提供,不要求參加者的英語水平。
2.3 參加者規模和地理分布
75 名全科醫生(51%為女性)參與了第1 輪調查,其中大多數全科醫生在近郊區CHC 工作(55%),其次是城區(35%),再次是遠郊區和邊界區(10%)。參加第2 輪調查的全科醫生有59 名(保留率為79%)。盡管有全科醫生退出調查,但在兩輪調查中,按地區和性別劃分的總體百分比相似。具有心理健康服務證書的全科醫生參與兩輪調查的可能性更高。
2.4 德爾菲問卷開發
交給全科醫生做判斷的表述是通過本研究之前的質性研究主題分析產生的[51],該質性研究咨詢了全科醫生對mhGAP-IG.v2 在CHC 使用的可接受性、適用性、可轉移性觀點。納入德爾菲調查的表述包括10 個方面:(1)“以人為本”的指南;(2)抑郁障礙的表現特征;(3)篩查工具的獲得和使用;(4)醫療服務及社會系統的內部關系;(5)藥物治療選擇;(6)雙相障礙中的躁狂和抑郁發作;(7)針對抑郁的溝通;(8)隨訪;(9)管理患者信息;(10)指南的整體結構。將mhGAP-IG.v2 中這些表述提取出來并翻譯成中文,經過回譯測試,并邀請3 名深圳市CHC 醫生和2 名澳大利亞全科醫生/研究人員做預調查,對咨詢內容進行迭代完善。最后提出199 條表述,作為本德爾菲研究的咨詢內容。
使用Likert 5 級計分法對表述進行評分,請參加者判斷“如要把該表述用在深圳市,是否贊同調整其內容和結構”,5 分表示“肯定贊同”,4 分表示“有些贊同”,3 分表示“既不贊同也不反對”,2 分表示“有些不贊同”,1 分表示“肯定不贊同”。預先設定“達成共識”的條件:如>80%的全科醫生選擇“有些/肯定贊同”調整某表述,則視為全科醫生對調整該表述達成共識;如>80%的全科醫生選擇“有些/肯定不贊同”調整某表述,則視為全科醫生對不調整該表述達成共識。參加者也有機會提出添加其他表述,或通過開放式提問表達保留意見。
2.5 調查和分析過程
在Qualtrics 調查平臺進行兩輪調查,第1 輪的開展時間為2019 年12 月—2020 年1 月,第2 輪的開展時間為2020 年12 月—2021 年2 月。主要研究人員負責對每輪信息進行分析,并向參加者反饋。在第1 輪調查中,參加者對152 個表述(76%)達成需調整的共識。研究者對開放式答復進行了評估,參加者沒有提出新的表述。在第2 輪調查中,研究者把47 條未達成調整共識的表述重新提交給參加者,并附第1 輪調查的平均分。第2 輪調查返回的數據顯示,有6 個表述獲得需調整的共識。最終共識的需調整表述數量為158 個(占所有表述的79%),對其他41 個表述(占所有表述的21%)未達成需調整的共識。最后,通過將共識(和非共識)項目與mhGAP-IG.v2 的相關部分進行比較,提出對mhGAP-IG.v2 的調整建議。從問卷開發到達成表述調整共識的德爾菲過程見圖1。

圖1 從問卷開發到達成是否需要調整共識的德爾菲過程Figure 1 Delphi process from questionnaire development to statement consensus
2.6 倫理學審批
本研究于2019 年11 月經墨爾本大學人口與全球健康學院(MSPGH)的人類倫理學評估小組(HEAG)審核批準(倫理學批準文號:1,852,773.1)。
3 結果
3.1 參加者特征
參加者平均擁有超過6 年的全科臨床服務經驗。在第1 輪調查中獲得心理健康服務證書者占15%,在第2輪調查中獲得心理健康服務證書者占24%,即有證書者更傾向于完成德爾菲調查;參加者所在CHC 至少有另1 位有證書全科醫生的比例,從第1 輪的57%增加到第2 輪的68%。參加者所在的團隊有7~8 名醫生。開展第2 輪調查時,正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COVID-19)疫情期間,故參加者每周接診患者的數量(176 名/周)低于第1 輪(275 名/周),醫生記錄的抑郁患者數量(1.9名/周)也低于第1 輪(2.7 名/周)。
3.2 主要結果
參加者同意對mhGAP-IG.v2 中199 條涉及抑郁障礙表述的158 條進行調整,調整建議的平均得分從第1輪的4.25 分提高到第2 輪的4.26 分。10 個主題的平均分為4.05~4.65 分,其中“'以人為本'的指南”獲得最高平均分(即全科醫生最贊成調整該條目),“隨訪”獲得最低平均分(即全科醫生最不贊成調整該條目)。
在第1 輪調查中,“'以人為本'的指南”和“雙相障礙中的躁狂和抑郁發作”兩個主題的所有條目達到了100%的調整共識。由于第1 輪調查達成共識的程度比較高,故第2 輪在47 個表述中得到新的調整共識的程度有限。波動最大的是對“隨訪”主題的調整看法,在兩輪調查中,對“隨訪”主題進行調整的共識百分比從61%增加到73%。在兩輪調查中,任何主題的任何表述沒有被直接拒絕(表1)。

表1 按主題劃分的第1 輪和第2 輪德爾菲調查獲得的共識Table 1 Wave 1 & 2 Delphi survey consensus by thematic domains
表2為兩輪德爾菲調查后獲得共識表述的調整建議,其按10 個主題分組,并根據各主題平均得分遞減列出。

表2 全科醫生對mhGAP-IG.v2 條目的調整建議Table 2 Primary care recommendations for an adapted mhGAP-IG.v2
4 討論
4.1 評估指南的特定背景需要
本研究是在對深圳市全科醫生進行初步研究的基礎上開展的[51]。研究證實了CHC 醫生傾向于認為抑郁診斷是基于“一系列癥狀,而非核心癥狀”,如表2 中的8.3,全科醫生認為應該把核心癥狀和附加癥狀合并到mhGAP-IG.v2 的癥狀列表中,這反映出初級保健的務實性。這一建議可以避免過早地排除潛在診斷,進而有利于病情的持續監測和服務。這也意味著全科醫生有機會突破僅由專家開發mhGAP-IG.v2診斷標準的局限,而是采用更適合初級保健的生命全程方法(即抑郁是一種復雜的多維疾病,其癥狀可以在一生中以任何順序出現)來做出判斷[33,52-53]。盡管本研究參加者不贊同前期研究中把抑郁的軀體癥狀、焦慮及其他行為指標都納入列表的建議[51],但參加者普遍認為mhGAP-IG.v2 應建議醫生探索有哪些觸發潛在抑郁的風險因素,并闡明抑郁是如何隨時間變化的。
本研究的一個關鍵結果是:全科醫生一致認為應該對整體mhGAP-IG.v2 進行調整,并重點加強初級保健對有自殺風險患者的監督責任。這需要重新組織、制訂mhGAP-IG.v2 中的決策流程,以便在患者早期就診時就檢查出自殺企圖的既往史,發現癥狀列表中的自殺傾向,并將醫生引導至mhGAP-IG.v2 的自殘模塊。這些調整既符合中國“到2030 年將自殺率減少30%”的目標[54],也響應了當地對某些職業人群和弱勢群體自殺率高的擔憂[55-56]。國際上類似的做法是突尼斯的情景化研究,其也將自殘和自殺確定為優先管理的精神障礙[50]。
盡管西方有一些經過驗證的、可供全科醫生使用的抑郁量表,但mhGAP-IG.v2 并沒有提供可以在全科醫療服務中使用的抑郁篩查工具指南[57]。既往研究結果表明,CHC 沒有標準且統一的抑郁篩查工具[22]。本研究的參加者看到了機會,認為應該在mhGAP-IG.v2 中補充該方面內容,以鼓勵CHC 采用適當的篩查工具(假設接受適當的培訓)。參加者們認為應該讓護士有機會參與抑郁篩查過程,并應該在mhGAP-IG.v2 中強調(表2 的5.3)。參加者對抑郁管理的開放態度,反映了CHC 團隊服務中對任務進行授權分擔的需求,全科醫生愿意采用團隊模式來改善抑郁的篩查和管理,而非依靠個人。
參加者不認為應調整mhGAP-IG.v2 中所有的表述內容,比如其認為應該保持與雙相障礙有關的所有指南信息。據報道,中國的雙相障礙患病率較低[58]。初步研究表明,初級保健醫生對此知之甚少,并認為這是需要專科診治的嚴重精神疾病[51]。全科醫生尊重mhGAP-IG.v2 提出的在初級保健培訓中加強培訓以彌合差距的建議,并認為應該在mhGAP-IG.v2 中保留鑒別和治療抑郁和雙相障礙(抑郁發作)的建議。
4.2 應對衛生系統差異
將本研究結果與前期研究和其他情境化研究結果進行比較,以確定mhGAP-IG.v2 中針對特定國家(地區)的轉診選擇和醫療專業人員職責劃分的適宜性[30,48,50]。中國已經提出將精神衛生納入基層醫療范疇[59-60],但仍期待有關鍵政策文件能提供如何改革和管理的詳細信息[61-62]。雖然許多西方國家全科醫生已經能積極參與抑郁的診斷和治療[63-64],但中國仍由精神科醫生主要負責抑郁的診斷和治療,因此不同國家的系統間做法有很大不同[37,65]。對mhGAP-IG.v2 的調整研究給擁有心理健康服務證書的CHC 醫生在心理健康方面的發展提供了更多機會[21-22],并能加強CHC、綜合醫院、家庭在精神衛生服務中的參與度(表2 的4.1~4.4)。
這項深入的研究能讓全科醫生認可與緊急心理服務相關的指南內容,特別是將初級保健服務與社區機構(如社會服務、公安機關、學校、志愿部門、殘障人士聯合會)、雇主和家庭相結合的內容。全科醫生更傾向于和強有力的社區、家庭結合,這一關注點既有文化先例也有法律先例。中國的精神衛生法規定,家庭成員必須負責照顧有精神健康問題的家庭成員(即幫助管理藥物、確保患者就診、進行情緒監測)[37,53,61-62]。其他公共衛生干預措施(如精神健康問題緊急援助)也根據法律要求來識別和支持社區中的抑郁病例[66]。目前,mhGAP-IG.v2的管理和隨訪部分僅強調了醫生的疾病管理責任,這與將心理健康納入更廣泛的、社區參與的衛生體系的做法不一致。
4.3 考慮當地可用的藥物治療
與其他對指南的情境化研究[30,48]一樣,本研究強調了抗抑郁藥物清單應與國家處方要求保持一致。如果CHC 沒有使用抗抑郁藥的標準,則應提供可提供處方的機構及藥物報銷規定。全科醫生還認為應該使用最新一代選擇性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SSRI)藥物清單,并建議給出品牌名稱舉例,以提高指南的更新頻率。在深圳市這一人均可支配收入較高的城市[67],患者也會意識到藥品能從面向消費者的市場直接獲得。然而,在mhGAP-IG.v2 中不宜給出藥物品牌名,因為指南應保持中立,避免利益沖突,而衛生行政部門也希望能避免過度處方和潛在藥物成癮的發生。
4.4 接受“以人為本”的指導方針
本研究在情景化研究中的獨特之處是探索全科醫生(作為指南的最終用戶)對在mhGAP-IG.v2 中納入“以人為本”建議的看法。WHO“以人為本”的綜合服務框架指出:所有人可以平等地獲得優質的衛生服務,這些服務是滿足生命歷程需要的,尊重社會偏好的,在整個服務過程中得到協調的,并且是全面、安全、有效、及時、高效和可接受的;所有服務人員積極主動、技術熟練,并在獲得支持的環境中工作[69-70]。“以人為本”的核心是患者“賦能”,在患者主導的就診期間尊重患者的治療偏好,并與患者“共同制定”治療管理計劃。本研究參與者普遍接受mhGAP-IG.v2“以人為本”的主題,并贊同開發和使用患者管理計劃。全科醫生更喜歡以行動為導向的計劃,以清單的方式逐項列出“以人為本”的做法,而不是當前版本那樣使用原則性的術語(如“評估改進”“評估當前治療的參與和體驗”)。全科醫生希望由具有心理健康服務證書的全科醫生制定患者管理計劃,這可以給指南的背景化和長期可持續使用帶來潛在好處。
由全科醫生制定抑郁的患者管理計劃還有其他優點。中國正在加快建立社區精神衛生康復服務機構[71],全科醫生的工作可能與這些精神康復服務有合作或重疊,應預見式地避免服務提供者之間溝通和協調不暢問題[22]。由最接近和熟悉患者的全科醫生制定“以人為本”的管理計劃,可有效地在服務提供者之間共享患者記錄,簡化服務在提供者之間的轉介過程。
4.5 情境化的健康教育
全科醫生認為要對mhGAP-IG.v2 中絕大多數“改善社會心理交流”的表述進行調整,這表明患者教育信息的情景化是有相當大改進空間的。調整這些表述意味著全科醫生要給患者提供更好的信息(表2 中的3.1~3.4),并提高社區對抑郁的認識,強調要以當地參與模式(即以前的成功案例)來實現患者教育的目標。這需要全科醫生掌握專業“軟技能”(如傾聽和同理心)。盡管有證據表明“軟技能”對治療結果有積極影響[72-74],但其在醫學院教育中卻經常被忽視[75]。一項近期發表的研究關注亞洲(包括中國)衛生專業人員與患者之間復雜和特定背景的溝通互動特點,發現亞洲專業人員需要掌握比西方專業人員更多的溝通方法才能為患者提供適合文化背景的醫學服務[76]。在深圳市這樣的新型“移民城市”,患者的心理教育需求因居住區和原籍而異,故患者教育的方法也需要做更多的考慮。
5 研究的局限性和進一步研究計劃
5.1 本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的局限性與COVID-19 疫情相關,COVID-19 疫情發生時間與本研究開展時間有重疊,使得原設計在實際開展中可行性較低,直接影響了研究結果。包括:(1)第2 輪調查延遲,從預定的間隔1 個月變成間隔近1 年,與時間相關的衛生系統變化因素和醫生的觀點改變在分析時難以控制(如醫生心理健康認證的增加、CHC 負責人層面的內部變化)。(2)參與調查的全科醫生保留率下降了21%。幸運的是,研究設計考慮到了額外招募,允許潛在的失訪,因此參與者的最終數量滿足研究需求[59],且納入全科醫生所處的地理位置分布良好。本研究的實際參加人數仍然遠高于建議的最小人數(10~18 人)[77]和德爾菲研究要求的穩定性人數[78]。(3)經過兩輪在線調查后決定終止研究,研究結束時全科醫生對21%的表述仍未達成進一步共識。雖然許多德爾菲研究繼續進行第3 輪調查,以遵循實現共識的方法論原則[45],但在心理健康領域進行兩輪德爾菲的研究并不罕見[79-80]。在這種情況下,兩輪調查之間只產生了微小的共識變化,可以說任何進一步的研究均會產生更小或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觀點變化。此外,79%達成共識的表述所產生的信息主體為指南調整已經提供了豐富、具體和詳細的方向。
本研究旨在獲取全科醫生的觀點,但并非僅有全科醫生提供抑郁診療服務。因此,對指南的進一步研究應向更多的利益相關者尋求建議,包括接受轉診的專家團隊、與康復有關的其他社區機構,以及患者的看法。
最后,全科醫生可能難以理解之前研討會中的一些概念/項目翻譯。為了最大限度地減少翻譯問題,所有項目由一位經驗豐富的翻譯人員進行回譯,并在進行正式調查前由2 名精通雙語的深圳市CHC 醫生進行測試。
5.2 建議的進一步研究方向
(1)開發培訓軟件/在線模塊,以滿足當地需要,并與試點地區分享研究結果,以獲得進一步咨詢和測試結果。(2)制定患者管理計劃,全科醫生與多個合作伙伴(包括家庭)分擔服務,請各方參與到患者的社區康復中。認真咨詢有生活經歷者,以幫助確定這些互動的性質和內容。(3)進行質性研究,探索全科醫學如何更好地教育社區居民認識抑郁,并遵從醫療指導。(4)擴大研究范圍,考慮到焦慮問題及焦慮、抑郁共病問題的診斷和治療。(5)探索研究結果的可轉移性,使其能夠適應中國其他社區健康服務場所。(6)重要的是要把修訂的mhGAP-IG.v2 提交給國際醫療保健研究者進行評估,以保證其他國家可以分享相似(或不同)的發現,并為更新全球服務標準的持續對話做出貢獻。
6 結論
對mhGAP-IG.v2 的調整與深圳市CHC 醫生的決策內容和算法流程完善過程一致。全科醫生同意實施的指南應該與通用指南有所不同,能實施的指南應該適應當地居民抑郁問題的具體情況、衛生系統組織形式、初級保健治療的優先級和可及性,以及中國對21 世紀“以人為本”的健康服務的總體愿望。本研究的獨特之處是全科醫生認為自身更喜歡能反映疾病發展過程的指南,以及記錄更廣泛的精神健康團隊和家庭參與范圍的指南。全科醫生認為mhGAP-IG.v2 應該包含雙相障礙患者診斷和治療的關鍵措施,即便這些措施超出了其目前的實踐標準。針對深圳市背景的mhGAP-IG.v2 調整,不僅給當地CHC 提供了相關培訓工具,而且還為其他國家提供了額外的資源,使其能夠進一步改進對抑郁問題的診療和服務。
致謝:感謝所有參加研究的深圳市全科醫生,在COVID-19 疫情防控期間,醫護人員面臨困難、壓力和巨大工作負荷,感謝其愿意抽出寶貴時間參與兩輪研究。也非常感謝本研究學術督導組7 名成員的持續支持,督導組的專業建議為研究的成功完成提供了助力。
作者貢獻:Kendall Searle 負責設計、協調和開展德爾菲研究,分析數據,并起草手稿;Grant Blashki、Ritsuko Kakuma、Harry Minas 為研究設計提供建議,并對研究過程提供支持;楊輝促進了與深圳市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持續聯系,并就文化適應問題提出寶貴建議;呂淑榮為德爾菲方法提供方法和軟件培訓,并提供具有文化敏感性的翻譯支持;李寶琪、肖瑩瑩負責翻譯項目報表,并就如何執行和完成招募提供具體方案;所有作者對文章初稿發表了意見,并對文章終稿進行校對。
本文無利益沖突。
(原文見:https://ijmhs.biomedcentral.com/articles/10.1186/s13033-022-005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