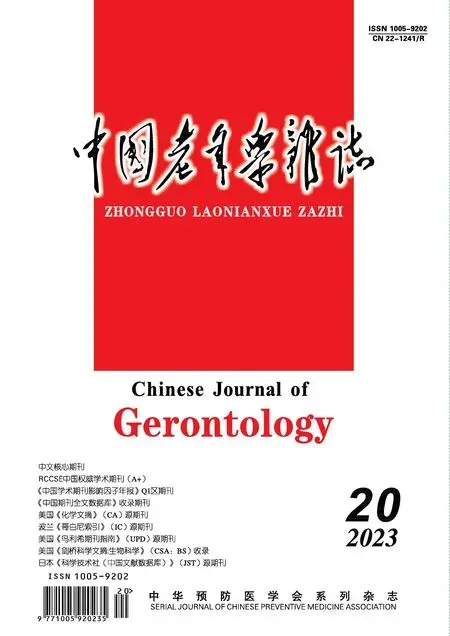老年脊柱全麻患者術后不同拔除尿管方案的臨床效果對比
耿貴敏 王艷 羅順梅 蔡小軍 申雄成 鐘天才
(遵義市第一人民醫(yī)院(遵義醫(yī)科大學第三附屬醫(yī)院),貴州 遵義 563000)
排尿過程是尿液經腎臟生成后經輸尿管存儲于膀胱中,并經尿道排出體外〔1〕,是受中樞神經系統(tǒng)控制的復雜反射活動,其易受多種因素干擾。脊柱全麻手術時間較長且術中出血量較多,加之老年患者身體功能逐漸衰退,其對手術質量的要求更為嚴格,臨床為了避免老年脊柱全麻患者尿潴留發(fā)生,常在術前留置尿管以觀察患者尿液,指導臨床補液,以保障手術質量〔2〕。但尿管留置時間越長,患者出現(xiàn)尿道疼痛、麻醉蘇醒期躁動、泌尿系統(tǒng)感染等風險越高,嚴重影響患者的術后康復進程〔2〕。且相關研究證實,在醫(yī)院獲得性感染中,尿管相關性尿路感染占比高達40%,尿管留置時間與感染發(fā)生率呈正比,尿路感染與尿管置入時間呈線性增加〔3~5〕。因此,在患者術后早期拔除尿管具有積極意義。但目前,臨床上關于尿管拔除時間及拔管操作規(guī)范甚少且未達成統(tǒng)一標準。因此,探究老年脊柱全麻患者術后尿管拔除時機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脊柱全麻術后常規(guī)次日拔除尿管及麻醉清醒后即拔除尿管是臨床上較為常用的兩種尿管拔除方案,但關于這兩種方案對老年脊柱全麻患者的影響及安全性尚存爭議。基于此,本研究旨在對比老年脊柱全麻患者術后不同拔除尿管方案的臨床效果。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本研究經醫(yī)院醫(y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選取2021年4月至2022年2月在遵義市第一人民醫(yī)院實施全麻脊柱手術治療的108例患者,依據入院次序依次將病例編號分為A組及B組,各54例。A組男30例,女24例;年齡60~75歲,平均(62.74±6.39)歲;手術持續(xù)時間2.0~3.5 h,平均(2.46±0.14)h;基礎疾病:高血壓23例,糖尿病7例。B組男29例,女25例;年齡60~73歲,平均(62.28±6.28)歲;手術持續(xù)時間2~3 h,平均(2.51±0.11)h;基礎疾病:高血壓20例,糖尿病9例。兩組一般資料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研究具有可對比性。患者及其家屬均自愿簽署知情同意書。
1.2入選標準 納入標準:①符合脊柱全麻手術指征;②凝血功能、肝腎功能正常;③入院前并未留置尿管;④均使用統(tǒng)一型號的導尿管。排除標準:①患者有其他影響排尿功能的疾病,如盆腔損傷、脊髓損傷等;②尿管置入過程中損傷尿道;③不能堅持配合研究方案;④存在自身免疫系統(tǒng)疾病或血液系統(tǒng)疾病;⑤存在感染性或傳染性疾病。
1.3全麻 兩組術前均行尿常規(guī)檢查,術前常規(guī)禁食8 h,禁飲4 h,并視患者口渴及手術時間情況補充適量平衡鹽溶液。患者均由同一組醫(yī)師進行脊柱全麻手術,患者入室后開放靜脈通路,監(jiān)測生命體征,行麻醉誘導,靜脈注射0.1~0.2 mg/kg羅庫溴銨、15~20 mg依托咪脂、0.02~0.04 mg/kg咪達唑侖、舒芬太尼15~20 μg,誘導成功后,行氣管插管全麻,術中0.5 μg/(kg·h)右美托咪定,0.5~2.0 μg/(kg·h)瑞芬太尼持續(xù)泵入,七氟烷1%~3%吸入維持麻醉。A組術后次日或第2日,告知患者需進行拔除尿管操作,指導患者取仰臥位,充分暴露外生殖器部位,應用碘伏消毒外生殖器,打開導尿管將膀胱內尿液流盡后,備好排尿器,應用20 ml的注射器將尿管氣囊中的氣體抽吸干凈后,輕輕牽拉導尿管,使尿管順尿道的自然彎曲順暢拔除,拔除過程中需叮囑患者避免過度用力,尿管拔除后,再次進行尿道外口消毒,完成拔除尿管操作。留置尿管期間均不夾閉尿管,不進行膀胱功能鍛煉。B組術后返回病房后,采用Steward蘇醒評分量表評估麻醉清醒,量表共包括清醒程度,呼吸道通暢程度及肢體活動程度3個指標,每項指標采用2級評分法(0~2分),總分6分,Steward蘇醒評分6分為完全清醒,患者完全清醒后,應用碘伏消毒外生殖器,采用注射器接氣囊管道外口,讓氣囊內的液體自動流出,使氣囊表面需維持在柔軟、光滑狀態(tài),避免負壓所致的氣囊皺襞銳角,進而在拔除尿管過程中損傷尿道黏膜,男性患者拔除尿管時采需提起陰莖,使其與腹部成60 °,輕輕拔除尿管。留置尿管期間均不夾閉尿管,不進行膀胱功能鍛煉。
1.4評價指標 尿管相關膀胱不適分級情況,應用醫(yī)院自制的尿管相關膀胱不適分級表進行評估,0級:無不適癥狀;1級:輕度不適,被詢問時主訴存在不適癥狀,但不影響日常活動;2級:中度不適,患者主動表達下腹存在憋脹感、尿急尿痛或恥骨上弓排尿感等不適癥狀,無行為反應,尚可忍受;3級:重度不適,患者存在顯著下腹憋脹、尿急尿痛等不適癥狀且難以忍受,伴煩躁不安、想拔除尿管等身體行為反應。尿動力學于拔管72 h時采用尿動力學分析儀(成都維信電子科大新技術有限公司,型號Nidoc970A+)進行測定,患者取半坐體位,在膀胱中置入雙腔測壓導管,采用生理鹽水進行灌注,灌注速率50 ml/min,記錄患者膀胱內殘余尿量、最大尿流率、最大膀胱測壓容量(MBC)。再次置管率(患者拔除尿管4~6 h內未進行排尿,且主訴尿意強烈,觀察恥骨上方有凸起,觸診膀胱充盈呈球狀,有壓痛,叩診為濁音,經誘導后難以自行排尿,需重新置管排尿)、膀胱刺激征(患者在尿管拔除后出現(xiàn)血尿或存在尿頻、尿急、尿痛等癥狀)、拔管后首次排尿不適、尿路感染(患者中段尿細菌定量培養(yǎng)結果顯示≥105/ml)發(fā)生情況。
1.5統(tǒng)計學方法 采用SPSS20.0軟件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χ2檢驗、秩和檢驗。
2 結 果
2.1兩組首次排尿時間、住院時間比較 A組首次排尿時間、住院時間均長于B組,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首次排尿時間、住院時間比較
2.2兩組尿管相關膀胱不適分級情況比較 A組尿管相關膀胱不適分級(0級2 vs 10例、1級21 vs 27例、2級26 vs 16例、3級5 vs 1例)高于B組,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Z=10.339,P=0.001)。
2.3兩組尿動力學比較 A組殘余尿量、MBC均高于B組,最大尿流率低于B組,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尿動力學比較
2.4兩組并發(fā)癥及再次置管發(fā)生情況 A組再次置管率〔18.52%(10例)vs 5.56%(3例)〕及尿管拔出后相關并發(fā)癥發(fā)生率(14.81% vs 1.85%,其中膀胱刺激征2 vs 0例、拔管后首次排尿不適4 vs 1例、尿路感染2 vs 0例)均高于B組,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χ2=4.952、4.364,P=0.026、0.037)。
3 討 論
中樞、外周神經、膀胱逼尿肌、尿道括約肌等器官組織共同協(xié)作以完成正常排尿反射,隨著膀胱內壓力提高,會刺激膀胱壁上的牽張感受器,進而通過盆神經刺激脊髓,并上傳至腦干、大腦皮層,進而產生排尿意識,腦橋排尿中樞產生沖動,致使副交感神經興奮,膀胱逼尿肌收縮、尿道括約肌舒張,進而建立排尿反射,促進患者排尿〔6,7〕。而老年脊柱全麻手術患者,當麻醉藥物起效后,中樞神經系統(tǒng)被可逆性抑制,患者暫時喪失了感覺、意識及反射等,致使肌肉松弛,保證手術完成,但這會阻斷正常的排尿中樞及傳導通路,因此,臨床上對老年脊柱全麻患者在術前留置尿管,以輔助臨床醫(yī)師觀察患者術中尿量,控制輸液量,降低或預防術后尿潴留。但長期留置尿管,會增加患者尿道黏膜損傷、出血、尿路相關性尿路感染等發(fā)生風險。因此,為減輕脊柱全麻患者痛苦程度,提高尿管留置期間的舒適程度,促使患者排尿,脊柱外科全麻術后患者需要選擇最佳時間拔除導尿管。
本研究結果提示,相較常規(guī)次日拔除尿管,老年脊柱全麻手術患者在麻醉清醒后即拔除尿管可有效縮短首次排尿時間及住院時間。分析其原因為:行脊柱全麻手術的老年患者,在全麻藥物的肌松作用下,機體肌肉自上而下進行松弛,當麻醉效果消失后,肌松效果由下而上依次消失。這表明當患者眼輪匝肌恢復自主活動時,膀胱逼尿肌已恢復生理功能,患者逼尿肌可以進行有效收縮并自主排尿〔8,9〕。而常規(guī)次日拔除尿管,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對膀胱壁上牽張感受器的刺激效果,致使患者難以建立排尿反射,且術后次日,部分老年患者因身體虛弱,會降低液體輸入量,致使膀胱充盈度較差,從而延長患者尿管拔除后首次排尿時間〔10,11〕。而且尿管置入是侵入性操作,其可損傷尿道黏膜,破壞尿道黏膜屏障,但長期留置導尿管會刺激患者的尿道黏膜,增加尿道黏膜損傷、出血等風險,這在一定程度上延長了患者的住院時間〔12〕。而老年脊柱全麻手術患者麻醉清醒后即拔除尿管,此時術中補液會增加患者機體的水成分,利于膀胱充盈,進而加強對膀胱牽張感受器的刺激力度,促進興奮傳導,建立患者排尿意識,進而縮短首次排尿時間。同時麻醉清醒后即拔除尿管可降低對尿道黏膜損傷風險,進而在一定程度上縮短患者的住院時間〔13〕。
本研究結果提示,相較常規(guī)次日拔除尿管,麻醉清醒后即拔除尿管可有效減輕老年脊柱全麻手術患者尿管相關膀胱不適程度。分析其原因為:常規(guī)次日拔除尿管,其尿管置入時間相對較長,尿管與尿道的接觸及摩擦時間也相對延長,致使其對尿道黏膜產生機械刺激,增加患者不適程度;且隨著留置時間的延長,患者麻醉效果及術后鎮(zhèn)痛效果減弱,尿管所產生的不適感更為明顯,且膀胱括約肌收縮及舒張功能下降,致使患者在尿管拔除后,易出現(xiàn)膀胱不適情況〔14〕。而且,尿管留置時間較長,尿道黏膜損傷程度較重,且尿管的球囊與膀胱壁緊密貼在一起,球囊周邊會存在少許殘余尿滯留,并在膀胱局部形成沉淀物,附著在尿管外壁,當進行拔管時,易將分泌物遺留在尿道或膀胱內,形成異物刺激膀胱,加重膀胱不適感,且長時間尿管留置會持續(xù)引流尿液,降低膀胱充盈度,膀胱處于無張力狀態(tài),喪失了其規(guī)律性收縮及舒張功能,更易發(fā)生攣縮,造成容量減少,增加膀胱不適程度〔15,16〕。而麻醉清醒后即拔除尿管,尿管對尿道黏膜的機械刺激相對較弱,加之術后鎮(zhèn)痛藥物的作用,可在一定程度上減輕老年脊柱全麻患者尿管相關不適程度〔17〕。
本研究結果提示,麻醉清醒后即拔除尿管可有效促進患者尿動力學恢復。分析其原因為:導尿管在留置期間,膀胱一直處于一種空虛狀態(tài),膀胱反射難以建立,這導致患者在拔除尿管后難以自行排尿。而麻醉清醒后即拔除尿管可縮短尿管留置時間,利于患者排尿反射建立,對排尿功能恢復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進而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尿動力學。本研究結果顯示,相較常規(guī)次日拔除尿管,麻醉清醒后即拔除尿管可有效降低尿管拔除后相關并發(fā)癥發(fā)生風險。分析其原因為:尿道在正常情況下處于一種無菌環(huán)境,插入尿管可損傷尿道黏膜并破壞尿道屏障,增加致病菌侵襲及定植風險,進而增加尿道感染風險。常規(guī)次日拔除尿管,麻醉清醒后即拔除尿管可縮短尿管留置時間,降低其對尿道黏膜的機械刺激,減輕對尿道黏膜的損傷程度,繼而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留置尿管所致的相關并發(fā)癥發(fā)生風險;同時麻醉清醒后即拔除尿管,可降低患者尿管所致的膀胱不適程度,避免患者因迫切要求拔管或自行拔管所致的尿道損傷風險,進而降低尿管相關并發(fā)癥發(fā)生風險〔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