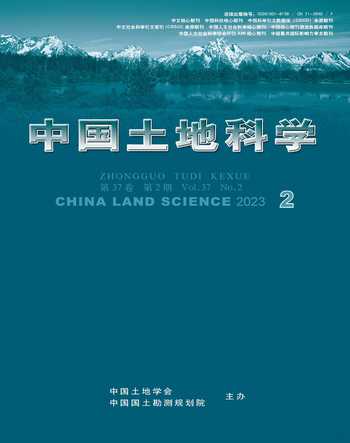空間均衡導向下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及演進
楊和平 李紅波



摘要:研究目的:測度2015—2020年全國31省的物質和生態財富價值變化,探討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空間均衡框架,為不同區域的實踐探索提供參考。研究方法:改進四象限模型、歸納總結法和案例分析法。研究結果:(1)2015—2020年全國31省GEP和人均GEP分別增長了19.35%和16.80%,但空間不均衡的格局差異愈發明顯。(2)以物質和生態財富的均衡狀態構建基于改進四象限模型的空間均衡框架,將31省劃分為6個象限分區,各分區生態產品的供需強度存在相對勢差。(3)處于不同象限的地區應在生態修復整治、生態保護補償、生態權益交易、生態產業開發、產業生態轉型5種主要路徑中因地制宜進行匹配組合,并朝著物質與生態財富協同的理想均衡線演進。研究結論:剖析物質與生態財富的協同關系及生態產品供需強度對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的指導依據,探索價值實現的空間均衡方向和路徑演進策略,有利于實現區域間“富綠”協同。
關鍵詞:空間均衡;生態財富;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研究
中圖分類號:F06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8158(2023)02-0092-10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城鄉融合導向的土地多功能利用空間關聯網絡演變機制”(41871179);江西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新發展格局下江西加快城鄉融合促進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研究”(22JL09)。
生態文明建設不斷向縱深推進,使得長久以來物質經濟效益最大化的區域發展目標失衡得以改善。在歷史性地消除了絕對貧困、解決了物質財富絕對匱乏后,建設生態文明、推動綠色低碳循環發展,不僅可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而且可以推動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1]。新時代國土空間發展模式已由唯經濟增長的單一目標模式逐漸轉向區域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生態環境“三維”目標的高質量發展模式[2],通過不斷提升人民群眾的生態環境福祉,協同推進區域經濟綠色轉型升級,真正實現“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的雙向轉化,推動區域物質財富和生態財富協同發展的空間均衡[3]。生態產品價值實現作為“兩山”轉化的關鍵抓手,是促進人均物質財富和生態財富協同均衡的重要手段。2018年4月,習近平在深入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指出:“要積極探索推廣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的路徑,選擇具備條件的地區開展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試點。”2021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建立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意見》,在全國范圍內推動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機制探索,2020年4月—2021年12月,自然資源部陸續推出三批共計32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典型案例,為各地區探索創新提供學習借鑒。2022年10月16日中共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建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完善生態保護補償制度”。
已有研究從生態學、經濟學、地理學等多學科視角對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概念內涵、邏輯機制、路徑模式和實踐案例等進行了富有意義的研究[4-7],但對于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區域差異討論還不夠深入,尤其在當前全國大范圍試點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背景下,受制于區域稟賦、發展模式、社會結構以及自然生態的生產特點和服務屬性等因素異質性影響,各地區探索方向和實踐重心存在一定差異。因此,強化各區域間個性與均衡、發展基礎與未來方向之間的關系剖析,引導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政策工具的區域特色化與協調性,進而因地制宜探討不同地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路徑選擇和價值收斂,有利于實現物質財富與生態財富空間均衡與協同的高質量發展目標。基于此,本文試圖梳理生態產品及其價值實現的概念內涵與主要模式,引入物質財富與生態財富狀態測度的改進四象限模型,構建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空間均衡分析框架,并基于GEP核算和實際案例討論不同區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路徑選擇及演進,以期為不同地區探索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提供差異化路徑與對策參考。
1 概念內涵
1.1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及其模式路徑
生態產品是我國在探索生態文明建設中的獨創概念,指的是良好的自然生態系統基于自身生物生產以及與人類共同生產提供的滿足人類美好生活需要的最終產品或服務[4-5],其價值實現是將自然生態資源及其服務以市場化或非市場化形式實現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協調統一的過程[8],既包括生產主體供給生態產品的生產活動和環境保護活動,也包括消費主體以交易或補償方式支付費用的過程,其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區域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的均衡發展狀態,達到生產主體、消費主體、制度策略、價值收益等多區域、多主體、多要素的利益協同。關于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模式路徑研究比較豐富,張林波等[5]基于生態文明建設角度將其分為生態保護補償、生態權屬交易、經營開發利用、綠色金融扶持、刺激經濟發展、政策制度激勵等方式。劉伯恩[9]從基礎發展型、拓展發展型、支撐發展型基礎上將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分為產業生態型、生態產業型、產權交易型、生態溢價型、生態補償型、生態倡議型、綠色金融型7種具體模式。王會等[10]基于支付機制和制度供給主體兩個視角提出了政府購買租用、政府財政補償、要素權益交易、生態服務交易、公眾自愿捐贈、產品認證出售、自發捆綁交易和自發直接交易8種實現模式。
基于實現物質財富與生態財富的空間均衡與協同目標,不同的空間治理單元在推進生態產品價值實現中的路徑組合與差異,本文將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主要路徑分為生態修復整治、生態保護補償、生態權益交易、生態產業開發、產業生態轉型5種類型:(1)生態修復整治,主要指通過自然生態系統保護修復、農田生態系統保護修復、城鎮生態系統保護修復、礦山和海洋生態保護修復等方式對全域國土空間進行系統修復和綜合整治,恢復并提升自然生態系統功能,強化生態產品的供給能力。(2)生態保護補償,主要是指對于為保護自然生態而付出勞動價值或限制部分經濟發展機會的生態產品供給能力強的區域空間進行經濟補償付費的模式,一般包括以財政轉移支付為主的縱向補償、流域上下游跨區域的橫向補償和以保護資金補助、財稅補貼等為主的政府購買服務方式[11]。(3)生態權益交易,指的是建立在生態資源確權和價值核算基礎上,生態產品供需雙方通過市場化機制進行產權權益交易的模式,其本質在于固化生態資源產權屬性轉化為可交易流通的市場價值,空間尺度表現為經濟發達地區向自然生態優勢區域購買水權、碳匯、排污權等生態產品的形式。(4)生態產業開發,即生態產業化,主要指生態產品供給能力強的區域推動生態產品以產業化方式形成經濟資產并進行經營運作的產業體系,如大力發展以生態產品為依托的現代生態農業、生態工業和生態文化旅游業等,其重點在于將經營性生態產品與傳統三大產業有機耦合,構建生產、流通、消費和產業資本投資的價值增殖系統。(5)產業生態轉型,即產業生態化,主要是指生態產品需求強度大的地區基于生態環境綜合承載能力,以生態經濟為發展主線引進綠色生態技術,對區域產業如采掘工業、原材料工業、加工工業等進行生態化改造,因地制宜培引節能高效、生態環保的新興產業,引導物質財富部門實現綠色化、數字化、低碳循環的產業高質量轉型升級。
1.2 物質財富與生態財富的內涵與關系
傳統的財富觀指向單一的物質財富,是公眾從經濟生產系統獲得的產品和服務。新古典經濟學家理查德·斯通在完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的基礎上建立了以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衡量物質財富價值的指標系統,但是現行的GDP指標局限于實物資產、金融資產等物質財富的統計,忽視了自然生態環境在經濟發展中提供的隱形服務和資源支持。生態財富是隱藏于自然生態中的價值形態,必須依賴于良好的生態環境供給及與人類共同生產的服務產品才能顯化,生態產品是其中的關鍵媒介。在“兩山理論”成為綠色發展共識的背景下,優質的水資源、空氣、生物多樣性等環境資源及其提供的服務已經成為與物質產品擁有同等地位的生態產品,其價值可作為生態財富的表征指標[2,12]。
中共二十大報告提出“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和國土空間體系”,既要推動以生產力進步為導向的物質財富增長與分配,也要謀求生態財富帶來的福祉增益,在綠色發展中減弱兩者的權衡關系而強化其協同促進,構建人均生態財富與人均物質財富辯證統一、相互促進的國土空間發展格局。首先,生態財富積累是物質財富的增長前提和環境基礎,人類進行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生產的物質經濟活動離不開自然生態資源供給的產品與服務,忽視人對生態財富的訴求而造成的氣候變暖、生物多樣性減少、土地荒漠化等環境破壞問題,反過來會限制物質經濟持續增長的拓展空間;其次,物質財富有助于增強生態財富的福祉效應,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離不開物質財富的持續投入,如“十三五”期間中央財政總計投入8 779億元支持生態保護修復,“天更藍、山更綠、水更清”正是物質財富推動生態財富不斷增長的客觀印證;最后,生態財富與物質財富可以互相轉化,基于國土空間均衡的視角,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就是兩種財富價值相互轉換的關鍵路徑。生態財富相對盈余的區域可以將自然生態資源與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相結合,生產出滿足公眾需求的產品或服務,最后經市場化機制實現“驚險的跳躍”,以供給生態產品的方式推動生態財富向物質財富的價值轉化和增殖。物質財富相對富裕的地區可以通過生態補償轉移支付、生態權益購買等方式滿足群眾對生態財富的向往和需求,不同地域依據其物質財富和生態財富差異及供需強度因地制宜探索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政策實踐,推進國土空間“富綠”協同[13]。
2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空間均衡分析框架
2.1 空間均衡理論
一般認為,空間均衡理論是經濟學一般均衡理論在地理學、區域經濟學等學科上交叉產生的理論,主要研究商品市場在空間層面的流動配置、經濟發展的空間形態及影響因素等,其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區域分工理論、產業區位選擇及基于新經濟地理學的空間均衡框架等階段[14-15]。隨著生態文明建設與高質量發展理念的深入推進,空間均衡已經不局限于經濟指標的均衡,而是向經濟、社會、生態環境協調的均衡目標轉變。《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明確提出要“樹立空間均衡理念,把握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的平衡點推動發展”,建立“經濟—社會—生態”的三維空間均衡框架,通過空間開發供給能力與保護需求相匹配以及區域間的分工協調實現空間尺度的帕累托最優狀態。多維目標下的空間均衡不是物質財富和生態財富的簡單對立博弈,而是人在不同階段因不同的發展需求所做的順序選擇。在基本物質生活需要未得到滿足的發展階段,人對生存的需要迫使其以物質財富增長為主要目標;在完成物質財富的增長與分配后,對生活質量的需要使得生態財富的福祉增益得到更多關注[16];隨著人們對人與自然的關系認識進入和諧共生的階段,推動兩種財富的協同增長成為綠色發展理念的重要目標,以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推動兩種財富空間均衡成為“綠色共富”的關鍵手段。
2.2 基于改進四象限模型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匹配
與土地利用空間均衡類似[17],不同地域物質財富和生態財富的態勢差異導致其生態產品供給能力和需求強度也存在空間不一致。本文引入多應用于景觀生態和生態系統服務領域的四象限模型[18],討論省域間物質財富和生態財富的狀態差異及生態產品供需關系。文中的生態財富以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為表征,物質財富以GDP為表征,參考生態系統服務供需研究[19],生態財富充裕的區域生態產品供給能力相對較強,物質財富充裕的區域生態產品的需求強度相對更大。參考易家林等[3]的分類方式,以區域人均物質財富和人均生態財富分別作為橫縱坐標軸建立坐標系,并引入均分一、三象限的均衡線,討論不同象限生態產品供需能力的相對勢差,與前文界定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5種主要路徑進行復合匹配,構建基于空間尺度的改進四象限模型(圖1)。
第一象限表示該地區的物質生產和生態建設達到了均衡狀態,將其命名為均衡象限Ⅰ,位于這一象限的均衡線稱為理想均衡線。其中,理想均衡線與人均生態財富縱軸構成的區域為均衡象限Ⅰ-1,處于該象限的地區生態產品的供需水平屬于“強供給—較強需求”類型,人均物質財富和生態財富均屬于正向區間,相較而言生態財富更占優勢,具備充分的生態基礎和物質動力去推動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生態保護補償”的路徑模式;理想均衡線與人均物質財富橫軸構成的區域為均衡象限Ⅰ-2,處于該象限的地區生態產品供需水平屬于“較強供給—強需求”類型,區域人均生態財富和物質財富都高于平均水平,且物質財富相對更占優勢,具備擴容區域生態潛力的物質條件和生態訴求,可采用“生態產業開發”的路徑模式。第二象限表示該區域物質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而生態財富相對匱乏,有可能是區域生態本底較為脆弱,或是“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思路忽視了對生態環境的有效保護,將這類地區劃分為發展象限Ⅱ,區域生態產品供需水平屬于“弱供給—強需求”類型,建議采用“生態修復整治”的路徑模式。第三象限表示區域內物質財富和生態財富均處于較低水平的均衡狀態,位于這一象限的均衡線稱為低級均衡線,這類地區劃分為原始象限Ⅲ。其中低級均衡線與橫軸構成的區域為原始象限Ⅲ-1,該象限區域的人均物質財富和生態財富都低于平均水平,相較而言人均生態財富相對差距較小,區域生態產品供需水平屬于“較弱供給—弱需求”類型,建議從勢差相對較小的生態財富著手,采用“生態修復整治+生態產業開發”的復合模式;低級均衡線與縱軸構成的區域為原始象限Ⅲ-2,該象限的地區人均物質財富相對差距較小,區域生態產品供需水平屬于“弱供給—較弱需求”類型,可從勢差相對較小的物質財富出發,采用“生態修復整治+產業生態轉型”模式。第四象限表明該類型地區物質經濟水平相對落后,可提供的生態空間和生態服務比較充裕,人均生態財富相對充裕,對探索生態產品價值轉化為物質財富的訴求最為迫切和緊要,這類地區劃分為生態象限Ⅳ,生態產品供需水平屬于“強供給—弱需求”類型,可與“生態權益交易”路徑進行匹配。
3 基于改進四象限模型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實證
3.1 數據來源與處理
國內GEP核算與應用仍處于激烈的探索和試點階段,受限于數據可得性和時效性,本文采用生態系統服務價值作為GEP的數值表征,2015年、2020年兩期數據來源于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與數據中心(http://www.resdc.cn)的中國陸地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空間分布數據集,分辨率為1 km。數據參考謝高地的生態服務價值當量因子法[20],總價值由供給服務價值Vps(食物生產、原料生產、水資源供給)、調節服務價值Vrs(氣體調節、氣候調節、凈化環境、水文調節)、支持服務價值Vss(土壤保持、維持養分循環、生物多樣性)、文化服務價值Vcs(美學景觀)4大類共11種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構成。全國31個省級行政區(以下均未統計港澳臺地區)的人口和社會經濟數據來源于2016—2021年《中國統計年鑒》。
3.2 生態產品總價值時空分異特征
基于上述方法計算得到2015—2020年全國31省 GEP及構成,如表1所示,2015—2020年31省份GEP由39.99萬億元增長至53.27萬億元,整體增長了13.28萬億元,剔除價格因素后實際增幅19.35%。其中供給服務價值Vps實際增幅23.26%,調節服務價值Vrs實際增幅20.05%,支持服務價值Vss實際增幅13.19%,文化服務價值Vcs實際增幅34.61%。從空間分布來看,GEP單位面積價值具有明顯的“南高北低”特征,云南、貴州、廣西、廣東等西南、華南片區的單位面積GEP顯著高于天津、北京、河北、寧夏等華北、西北片區,這也與謝高地等[20]研究的2010年中國生態系統服務的分布特征保持一致,且10年間這種不均衡分布的格局趨勢愈發明顯。全國31省人均GEP從2015年的2.90萬元增長至2020年的3.78萬元,實際增幅達16.80%。“十三五”期間新疆、陜西、山西、安徽、湖北、福建6個省份人均GEP在全國的排序略有下降,而吉林、遼寧、四川、貴州、廣西、湖南、廣東和浙江8個省份排序有所上升,整體上西藏、青海、云南等西部地區人均生態財富高于上海、江蘇、山東等東部地區,“西高東低”的空間格局仍然明顯,單位面積GEP和人均GEP的空間格局明顯不一致,各地區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水平存在較大的差異性。
3.3 改進四象限模型的分區結果
積極探索創新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是深入踐行“兩山”理論的核心路徑,以全面生態文明建設促進人均物質財富與生態財富的“富綠”協同,必須考慮區域差異性并制定差異化策略[21]。本文以全國31個省人均GDP和人均GEP分別作為各地區人均物質財富和人均生態財富的數據表征,以人均GDP和人均 GEP的平均值作為原點建立坐標系,構建兩種財富價值協同均衡的改進四象限模型進行分析,結果如圖2所示。2020年處于均衡象限Ⅰ-1的地區包括內蒙古和湖北2個省份,其中湖北由2015年生態象限Ⅳ發展“前進”而來;處于均衡象限Ⅰ-2的僅有福建1個省份;處于發展象限Ⅱ的地區包括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天津、廣東、重慶、山東8個省份;處于原始象限Ⅲ-1的有山西、甘肅2個省份;處于原始象限Ⅲ-2的有陜西、安徽、遼寧、寧夏、河南、河北6個省份,陜西和遼寧分別由2015年生態象限Ⅳ和發展象限Ⅱ“跌落”進入,安徽由原始象限Ⅲ-1轉移進入;處于生態象限Ⅳ的地區有西藏、青海、云南、黑龍江、新疆、廣西、江西、海南、四川、貴州、湖南、吉林12個省份,其中湖南由2015年原始象限Ⅲ-1“前進”而來。

3.4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路徑選擇及演進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以及各部委推進了一系列關于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試點,如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國家生態產品市場化省級試點、國家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試點城市、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示范市縣(區)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實踐創新基地等,各地區積極探索并貢獻了大量富有試點意義和現實亮點的路徑方案。基于此,分析各省級行政區物質財富和生態財富兩種財富價值協同均衡的象限分區結果,結合區域生態產品供需強度的相對勢差和區域試點特色,討論各省探索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路徑匹配及演進案例(表2)。
位于均衡象限Ⅰ-1的內蒙古和湖北兩省處于人均物質財富和生態財富均實現正向均衡的狀態,且生態財富水平相對更高,生態產品供需強度屬于“強供給—較強需求”類型,建議采取“生態保護補償+生態產業開發”的復合路徑。首先充分開展自然生態資源調查監測和評估定價,由政府與市場構建“財政補助+金融扶持”的模式,為區域保護生態環境供給生態產品而付出的勞動價值和損失的經濟效益提供定向補償和金融支持。如湖北從2015年生態象限“前進”至均衡象限,人均物質財富增長的同時堅持探索綠色發展保護自然生態價值,鄂州建立區域間橫向生態補償機制,試行階段已支付梁子湖區2.4億元生態服務價值溢出補償資金,全面推進城鄉重大生態工程,并積極探索水庫灌溉權質押融資、林權收益權轉讓及融資、排污權交易等市場化運作的生態價值實現路徑。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利用生態產品強供給優勢,如內蒙古積極推進烏蘭察布馬鈴薯、科爾沁牛、呼倫貝爾草原羊等“蒙字號”生態農牧業區域品牌,以構建生態產品“第四產業”產業鏈提高生態溢價,推動區域人均物質財富和生態財富向理想均衡線持續協同演進。
位于均衡象限Ⅰ-2的福建在“十三五”期間物質財富與生態財富保持均衡富裕,且物質財富略占優勢,生態產品供需強度屬于“較強供給—強需求”類型,建議采取“生態產業開發+生態權益交易”的路徑模式,充分發揮區域生態領先優勢和豐厚物質基礎的耦合協同,通過大力發展生態農業、生態文化旅游業、生態工業等,加快促進生態資源向資產資本的高效轉化,創新優化生態產品的供給結構,打造形成具有區域特色優勢的生態產品品牌。同時積極響應人們對生態產品的強需求,積極打造生態產品的資本化運營市場,通過運營收儲、營銷推介、項目轉化等方式整合優化生態資源資產,搭建生態產品權益交易平臺,綜合提升區域生態賦能社會經濟增長的動能動力,如福建光澤縣“水美經濟”構建賣資源、賣產品、賣環境和賣高端食品的水生態全產業鏈,建立“水生態銀行”和“武夷山水”區域公用品牌,搭建了整合資源、優化資產、引入資本、品牌建設的綜合平臺,成功實現了生態產品市場化開發和交易的轉化機制。
位于發展象限Ⅱ的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等8個省份大多屬于人口和物質經濟分布密度相對較高的區域,物質財富較為富裕但生態財富相對稀缺,生態產品供需強度屬于“弱供給—強需求”類型,建議采用“生態修復整治+生態權益交易”的復合路徑。首要的重點任務是增強區域生態產品生產供給能力,加快推進生態修復和環境綜合整治,積極探索以政府為主導、社會資本和公眾共同參與的區域生態綜合治理工程,提高區域人民群眾生態財富的獲得感和幸福感。同時充分發揮區域物質經濟基礎驅動,引導針對市場強需求開發新的生態產品,構建多元主體協同的生態權益認證流轉交易機制,創新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推動區域進入均衡象限。如山東威海以產權出讓方式公開引進華夏集團,對龍山區域開展礦坑生態修復治理和文化旅游產業相結合的治理新模式,實現了生態資源資產化、區域生態修復、富民產業融合發展的多重目標。浙江麗水則通過探索發展生態工業,以“驗地、驗水”制度確保工業企業用地污染的及時修復,并與上海、杭州等地創新“飛地互飛”機制,合作探索生態產品價值異地轉化路徑。
位于原始象限Ⅲ-1的山西、甘肅兩省屬于中西部地區,受區位歷史和發展模式等因素影響,區域人均物質財富和生態財富處于匱乏水平的低級均衡狀態,且生態財富的差距相對較小,生態產品供需強度屬于“較弱供給—弱需求”類型,迫切需要探索“生態修復整治+生態產業開發”的復合路徑。首先從差距相對較小的供給弱側出發,推動區域積極開展國土綜合整治和生態修復,如山西以丘陵溝壑區水土流失綜合治理、礦山生態修復、黃河生態保護修復等方式重點推進“兩山七河一流域”生態修復治理,統籌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修復。在此基礎上引導區域開發對環境影響小、生態產品需求較少的綠色產業,積極發掘具備區域優質特色的生態產品,因地制宜發展數字經濟、清潔能源等環境敏感型產業,積極爭取國家EOD模式項目,推動生態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大力招引發展生態友好型產業和企業,打造一批具有示范帶動作用的綠色工廠和綠色供應鏈企業,減少污染排放對生態產品調節服務功能的損耗。如甘肅酒泉精準識別區域風能資源的生態價值屬性,以風電產業發展推動能源產業轉型創新。
位于原始象限Ⅲ-2的陜西、安徽、遼寧等6個省份也處于人均物質財富和生態財富都匱乏的狀態,且物質財富的差距相對更容易縮小,生態產品供需強度屬于“弱供給—較弱需求”類型,建議采用“生態修復整治+產業生態轉型”的復合路徑,尤其是遼寧、陜西、安徽分別由2015年的發展象限Ⅱ、生態象限Ⅳ和原始象限Ⅲ-1“跌落”到該類型,表明經濟社會發展與自然生態保護存在失衡現象,亟需開展全域生態修復和國土綜合整治,以系統化思維統籌物質財富和生態財富的均衡協調,強化區域生態產品供給能力。同時要積極探索產業綠色循環轉型的新發展形態,以綠色、低碳、節能為導向,將區域內產業經濟系統、自然生態系統和社會文化系統進行耦合協調及優化,以綠色發展理念創新發展先進生態技術,積極培育綠色低碳產業,降低原有傳統高耗能、高污染產業對生態環境的空間壓迫,引導傳統產業向著節能綠色的方向轉型,推進地區產業經濟綠色化轉型升級。如陜西神木積極推進資源型城市造林修復、減污降碳,探索煤礦開采、生態種植和新能源發展有機結合的產業綠色轉型新模式。
位于Ⅳ生態象限的西藏、青海、江西等12個省份的人均生態財富相對充裕而人均物質財富相對匱乏,生態產品供需強度為“強供給—弱需求”水平,這些地區迫切期待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對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正向驅動,建議采用“生態保護補償+生態權益交易”的復合路徑。首先充分把握生態產品強供給能力,在政策上構建府際間橫縱雙向補償制度,以財政轉移支付、生態專項工程、資源配額交易等方式,適當向中西部生態富裕省份傾斜政策扶持,將生態補償與鄉村振興、區域協調發展等工作結合起來,引導建立生態公益組織和公益基金會等,充分調動政府、社會資本、民眾多主體共同參與生態保護與建設,形成生態價值向物質價值的合理高效轉化。如廣西探索石漠化綜合治理與生態觀光農業協同推進,結合選聘貧困戶為生態護林員,實現生態補償脫貧與鄉村振興的有機銜接。江西省資溪縣建立“兩山銀行”,積極探索“景區收費權質押貸款”“林權補償收益權質押貸款”“竹木產業鏈融資”等創新模式,為區域物質財富增長提供生態渠道。
混合策略選擇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均衡,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空間均衡體現為物質財富與生態財富的均衡及協同促進。基于對物質、生態、精神等多維共同富裕的追求,均衡象限Ⅰ-1和生態象限Ⅳ的區域將積極推動生態產品從強供給向強需求流動,探索生態財富向物質財富轉化,由順時針方向往理想均衡線演進,如湖北省;均衡象限Ⅰ-2和發展象限Ⅱ的區域發展將探索物質經濟對生態環境的反哺,通過修復、補償、購買等方式滿足區域對生態產品的強需求,由逆時針方向往理想均衡線演進。而位于原始象限Ⅲ的地區似乎擁有演進方向的選擇權,一般而言生態差距相對更小的原始象限Ⅲ-1區域傾向于提高生態財富水平,經生態象限Ⅳ向理想均衡線演進,如湖南省;物質財富差距更小的原始象限Ⅲ-2更傾向于加快物質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經發展象限Ⅱ向理想均衡線演進。研究也發現部分地區在探索多維目標空間均衡的過程中未能充分識別自身稟賦優勢和發展邏輯,導致在演進中發生了“象限跌落”,在下一步謀求綠色發展的動態演進中需要探索更清晰的路徑選擇。
4 結論與討論
4.1 結論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是“兩山理論”轉化的發展新范式,也是推進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等系統性改革工程的重要抓手。本文梳理了生態產品及其價值實現的概念內涵和主要模式,以物質財富和生態財富的價值協同及生態產品供需強度構建了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空間均衡分析框架,在核算2015—2020年全國GEP構成及變化的基礎上,采用改進四象限模型對31省進行經濟—生態象限分區,并基于實際案例討論不同區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路徑選擇和演進策略。得出以下結論:(1)“十三五”期間全國GEP和人均GEP均實現增長,但空間不均衡的格局差異愈發明顯。2015—2020年全國31省GEP總值由39.99萬億元增長至53.27萬億元,實際增幅達19.35%;人均GEP從2015年的2.90萬元增長至3.78萬元,實際增幅為16.80%。單位面積GEP呈現“南高北低”的空間特征,與人均GEP“西高東低”的空間格局存在明顯的錯配不均。(2)基于改進四象限模型構建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空間均衡框架,以物質和生態財富的協同均衡關系將31省劃分為均衡象限Ⅰ-1和Ⅰ-2、發展象限Ⅱ、原始象限Ⅲ-1和Ⅲ-2、生態象限Ⅳ共6個象限分區,各分區生態產品的供需強度存在不同的相對勢差。(3)處于不同象限的地區應在生態修復整治、生態保護補償、生態權益交易、生態產業開發、產業生態轉型等5種主要路徑中因地制宜進行匹配組合,并朝著物質與生態財富協同的理想均衡線演進。不同地域在探索多維目標空間均衡的演進過程中,應充分厘清稟賦優勢和發展邏輯進行價值實現的路徑選擇和演進策略。
4.2 討論
尋求不同區域間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路徑匹配是“兩山”理論下實現物質財富和生態財富空間均衡的關鍵問題。本文嘗試討論了生態產品價值實現中兩種財富價值的空間均衡與協同,并基于不同區域生態產品供需強度的相對勢差討論了區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路徑選擇與演進,對如何以生態文明思想指導異質性區域實現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的雙向互動轉化以及空間均衡提供了一定的指導和參考。同時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區域間生態財富的數據測度還存有優化空間,尤其是各地GEP進行大范圍核算試點后,全國尺度如何進行統一標準化核算仍具有較大難度,以GEP為表征的生態財富價值如何克服傳統物質財富以GDP為表征的短期效益、福利缺失、成本模糊等缺陷還需深入討論。然后是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選擇的相互協同與轉化尚待進一步明晰,如張林波等[22]認為多數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案例都需要綜合采用多種路徑模式,各種實踐模式相互之間存在很大的關聯性和相似性。精準識別不同地區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匹配與復用性,既需要厘清各路徑間存在的復雜交互協同,更需要從宏觀制度框架到微觀方案設計上進行不斷的適應性動態調整。最后是研究的空間尺度還有待豐富,我國因幅員遼闊而天然存在資源分布的空間非均衡,嘗試討論均衡的目的在于以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推動“兩山”相互轉化,引導區域間功能互補、價值流動和利益聯結,以構成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的支撐途徑之一。文中主要依據生態產品供需強度和緊缺亟需原則對省域單元的路徑選擇進行整體方向和多數意志的歸類,市縣鄉等多尺度單元探索其價值實現還需基于政策選擇偏好和響應強度構建完整的路徑匹配與演進體系,尤其是縣域單元定位于國家治理的載體節點和國土空間基本單元,為尋找自身特色的經濟與生態均衡協同發展道路尋找新的發力點。另外,共同富裕中精神財富對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提出的新要求也有待進一步討論。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 習近平. 努力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J] . 求是,2022(11):4 - 9.
[2] 白謹豪, 劉儒, 劉啟農. 基于空間均衡視角的區域高質量發展內涵界定與狀態評價——以陜西省為例[J] . 人文地理, 2020,35(3):123 - 130,160.
[3] 易家林, 郭杰, 林津, 等. 生態文明理念下的國土空間均衡:基于兩種財富的分析框架[J] . 地理研究, 2022,41(4):945 - 959.
[4] COSTANZA R, DARGE R, DE GROOT R, et al. 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J] . Nature, 1997, 387(6630): 253 - 260.
[5] 張林波, 虞慧怡, 李岱青, 等. 生態產品內涵與其價值實現途徑[J] . 農業機械學報, 2019,50(6):173 - 183.
[6] 曾賢剛, 虞慧怡, 謝芳. 生態產品的概念、分類及其市場化供給機制[J] .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4,24(7):12 - 17.
[7] 孫博文.建立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瓶頸制約與策略選擇[J] .改革,2022(5):34 - 51.
[8] WANG J N. Environmental costs: revive Chinas green GDP programme[J] . Nature, 2016, 534(7605): 37.
[9] 劉伯恩.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內涵、分類與制度框架[J] . 環境保護, 2020,48(13):49 - 52.
[10] 王會, 李強, 溫亞利.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邏輯與模式:基于排他性的理論分析[J] . 中國土地科學, 2022,36(4):79 - 85.
[11] ZHOU Z X, SUN X R, ZHANG X T, et al. Inter-region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based on the value of ecosystem services[J] .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22, 322. doi: 10.1016/j.jenvman.2022.116073.
[12] 洪銀興. 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學問題[J] .求是學刊,2021,48(3):19 - 33.
[13] 孫慶剛,郭菊娥,安尼瓦爾·阿木提. 生態產品供求機理一般性分析——兼論生態涵養區“富綠”同步的路徑[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5,25(3):19 - 25.
[14] 大衛·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M] . 郭大力, 王亞南, 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21: 106 - 124.
[15] 陳雯. 空間均衡的經濟學分析[M] .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10 - 31.
[16] GIANNICO V, SPANO G, ELIA M, et al. Green spaces, quality of life, and citizen perception in European cities[J] . Environmental Research, 2021, 196. doi: 10.1016/ j.envres.2021.110922.
[17] 楊清可,王磊,李永樂,等. 供需匹配視角下土地利用空間均衡的理論分析與狀態評價——以江蘇省為例[J] .資源科學,2021,43(5):932 - 943.
[18] SUN Y X, LIU S L, SHI F N, et al.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and coupling of human activity inten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based on the four-quadrant model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J] .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20, 743. doi: 10.1016/j.scitotenv.2020.140721.
[19] 易丹,肖善才,韓逸,等. 生態系統服務供給和需求研究評述及框架體系構建[J] . 應用生態學報,2021,32(11):3942 - 3952.
[20] 謝高地, 張彩霞, 張昌順, 等. 中國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J] . 資源科學, 2015,37(9):1740 - 1746.
[21] 葉頔, 蔣婧博, 張文進, 等. 中國省域生態文明建設進程區域差異化研究[J] . 生態學報, 2023,43(2):569 - 589.
[22] 張林波, 虞慧怡, 郝超志, 等. 國內外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實踐模式與路徑[J] . 環境科學研究, 2021,34(6):1407 - 1416.
Path Selection and Evolution of Valu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Oriented at Spatial Equilibrium: Based on the Improved Four-quadrant Model
YANG Heping1, 2, LI Hongbo1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2. Party School of Jiangxi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Nanchang 330108, 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to quantitatively measure the material wealth and ecological wealth of 31 provinces from 2015 to 2020, and to explore the spatial equilibrium framework of valu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so as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the value realization explor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n different regions. The methods of improved four-quadrant model, inductive abstraction and case analysis were employ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from 2015 to 2020, the GEP and per capita GEP in 31 provinces increased 19.35% and 16.80% respectively, but the spatial imbalance became more obvious. 2) The spatial equilibrium framework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equilibrium states of material and ecological wealth within an improved four-quadrant model. The 31 provinces are divided into six quadrant partitions, while the potential differences of supply and demand intensity of ecological products are shown in each partition. 3) Regions in different quadrants make matching and combine in five main paths, i.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ecological protection compensation, ecological rights trading, ecologic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ecological transition, and evolve toward the ideal horizontal line of material and ecological wealth synergy. In conclusion, analyzing the synerg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ial and ecological wealth and the supply and demand intensity of ecological products, and exploring the spatial equilibrium direction and path evolution strategy of valu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s conducive to the realization of “green-rich” synchronous development.
Key words: spatial equilibrium; ecological wealth; valu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path exploration
(本文責編:張冰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