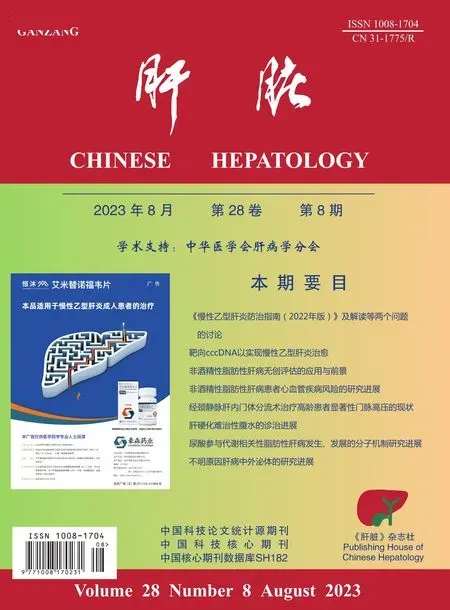不明原因肝病中外泌體的研究進展
汪增秀 趙宏宇 吳衛鋒 宋金云
外泌體是一種直徑30~150 nm雙磷脂膜囊泡,攜帶著大量的蛋白質、核酸、脂質等多種生物活性成分,存在于各種體液中,包括血液、尿液、唾液、乳汁、腦脊液、胸腔積液、羊水和腹水等[1]。外泌體作為一種信息交流的媒介,將攜帶的mRNA、miRNA、蛋白質、脂質等多種組分傳遞至近鄰細胞,通過體內循環系統到達身體其他細胞和組織中,影響靶細胞的生物活性,并可影響多種生理和病理過程[2]。
“不明原因肝病”是指肝功能生化指標反復異常(一般持續6個月以上),或肝臟影像學檢查異常,甚至發展為肝硬化等病變,無法通過病史詢問、體格檢查和血清學檢查等常規診療手段明確病因。不明原因肝病病因繁多,主要以非感染因素為主,如自身免疫性肝炎(AIH)、原發性膽汁性膽管炎(PBC)、原發性硬化性膽管炎(PSC)、藥物性肝損傷(DILI)、非酒精性脂肪肝病(NAFLD)及其他系統疾病累及肝臟等[3]。肝穿刺活組織檢查是確認不明原因肝病原因的金標準,但是肝穿刺活檢的有創性使得該診斷方法在效率上仍受到限制。大量研究顯示,外泌體可能參與了不明原因肝病的發生和發展過程。目前,尿液中的外泌體被認為是非侵入性的分子生物標志物,血液中的外泌體被認為是微創分子生物標志物,有可能代替以往的肝穿刺活組織檢查技術,用于不明原因肝病的早期檢測和預后。另外,外泌體及其攜帶組分參與了肝細胞的修復、再生和遷移等生理過程,因此可能是不明原因肝病的潛在治療手段和治療靶點。以下簡要概述外泌體在不明原因肝病的發生和發展中的作用。
一、泌體形成過程與組成成分
(一)外泌體形成過程 首先在胞吞作用下,細胞膜內陷形成包含細胞表面蛋白與細胞外環境成分(蛋白質、脂質、代謝物、小分子和離子)的杯狀結構,早期核內體形成。早期核內體還可以與內質網和反式高爾基體融合,所以一些早期核內體可能包含不同起源的膜和管腔成分。早期核內體成熟,形成晚期核內體。晚期核內體通過二次內陷,形成腔內小囊泡。腔內小囊泡不斷累積并逐漸成熟,最終形成包含一定數量和大小不一小囊泡的多泡體。多泡體可以通過細胞骨架和微管網絡運輸到細胞膜,與細胞膜融合,最終釋放出外泌體。另外,多泡體可以與溶酶體或自噬體融合后降解,降解產物可由細胞回收[4]。
(二)外泌體組成成分 外泌體包含不同類型的細胞表面蛋白質、細胞內蛋白質、RNA、DNA、氨基酸和代謝物等成分。四跨膜蛋白家族(CD9、CD81和CD63)、脂筏標記蛋白(flotillin)、凋亡轉接基因2互作蛋白X(ALIX)、腫瘤易感基因101蛋白(TSG101)、神經酰胺是外泌體的標志蛋白質。多種細胞可分泌外泌體,如間充質干細胞(MSC)、腫瘤細胞、人羊膜上皮細胞、內皮細胞、神經元細胞、肥大細胞、巨噬細胞、樹突狀細胞及T淋巴細胞等[5]。
(三)外泌體功能 外泌體作為細胞間通信的關鍵介質,能夠輸送核酸、蛋白質及脂質到靶細胞,在抗原呈遞、炎癥、血管形成、細胞凋亡等生物過程中發揮作用,從而維持正常生理過程和介導病理過程,包括癌癥、感染、神經退行性疾病、代謝性疾病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等[6-10]。
二、外泌體在不明原因肝病中的作用
肝臟是人體新陳代謝的重要器官,參與機體的再生、凝血、免疫、解毒、三大物質代謝、生物轉化和內分泌調節、存儲等功能。肝臟細胞既可以分泌外泌體,同時也是自身分泌的和其他組織細胞產生的外泌體的作用靶點。以肝臟細胞為靶點的外泌體廣泛參與了不明原因肝病的多項生物學進程,與不明原因肝病的發生和發展均有密切聯系。
(一)外泌體與AIH AIH是一種由免疫介導的攻擊自身健康肝細胞而引起的慢性肝臟實質性炎癥,臨床特征為血清轉氨酶異常升高、自身抗體(主要為抗核抗體、抗平滑肌抗體及抗肝腎微粒體抗體等)陽性、免疫球蛋白和γ球蛋白水平升高。肝組織學特征為肝小葉內,肝細胞存在不同程度的界板炎,以及所謂的“玫瑰花結”樣肝細胞變性團。AIH如果不治療,將可進展為肝硬化和肝衰竭[11]。雖然使用皮質類固醇是AIH的常見治療方法,但一些AIH患者對皮質類固醇治療反應嚴重,一些康復患者在停止使用類固醇后可能會產生嚴重的不良反應或者疾病復發[12]。因此,需要新的替代療法用于AIH 的治療。
由于MSC具有較強的分化能力、低免疫原性和免疫調節功能,常被用于組織修復和炎癥性疾病的治療[13]。有研究發現,MSC通過其分泌的外泌體靶向恢復肝臟穩態,并使肝細胞修復和再生,可能具有治療肝臟疾病的特性[14]。MiR-223-3p(曾稱為MiR-223)是骨間充質干細胞(BMSC)中表達最高的miRNA,可以負向調節許多炎癥基因的表達,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發揮重要作用。在肝抗原S100誘導的小鼠AIH實驗模型中,BMSC來源的外泌體作為載體,遞送miR-223,可減輕AIH 引起的肝損傷,這可能與外泌體miR-223能夠降低NOD樣受體熱蛋白結構域相關蛋白3(NLRP3)及 caspase-1蛋白的表達有關[15]。另一項研究也發現BMSC外泌體能夠與miR-223-3p成功結合,并將miR-233-3p輸送到巨噬細胞,同時對巨噬細胞無毒性作用。用攜帶 miR-223-3p 的BMSC外泌體治療S100/CFA 誘導的AIH小鼠,可以減輕AIH小鼠肝臟的炎癥反應及巨噬細胞中的炎性細胞因子釋放。其機制可能與 miRNA-223-3p 介導的 STAT3 基因和炎性細胞因子(IL-1β 和 IL-6)表達的調節,以及 Treg/Th17升高有關[16]。在炎癥相關細胞中,巨噬細胞在AIH的觸發和過程中起主導作用。由于外泌體作為一種具有高生物相容性和低免疫原性的藥物載體,而地塞米松(DEX)又是一種強效抗炎藥,所以Zhao J等結合外泌體和DEX的優勢,構建了攜帶DEX的外泌體(Exo@DEX)。研究發現,Exo@DEX可以在刀豆蛋白 A誘導的AIH小鼠肝臟中大量累積,有效地內化到巨噬細胞中,并且對巨噬細胞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進而對刀豆蛋白A誘導的AIH小鼠肝臟具有有效的保護作用。該研究發現,與傳統的DEX治療相比,MSC衍生的外泌體作為DEX載體給藥,對AIH具有更好的治療效果[17]。這些研究結果表明,外泌體可能為AIH的治療提供一定的方向和依據。
(二)外泌體在PBC和PSC中的作用 PBC以前稱為原發性膽汁性肝硬化,是一種以肝內中小膽管的非化膿性進行性破壞性損傷為特征的慢性肝內膽汁淤積性疾病,最終可發展至肝硬化。PBC多見于中老年女性,其發病機制可能與遺傳、環境及免疫等因素有關。抗線粒體抗體是PBC的特異性標志物,且PBC最典型的臨床癥狀為乏力、瘙癢、黃疸及消化不良[18]。PSC也是一種慢性膽汁淤積性病變的自身免疫性肝病,其主要特征為特發性肝內外膽管炎癥和纖維化,進而導致多灶性膽管狹窄,最終可發展為肝硬化和肝衰竭。PSC多見于中青年男性,主要癥狀表現為乏力、瘙癢、骨質疏松和脂溶性維生素缺乏等,其病因可能與感染、腸毒素吸收、遺傳、免疫及膽管缺血等因素有關[19]。研究發現,從PBC患者血漿中分離出的外泌體雖然不會改變細胞因子的產生,但它們確實顯著改變抗原呈遞細胞上的共刺激分子表達,如CD14+單核細胞上的CD86表達上調,以及CD11c+樹突狀細胞的CD40表達上調。這些共刺激分子在調節T細胞活化中發揮不同的作用,可能參與PBC的發病機制[20]。Liu R等研究發現,PBC、PSC患者的血清外泌體H19水平顯著上調,通過real-time PCR、western blot、組織學和免疫組織化學分析小鼠和人PSC/ PBC肝臟樣本,發現肝H19水平與肝纖維化的嚴重程度密切相關。肝星狀細胞(HSC)在膽汁淤積性肝病進展中起著關鍵作用,體外實驗發現富含H19的外泌體能夠增強小鼠原代HSC的轉分化,并促進HSC衍生的成纖維細胞的增殖。體內實驗表明在膽汁淤積條件下,膽管細胞來源的富含H19的外泌體快速且優先被HSC及HSC衍生的成纖維細胞吸收,然后通過上調成纖維細胞的纖維化基因表達,從而促進肝纖維化。這項研究表明,膽管細胞源性外泌體H19可以作為膽汁淤積性肝纖維化的潛在診斷標志物和治療靶點[21]。膽管細胞衰老是PBC和PSC的重要病理過程。Chen W等將氧化應激刺激的膽管細胞類器官與人胎盤間充質干細胞(hPMSC)衍生的外泌體共培養,使用免疫組織化學、免疫熒光染色及ELISA等試驗分析,發現hPMSC衍生的外泌體治療可延緩膽管樣衰老進程并降低SASP成分和趨化因子的表達,如CCL2、CX3CL1、IL-6、TNF-a、CXCL1和CXCL10,表明hPMSC衍生的外泌體可能對PSC或PBC具有治療潛力[22]。這些研究結果表明,外泌體既可以作為PSC或PBC微創分子生物標志物,也可能是PSC或PBC的潛在治療靶點。
(三)外泌體與DILI DILI是指由藥物本身,如化學藥物、傳統中藥、保健品等,及其中間代謝產物所誘發的肝損害[23]。由于DILI無特異的臨床表現,診斷困難,多通過測定患者肝功能指標、常規影像學檢查及肝活檢來輔助診斷。近年來,一些研究認為外泌體可能作為潛在分子生物標記物,用于DILI的早期檢測、監測和評估。乙酰氨基酚(APAP)引起的急性肝衰竭是DILI和死亡的主要原因。在APAP-DILI的SD大鼠中,循環miR-122的數量增加,并且miR-122主要存在于外泌體中。此外,當人原代肝細胞暴露于10mM APAP 24 h后,外泌體中miR-122的水平明顯增加[24]。在另一項研究中,APAP給藥能顯著提高外泌體中miR-122、miR-192和miR-155的表達量,這三種外泌體miRNA可以反映肝細胞損傷情況[25]。Zheng等對苦楝水提取物(FMT)暴露的小鼠血清循環外泌體中的miRNA進行差異表達分析,發現外泌體miR-370-3p是變化最顯著的miRNA。外泌體miR-370-3p通過升高p21和細胞周期蛋白E,從而加重中藥的細胞毒性作用,提示外泌體miRNA參與了中藥肝損傷的發病機制[26]。這些研究表明,外泌體中miRNA可以作為診斷DILI的生物標記物。除了miRNA,血液中外泌體mRNA,如白蛋白(Alb)、纖維蛋白原Bβ-多肽(Fgb)、結合珠蛋白(Hp)和β-肌動蛋白(Actb),鳥嘌呤核苷酸結合蛋白(G蛋白),β多肽2樣蛋白1(Gnb2l)和血漿視黃醇結合蛋白4(Rbp4)等均可作為DILI的生物標記物[27,28]。在DILI小鼠模型中,APAP治療影響了138種外泌體蛋白的豐度,如CES1、ADH1、GST、APOA1、ALB、HP和FGB蛋白,外泌體蛋白的表達水平與APAP劑量和暴露時間有關。這些研究表明血液中除了外泌體miRNA和mRNA外,外泌體蛋白也可以作為DILI的敏感生物標記物[29]。此外,研究還發現,來源于 MSC和肝細胞的外泌體能夠促進肝臟再生,調節炎癥反應,減少肝細胞凋亡,可以作為DILI的潛在治療藥物和靶點[30]。Tan CY等通過不同的給藥途徑將外泌體與CCl4同時引入小鼠模型,發現MSC衍生的外泌體通過促進肝細胞的增殖,增加細胞核抗原(PCNA)、細胞周期蛋白D1和細胞周期蛋白E的表達,逆轉CCl4誘導的損傷。體內研究表明,在APAP和H2O2引起的損傷后,MSC來源的外泌體可以通過上調 Bcl- xL 抑制 APAP誘導的肝細胞凋亡蛋白表達,通過激活增殖和再生反應來引發針對毒物誘導的損傷的肝保護作用[31]。大多數藥物誘導的肝損傷是由肝臟的適應性免疫攻擊引起的。Holman NS等通過聚合物沉淀法從原代人肝細胞的條件培養基中分離出外泌體,然后用肝細胞來源的外泌體(HDE)處理THP-1單核細胞,并用LPS刺激,發現HDE能夠導致LPS誘導的IL-1β 和IL-8水平顯著降低。另外,通過差異表達基因發現,HDE導致72個轉錄本減少,其中許多轉錄本涉及免疫功能。在這些差異表達基因中第二豐富的信號通路是“先天免疫細胞和適應性免疫細胞之間的通信”,表明先天免疫細胞(如單核細胞)內的變化可能影響適應性免疫反應。這些數據表明,在DILI中,HDE能夠被單核細胞吸收并傳遞功能性miRNA,這些調節性miRNA和其他外泌體內容物靶向多種免疫介導的轉錄物,并抑制LPS刺激的細胞因子釋放,從而促進肝臟的免疫耐受[32]。
(四)外泌體與NAFLD NAFLD是指排除飲酒史或酒精攝入過多、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藥物性肝損傷等所導致的肝臟疾病,其主要病理特征為肝細胞的脂肪蓄積和大泡性脂肪變。NAFLD包括單純性脂肪肝(NAFL)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 到肝硬化及肝癌的一組疾病[33]。外泌體對脂質代謝具有顯著影響,包括脂質的合成、運輸和降解[34]。將帶有miR-199a-5p的外泌體遞送到高脂飲食誘導的脂肪變性模型小鼠中,發現小鼠肝細胞中的脂質積聚加重,同時伴有肝哺乳動物不育系 20 樣激酶 1(MST1)表達的下調,最終加劇肝細胞中脂質的積累[35]。AMPKα1是調節白色脂肪組織中外泌體合成、組成成分和脫落的關鍵分子。Yan C 等發現AMPKα1基因敲除增加了來源于脂肪細胞的外泌體的脫落,并促進了CD36在外泌體中的積累,然后含CD36的外泌體被肝細胞內吞,誘導脂質積聚和炎癥。另外高脂飲食可減弱脂肪細胞中的AMPKα1,從而誘導外泌體分泌,增強了白色脂肪組織與肝臟之間的通信,促使了NAFLD的發生[36]。在NAFLD患者的血清中 miR-192-5p 水平與疾病進展呈正相關,且M1巨噬細胞(CD11b+/CD86+)激活是 NAFLD 進展中的重要過程。Liu XL等發現在高脂、高膽固醇飲食喂養的大鼠中,血清miR-192-5p水平、M1巨噬細胞數量及肝臟促炎因子的表達水平與疾病進展相關。脂毒性肝細胞分泌富含miR-192-5p的外泌體,該外泌體能夠促進M1巨噬細胞活化,增加誘導型一氧化氮合酶、IL-6和TNF-α的表達。另外,肝細胞源性的外泌體miR-192-5p抑制雷帕霉素不敏感伴隨物(Rictor)的表達,進一步抑制Akt和叉頭盒轉錄因子O1(FoxO1)的磷酸化水平,導致FOXO1的激活,最終誘導炎癥反應,從而推動NAFLD的進展,表明血清外泌體miR-192-5p可以作為NAFLD的潛在無創生物標志物和治療靶點[37]。脂肪毒性和巨噬細胞介導的炎癥在NASH的發病機制中起關鍵作用。Zhao Z等使用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ox-LDL)和甲基-β-環糊精(MβCD)膽固醇處理Huh7細胞,發現膽固醇減少了溶酶體的數量,抑制多泡體在溶酶體的降解,促進Huh7細胞釋放含有miR-122-5p的外泌體。外泌體miR-122-5p誘導巨噬細胞M1極化及相關炎癥,促進了NASH的發生與發展[38]。內質網(ER)參與調節脂代謝穩態,ER應激引起脂質代謝功能障礙,導致肥胖誘導的肝脂肪變性進展為NASH。Gu H等利用重組慢病毒載體基因沉默方法和基于LC-MS/MS的蛋白質組學和脂質組學,發現ER應激誘導的脂肪細胞分泌外泌體(ATEx)能夠協調肝臟中的脂質動態變化。ATEx通過向肝細胞遞送外泌體醛酮還原酶1b7(Akr1b7)并升高甘油水平觸發NASH的發生[39]。IL-6誘導巨噬細胞和中性粒細胞(盡管程度較小)釋放富含miR-223的外泌體,然后外泌體miR-223轉移到肝細胞,抑制具有PDZ結合序列的轉錄共活化因子(TAZ)、Nlrp3、C-X-C基序趨化因子10(Cxcl10)及胰島素樣生長因子1受體(Igf1r)的表達,這幾種miR-223靶向促纖維化基因具有促進NASH纖維化作用,從而為NAFLD的治療提供了新思路[40]。這些研究都表明,外泌體作為細胞間信息交流載體,推動了NAFLD進展,臨床上可將其作為NAFLD治療中的重要靶點。
三、展望
基于目前研究,外泌體攜帶miRNA、mRNA、lncRNA、DNA、蛋白質、脂質等多種物質,在肝內進行細胞間通信,轉運各種信號分子,是細胞之間進行生命活性物質交換的重要載體。外泌體因其具有運輸性質、循環能力及優異的生物相容性,可作為一種理想的藥物載體,遞送多種藥物、蛋白質、核酸和基因治療劑,以提高靶向準確性,同時降低最小劑量和不良反應,為疾病診斷和治療創新提供新的機遇。雖然國內外學者已經對外泌體的靶向給藥、分子標志物及發病機制等方面進行了研究,但是外泌體的臨床應用外尚未展開,故外泌體在不明原因肝病中的發展空間巨大。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外泌體將會為不明原因肝病的預防、診斷、治療提供新的方法和策略。
利益沖突聲明: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