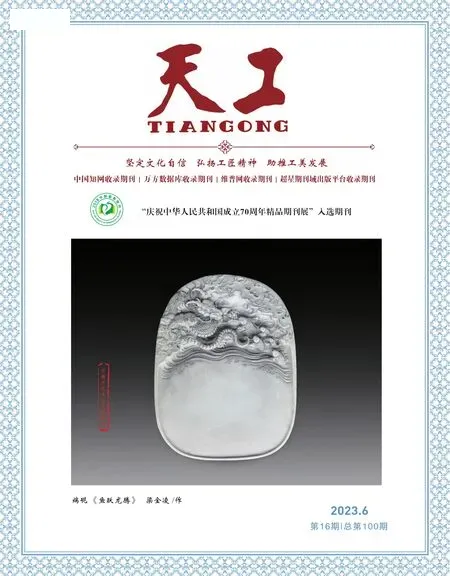“搜妙創真”——郭熙《早春圖》藝術研究
郝夢哲 太原師范學院
一、背景
隨著唐末、五代時期戰亂的結束,我國進入了北宋時期。北宋經濟、社會穩定發展,儒家、道家等各種學說空前繁榮,在這一時期“求真”與“重理”成為文人追求的主要目標。在這種思潮影響下,北宋畫壇中也主張“格物致知”,提倡畫家外出寫生,觀察自然,親近自然,改變了魏晉南北朝到隋唐時期對山水自然的美學認識,更加注重山川河流等自然物象的合理性與準確性。同時,五代時期荊浩在《筆法記》中也提出了“圖真”論,認為“真”是繪畫的目標。他提倡到自然中觀察物象、認識物象。這種“圖真”的思想一直成為北宋中前期畫壇的主流思想。郭熙正是在這種求“真”的思想下逐漸成長起來的。郭熙布衣出生,喜好道學,又愛游歷,他對描摹的山石、樹木、云水、樓閣等賦予了情感化的擬人意義,這種情感符合我國幾千年來的天人合一思想,并且在他的《林泉高致》中進一步發展了和闡述了“真”的含義,同時在他傳世的繪畫作品《早春圖》中又得以充分體現。
二、畫面分析
(一)空間的營造
在畫面空間營造上,郭熙運用了“高遠”“平遠”“深遠”的方法拉開畫面,使畫面有一種朦朧的透氣感。郭熙曾在《林泉高致》中寫道:“自山下而仰山巔,謂之高遠;自山前而窺山后,謂之深遠;自近山而望遠山,謂之平遠。”郭熙將“三遠”法的空間法則完美地運用在《早春圖》中。首先,畫面中主峰就運用了自下而上仰視的角度刻畫,主要目的是突出主峰高聳入云、挺拔的氣勢,給觀者帶來一種強烈的壓迫感,同時還運用了“云煙鎖其腰”的方法,使主峰不僅高聳還充滿了神秘感,使讀者想要深入其中,去探尋其中的奧秘。其次,畫面右側運用了深遠法,巨大、突兀的山石和彎曲遒勁的雜樹層層遞進,把畫面推向了遠處幽深的建筑物,使畫面顯得朦朧幽靜,充滿靜謐感。最后,在畫面左側運用了平遠法,從近景的松樹、磐石再到遠處虛無縹緲的煙崗、丘壑,不僅拉開畫面的前后關系,同時還給讀者一種平淡天真的感覺。
“三遠”法在《早春圖》中得到了完美的應用,郭熙將畫面中的山石樹木、行人屋舍安排得井然有序、處處和諧,使觀者隨著畫面逐漸看向遠方再關注畫面外的精神世界,讓觀者欣然向往這片世外桃源,滿足廟堂之上士大夫的“林泉之心”,這也是郭熙在繪畫中所主張的繪“可行”“可望”“可游”“可居”之景。“三遠”法是郭熙常年觀察自然山川所總結出來的規律,是根據自然空間所建立的法則,是對自然物象的真實描繪。
(二)物象安排
這幅山水畫采用的是當時北宋流行的巨嶂式的構圖方式。在自然界中,自然物象是雜亂無章的,這就需要畫家在創作時把握自然萬物的規律,透過現象,捕捉內在的本質,按照物象的特點合理經營畫面,使其達到和諧。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指出:“大山堂堂為眾山之主,所以分布以次岡阜林壑為遠近大小之宗主也。其象若大君赫然當陽而百辟奔走朝會,無偃蹇背卻之勢也。長松亭亭為眾木之表,所以分布以次藤蘿草木為振契依附之師帥也,其勢若君子軒然得時,而眾小人為之役使。無憑陵愁挫之態也。”從《早春圖》整體畫面來分析,郭熙選擇了三塊巨大的山石放在畫面的中心,通過近景的巨石和松樹一點點把畫面引向主峰,其中,主峰象征著帝王,其他山川丘陵、樹木井然有序地依附在它的身下,寓意著宋朝在宋神宗的帶領下呈現出繁榮昌盛的局面。畫面中心聳立著兩棵古松,其他雜樹彎曲盤旋依附在周圍。這種畫面的主次、從屬關系是對當時社會的一種映射,是一種“真”。

《早春圖》 郭熙 /作(絹本,108.1 cm x158.3 cm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三、物象“真”
《林泉高致》中指出:“春有早春云景,早春雨景,殘雪早春,雪霽早春,雨霽早春,煙雨早春,寒云欲雨,春雨春靄,早春曉景,早春晚景,曉日春山,春云欲雨,早春煙靄,春云出谷,滿溪春溜,春雨春風,春山明麗,春云如白,皆春題也。”在《早春圖》中主要表現了寒冬剛過,冰雪融化、萬物復蘇的景象。作者并沒有在畫面中用任何顏色點綴,卻春意十足。首先,畫家通過描繪遠處逐漸融化的溪流再到中景處瀑布匯聚而成的湍急水流,似乎傳遞著冬天即將過去、春天馬上到來的信息。其次,巨石周圍一棵棵遒勁、曲折的枯樹不斷向上生長,同時剛發出嫩芽的枝條預示著強大的生命力和韌性。最后,畫面中的點景人物雖小卻刻畫生動、有血有肉,有漁人已經下河打魚,岸上婦孺帶著仆人春游,遠處有披著蓑、戴著笠去遠游的旅客,整幅作品都充滿了春天將要來臨時的歡快氣息。
(一)山石“真”
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描述山的形態時說:“山,大物也。其形欲聳拔,欲偃蹇,欲軒豁,欲箕踞,欲盤礴,欲渾厚,欲雄豪,欲精神,欲嚴重,欲顧盼,欲朝揖,欲上有蓋,欲下有乘,欲前有據,欲后有倚,欲下瞰而若臨觀,欲下游而若指麾,此山之大體也。”在《早春圖》的畫面中心,幾塊巨石如洪水猛獸一般“霸占”著畫面的中心,下面巨石蜿蜒曲折,把畫面引向主峰,主峰高聳入云,呈“之”字形走勢,山頭仿若回首作揖,旁邊山峰圍繞在其周圍好像在回禮一般。同時,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指出,畫山石應遠觀取其勢,近觀取其質,多角度、全方位觀察,全身心地投入自然中,用心感受山石、樹木、云水的變化,發現其中的奧妙,同時用相應的筆墨表達出自然萬物。在《早春圖》中,作者在勾勒山石輪廓時,由山石頂部到側面用筆從圓潤的中鋒轉向側鋒,用筆粗獷豪放,線條不僅力量十足而且流暢,圓轉富有變化、抑揚頓挫,有橫掃千軍之勢,用線沒有絲毫的猶豫,這不僅體現了郭熙扎實的繪畫功底,還體現了他的構思巧妙、觀察細致。
在皴山石內部結構上,郭熙為了表現出山石的渾厚感,根據山石的質地,運用長短不一、粗細不同的“卷云皴”,按照山石的陰陽向背來皴擦,以表現出山石外緊內松的質感。在具體繪畫過程中,山石內部用扭動皴法,中側鋒所用線條有長有短,有粗有細,墨色有濃有干。近處山石外輪廓線條溫潤如玉,彈性十足,內輪廓用筆肆意縱橫,線條變化豐富,表現出山石內部毛而松的質地,之后用墨色按照石頭的陰陽向背關系層層渲染,揮灑恣意,使山石雄渾、大氣,融為一體。郭熙運用溫潤而又細膩的墨色表現出山石的結構、虛實關系、陰陽向背,這體現了他常年觀察自然物象,總結規律再不斷探索筆墨之法,最終用相應的筆墨合理地表現自然規律的“真”理。
(二)樹木“真”
畫面中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兩棵聳立的古松,用筆遒勁有力,枝干如蛟龍虬曲一般,細枝為“蟹爪”造型,這是典型的李成一派的特點,這兩棵松樹在畫面中仿佛威武的將軍統領著其他樹木。細看松樹,在用筆力量上呈現出階梯式的分布,首先,樹干用筆最為強勁有力、抑揚頓挫,再到枝干的用筆,最后到伸出來的細小的枝干,這種力量的變化是符合真實的自然物象生長規律的。松樹上剛生長出來的嫩枝,郭熙用中鋒長線細筆迅速地勾勒出來,到枝頭時彈射而出,所以畫面中的新枝雖然細小卻韌性十足,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畫面中的老枝郭熙用略微老澀、抑揚頓挫的筆觸表現出老干上面的褶皺和結疤,老干雖然用筆較粗卻有一種松散、脆弱之感。之后,郭熙又根據樹上的結疤、質地,用相應的筆觸,不厭其煩地表現出來。最后再用淡墨渲染樹木的暗部,分出陰陽,用細筆勾畫松針,穿插其中,強調松樹在畫面中的位置。在松樹下面陪襯著點葉樹,用筆力度較小,結構較少,點葉用淡墨點染,沒有過多的變化,主要是為襯托主樹和拉開前后關系服務的。在遠山上,郭熙用“泥里拔丁皴”來表現遠處茂密的樹木,這些筆墨的總結都是郭熙在生活中長期觀察所得。
(三)水“真”
《林泉高致》中寫道:“水欲遠,盡出之則不遠,掩映斷其脈則遠矣。”從《早春圖》中可以看到,在畫面左端,伴隨著一層層深谷、丘陵,若隱若現地流出一股清泉,可能是由于冰雪剛剛融化,水量較小。之后分為兩支,從畫面左右兩端的山澗處噴涌而出,匯入下端的河流中。郭熙用富有彈性的弧線表現水流的湍急,用平滑、略帶彎曲的線條表現出水面的平靜。同時為了表現出山澗兩邊由于常年背光和河水沖刷后陰暗潮濕的山體,郭熙用淡墨反復渲染,將其完美地表現出來。
(四)點景“真”
在《早春圖》中有著許多點景,這些點景雖小,卻在畫面中起著畫龍點睛的作用。首先看畫面左半部分岸邊停著一艘漁船,郭熙在靠近岸邊的部分用直線勾勒,意在表現出船體的穩定感,在遠離岸邊的部分用抖動的線條表現,旨在體現船體受到水流沖撞的不穩定感。岸上,有一位婦人抱著一個小孩,可能剛從船艙出來,旁邊還有兩個挑著包袱的仆人,走向遠處山腳下的一間破舊房子。郭熙用斷斷續續、抖動的線條將房屋的殘缺表現出來,這一組場景的刻畫生動反映了當時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情景,體現了郭熙游歷之廣、觀察之微妙。
畫面最左側的山間小路上有幾位挑著貨物的商旅,他們沿著彎曲的山路通向畫面右側的建筑。這就是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所提到的:“山之人物以標道路,山之樓觀以標勝概,山之林木映蔽以分遠近,山之溪谷斷續以分淺深。”山路斷斷續續寓意著旅途之遠,這些旅客可能是作者也有可能是觀者,通往那內心向往的“可游”“可居”之地。
畫面右側有兩個漁夫,其中一位在前面劃船,后面的半蹲著,似乎在弄漁網,郭熙用準確的線條勾勒出漁夫健壯的肌肉,表現出漁夫的力量感。
畫面中的點景不僅造型準確、神態各異,同時還十分具有生活氣息,是對自然物象的真實描繪。這些都得益于郭熙常年游歷四方,體驗社會不同階層的生活百態,細心總結內在的道理,最后才能夠準確地將其表現出來。
四、總結
《早春圖》描繪了早春時節萬物復蘇、煙巒萌動的場景,用獨特的筆墨技法表現出早春時節的裊裊云煙、霧氣蒸騰的美感,畫面中筆墨干濕結合,淡墨層層渲染,筆墨相互融合、交織在一起,形成一種既濕潤又朦朧的神秘景象。清代乾隆皇帝也寫下了“不籍柳桃閑點綴,春山早見氣如蒸”來贊美這幅畫的霧氣蒸騰之美。
郭熙在李成的基礎上對自然物象的描繪更加細致,通過全身心觀察,同時又師法自然,在觀察寫生自然物象中總結出“真山水之風雨,遠望可得,而近者玩習,不能究錯縱起止之勢;真山水之陰晴,遠望可盡,而近者拘狹不能得明晦隱見之跡”。也就是說真山水是遠觀取其勢,把握其神韻,領略山川的氣質和脈絡,用心感受風雨云霧。近看感受山石的質地,聆聽山林風聲,品味山中甘露,細心感受不同季節物象的特點,用心捕捉山川萬物的自然變化規律,最后用“五日一水,十日一石”的嚴謹態度去對待繪畫,這樣才能描繪出“可行”“可望”“可游”“可居”之景。這其中體現出人與自然的一種親和關系,也是對“理”的一種追求,同時,郭熙對“理”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從“觀物”“審物”“體物”這三個階段對事物進行觀察、揣摩和分析,獲得描繪事物的技法,進而把握事物的本質規律,獲得對事物之“理”的真正把握。其繪畫思想是對張璪“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完美體現,是郭熙深刻的生活體驗、生動的繪畫表現能力和全身心投入創作的精神的完美結晶。最后,觀者在觀賞的過程之中,滿足了自己的審美需求,這才是“真”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