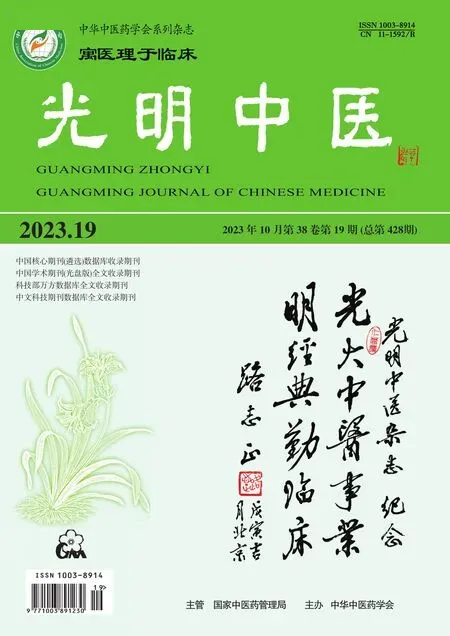聰耳通竅湯聯合耳聾左慈丸治療慢性分泌性中耳炎臨床觀察
劉厥軍 焦 敏
分泌性中耳炎是耳鼻喉科常見且多發一種疾病,也是導致患者聽力損失的一種疾病,主要是由于中耳常含乳突,引發腔內逐漸形成積液,導致聽力下降的炎癥疾病,慢性分泌性中耳炎主要指的是病情反復遷延大于3個月或病程持續大于8周的患者[1]。臨床常通過給予患者糖皮質激素、抗生素等藥物進行聯合治療,具有一定的治療效果,但可能出現反復發作的情況,致使病情遷延不愈[2]。中醫學認為該病屬于“耳脹、耳閑”等范疇,在發病初期以耳脹較為多見,主要表現為耳內脹悶的癥狀,可能還會伴有一定的疼痛;病之久者則見耳閉,可表現為聽力下降、清竅閉塞、有物阻隔,通常由于耳脹遷延不愈、反復發作致使邪毒在耳竅內滯留所導致[3]。聰耳通竅湯包含有白術、黨參等多種中藥成分,具有通竅聰耳、行氣活血之功效[4]。耳聾左慈丸主要由牡丹皮、熟地黃等多種中藥配制而成,具有通利耳竅、疏肝解郁之功效[5]。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慢性分泌性中耳炎患者應用聰耳通竅湯聯合耳聾左慈丸治療的療效,研究結果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選取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區人民醫院2021年6月—2022年6月收治的慢性分泌性中耳炎患者76例,按隨機數字表法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各38例。所有患者及家屬均知曉并簽訂知情同意書,且本研究已經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區人民醫院的醫學倫理委員會部門許可。觀察組和對照組的病程、年齡、性別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2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 (例,
1.2 診斷標準中醫參照《中醫耳鼻喉科常見病診療指南》[6]、西醫參照《臨床實踐指南:分泌性中耳炎(更新版)》[7]中關于慢性分泌性中耳炎的診斷標準。
1.3 納入標準符合上述中醫和西醫的相關診斷標準者;均屬于單耳發病者;近3個月內未接受其他中成藥治療者;心、肝、腎功能均無異常者;認知功能及精神狀態均正常者等。
1.4 排除標準伴有耳鼻喉占位性病變者;其他原因致使中耳發生積液者;妊娠期或哺乳期女性;對本研究所使用藥物(阿奇霉素)過敏者等。
1.5 方法
1.5.1 治療方法對照組實施常規治療措施,早餐前口服阿奇霉素片(規格:0.25 g/片,國藥準字 H20023655,國藥集團汕頭金石制藥有限公司),0.5 g/次,1次/d;飯前口服標準桃金娘油腸溶膠囊(成人裝)(規格:300 mg/劑,注冊證號:Z20100008,德國保時佳大藥廠),300 mg/次,3次/d;每晚睡前口服氯雷他定片(江蘇蘇中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國藥準字 H20041016,規格:10 mg/片),10 mg/次;外用鹽酸賽洛唑啉滴鼻液(湖北遠大天天明制藥有限公司,國藥準字 H10940166,規格:10 ml/劑),2滴/次,2次/d。觀察組在對照組基礎上聯合聰耳通竅湯,組方:白術、黨參、陳皮各15 g,法半夏、茯苓各12 g,白芥子、香附、川芎、桔梗、路路通、石菖蒲各10 g,柴胡9 g,炙甘草、升麻各6 g。水煎至400 ml為1劑,1劑/d,分早晚2次服用。耳聾左慈丸治療(陜西渭南華仁制藥有限責任公司,國藥準字 Z20063331,規格:1.6 g/丸),1.6 g/次,2次/d。2組均連續治療10 d。
1.5.2 觀察指標①臨床療效:對2組治療后的臨床效果進行比較。②中醫癥狀積分:分別于治療前后,依據《中醫耳鼻喉科常見病診療指南》[6]評估2組中醫癥狀積分,包括頭暈眼花、手足心熱、聽力下降、耳閉,根據癥狀情況分別評為0分(無癥狀表現)、2分(偶爾有癥狀發生)、4分(長期存在癥狀表現,偶爾有所好緩解)、6分(存在難以忍受的癥狀表現,且難以緩解)。③血清水通道蛋白(AQP-1)、復合性粘蛋白(SIL-2R)、缺氧誘導因子(HIF-1α)水平:分別于治療前后,對2組靜脈血進行采集,約5 ml,置于離心設備進行處理15 min(轉速為3000 r/min),檢測血清AQP-1、SIL-2R、HIF-1α水平,檢測方法:酶聯免疫吸附法。④骨導、氣導閾值:分別于治療前后,使用純音型聽力計(杭州惠耳聽力技術設備有限公司,浙械注準:20142070249,型號:HT001-B)在標準隔音室中對2組患側耳進行純音測聽檢查,分別記錄在1、2、4、8 kHz頻率的骨導閾值和在0.5、1、2 kHz頻率的氣導閾值。⑤不良反應:記錄并比較2組治療期間不良反應的發生情況,包括肝腎損傷、腹瀉、嘔吐。總發生率=總發生例數/總例數×100%。
1.5.3 療效判定標準依據《臨床實踐指南:分泌性中耳炎(更新版)》[7]評估2組治療后的臨床效果,將癥狀體征消失,鼓室曲線為A型,鼓膜和聽力均恢復正常,癥狀積分降低幅度超過90%評為治愈;將癥狀體征消失,鼓室曲線為As型或A型,鼓膜基本恢復正常,癥狀積分降低幅度處于60%~90%評為顯著改善;將癥狀體征有所好轉,鼓室曲線為As型,鼓膜有所改善,癥狀積分降低幅度處于30%~59%評為改善;將癥狀積分降低幅度低于30%,癥狀體征、鼓膜情況均無緩解,鼓室曲線為C或B型評為無效。計算臨床總有效率:治愈率+顯著改善率+改善率=總有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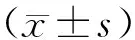
2 結果
2.1 2組患者臨床療效比較觀察組治療后臨床總有效率與對照組相比較高(P<0.05)。見表2。

表2 2組患者臨床療效比較 (例,%)
2.2 2組患者中醫癥狀積分比較與治療前比較,2組患者治療后中醫癥狀各項積分降低,且觀察組比對照組低(P<0.05)。見表3。

表3 2組患者中醫癥狀積分比較 (分,
2.3 2組患者血清AQP-1 SIL-2R HIF-1α水平比較與治療前比較,2組患者治療后血清AQP-1水平均升高,且觀察組比對照組高;2組患者治療后血清HIF-1α、SIL-2R水平均降低,且觀察組較對照組更低(P<0.05)。見表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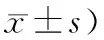
表4 2組患者血清AQP-1 SIL-2R HIF-1α水平比較 (例,
2.4 2組患者骨導 氣導閾值比較與治療前比較,2組治療后不同頻率的骨導、氣導閾值均降低,且觀察組比對照組低(P<0.05)。見表5。

表5 2組患者骨導 氣導閾值比較
2.5 2組患者不良反應比較觀察組和對照組治療期間的不良反應總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6。

表6 2組患者不良反應比較 (例,%)
3 討論
分泌性中耳炎的發病機制和病因較為復發,且可能是由于多種因素相互作用所導致,目前臨床認為其發病可能與免疫學、變態反應、感染、咽鼓管功能障礙等多種因素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聯系,且具有遷延難愈、反復發作等特點。臨床上常通過聯合多種藥物進行綜合治療,如抗組胺藥可對患者咽鼓管或鼓室的水腫癥狀進行改善,顯著降低分泌物的釋放;表面活性物質藥物可促進咽鼓管開放,致使中耳積液快速排除,緩解咽鼓管發悶、堵塞的癥狀,具有一定的臨床療效,但長期使用可能出現一系列的不良反應,影響預后恢復[8]。
中醫學理論中認為慢性分泌性中耳炎的發病與脾胃損傷密切相關,主要病理機制在于脾虛濕滯、風邪侵肺,是實虛夾雜之證,應以健脾利濕、疏風通竅、清熱化痰為主要治療原則。聰耳通竅湯中的白術可燥濕利水;黨參可健脾益肺;陳皮可燥濕化痰;法半夏可消腫散結;茯苓可利水滲濕;白芥子可通絡化痰;香附可疏肝解郁;川芎可活血化瘀;桔梗可化痰宣肺;路路通可通絡祛風;石菖蒲可化濕和胃、開竅豁痰;柴胡可解熱鎮痛;炙甘草可清熱解毒;升麻可清熱解毒;諸藥合用共奏通竅聰耳、化痰除濕之功效。耳聾左慈丸中的澤瀉可利水滲濕;山萸肉可補腎固精;熟地黃可滋陰補血;牡丹皮可活血化痰;磁石可聰耳明目、平肝潛陽,諸藥合用共奏通利耳竅、疏肝解郁、滋肝益腎之功效。本研究結果顯示,治療后觀察組臨床總有效率與對照組相比較高;治療后觀察組中醫癥狀各項積分比對照組低;治療期間,2組不良反應總發生率經比較無明顯差異,表明聰耳通竅湯聯合耳聾左慈丸治療慢性分泌性中耳炎可有效改善患者臨床癥狀,提高臨床療效,具有較高的安全性,與張志敏等[9]研究結果相似。
AQP-1可參與到中耳腔內液體的調節過程;SIL-2R可與白介素2受體進行結合,抑制免疫作用;HIF-1α具有放大炎癥的作用,促使中耳積液合成。慢性分泌性中耳炎患者多伴有聽力下降的癥狀,骨導、氣導閾值是臨床評估聽力損失程度的常用指標。現代藥理學研究顯示,白術中包含的內酯類成分可對機體內巨噬細胞的表達產生作用,降低炎性因子的合成和釋放,發揮抗炎的作用,且其多糖成分可對機體淋巴細胞產生激活作用,誘導淋巴細胞的轉化,發揮免疫調節作用,進而調節血清因子水平[10]。山萸肉中的多糖和總苷類成分可對黏膜分泌細胞的生長繁殖和黏膜上皮化生等產生抑制作用,減輕炎癥反應對機體系統造成的損傷,減少分泌液的產生,進而達到改善聽力下降的癥狀,促進聽力水平的快速恢復[11]。本研究結果顯示,治療后觀察組血清SIL-2R、HIF-1α水平、不同頻率的骨導、氣導閾值比對照組低;觀察組血清AQP-1水平比對照組高,表明聰耳通竅湯聯合耳聾左慈丸治療慢性分泌性中耳炎可有效提升聽力水平,調節血清AQP-1、SIL-2R、HIF-1α水平,與霍炳杰等[12]研究結果相似。
綜上,聰耳通竅湯聯合耳聾左慈丸治療慢性分泌性中耳炎可有效改善患者臨床癥狀,提升聽力水平,調節血清AQP-1、SIL-2R、HIF-1α水平,提高臨床療效,具有較高的安全性,值得臨床應用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