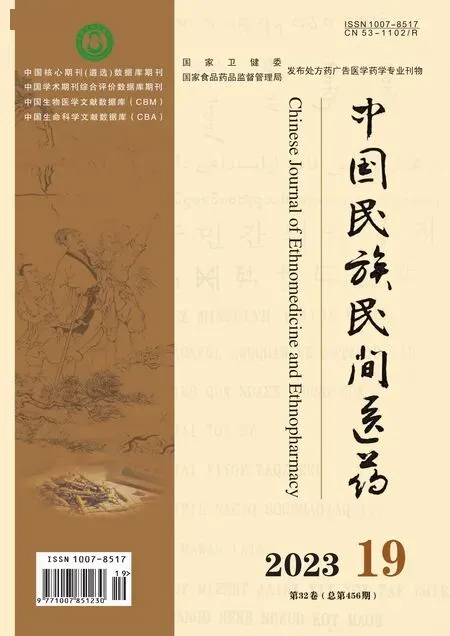花椒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的運用探析
黃詩雅 施聞華 陳本澍 林書馨 張曉軒
1.廣州中醫藥大學,廣東 廣州 510105;2.省部共建中醫濕證國家重點實驗室(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廣東 廣州 510120
花椒是古代椒類藥材的主要品種,為現代蕓香科花椒屬植物花椒的干燥果皮,又名蜀椒、川椒。作為藥食兩用的藥物,花椒在我國最早的本草專著《神農本草經》(以下簡稱《本經》)中被奉為“上品”,但在現代臨床中因醫家畏懼其大辛大熱之性,多將其用于濕疹外洗或腹部熱敷[1-2],使之成為遺珠棄璧。《備急千金要方》(以下簡稱為《要方》)與《千金翼方》(以下簡稱為《翼方》)由唐代醫家“藥王”孫思邈所著,集唐以前醫學之大成,是我國醫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醫學典籍,書中多篇均有運用花椒的記載。本文對《要方》《翼方》兩書中花椒的功效、運用及配伍規律進行整理挖掘,為臨床應用花椒提供思路。
1 研究方法
1.1 版本選擇 研究統一版本:《備急千金要方》統一為《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為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耀州喬世寧小丘山房刊本(國家圖書館掃描本);《千金翼方》統一為清同治戊辰七年掃葉山房藏版(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掃描本)。
1.2 方劑檢索 以“花椒”“蜀椒”“川椒”為關鍵詞,對《要方》《翼方》進行全文檢索。
1.3 方劑錄入規范標準
1.3.1 方劑命名 若原文有記載方劑名稱則以原文為主,若原文無方劑名稱,則按以下規則進行命名;若方劑所含藥物在3味或以內,則根據藥物名稱命名;若方劑藥味超過3味,則以所主的第一個證候或癥狀為主,命名為“xxx方”。
1.3.2 重復方劑的處理 對于方名不同而組成相同的方劑不予重復累計,方名相同而組成不同的方劑按不同方劑累計,另一方名按“1.2.1”中無方劑名稱處理。
1.3.3 藥物名稱、性味歸經 按照《中國藥典》2020版[3]進行規范,對于未被《中國藥典》收錄的藥物,則依照《中華本草》[4]進行檢索保留。
1.4 數據庫的建立 錄入相關方劑所在的章節、方劑名稱、組成及劑量、所治疾病、劑型等內容。
1.5 統計處理 利用Excel 2019進行處方錄入,建立數據庫并進行藥物功效類別的頻次統計;使用IBM SPSS Modeler 18.0軟件進行關聯規則分析,建立“數據源→類型→網絡”關聯規則數據流,并利用Apriori建模進一步挖掘藥物之間的配伍關系,分析對藥使用情況;支持度≥15%,置信度≥80%,提升度>1分析,并對藥物潛在關聯規則進行復雜網絡視圖展示。
2 研究結果
2.1 主治病種 兩書中涉及花椒的篇數為33篇,超過總篇數(60篇)的一半,主治疾病有57種,包括五臟風冷、咳嗽上氣、下痢、虛勞、積聚等內科雜病;傷寒、卒中、風痹、偏枯等風寒所致急癥;耳聾齒痛等頭面五官受邪病患;金瘡、癰疽等外科疾病;還包括婦人無子、產后病等婦科疾患(詳見表1)。

表1 《要方》和《翼方》中含花椒組方應用統計表
2.2 常見配伍 198首含花椒的處方共配伍藥物280味,其中頻次≥30次的有干姜、肉桂、附子、細辛、當歸、人參、甘草、防風、川芎、草烏等(詳見表2),常見配伍包括蜀椒-干姜、蜀椒-肉桂、蜀椒-細辛等。

表2 高頻配伍藥物頻次分布表(X≥30)

表3 高頻藥物關聯規則分析表(前項數為1)
2.3 服用方法 《要方》《翼方》中花椒所在處方提及使用方法的有184條,內服劑型包括湯劑、丸劑、酒劑,丸劑以蜜丸為主;外用劑型包括栓劑、熨劑、浴劑,可外用也可內用的劑型為散劑、膏劑。

圖1 高頻藥物之間的關聯規則網絡展示圖 (線條粗細代表關聯強弱)
3 討論
3.1 花椒的功效 作為藥食兩用的藥物,花椒在《要方·食治篇》中相關記載為:“辛,大熱,主邪氣,溫中下氣,留飲宿食;能使痛者癢,癢者痛。主咳逆;逐皮膚中寒冷;去死肌:濕痹痛;心下冷氣;除五臟六腑寒,百骨節中積冷,溫瘧;大風汗自出者,止下利,散風邪。”對其具體作用進行歸納,可分為以下方面。
3.1.1 溫中補虛 從其性味看,花椒性溫熱,針對證候以寒性為主,條文中“溫中下氣”“心下冷氣,除五臟六腑寒”“止下利”與方劑主治內科病中“久寒虛冷”“寒冷虛損”“寒中”“腹中有冷水”等病性虛寒的描述一致,故花椒具有溫中補虛的功效。
3.1.2 解表散寒,逐濕止痹 花椒味辛,藥效多走表,辛熱解表故“能使痛者癢,癢者痛”“逐皮膚中寒冷,去死肌,濕痹痛”“百骨節中積冷,溫瘧,大風汗自出者”“散風邪”,結合風寒所致急癥、外科疾病、五官疾患方劑主治中常強調“寒氣支節疼”“傷寒”“中風濕冷”等寒濕病邪性質以及“頭痛項強”“腰背強引頸”等寒性收引凝滯癥候特點的記載,可見花椒具有解表散寒,逐濕止痹之效。
3.1.3 溫經通脈 在主治婦科疾病的方劑條文中常強調“此大寒冷所為方”“產后中風寒經氣”等寒性致病因素,“血得溫則行,得寒則凝”,寒凝血脈為花椒治療婦科病針對的病機靶點,因而花椒還具有溫經通脈的作用。
3.1.4 辟瘟解毒 值得一提的是,在《要方·卷十七肺臟方》中,含有花椒的方劑主治疾病反復提及而現今鮮見的病名:“鬼疰飛尸”“疰忤”“十種疰”。“鬼疰”首見于《本經》,原指與神志不清有關的疾病,至隋唐時期演繹為“具傳染性的疾病”,“疰”指具有傳染性的慢性疾病[5],故孫思邈將其置于肺系疾病中,并有“治疰病相染易”的說法。聯系花椒所在方劑還有“主南方瘴氣疫毒”(《翼方·卷第二十雜病下》)、“辟疫氣令人不染溫病及傷寒之方”(《要方·卷九傷寒方上》)的記載,可見花椒味辛性溫,氣味皆重,可除濕破瘴,確有抑制傳染病傳播的作用,故在該書中有“以絳囊佩帶之,男左女右”,將藥物制成香囊以辟瘟防病。而另一反復出現的疾患:“蠱毒”“中蠱”“蠱疰”,蠱為一種毒蟲,對人體造成的危害稱為蠱毒,《隋書》中便有“使人食之入腹,蠱食其人五臟”的記載[6],故花椒還具有殺蟲解毒之效。
3.2 花椒在《要方》《翼方》中的配伍規律
3.2.1 配伍溫里藥而溫中止痢、散寒止痛 干姜作為配伍頻次最高的藥物,味辛性熱,主“濕痹,腸澼,下利”(《本經》),對治中焦虛證寒證,守而不走,是一味純粹的里藥,在書中花椒與干姜的配伍最常見于治療“冷痢”,且多為久痢,伴有飲食不消、虛勞的表現。桂心具有溫經通脈、散寒止痛、助陽的功效,兼走表位,可解表溫里,又入心經,故與花椒的配伍多見于治療心痛疾患,因寒邪入心凝結血脈,故需以桂心、花椒溫經通脈,散寒止痛。
附子、烏頭同為毛茛科烏頭屬植物,附子溫陽益火,走而不守;烏頭走竄之性更強,善祛風除濕、通痹止痛[7]。附子搭配花椒多用于治療風寒邪氣入里之疾,如積聚、冷痢等;烏頭搭配花椒則多用于風寒濕邪襲表所致之痹痛、眩冒、偏枯等。
3.2.2 配伍補虛藥而散寒養血、補虛緩急 《金匱要略》中仲圣以“白術四分,芎四分,蜀椒三分,去汗,牡蠣二分”成白術散用于“妊娠養胎”。可見花椒雖性溫味辛,藥性走竄,實則并無動胎之弊,反有溫經養血之功。藥王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擴大了花椒在婦科疾患中的運用,有文獻[8]指出孫思邈對于婦科病的治療強調“胞中風寒”“產”“墮”“瘀血”等寒凝、血瘀的病機。而花椒可溫散血脈,與藥王重視的病機相契合,配伍性溫味甘入血分的當歸,可溫血養血,對治血虛血寒之證。在《金匱要略》另一含有花椒的處方大建中湯中,則以花椒配伍溫里的干姜與甘滋補虛的人參、飴糖,以對治陽虛寒凝所致的虛寒性腹痛[9],《千金》仿此配伍,以花椒配伍人參、甘草等甘味補虛藥,取花椒大辛大熱散寒解表,甘藥補中緩急對治里位,用于治療風寒入里所致的虛損性病癥如驚悸、疼痛等。
3.2.3 配伍辛溫解表藥而祛風散寒,通竅除痹 在高頻配伍辛溫解表藥中,細辛可除“風濕痹痛”(《本經》),“下氣,破痰,利水道”(《別錄》),溫化表上寒飲,配伍花椒共同發揮解表散寒,逐濕止痹的功效,適用于風寒濕邪束表所致的痹痛、金瘡、癰疽、鼻竅不利。防風為“風中潤藥”,發散風邪的同時可顧護表上津液,能勝濕止痙[10],配伍花椒以對治外寒束表而津血不足所致的外感表證、風疹瘙癢、肢體麻木痹痛等癥。川芎為“血中之氣藥”,能“上行頭目,下調經水,中開郁結”,故除辛溫解表外,尚有活血補血之功,與花椒配伍可對治寒邪束表、結于血分所致偏枯痙攣,尤以治療婦科雜病中婦人受寒后寒入胞宮,遂致經血不利、癥瘕不孕居多。
3.3 劑型多樣,用藥靈活
3.3.1 內服劑型 內服劑型中,丸劑多“搗篩為末,煉蜜和丸如梧子”,蜂蜜“味甘,平。……安五臟,諸不足,益氣補中,止痛解毒。除眾病,和百藥”(《本經》),味甘而緩,補中安和五臟。因積聚、婦科雜病、咳嗽氣逆等久病舊疾,雖有積聚癥瘕、寒飲停聚等實邪,但因病久體虛,不可妄用攻下除結,故以蜂蜜和藥,可緩攻補虛。又花椒味較辛辣,若入丸劑并以蜜和之,可改善服藥口感。且因久病病況復雜,處方藥味時可多達二十余味,若以湯劑服用未免劑量過大,故以丸劑和合,可同時容納多味藥物。酒劑是將藥物放在酒中浸漬,以對治中風偏枯諸證,孫思邈認為中風病多是由于風寒外邪入里導致,故在治療中尤其重視汗法以驅散表邪[11],而酒為辛甘微溫之品,可顧護營血而發表,酒漬法可減少煎煮導致的藥物氣味揮發,避免降低藥效,并借助酒將藥勢帶到人體之表。
3.3.2 外用劑型 花椒作為栓劑,常用于婦科疾患中,具體做法為將藥物搗篩置于布袋中,或熬為末,“以棉裹如雞子大”,置于陰道中,取花椒溫中殺蟲的功效,對治“產后陰下脫”。同時花椒以其辛溫走表,養血散寒之效,可作為浴劑單獨使用,或作為熨劑,加熱后置于疼痛部位,可治療因寒凝氣滯引起的痛癥。此外,花椒還具有殺蟲之效,可破瘴防疫,故制成香囊佩戴而能“主南方百毒,瘴氣疫毒,腳弱腫痛,濕痹風邪鬼疰方”。
3.3.3 內外用劑型 內外用劑型包括散劑和膏劑。散劑多用于金瘡、皮膚、外傷以及風邪所致之病,因散劑輕清上行,“散者,散也”,可應用于發散、散結等方面[12],兼之花椒味辛,本身藥性偏升浮發散,故可對治表之疾患。膏劑則多用于治療五官、皮膚疾病,且賦形劑多為豬膏,豬膏味甘性寒,質潤而滑,可潤燥補虛,當皮膚癰疽為表寒困束而內里已化熱熏蒸腐肉時,常用花椒、川芎等辛溫解表、溫散血脈,搭配豬膏以清里熱并化腐生肌。
4 小結
作為藥食兩用的藥物,《本經》中的“上品”,花椒在現今臨床中的運用還有很大的拓展空間。本文通過《要方》和《翼方》中含有花椒的方劑進行整理,并對方劑主治疾病“鬼疰”、“蠱毒”等進行分析外推,得出花椒具有溫中補虛、解表散寒、逐濕止痹、溫經通脈、辟瘟殺蟲的功效。結合書中花椒的藥物配伍規律、劑型,可看出孫思邈對花椒的運用較現今用藥更為靈活豐富,具有一定的文獻參考價值,可進一步指導相關藥理及臨床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