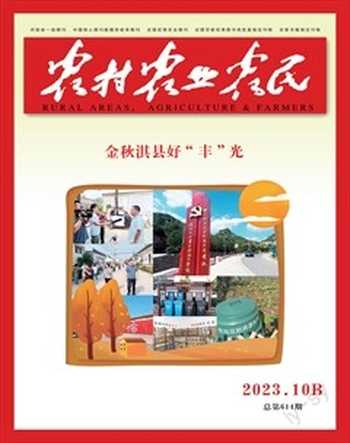農村勞動者法律地位的完善路徑
劉強
摘 要:后脫貧時代下通過制度建設防止農戶返貧是確保扶貧產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手段,而相關制度建設的前提就是要明確農村勞動者的法律地位。現行法律體系對農村勞動者的法律地位定性不太符合農村經濟社會的現實,主體上缺少對農村勞動者特殊性的考量,內容上與農村勞動者權益不夠匹配。對此,可構建以“農務者”為核心的農村勞動者法律地位,以農務法律關系為紐帶,形成以農戶為主體,農戶、組織者與協作者三方共贏的權利義務體系,并增設涉農專業化審判庭,促進涉農糾紛妥善處理。以制度建設為農村勞動者賦能,鞏固拓展脫貧成果,進而實現鄉村振興。
關鍵詞:產業幫扶;全面脫貧;農村勞動者;法律地位
一、產業幫扶中的勞動法律問題
從法律角度看,產業幫扶中的一個首要法律問題就是農村勞動者的法律地位問題。而這一問題的解決對于實現鄉村全面振興至關重要。首先,明確的法律地位可以保障農村勞動者的利益分配。在法治社會中,利益的規范化分配以權利為依托,可以說權利是獲得利益的基礎,而從實證主義法學來看,權利的產生、獲得或賦予則依存于法律。正所謂“權利是法律制度賦予個人保護自身利益的法上之力”。從實證法的角度明確農村勞動者法律地位可以進一步確定其在相應法律關系中的權利義務,進而為維護其合法權益提供依據。其次,明確的法律地位可以為各方提供有效的救濟途徑。產業幫扶涉及多方主體,而且是政策主導,比較容易發生糾紛,而一旦發生法律糾紛應如何處理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產業幫扶雖然是政策導向,但只有為其提供堅實法律基礎從而使糾紛得到妥善解決,才能使扶貧政策行穩致遠、多方共贏。最后,明確的法律地位可以防止制度性返貧。產業幫扶激發的內生型發展模式是變“輸血”為“造血”,強調以持續性發展防止日后返貧現象出現。
綜上,產業幫扶過程中農村勞動形態發生變化的事實需要進一步從法律的視角予以規范,農村勞動者法律地位不明確構成了貧困戶永久脫貧面臨的機制性障礙,而只有首先明確農村勞動者法律地位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二、現行法律體系對農村勞動者地位定性與產業幫扶的脫節
(一)主體上缺少對農村勞動者身份特殊性的考量
產業幫扶的順利開展離不開對農民法律地位的定性。從學理上看,20世紀80年代就有學者提出了農村經濟形態較為特殊,需要針對農村經濟發展現實制定單行的法律。從現實層面看,我國城鄉二元體制是一個不能回避的事實。而現行相關民事法律規則體系對具有農村身份的主體在農村從事經濟活動現狀缺乏充分考慮,除了土地承包法等法規,對于農村身份的勞動者從事勞動缺乏專門的法律法規。只有農村勞動者以城市勞動者面貌參與城市類型中的經濟活動才能受到相關法律保護。也就是說,農村勞動者要參與到市場經濟活動中,只能按照城市勞動者的規則體系參與,但這種情況不利于農村勞動者的利益保護。現行勞動法律體系主要是解決改革開放后國家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勞動力自由配置的問題,主要著眼于保護勞動關系下的勞動者權益。鑒于我國城鄉二元結構這一社會現實,勞動法律體系的實際適用范圍主要是城市中的企業與勞動者,對于農村勞動者在農村經濟組織中的勞動則鮮有涉及。根據《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一條第四款規定,公務員和比照實行公務員制度的事業組織和社會團體的工作人員,以及農村勞動者(鄉鎮企業職工和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除外)、現役軍人和家庭保姆等不適用勞動法。該法從原則上就將農村勞動者排除在適用之外,除非農村勞動者進城務工、經商或者去鄉鎮企業就職。這從規則層面就忽視了農村勞動的特殊性,只有農村勞動者像城市勞動者一樣參與到城市化的經濟形態中,勞動才會受到勞動法保護。無論是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九條、第十一條規定,還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條規定,狹義的勞務關系法律調整作用有限,相關特殊規定也大都集中在侵權損害賠償方面,勞務費則按照一般合同關系處理,相關規則對農村勞動者的勞動形態缺乏針對性。脫貧攻堅作為鄉村振興的基礎并不是要消除農村的特點,而是要將其發揚光大,實現鄉村的本土振興。所以,農村勞動者需要符合其特點的法律法規。
(二)內容上與農村勞動者權益不夠匹配
如果將農村勞動者按照現行體系歸類,大體存在勞動者、勞務者、投資者三種,但這種歸類下的法律形態既無益于農村勞動者,也不利于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就勞動關系而言,勞動關系主要保護的是勞資結構中處于弱勢的勞動者,重點維護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權、休息休假權、集體協商權等,而產業幫扶是幫助農村勞動者脫貧致富的工程,二者并沒有勞資關系那樣的對抗性,如果強行把勞動法律的規則套用到產業幫扶中,則不利于幫扶工作的開展,對幫助農民脫貧的主體會造成經濟負擔,甚至會增加其法律風險,導致其責任感降低。另外,就被幫扶的農村勞動者而言,給予未簽合同雙倍工資賠償權等方面的幫助也并非其真正所需。農村勞動者需要有利于鞏固拓展脫貧成果的法律幫助,現行勞動法體系缺乏這一基礎考量。就勞務關系而言,與勞動關系相反,勞務關系的前提是雙方地位平等,按照民事法律規則確定權利義務,只是在侵權損害賠償方面有一些特殊規則,然而這與幫扶實際又不完全符合。貧困戶往往在某些方面處于弱勢,其與交易對方或者帶領扶貧方缺乏充分的信息對稱和能力對稱,如果法律對這一事實不予以考慮,則無疑會削弱貧困戶的脫貧能力,不利于持續性減貧脫貧。貧困戶畢竟能力較弱,完全套用勞務關系也并不適合。而就投資關系而言,貧困戶以土地或者其他方式出資入股來獲取收益這種方式也有不利之處。一方面,資本市場瞬息萬變,偶然性較多、風險性大,這不利于從根本上保障農村貧困人口脫貧,因為勞動致富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目標,按勞分配才是持續創造財富的源泉,按資分配并不是長久脫貧之策。另一方面,資本收益相關規則的運用需要充分的金融知識、經濟知識、法律知識,即便在城市中,中小股東利益也往往難以得到與大股東同等水平的保護,何況對于貧困戶這一缺乏基本知識儲備的群體。如果為此又專門設立中介機構則相關費用就會成為其新的負擔。所以,現行規則體系的內容與農村勞動者的所需并不匹配,甚至會損害其長遠利益、整體利益,不利于鞏固拓展脫貧成果。
三、賦予農村勞動者以“農務者”的法律地位
(一)農務者法律地位的建立是適應農村社會發展的需要
馬克思主義認為:“法的關系正像國家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法律并非一成不變,只不過其改變要適應社會關系的發展變化。勞動關系也并非自古即有,它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興起而產生的,目的在于保護勞資關系中處于弱勢地位的勞動者。我國的產業幫扶事業引領了農村經濟形態、社會形態的變革,農村不再在是工業剪刀差下的財富提供者,農村的經濟發展需要一條與城市不同的道路,并不是要先城市化再發展出與城市經濟發展相同的道路,而是要結合農村特定的時空地理環境和文化習俗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發展道路。扶貧工作的根本不能背離了國家精準扶貧的政策目標,忽視了農業經營的基本規律。脫貧工作的完成則全面促進了這條發展道路的探索,產業幫扶這種內生性發展模式是發展道路的集中表達。以幫扶為抓手的農村經濟發展不同于城市的經濟發展,后者主要是依靠資本在社會主義市場中的運作而生產財富,發展生產力。而前者則是以勞動與生活有機結合為目標,將農村特有的生產要素和時空要素相結合,在勞動中體悟生命的意義并同時獲取財富。現階段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實現有效銜接,就是要修補農村破碎的時空體系,對其賦能,激發出鄉村的活力,讓農民持續性獲得改革紅利,進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農務者法律地位的出現也是隨著社會功能性分化產生的新型經濟形態需要調整而產生的,正所謂“功能分化創建了為解決具體社會問題而出現的社會子系統”。在這一背景下,應賦予農村勞動者以“農務者”這一獨特的法律地位,從而保護農村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這也是人文科學對人類在特定政治經濟組織中的創造活動的理解、尊重、發揚。
(二)農務者法律地位下農務法律關系的規制對象
農務者法律地位的法律意義在于形成以農務法律關系為核心的權利義務體系,從學理上明確農務法律關系的內涵亦可以為相關法律制度的構建奠定基礎。農務法律關系的主體涉及多方,一方為農戶,一方為組織者,另一方為協助者。這三方主體是產業幫扶工作的核心力量,也是農務法律關系所要協調的對象。需要強調的是,雖然脫貧工作已經完成,但后續的扶助工作等仍離不開這三大主體的協調配合。農務法律關系的內容包括多個方面,既包括農戶與組織者的引領關系,也包括農戶與協作者的合作關系,還包括組織者與協作者的監督與激勵關系。現行法律體系的分散化規定不利于三方權利義務的明確,也不利于農村的可持續發展,新型的農務法律關系可以進一步明確三方的權利義務。原則上,農戶與組織者的關系要發揮組織者的溝通聯系功能,防止組織者不當獲利或不尊重農戶意愿的強制攤派。農戶與協助者的關系要在一般經濟行為外加強幫扶內容,并將其法定化。既要體現先富帶后富的幫扶觀念,也要尊重各方意愿,不能把能力培養變相轉變為財產的“轉移支付”。組織者與協作者之間的關系既要體現以幫扶農戶為目標、激發協作者的動力,也要體現監督制約的關系,不能導致政企共謀,造成產業幫扶陷入“成本持續走高,收益持續遞減”的局面。在鄉村振興背景下,農村不再是落后的代名詞,而是在工業文明下保持生命與生活相統一的場域,它依然可以在保持自身特點的前提下分享法治的成果,并為克服人類生活的異化提供實現路徑。
(三)農務者法律地位的制度表達
對于學理上的農務法律關系的制度化,理論上有兩種路徑,一種是制定單行法。其實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有學者提出要建立單行法律法規來調整農村法律關系。對農村勞動關系的調整,單靠勞動法典的總則和分則中的原則性規定還不夠,需要另外制定單行勞動法規或在其他經濟法規里設立調整農村勞動關系的條文來承擔這一任務。另一種是依附于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在其中增設一章專門調整農務法律關系。后者相對簡便,可以以法律修正案的方式提出,但在整部法律體系的融合上可能存在問題,雖同為勞動,但二者畢竟有所不同,長久來看會出現一定的問題,畢竟《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主要是以城市中的勞動形態為規制對象。為了實現鄉村振興,防止制度性返貧現象出現,明確農村勞動者的法律地位至關重要。對此,可以分兩步走,先通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的方式增設專門章節,待時機成熟后再出臺專門單行法律,從而穩妥地構建符合農村勞動實際、符合農村勞動者利益的單獨的法律法規。另外,在相關糾紛處理方面也需要進一步完善制度,可以在法院內部設立專業的涉農審判庭,在必要的農村基層法院可以設立專門的農業法庭,通過專業化審判體系的建設維護農務法律關系的順利運行。
參考文獻:
[1]魏德士.法理學[M].丁曉春,吳越,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33.
[2]史探徑.勞動法和農村勞動關系[J].政治與法律,1984(3):33-36.
[3]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
[4]許漢澤,李小云.精準扶貧背景下農村產業扶貧的實踐困境:對華北李村產業扶貧項目的考察[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17(1):9-16.
[5]尼克拉斯·盧曼.法社會學[M].賓凱,趙春燕,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235.
[6]H.科殷.法哲學[M].林榮遠,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83.
[7]尤琳,魏日盛.“村黨支部+合作社”產業扶貧模式:運行成效、實踐困境與政策建議[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22(1):1-10.
[8]李小藝.產業扶貧中的“行政外包制”及其影響[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19(3):24-32.
[責任編輯:朱松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