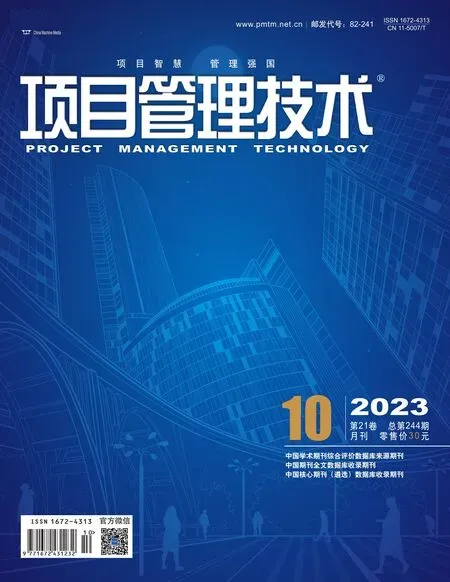系統動力學視域下教學狀態監測項目管理人員能力提升研究*
周益名 宋瑤瑤 李洋
(海軍航空大學教學考評中心,山東 煙臺 264000)
0 引言
《教育部關于普通高等學校本科教學評估工作的意見》(教高〔2011〕9號)提出,高等學校要充分利用信息技術,采集反映教學狀態的基本數據,建立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基本狀態數據庫;高等學校對數據庫數據要及時更新,及時分析本科教學狀況,建立本科教學工作及其質量常態監控機制[1]。由此可見,教學狀態監測活動在教學項目管理中十分重要。
參照《質量管理 項目質量管理指南》(GB/T19016—2021/ISO10006:2017)有關定義可知,教學狀態監測活動是指為實現“教學質量監控和提升”這一目標所開展的獨特過程。每次活動均有起止日期,均受相關資源約束,且隨著項目的進展,數據采集、分析挖掘等活動的目標和范圍會更新,產品或服務特性會逐步確定[2]。教學狀態監測作為一種技術含量高、敏捷性強的項目,對項目管理人員的能力素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項目管理專業人員能力評價要求》(GB/T41831—2022)等指導性規范指出,教學狀態監測項目管理人員能力提升任重而道遠,已成為一項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課題。
從研究現狀上看,雖然直接針對教學狀態監測項目管理人員能力提升的研究匱乏,但近年來針對項目管理能力提升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劉陽等[3]通過開展文獻分析,提出建筑企業組織級項目管理能力提升相關策略;張江等[4]基于CMMI模型,采取與5階段成熟度標準逐項對照的方式,研究提出項目管理能力提升的實現路徑及措施;陳征宇[5]綜合運用成熟度模型成長路徑設定及PDCA管理方法,針對某公司項目管理能力提升提出具體改進舉措;陰超斌[6]基于冰山模型、晉升激勵理論等,從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兩個方面探討了某企業項目現場管理人員職務晉升影響因素。
綜合來看,相關研究仍存在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關注組織有余而聚焦個體不足,對標組織級項目管理相關標準和成熟度模型對整個組織項目管理能力提升的研究較多,但深入細化到項目管理者這一顆粒度并對項目管理人員能力提升而開展的研究較少;二是見“樹木”有余而見“森林”不足,主要對能力提升影響因素進行相對孤立的探討,缺乏對各因素相互關系及作用機理的有機性聯立和全局性審視,基于系統觀的方法論亟待強化;三是靜態分析有余而動態推演不足,在某種程度上局限于當前時間切片,對于能力提升相關因素的發展趨勢和演進變化等研究相對薄弱。針對上述問題,本文運用系統動力學原理和方法,聚焦項目管理人員能力提升,通過識別影響因素、解析作用機理、構建結構化模型、仿真推演相關因素演進過程,以期為提升教學狀態監測項目管理人員能力提供有益參考。
1 系統動力學概述
系統動力學(System Dynamics,SD)是一門將系統科學理論與計算機仿真緊密結合,研究系統反饋結構與行為的科學[7]。系統動力學是研究大型復雜系統的有力工具,亦被稱為“社會實驗室”,主要優勢如下:
(1)引導研究者強化系統思維,看整體而非看局部,深入到系統黑盒內部研機析理,厘清各關鍵要素和變量,把握其相互作用關系。
(2)關注和反映狀態的發展變化特征。當系統結構搭建好后,可以進行時序性仿真分析,幫助研究者更好地分析各變量的發展變化趨勢;在掌握翔實數據的基礎上,可以實現精確的仿真和預測。
(3)通過繪制存量流量圖,使系統結構所蘊含的晦澀方程式“可視化”;通過對存量流量圖開展交互式調整,實現對方程式的調優。
2 系統動力學模型構建
2.1 影響因素分析
基于實踐總結,通過與多名相關領域專家進行深入訪談,系統梳理和識別出教學狀態監測項目管理人員能力提升影響因素(表1),重點圍繞以下4個方面展開:

表1 各影響因素關系一覽表
(1)厘清“因果”。本研究以項目管理人員能力為研究對象,以人員能力提升為研究目的,因此,將教學狀態監測項目質量視為最終結果。在關注人員能力提升直接影響因素的同時,重點關注教學狀態監測管理人員能力這一因素及其影響因素,將二者緊密聯系進行分析。經梳理和辨識可知,F0被F1、F2兩個因素直接影響,F4被F0、F8、F9三個因素直接影響,而F0與F4兩個子系統之間呈現相輔相成的關系。因此,在整個系統中,可用F0和F4表征系統發展運行的結果,重在觀察結果變化;其他因素可視為上述結果產生的原因,重點進行溯因分析。
(2)厘清“遠近”。研究對象F0受F1、F2直接影響,因此,F1、F2可視為“近距”影響因素;由于F7、F10、F12、F14等因素對F0產生的影響是通過多種因素多級傳遞而成的,可視為“遠距”影響因素;其余因素可視為“中距”影響因素。
(3)厘清“內外”。基于教學狀態監測項目管理人員視角分析可知,F1、F2、F3、F5、F6、F7、F8是人員自身因素,可視為內部因素;其他因素屬于外部環境條件,可視為外部因素。
(4)厘清“正反”。F3、F5、F7、F11、F13對研究對象F0具有較為明顯的正向促進作用;F6、F9、F16對F0具有較為明顯的反向削弱作用。同時,與相關因素緊密聯系的還有F17、F18等約束性因素。
綜上所述,分析得到各影響因素關系一覽表(表1)。由表1可知,各因素之間存在復雜的作用關系,整體呈現出復雜的系統結構。
2.2 系統動力學SD模型構建
基于以上影響因素分析,運用Vensim軟件繪制影響因素存量-流量圖,如圖1所示。將F0與F4作為存量,將“教學狀態監測能力增長率”和“教學狀態監測工作質量增長率”作為流量,設為F01、F41,將其余變量作為輔助變量和常量。

圖1 影響因素存量-流量圖
通過與專家討論并進行多輪調優,確立各變量方程式及系數,見表2。時間跨度設為0~50周,迭代步長設為1周。

表2 各變量方程式及系數
2.3 仿真分析
通過SD模型得到各因素變量圖像,選擇重要影響因素的趨勢變化情況進行分析。F0及其直接影響因素趨勢變化如圖2所示。其中,F0在仿真的50周內一直保持增長(圖2a),這是由于其流量F01及F01的直接影響因素F1、F2是健康發展的,如圖2b、圖2c、圖2d所示。

圖2 F0及其相關因素變化趨勢
F4及其相關因素變化趨勢如圖3所示。F4持續增長(圖3a),其流量F40總體上也是持續增長的,并且發生兩次轉折變化,如圖3b所示。追蹤兩次轉折變化的根源,第一次是由于F10經過約20周的延遲而顯現出數據治理成效,如圖3c所示,逐級傳導到F41,最終令F41在20周附近產生一個階躍提升;第二次是由于F8在43周左右達到約束上限,如圖3d所示,逐級傳導到F41,最終令F41

圖3 F4及其相關因素變化趨勢
在43周左右使增速向下偏折,而系統內各因素已形成良性循環,因此,F41、F4在趨勢上仍保持提升,這也揭示了質量提升永無止境之義。
經系統調控改善后的F0變化趨勢如圖4所示。若強化主觀能動因素F13(可通過將其對F4的傳導倍率由0.9調增為1.35表征),調整后的F0變化趨勢如圖4a所示,可見相比調節前(圖2a),F0由低于600變為超過700。若克服消極因素F6(可通過將其對F7的傳導倍率由0.3削弱至0.1表征),則調整后的F0圖像如圖4b所示。若將約束性條件F18由0.35放寬至0.1,則調整后的F0圖像如圖4c所示,可見相比調節前圖像(圖2a),F0由低于600變為超過600。若F19的初始水平能夠由10 000調整為7000,調整后的F0圖像如圖4d所示,可見相比調節前圖像(圖2a),F0可由低于600上升為800左右。

圖4 經系統調控改善后的F0變化趨勢
綜上所述,該模型通過因素識別、關系確立、系數調優,建立了一個穩健的系統結構,不僅有助于深化對教學狀態監測項目管理人員能力提升機理的認知,而且明確了實際工作中機制建設目標。相關系數表征關系可為優化相關資源配置提供有益啟示。同時,調控仿真結果顯示,該模型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和合理性。
3 策略與建議
教學狀態監測項目管理人員能力提升受多重因素交疊影響,且各因素關系復雜,因此,必須將細致入微的機理分析與抓主要矛盾的宏觀把控有機結合起來,科學統籌、綜合施策。
(1)提升主觀能動性。人是項目管理中的關鍵變量,且具有較強的可塑性。可以通過匯報溝通,獲得上級領導的支持,使項目推動更加順暢;可以通過提升自身主觀能動性,弱化消極情感帶來的不利影響。
(2)創設有利條件。對于教學狀態監測項目而言,信息化、數字化建設水平及干擾本職工作的其他事務性工作等都是影響能力提升的不利條件,因此,需要提升數字化建設水平,為項目質量持續提升創造前提條件。
(3)健全管理機制。構建一個穩健的系統結構,使相關要素穩健發展,是系統動力學的本義。對于教學狀態監測項目而言,應在深刻理解能力提升機理的基礎上,建立科學合理的信息傳遞機制,完善相關激勵政策,以能力提升、質量提升、經驗提升、內驅力提升為目標,從根本上推動管理人員能力穩步提升、項目質量持續向好。
4 結語
當前,推動教學狀態監測項目管理人員能力提升需求迫切、任務艱巨。面對影響因素眾多、影響關系復雜的現實情況,系統動力學提供了一種既能引導相關研究由表及里,又能直觀表達研究結果的工具方法,可以借助其構建教學狀態監測項目管理能力提升系統模型,將各因素納入良性循環,實現人員能力和項目質量互促相長。
在后續研究中,可以圍繞教學狀態監測項目管理人員能力提升相關影響因素的量化表征和觀測計量開展深入研究,采集和積累更加精確、翔實的指標數據,提升模型仿真精準度,以更好地提升教學狀態監測項目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