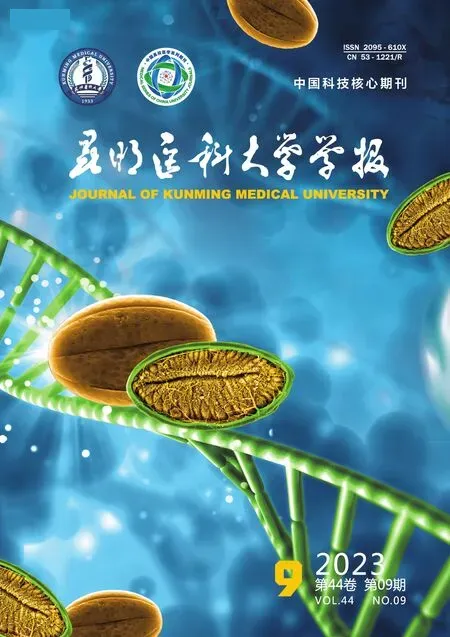數字化技術對上頜唇向低位尖牙矯治的干預
季娟娟 ,劉亞麗 ,周 治 ,許艷華 ,朱亞玲 ,王 睿
(1)云南大學附屬醫院口腔醫學中心口腔正畸科,云南 昆明 650021;2)昆明醫科大學附屬口腔醫院口腔正畸科,云南 昆明 650011)
在牙列擁擠的人類學調查中,中國人和日本人嚴重擁擠患病率較高[1]。牙列擁擠易發生在前牙區[2],且隨年齡增加,擁擠加劇[3-4]。上頜唇向低位尖牙在前牙擁擠病例中高發,這與牙弓長度、寬度發育不足密切相關[5-6]。Akram[7]在上頜唇向低位尖牙的CBCT 研究中發現,上頜唇向低位尖牙因不能行使正常咬合功能,牙根較短,骨體積、頰側骨密度比正常尖牙組減少。這不僅影響患者美觀,也造成牙周組織的損傷,需進行正畸治療。但唇向低位尖牙因其牙周退行性變,正畸治療過程中受力更易發生牙齦退縮、牙槽骨吸收[8-9]。
牙齒受到各種內在、外在、動態、靜態的機械力,這些力共同驅動和維持生理性牙槽骨生長發育和平衡。有動物研究表明,恢復咬合功能低下牙的咬合刺激可誘導骨附著、增加牙槽骨表面骨量。課題組提出設想在正畸之前給予患者力學干預,恢復其牙周組織活性再對其進行矯治,以減少牙槽骨喪失風險。如何給予適當的力干預?傳統固定矯治技術中,弓絲形狀、力學行為、牙齒運動情況間的關系并不十分明確。臨床醫師無法準確預測應施加矯治力值的大小。近年來,無托槽壓膜式矯治器以其可精準施力,精確設計的優點,越來越被醫生和患者接納。為解決這一難題,課題組使用數字化技術設計矯治器施力干預上頜唇向低位尖牙后再行常規矯治,探索此干預措施能否降低牙槽骨吸收量,提高正畸安全性。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及分組
1.1.1 研究對象 篩選自2021 年10 月至2023年8 月到云南大學附屬醫院口腔正畸科就診有上頜唇向低位尖牙的成年患者,且均在云南大學附屬醫院口腔臨床中心拍攝CBCT,所有患者簽署知情同意書,該研究通過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查(批準號:2021063)。納入標準:(1)年齡≥18 歲,恒牙列,牙根發育完成,根尖無暗影,牙冠形態完整規則;(2)牙周健康或牙周病控制良好;(3)上頜尖牙唇向低位(距離咬合平面2 mm 以上)患者。排除標準:(1)無正畸、正頜治療史、前牙牙體或修復治療史;(2)無唇腭裂或全身系統性、懷孕、遺傳性疾病史;(3)上頜尖牙無明顯扭轉,無外傷、囊腫或手術史。
1.1.2 研究對象分組 課題組選擇用數字化設計干預矯治器,給予無咬合力接觸的尖牙沿長軸方向壓低0.1 mm,每日佩戴4 h,連續佩戴3 個月后開始常規的固定或隱形矯治。與患者溝通交流,將愿意進行干預的患者納入干預組,否則進入對照組。
1.2 研究方法
1.2.1 釉牙骨質界到牙槽嵴頂的距離(CEJ-AC) 納入的患者,在治療前及低位尖牙納入牙弓后均進行CBCT 檢測(NNTviewer,New Tom,Italy),掃描視野15 cm×15 cm,電壓110 KVp,電流3.83 Ma,曝光時間3.6 s,掃描層厚0.3 mm。
選取尖牙最大矢狀截面為牙槽嵴頂與CEJ 距離的測量平面(圖1)。步驟如下:如圖A 在軸面上,使橫軸與豎軸垂直且交點位于牙體中心;在B、C 調節冠狀面、矢狀面上牙體長軸與豎軸的重疊,此時為牙根橫截面積最大面,以矢狀面 C 為測量界面。

圖1 確定上頜尖牙牙體長軸Fig.1 Confirmation of long axis of upper cannine
測量并記錄納入病例治療前后唇向低位尖牙唇側牙槽嵴頂與釉牙骨質界距離h1(圖2)。同一測量者在1 個月后重復測量,取2 次測量結果的平均值。

圖2 確定釉牙骨質界到牙槽嵴頂(CEJ-AC)的距離h1Fig.2 Confirmation of the distance of cemento-enamel bone junction(CEJ)-alveolar bone crest(AC)h1
1.2.2 牙齦生物型的臨床檢測 采用Kan[10]提出的牙周探針檢測牙齦生物型的方法,即將William 牙周探針插入齦溝內,觀察牙周探針若能透過牙齦被看到則為薄齦型,否則為厚齦型。
1.3 統計學處理
對納入的患者進行治療前后CBCT 測量,并對臨床檢測指標進行統計分析。采用 SPSS22.0 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前后差異比較采用配對t檢驗,兩組差異比較采用成組t檢驗;計數資料用n(%)表示。以P< 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情況
收集病例43 例(牙數54 顆),其中男性15 例(牙數21 顆),女性28 例(牙數33 顆),患者年齡18~40 歲。分為常規矯治組和干預矯治組,常規矯治組26 例(牙數32 顆),其中男性8 例(牙數11 顆),女性18 例(牙數21 顆),患者年齡18~33 歲;干預矯治組17 例(牙數22 顆),其中男性7 例(牙數10 顆),女性10 例(牙數12 顆),患者年齡18~40 歲。
2.2 干預措施對釉牙骨質界到牙槽嵴頂的距離(CEJ-AC)的影響
矯治前2 組無統計學差異,矯治后干預組CEJ-AC 降低(P< 0.05),常規矯治組CEJ-AC 不變,且干預矯治組干預前后CEJ-AC 差值大于常規矯治組(P< 0.01),提示干預措施有效,見表1。
表1 常規矯治矯治組和干預矯治組矯治前后CEJ-AC 情況[(),mm]Tab.1 CEJ-AC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the non-intervention group and the intervention group[(),mm]

表1 常規矯治矯治組和干預矯治組矯治前后CEJ-AC 情況[(),mm]Tab.1 CEJ-AC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the non-intervention group and the intervention group[(),mm]
*P < 0.05。
2.3 牙齦生物型對CEJ-AC 的影響
矯治前后,薄齦型低位尖牙患者的CEJ-AC變化,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干預組厚齦型低位尖牙患者的CEJ-AC 降低(P< 0.05),且變化值同常規矯治組相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干預措施對不同牙齦型矯治前后CEJ-AC 的影響[(),mm]Tab.2 Effect of interventions on CEJ-AC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ith different gingival type [(),mm]

表2 干預措施對不同牙齦型矯治前后CEJ-AC 的影響[(),mm]Tab.2 Effect of interventions on CEJ-AC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ith different gingival type [(),mm]
*P < 0.05。
2.4 矯治方式對CEJ-AC 的影響
固定矯治的低位尖牙患者,干預組矯治后CEJ-AC 值降低(P< 0.05),常規矯治組的CEJAC 值變化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干預組治療前后的CEJ-AC 差值大于常規矯治組(P<0.05);隱形矯治的低位尖牙患者,干預組矯治后的CEJ-AC 降低值大于常規矯治組(P< 0.05),見表3。
表3 干預措施對不同矯治方式矯治前后CEJ-AC 的影響[(),mm]Tab.3 Effect of interventions on CEJ-AC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ith different treatment methods [(),mm]

表3 干預措施對不同矯治方式矯治前后CEJ-AC 的影響[(),mm]Tab.3 Effect of interventions on CEJ-AC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ith different treatment methods [(),mm]
*P < 0.05。
3 討論
牙列擁擠病例中非常常見的唇向低位尖牙屬于咬合功能低下牙,失去正常咬合力的維持,其牙體牙周會出現如牙周膜和牙槽骨的退行性改變[11]。牙槽嵴頂的位置,即釉牙骨質界到牙槽嵴頂的距離(CEJ-AC)是正畸、正頜醫師為規避牙周風險如牙齦退縮、牙槽骨吸收等十分關注的解剖因素[12]。研究認為CEJ-AC 距離為2 mm 以內[13]。有許多研究表明CBCT 可準確提供牙周缺損的三維形態,優于傳統的口腔X 線片[14]。課題組選取的患者年齡在18~40 歲,治療前牙周情況均符合矯治標準,采用CBCT 測量CEJ-AC,43 例患者治療前CEJ-AC 的平均值為3.44 mm(95%CI:2.95~3.92),提示唇向低位尖牙牙槽嵴頂位置偏低,具有牙槽骨量不足的缺陷,在正畸過程中易出現牙槽骨吸收。這與課題組在前期的研究中發現,低位尖牙的患者正畸治療后更容易出現牙齦退縮[9]結果相一致。
動物實驗報道,咬合功能低下牙齒移動過程中PDL 和血管細胞發生凋亡[15],牙周組織易發生退行性變。基礎研究發現通過恢復咬合功能干預,牙周膜結構、松質骨和皮質骨骨密度有所恢復[8],還能通過增加 IGF-1 和其受體誘導牙周膜細胞增殖[16]。數字化設計無托槽隱形矯治器有可精確施力的特點,課題組對上頜低位尖牙設計了干預措施:給予所選牙沿長軸方向壓低0.1 mm 的移動量的力,每日佩戴4 h,即給予牙齒間斷力,連續佩戴3 個月后開始常規矯治。這樣牙周膜受輕力刺激,但基本不產生牙齒的移動。對照組則直接進行常規矯治。本研究選取上頜唇向低位尖牙進行研究,結果顯示:干預措施組與常規矯治組治療前CEJ-AC 無組間差異;但矯治后,干預組CEJ-AC 降低(P< 0.05),而常規矯治組CEJAC 與矯治前無差別,提示干預措施有效,干預措施減少了上頜唇向低位牙矯治造成的牙槽骨量的喪失。
牙齦厚度是牙齦退縮發生的相關因素。Marziyeh 等[17]評估出牙齦生物型與牙槽骨厚度成正相關,牙齦越薄牙槽骨也越薄。而薄齦型患者正畸后牙齦退縮發生率更高[9,18]。課題組也探索了干預措施與牙齦生物型對治療后牙槽骨喪失的作用,提示:干預措施對上頜厚牙齦型唇向低位牙牙槽骨吸收干預有效,對薄齦型未見明顯效果。上頜薄齦型唇向低位尖牙患者對應更少的牙槽骨和牙齦量,在正畸力作用后,更容易發生缺失,尚需尋求其他干預措施提高正畸治療的安全性。
固定矯治使用的托槽和弓絲等影響口腔清潔,引起菌斑積聚,易形成牙周組織炎癥[19]。隱形矯治因其刷牙和進食可摘戴,對口腔清潔影響小,但其包裹性強,摘戴時產生力量大,對牙周的影響有爭議[20]。在本研究中,干預措施運用于兩種不同矯治方式的治療中,發現固定矯治上頜低位尖牙患者,干預措施矯治后CEJ-AC 值降低(P<0.05),治療前后的CEJ-AC 差值大于常規矯治組(P< 0.05),提示干預措施有效;隱形矯治的低位尖牙患者,干預組矯治前后的CEJ-AC 降低值大于常規矯治組(P< 0.05),也提示干預措施有效。
課題組通過對上頜唇向低位尖牙進行數字化設計無托槽矯治器進行治療前干預,發現干預措施對厚齦型患者矯治后的CEJ-AC 有改善作用,但對薄齦型無明顯作用;在固定矯治或隱形矯治前進行干預,均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