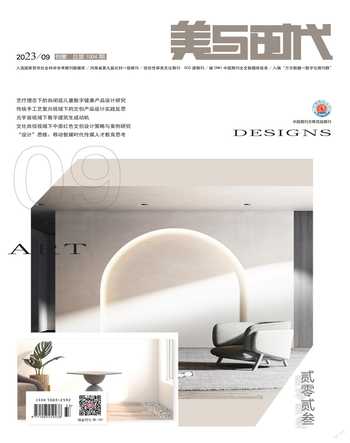從建筑紋樣意蘊角度談同里古鎮崇本堂的場所精神

摘? 要:本文主要從雕刻手法和文化內涵方面對江南典型民居崇本堂的磚雕門樓、庭院布局和建筑構件的紋樣進行研究,特別對三個院落的場所精神從始建者顧氏的初衷設計意愿和錢氏重新構建之間的呼應關系進行了對比分析。研究的過程不僅僅局限于同里古鎮,還將建筑紋樣和蘇州地區的園林和其他民居進行了時代對照,糾正了某些謬誤。
關鍵詞:建筑紋樣;詩書傳家;崇德思本;場所精神
基金項目:蘇州市2019年姑蘇教育人才資助“蘇州古典園林3D復原暨江南木雕技藝傳承研究”(RCZZ201931)。
李漁在《閑情偶寄·居室部》中談到:“吾愿顯者之居,勿太高廣。夫房舍與人,欲其相稱。”其強調了人與居住場所的相稱關系。著名建筑理論家諾伯格·舒爾茨所強調的“客觀物理環境與人的主觀意識系統相互交流而產生的一種情感體驗過程”也恰好體現了李漁表達的思想。蘇州園林雖經歷代興廢,經過無數研究專家和香山匠人的精心修復基本能夠還原舊貌,但是由于無歷史實物印證和資料的缺失,在復原的過程中很多建筑庭院空間的場所精神已經消失,成為憾事。正如陳從周先生所說“設若名園,必細征文獻圖集,使之復原,否則以己意為之,等于改園。”筆者在蘇州的周莊、甪直、東西山、同里等古村落進行建筑考察過程中,欣喜地看到了很多古宅院和園林陸續復原,由于修復的規劃設計師和匠人文化層次、地域底蘊和專業能力以及資金投入的差別,修復的水平也是千差萬別。20世紀90年代初太湖風景區建設辦公室出資購買的同里崇本堂五進并進行修復建筑所保留的歷史氣息和場所精神值得研究。
一、西宅別業堂前客 錢氏重構翻建新
古宅位于富觀街長慶橋北邊,面水而筑,舊時水陸兩路出現便捷,整體建筑符合計成所說“園基不拘方向,地勢自有高低;涉門成趣,得景隨形,或傍山林,欲通河沼”之意。
(一)歷史發展脈絡
西宅別業為明代萬歷年間江西兵備道顧自植的宅院,根據第四進門樓“棣萼聯芳”是康熙年間吳江人錢襄所書推測該宅院在康熙年間重新進行了修建,據史料記載有7進99間。而其側院就是現在的崇本堂在顧氏家道衰落后由同里富商錢幼琴在民國元年購得,除了保留第三進道光年間的建筑外,其余根據個人喜好和地形進行了規劃和布局,形成了目前的格局。根據倪浩文發表于蘇州日報2021年7月的《同里西宅別業顧宅》一文的實地考察,錢氏宅院應該一共是六進而不是目前官方界定的五進。第六進的門樓如果和前五進的三座門樓縱向貫通分析來看,四座門樓的文字所表達的內涵應該是與顧氏緊密相關,錢氏購買建筑之后,保留了門樓的整體讓我們可以還原顧氏修建四座門樓的真實意圖。
(二)崇本堂的建筑格局
整個建筑群體自民國至今100年來沒有經過大的改變,使我們能夠通過對建筑整體的布局分析感受清末民初蘇州民居建筑的設計理念。現為檢票處的應該是當年轎廳,出門幾步就可以乘舟前行,河道兩岸綠樹成蔭儼然是三進宅院二樓觀景所在,其借景手法運用巧妙,近可見嘉蔭堂和三橋,遠可眺同里湖。考慮崇本堂主要以居住為前提,最大化地解決實用功能布局問題,前后分別是門廳(轎廳)、正廳、前樓、后樓及下房等向縱深發展,均面闊三間,第三進、四進為兩層構架的走馬樓形成四方天井,由于古時都以木結構為主,考慮火災之類的安全隱患,建筑與東西他戶住宅都以高低錯落的封火墻分隔,整幢宅第東側有80cm左右的備弄貫穿南北五進,布局緊湊而精致其整體格局與蘇州市區的潘家舊宅(蘇州狀元博物館)、蘇州藝圃的住宅部分都有相似之處。門廳(轎廳)、正廳、前樓的地基和整體高度也是逐層提升,按照傳統的寓意為“連升三級”,如果從商業的角度也可以理解成“步步高升和節節高”之財富積累之意。
二、一進廳堂相趣映? ?場所精神妙古今
崇本堂是西宅別業的一部分,顧家一門文人輩出,詩書傳家是安身立命之本。其門樓和建筑的部分形制還具有明末清初時精巧簡雅的文人遺風,而留存的四座精美磚雕門樓《崇德思本》(乾隆年間)、《敬候遺范》《啇賢遺澤》《玉篇遺澤》(光緒年間)是按照歷史的順序得以留存,也說明錢幼琴深諳傳統文化保留了門樓和匾額,巧妙地和改建的建筑內部紋樣主題相呼應。
(一)一進門樓與正廳之院落的門樓紋樣寓意分析
轎廳到正廳之間的門樓硬山紋頭桁間栱磚細掛落荷花柱,磚雕斗三升置于定盤枋上,字碑、下枋額一塊玉雕刻精美紋樣。
1.崇德思本蘊深意。門樓磚額為“崇德思本”四個字,“崇德”語出《荀子·不茍》“君子崇人之德”。“思本”應語出唐代魏徵《諫太宗十思疏》:“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四個字的涵義代表了古人求學做人的道理,做人要學習君子的崇高美德,學習就要打好扎實的基礎才能在今后追求功名取得一番成就。
2.文人逸趣應主題。門樓兩邊的磚雕東面肚兜深浮雕雕刻松樹、山石和一老人與孩童振臂高呼的場景,左為疑為林和靖文人逸事之“西山放鶴”;西面肚兜深浮雕雕刻一船、柳樹、老人席地而坐而童子執扇煮茶之場景,左為疑為“陸羽煮茶”之典故。
3.精構細思寓吉祥。其下坊中間由三塊青磚拼貼“包袱錦”雕刻有深淺浮雕組合的寶相花、菊花、荷花等40多種寓意吉祥的花卉紋樣,兩邊對應了香草紋樣,中心深浮雕刻有“鯉魚跳龍門”的圓形開光畫面,與“崇德思本”相呼應,這樣的包袱錦在蘇州市區的眾多園林雕刻中屬于少見,只有在拙政園李廳第二進康熙隆年間門樓和西山仁本堂乾隆年間的磚雕門樓有相似的布局,而仿磚仿木結構的三升拱間隔處鏤空刻有五個夔龍文字變形紋樣,分別代表了福祿壽喜財的美好寓意,整座門樓造型簡潔、雕刻精美、寓意豐富,體現了乾隆年間建園主人的精神訴求表達。
(二)正廳木雕紋樣寓意分析
主廳面闊9.9m,進深8.5m為五架梁三開間扁作船棚軒正貼式樣,是錢氏議事和會客的重要場所,該廳的大梁、山界梁、軒梁、抱梁云、山霧云等處皆有精美的雕刻。
1.清白求財有祥瑞。中間前步柱與后步柱之間的大梁中心深挖雕刻有對稱的兩組包袱錦山水鞍馬人物紋樣,人物處理特別是柴王爺有前顧后盼的兩個形象。四個人物分別指代了東路財神比干,南路財神柴榮,西路武財神關公,北路財神趙公明,寓意“日進斗金、滿載而歸、一路發財”。梁下方左右兩邊分別雕刻了蔓帶如意、蔓帶筆和銀錠的紋樣,合稱為“萬代必定如意”之內涵。與錢文琴為經商之人的職業和祈求經營順風順水的心態相對應。而兩邊的山界梁、軒梁雕刻有纏枝牡丹,蜂頭四面圓雕的是纏枝荷花、山霧云和抱梁云鏤空雕刻有鶴鳴九皋紋樣,寓意是富貴、清白、祥瑞,都與經商的理念一致。
2.閑情雅致有梨園。六扇長窗、八扇半窗上夾堂板為十二時花卉紋樣、窗芯為十字川如意紋樣,中夾堂板雕刻有精美的鶯鶯辯琴、長亭送別、游殿驚艷等14幅西廂記故事,雕刻的手法、人物的造型和場景處理與蘇州拙政園后移建的秫香館的16扇長窗夾堂板(程宗駿先生的考證來自康熙間蘇州木瀆的遂初園)西廂記人物故事雕刻手法一致,不注重面部的精雕細刻,重意不重形為吳門畫派的特征之一。因此這有可能是錢氏在翻建之時保留了原來的長窗雕刻紋樣,與門樓落成時間也有了相近的對照關系。蘇州地區昆曲深受達官顯貴和文人雅士的歡迎,西廂記的戲曲故事更是在清末盛行,遙想百年之前崇本堂正廳錢氏大宴賓客之余聽歌、舞、引、白的梨園昆曲與夾堂板紋樣呼應,達到了虛實相生之意。
3.儒商兼具顯品行。六扇長窗的裙板雕刻是正廳最為精彩之處,分別以博古架花卉清供的紋樣構圖出現,從左向右分別雕刻有一盆盛開的蓮花、花幾古藤公案上的壽石、筆筒中的靈芝、毛筆等眾多紋樣的“和合如意”,代表夏;花瓶中插有折枝梅花、太湖石、香爐中如意云紋的“五福平安”,代表冬;聚寶盆、竹石、刻有福壽的花瓶和茶壺以及書卷紋樣的“福壽財旺”,代表財;蓮花坐紋樣收腰的葫蘆插有折枝牡丹、如意、水仙花等紋樣的“富貴神仙”,代表壽;水仙盛開、湖石、靈芝等紋樣組成的“群仙賀壽”,代表春;瓶中盛開菊花、湖石海棠、佛手等紋樣的“福壽滿堂”,寓意秋。六個裙板運用古代文人善用的花卉紋樣和代表福祿壽喜的紋樣表達了春夏秋冬、福壽財旺的美好愿望。
4.場所精神妙古今。舊宅的門樓字牌紋樣和廳堂、湖石植物的呼應更多地體現了詩書傳家、達則出仕之意;錢氏具有亦儒亦商的文化氣質,對前院進行了巧妙的構思,形成了以“財”為中心的場所精神。以從商的角度來看,“崇德思本”則是強調商人做生意要注重見利思義的優良商德、誠實守信的行商之本;紅楓、無花果、南天竺、書帶草等組成了春夏秋冬的四季植物與長窗的裙板紋樣進行了呼應;庭院備弄的山墻上兩個正方形亞式萬字漏窗的插腳分表堆塑有暗八仙紋樣以及正廳的梁架、長窗等處無不體現出了“出入平安、四季輪回、生財有道”的經商核心思想。
三、二進家風內涵深 十六長窗福祿意
第二座門樓在正廳墻面北,為三飛磚墻門,為硬山哺雞脊桁間定盤枋磚細荷花掛落式樣,在雕刻和構思上比第一座門樓簡潔。其門樓字牌、紋樣表達的內涵為顧家家風家訓的延續,也與后來居住者的重新定位相吻合。
(一)顧氏遺范聚門樓
門樓的上枋雕刻有五個穿梭于祥云的五只蝙蝠。從傳統文化角度來看,設計構思來源于《尚書·洪范》:“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它包含了顧氏家族對于德行、家庭、功名利祿的要求。從經商和民俗的角度來看,蝙蝠在上枋表示天降洪福、五福臨門和福祿壽喜財的美好愿望。字牌以回字紋走邊書寫“敬侯遺范”四個字,可能由于歷史變遷上款和下款已經遺失,其本意是指顧氏子孫要繼承明初灌園翁顧敬的文學才能和知書達禮、報效國家的處事原則,寒窗苦讀,博取功名。目前流傳的附會到漢代公主外嫁故事,強調女子安守本分,進行相夫教子之類的傳統規矩,這個無論是與門樓還是場所精神之間沒有聯系,應該為謬傳。東西肚兜的深浮雕人物故事,仔細研究分辨之后,左邊雕刻是官員手捧爵,道童雙手高舉花瓶,其中插有三戟,花鳥雕刻有喜鵲登梅;右邊雕刻師官員手捧官帽,道童手持如意,花鳥雕刻有雄鷹松樹,兩個肚兜對應還雕刻了2只左顧右盼的鹿的形象,整體的寓意應該是“加官晉爵、福祿如意、平升三級”,中心詞為“祿”,與字牌“敬候遺范”的寓意起到了呼應關系。下枋為對稱菊花纏枝紋樣,根部堆成雕刻成為如意造型,下枋正中心雕刻上下圓壽紋樣,整個門樓的三個部分構成了福祿壽主題。
(二)十六長窗意福祿
前樓十六扇長窗的中夾堂板和裙板雕刻紋樣豐富、造型精美,技法與前后廳堂雕刻迥異。窗芯都是十字如意壽紋,最東面四扇長窗裙板分別深浮雕有雙鹿、雙馬、雙猴、松鼠葡萄紋樣,與海上畫派的馬貽畫寶的風格相似,中夾堂板分別雕刻有茂叔賞蓮、漁樵耕的故事情節,其中茂叔賞蓮的雕刻手法與蘇州獅子林的指柏軒碧紗櫥夾堂板的風格相近,中間六扇長窗裙板雕刻有鳳凰牡丹、松鶴延年、梅花鸚鵡、錦雞繡球、鴛鴦荷花、桃花春燕等構思巧妙的花鳥圖案,西面四幅裙板也是雕刻的果熟來禽的花鳥圖案。而12扇中夾堂板雕刻有紅樓夢金陵十二釵人物故事,典型的人物造型和器物在其他民居和蘇州園林中未曾見到,遺憾的是其雕刻水平和技法不如東面四扇窗戶的水平。它包含了古人漁樵耕讀時出仕入世、榮華富貴、家庭和睦等美好寓意,而且都是以成雙成對的飛禽走獸出現,整個門樓和前樓紋樣圍繞了“福祿”寓意的場所精神。
四、啇賢遺澤奮讀書? 滿堂雕花技藝湛
第三座門樓在庭院第三進前為三飛磚墻門,為硬山哺雞脊桁間定盤枋磚細式樣,較前兩個門樓更為簡潔,門樓的雕刻技巧簡潔明了,其門樓的字牌和上下枋紋樣呼應主題較為明顯。
(一)啇賢遺澤奮讀書
門樓字牌雕刻有“啇賢遺澤”四字,很多書籍和導游都以為啇是商的錯字,其實啇古意是樹根之意思。綜合起來是姑蘇顧家歷史上是名門望族,有一代文學大家顧野王、文學大家顧敬、西宅別業第一任主人含素公顧自植、亭林先生顧炎武等祖輩先賢為顧氏的文脈相傳、家族興旺奠定了扎實的根基,比第二座門樓“敬侯遺范”更加強調希望子孫追根溯源,博采眾長,兩邊的肚兜深浮雕刻有喜鵲、梅花、鵪鶉、麥穗的形象,代表了喜鵲登梅和安居樂業的寓意。上枋有形態各異的立鶴、行鶴、飛鶴、翔鶴等形象。鶴在傳統文化中代表了長壽、吉利、祥瑞、高潔、爵祿之意,祥云瑞鶴也是明代一品官員的補子紋樣。上枋雕刻有纏枝牡丹,根部變形為如意紋樣,中心為柿蒂紋。柿樹根深蒂固,中國建筑裝飾和陶器、青銅鏡上多有類似紋飾,寓意堅實牢固。在這也代表希望家族興旺之意,與“啇”字相呼應。整座門樓紋樣的分析可以看出寓意“祿”,設計的初衷是希望家族興旺、子孫能夠得到祖上的承蔭庇護,取得一番成就光宗耀祖,從錢氏保留完整門樓的商人角度也可以解讀為后代只有誠信經商才是產業發揚的根本。
(二)滿堂雕花寓意深
后樓的可謂無處不雕花,雕刻的水平和圖案紋樣的設計在整個建筑中是精華所在,可惜在特殊歷史時期,內部正堂人物幾乎都被鏟除,花卉紋樣得以幸存,這一點與西山仁本堂和眾多古鎮保留的古建筑的遭遇類似。六扇長窗的裙板采取的深浮雕和陰陽雕相結合的方式進行,是我目前見到的蘇州園林民居之中木雕手法最高的可以與忠王府的人物木雕相媲美,應該就是文獻所說“第三進保留了道光年間建筑……”。中廳長窗的裙板分別雕刻了古供瓶插折枝菊花和張果老法器漁鼓、壽字古瓶牡丹花和曹國舅的云板、八卦器型的古供瓶一束荷花與何仙姑荷花法器、仿尊蓮花倒坐古供瓶山茶花與藍采和花籃、雙魚古供瓶芍藥花與鐵拐李葫蘆拐杖法器、寶相花古供瓶插枝桂花與漢鐘離的寶扇相組合的暗八仙與花卉組合的紋樣,包含了文人的清供、百姓的祈福和四季平安的美好寓意。中堂四幅隔扇的裙板雕刻有福祿壽喜的紋樣,東西兩側五架梁的八扇長窗正反兩面夾堂板和裙板都進行了雕刻。其中東面中夾堂板雕刻了淺浮雕八仙的人物紋樣,破損嚴重但是依稀可辨,裙板為花卉紋樣,西面夾堂板雕刻了漁樵耕讀、琴棋書畫的人物組合紋樣,裙板為花卉紋樣。整個樓廳無論是長窗、欄桿、結子還是騎馬樓的各處都進行了精心設計與雕刻,累計雕刻紋樣有一百多處,雖然目前已經開辟為陳列館,但是從門樓到廳堂的雕刻紋樣反映的主題表達涵義能夠感覺到當年在這一方天地宅院主人希望子孫能夠讀書立志、博取功名和祈福平安的“福祿”寓意場所精神。
崇本堂的場所精神得以延續也有賴于錢文琴亦儒亦商的文人情結,雖然和顧氏最初的寓意已有所區別但還是能夠人和物、環境進行精心交流。除了目前分析的門樓、木雕紋樣以外,其門樓、正廳、前樓屋頂正脊都雕刻有童子抱鯉、魚躍龍門的堆塑,寓意子孫繁盛、魚躍龍門、金玉滿堂的美好祈愿。由于各方面原因不開放的五進、六進所形成的場所氣息也應該與前三個門樓所表達的思想主題相近,通過第六進光緒年間范宗麟題寫的“玉篇遺澤”四個字門樓可以看出顧氏從明代建立西宅別業到光緒年間都是以先祖黃門侍郎兼太學博士顧野王為傲,只是家道中落,子孫無力保存而易主成為憾事。通過對同里古鎮崇本堂的建筑紋樣與場所之間關系的考證和論述,傳統建筑場所構建的表現手法和審美實用功能值得我們從事建筑和室內設計者去好好研究,能夠汲取精華將民族傳統文化元素運用到現代設計中去實現傳承與創新。
參考文獻:
[1]祝紀楠. 營造法原[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12.
[2]彭一剛.中國古典園林分析[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86.
[3]陳從周.說園[M].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17.
作者簡介:陳鑫,蘇州城市學院設計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