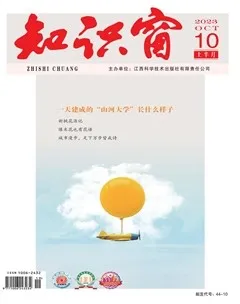光照臨川之筆
陳志宏

臨川給我的最初印象是一座橋。
小時候,父親騎自行車載著我上文昌橋,對我說:“這是文章(在撫州方言里,‘昌與‘章屬同音字)橋,多走幾遍,你長大后,就會寫文章了。”
走過文昌橋,我和父親就進了城。
抵達文昌橋之前,我和父親要先走羅家渡橋,再過楊泗橋和孝橋,至于星羅棋布的獨木橋、石板橋更是數不勝數。難怪湯顯祖會這樣描繪他的家鄉:“遠色入江湖,煙波古臨川。”
文昌橋橫跨撫河之上,橋西是寂靜的鄉野,橋東一派繁華,一座橋聯通城鄉。
到了城里,我像進了學堂一樣,眼要專注看,耳得用心聽,經耳過目,一一化作美好回憶,待回到城外十公里的小村,像牛反芻一樣,細細咀嚼,慢慢回味,又像雄雞司晨,給從未進過城的玩伴普及城市的不同之處。
堂姐家住文昌橋頭,那時還是低矮的棚戶區,水泥路面,锃亮的青石板直通撫河,彎彎曲曲可達熱鬧的菜市場。晴無灰撲,雨無泥滑,多好啊。每次過橋進城,人來人往,人多得像夜間擠滿天的星子。
文昌橋是一種誘惑,引導一個農家子弟朝著夜里有電燈光、路上鋪水泥的城市挺進。它是一座勵志橋,橫臥浩浩撫河之上,好似勸諭,又更像我的人生隱喻。
父親帶我進城,那是一個農民對兒子開設的城市文明課。有了進城經歷后,我和別的小孩就有些不同了。閑來無事,我會爬上村口最高處,癡癡地望東南,煙波浩渺,水天一色。那里正是臨川城。
水做的臨川另有一種淡雅的韻致,水潤柔和,自是一派溫婉。春來雨狂,撫河一片白,遠村、近村像漂在水上的夢幻世界,水邊的孩子快樂似神仙。撫河水滋潤著贛東平原,滋養著優質稻米和臨川才子。
文昌橋是一座擁有八百多年歷史的老橋。文昌之名,是才子之鄉的引言,抑或是明證。明朝萬歷年間,撫州府臨川縣有陳際泰、羅萬藻、章世純和艾南英四個文人以一副絕聯“上文章下文章,文章橋上曬文章;前黃昏后黃昏,黃昏渡前度黃昏”,把才子之氣放大,將才子之名光大。
早在幾十年前,我所在的小村從臨川被劃出,歸并到東鄉縣。臨川,他處風景裝飾了我的心靈之窗。多年后,離開家鄉,異鄉變故鄉——不管東鄉還是臨川,都不如客居的南昌待的時間久。
文昌橋西,那個古樸的鄉野搖身一變,成了文昌里歷史文化街區。入夜,星河璀璨,大有東京夢繁華的氣象。這里整舊如舊,古韻悠悠,人們深入其中,能感受到文風鼎盛的仙氣,領略到煙波臨川的古意。文藝家猛擲大把光陰,沉迷其間,不知歸。
那年初夏,我與同事到撫州出差,首訪文昌里,像踏入夢境一般,飄飄忽忽,幸福從天而降。夜色撩人,撫河水緩,風潤如歌,站在文昌橋頭,豎起剪刀手,咔嚓一聲,我首度與百年古橋同框。多年后,我終于和它代表的城市文明在這個夏夜完美相擁。
2021年國慶長假,我帶夫人回鄉,夜宿臨川。我們手牽手在文昌里走了九遍,走出了地老天荒的浪漫之感。
2023年春天,一群來自全國各地的作家暢游文昌里,歷史照進現實,一眾文人開啟了古今對話。湯顯祖家族墓園邊上,中國戲劇博物館氣象非凡。我們聚攏合影,沾染湯顯祖的才氣。
文昌橋西的鄉野已然成為文化重鎮。
文昌橋東頭的周學嶺倚山之高,俯瞰撫河之浩渺,深藏著一方洗墨池,粼粼波光,映照臨川之筆的鋒芒。這是一處風水寶地。一千六百多年前,大書法家王羲之任臨川太守,也登上周學嶺,一見心生歡喜,于是他修庭,筑宅,安身,名曰“新城”。公務之余,王羲之居新城,練大字,書香滿城春,書韻溢山嶺。
王羲之自幼喜書,常習“草圣”張芝的狂草,日夜苦練,“臨池學書,池水盡黑”,用力之深,用情之專,由此可見一斑。
臨川人為紀念王羲之洗筆硯處,立石碑,上刻“晉王右軍墨池”。王羲之書與文集大成,世稱“書圣”,在臨川獨創的“永字八法”被歷代習書者恭奉為圭臬。
臨川,以一座橋賜予我獨特的氣韻,賦予我這個寫作者的人生本色,讓我在書寫上不能懈怠,不敢褻玩。撫河清波緩緩流,流不盡我的思念。想文昌橋,念臨川城,回想來往無數次走過此橋,鄭重地在日記本上寫下兩行字——
文昌一橋,有愛故水近;
臨川四夢,未覺流風遠。